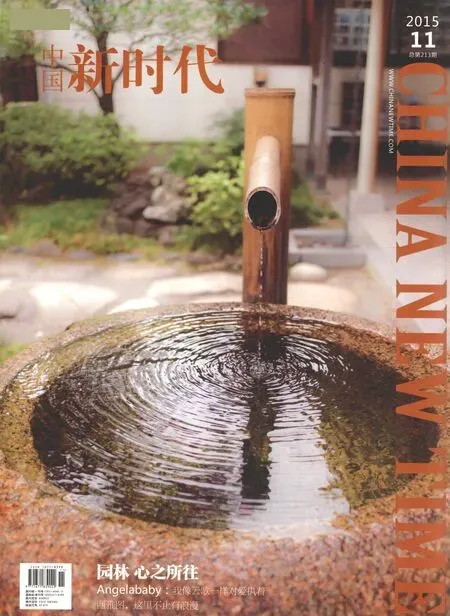荷兰农田中的“世界文化遗产”
撰文/图片>>>陈婷
荷兰农田中的“世界文化遗产”
撰文/图片>>>陈婷
世界文化遗产,一向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文化身份的标志。翻看荷兰本土7处世界文化遗产的介绍,我发现大部分也都与水有关,从远古时代荷兰人与大海顽强抗争,到围海造田,17世纪的棋盘式田地结构现在看来依然不过时,它们记录下的是人类与海相处的历史。

荷兰,当我数次来到这个只有两个半北京大,南北距离不过300公里,东西距离不过200公里的小国,与“水”有关的景物一直贯穿这片土地。连荷兰人提到自己的国家都会亲切地把她称作“潮湿的小国”,然而区区几个字却包含了人类历史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围海造田,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有1/4是从大海手里争夺来的,纵观荷兰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与水患斗争、与风车共存的历史,显然,这种自然缺陷已经成为了多少世纪以来荷兰最伟大的力量源泉,而与海争地的百年历史也使得荷兰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低地”文化与传统。
现在的荷兰已经放下了与水的恩恩怨怨,化敌为友,将“与水共存”列为国策。水与荷兰人的生活如此息息相关,在这个低地小国的旅行,自然也离不开这道独特的风景,那就让我们一起游弋在荷兰“水世界”中,感受一下身高马大的荷兰人治水、用水的智慧吧!
斯霍克兰低地(Schokland)遗址是荷兰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查看资料时,清楚地写明包括灯塔遗迹、北端的港口、南部的教堂遗址等,地图上也的确标记着一座“小岛”的轮廓, “如果是个小岛,那应该在海边才对。” 然而当我顺着GPS的指引,却将车子开进了一大片农田中,我迷惑地环顾齐整的田地,难道荷兰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就在这里?向一个当地人打听,“哦,那里就是你要找的小岛!”他一指农田中心的密林,我恍然醒悟,这些农田在四百年前应该就是海洋(须得海)的一部分吧。
我依然不敢确信这里真的是荷兰第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因为距离我们所了解的“世遗”待遇相差甚远:没有“大门”,没有售票处,甚至连一个参观者都没有。终于在田埂旁找到一块不起眼的牌子,标明了UNESCO(世界教科文组织)字样的斯霍克兰低地示意图,心里这才踏实许多。我穿过绿油油的农田,沿着一条通往密林深处的小径走上去,面前豁然开阔,然而,想象中的断垣残壁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灯塔遗址竟然只剩下了一个圆形地基,旁边则是教堂地基,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这应该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低调”的世界文化遗产了。
1948年设立的斯霍克兰博物馆(Schokland Museum)就建在圩田旁边,地方不大,主体建筑是当地古老居民区米德尔堡(Middelbuurt)的一所经过修缮的教堂。展馆中录像、图片和实物结合在一起,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发生在斯霍克兰低地和东北圩田(Noordoostpolder)上的故事,那些简陋粗糙的铁锹、小船便是当年人们用来对抗汹涌澎湃大海的工具,可以想象那与海搏斗的岁月该是多么艰辛。
时间拉回2000年前,当罗马人初次造访欧洲边缘这块遥远而孤独的土地时,大失所望,这里遍布湿地沼泽,渺无人烟。而当第一批日耳曼部落决定在此定居的时候,情形更恶劣,“无边无际,残酷无情的森林”是当时的真实写照,直到14世纪时荷兰森林中还有成群的野马。境内的三大河流莱茵河(Rhine),斯海尔德河(Scheldt)和马斯河(Maas)年年泛滥,连距离很远的陆地都被淹没了,荷兰的海岸线经常改变面貌。淫雨连绵,浓雾密布,冬季一天只有三四小时的日照,那时的荷兰甚至在古代地图上都无法辨认。
远古时代的斯霍克兰岛应该也是如此这般的荒蛮吧,然而这里最初的居民却顽强地生活了几千年。当我在博物馆外的咖啡座里遇到斯汀,一位60多岁的荷兰人,他正慢悠悠地喝着咖啡,晒着太阳,“我可是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斯汀有些骄傲地告诉我,他们家目前是斯霍克兰低地仅有的4户人家之一,“这里原本是个狭长半岛,一直到15世纪,海水不断侵蚀,便形成了内海——须德海(Zuider Zee)中一个人口稠密的独立岛屿。”说起那段久远的历史,好像他亲眼所见一般,“这里的居民一直在同入侵的海水顽强斗争,直到1859年才被迫撤离,之后小岛便被海水淹没了,后来因为有了须得海大坝,围海造田的时候,人们排干海水,从海底淤泥中出土了大量的古代狩猎工具、史前动物化石、各种生活用具,这才知道我们的祖先与海水侵蚀进行抗争的英勇行为甚至可追溯至史前时代。”
我顺着他深邃的目光望去,看到圩田旁一座座纪念铜像,“农妇”凝视着不远处的绿洲,似乎又能听到一声声劳动号角萦绕耳边,让人不禁想起镌刻在荷兰国徽上“坚持不懈”的字样,恰如其分地刻画了荷兰人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

除了与海搏斗保护自己有限的家园土地,在同样的精神力量驱动下,荷兰人便开始行使起了原本属于上帝的职责,重新设计和改造自己那片并不丰饶且频遭水患的国土,于是“沧桑变幻”就在荷兰人的手中成为了现实。自然的沧桑之变不易感觉,因为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人为的沧桑之变——围海造田,则表现得惊天动地,轰轰烈烈。
上世纪20年代在弗列佛兰省(Flevoland)与北荷兰省之间修建了北海大堤,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且上世纪40年代起随着水位下降,斯霍克兰岛重新浮出水面,“我父亲参与了当时的围海造田工程,那时的人只有一个信念,开拓出属于自己的土地。”“怎么做到呢?”我好奇地问,感觉海水变成耕地像变魔术一样,斯汀特地画了个示意图来解释,“大坝将须德海通往北海的海湾口拦腰截断后,形成一个内陆湖——艾瑟尔湖(Ijsselmeer),然后人们排出湖里海水,通过河流和降雨引入淡水,之后抽掉艾瑟尔湖的部分湖水填入沙土,又采取海水淡化方式排除盐分,分片围垦,先种上些耐盐碱的作物改良土壤,几年后再种农作物。”原来荷兰最大一片圩田就是这样获得的,包括环绕在“小岛”四周的“东北圩田”,1941年东北圩田自须德海中被围垦出来后,斯霍克兰便不再是“岛屿”了,周围遍布良田,如今辨别“小岛”的根据仅靠圩田中高耸之处以及海滨完好的挡土墙。

举目望去,农田中的庄稼在微风中拂动,我不禁想起世界教科文组织的评语:这座迂田中的“小岛”是“对于全世界具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所有开垦的土地被证明为各类新型文化和自然宝藏提供丰富养料。而把这片沼泽地改造成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并非每个民族都可以完成,顽强的毅力和耐性是必须的,一次次被洪水冲垮的堤坝,需要不断地重建,筑堤防河防海,利用风车产生的动力,抽干田间的水,还要解决吃住穿,抵御来自北海的刺骨寒风、低地的潮气,自然面前,需要的是天生团结、吃苦耐劳的人,这些难以想象的工程是需要集合一个民族通力合作才可以完成的,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现代荷兰人依旧推崇集体的力量,依靠团队来开展工作。
如今斯霍克兰低地在迂田景色中骄傲伫立,标志着荷兰人与大海抗争的精神,那也是人类文明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因此成为世界遗产名录中的第一个荷兰丰碑,也就不足为奇了。“上帝造海,荷兰人造陆地”,在荷兰人与海水争地的抗争过程中,他们学习在水的故乡生长,并将这片低洼水乡经营成一块世人向往的乐土,农田中的“世界文化遗产”——斯霍克兰低地和圩田,连同“人与自热”抗争的传奇,一起永久地留在了世人的记忆里,也让我们这些祖先自古就生活在“陆地”上的民族由衷地敬佩。
——以长荡湖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