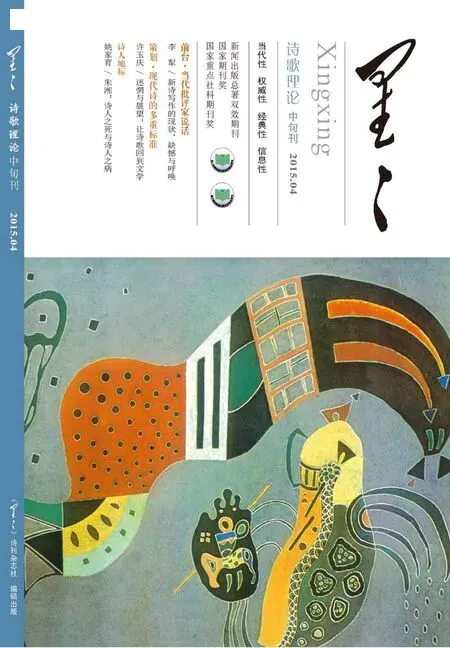“快”与“慢”的诗性逻辑
刘继林
每月诗歌推荐
“快”与“慢”的诗性逻辑
刘继林
记得看到过一则电视宣传片:“快城市,慢生活!”渲染是成都充满人情味的休闲生活方式。其实何止成都,我觉得为喧嚣浮躁所累的当下中国,这理应是我们追慕的一种诗性存在。当年,海德格尔用“筑居”和“栖居”将芸芸众生的现实存在和诗人的精神追求区别开来,强调人要“诗意地栖居在现实大地之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本月推荐的三位诗人,安徽的王妃、重庆的张守刚以及河南的刘高贵,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在近半个世纪的个体生命体验中,他们经历了中国社会由乡村到城市的深刻变化。小时候,在乡村田野中肆意奔跑,一心向往那座“城”;长大后,来到这座“城”,奋力打拼,为的是能够生根发芽;现在,在都市的某个角落,他们开始打捞沉淀已久的思绪,发现魂牵梦绕的还是儿时的那个故乡。王妃的诗集《风吹香》、张守刚的《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刘高贵的《寸草之心》,所表现的大都是这种主题。只不过,王妃的诗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语言,女性的沉静而温润、日常生活的诗意与审美,不经意地绵延于字里行间。张守刚则在乡下放过羊,在城里打过工,故乡的疼痛与温柔、城市
的冰冷与无奈,形成了他叩击灵魂的文字:“在工业区看老乡/我们和土地的心情/一样沉重”(《在工业区看老乡》)。刘高贵深受豫南民歌的影响,其诗简单、淳朴,“我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只想在早晨醒来,晚上安歇/整个白天/我都将用来劳作”(《简单的生活》),在诗人看来,故乡的一事一物总关乎情,关乎灵魂的所持所向。
张守刚的《在监控器下上班》以一个野丫头的视角,真实地揭示了她在工厂监视器下忐忑、惶恐、惴惴不安的心理现实:“总感觉有双眼睛/在背后偷偷地看/她的脊梁阵阵发凉”,“走进洗手间/她差点小便失禁/她怀疑厕所里/也装上了暗处的眼睛”。这位刚刚从故乡窄窄田埂上走过来的女孩,完全被工厂监视器下的生活给“异化”了。一个大大咧咧的野丫头,因为“招工启事上的待遇/将她喊了进来”,不得不放弃“妈妈从小就让她/挺直腰杆做人”,变得“连打哈欠伸懒腰/也得小心翼翼”。诗人写出了打工者为物质、技术所裹挟的无奈现实。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必须的,但“快”速的发展不能以压抑人性,尤其是不能以牺牲弱小、美好的事物为代价。
和张守刚快言快语的血性诗风有所不同,王妃的《好时光是用来浪费的》、刘高贵的《把桃花和杏花分开》则明显慢几个节拍,或优雅沉静,或素朴简单,他们注重的是日常生活品味与格调、人生在世的心态与情怀。记得台湾诗人萧萧有一首诗《21世纪的台北人》就一个音“ㄇㄤˊ”(máng),可解读为“忙”、“盲”,也可解读为“茫”、“氓”。在“忙”和“茫”的今天,如何不迷失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拥有一份闲适的生活格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王妃那里,她享受的就是那份“什么都
不想,和婆婆对坐在阳台上/拽着她细碎的话把子”的状态。在她看来,“好时光是用来浪费的”,人生的趣味就在于,漫不经心地把玩随心所欲的品味,将生命定格在某个瞬间,独自享受其中无穷的韵味。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很多个“一”:“我一转身”、“一滴寒露”、“一片落叶”。“一”看起来简单,细细品味,其中却有大世界,大哲学,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刘高贵的这首《把桃花和杏花分开》则重在一个“分”字:分什么?如何分?这本是一个抽象的方法论命题,诗人却用乡村生活的真实经验巧妙地化解了这一难题,认为“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就如将桃花和杏花、三月和四月、父爱与母爱、大麦与小麦、朋友和路人区别开来一样,“真的非常简单”。简单的背后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其实,“那妙不可言的 就是情怀”。诗歌传达的是一种审美的乡土存在,一种诗性的逻辑追求。
其实,城市也罢,乡村也罢,都是现代中国社会的有效存在,都有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凭个人好恶来作伦理或者价值的判断。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也不管是“快”,还是“慢”,最关键的是心态,是情怀,是看我们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