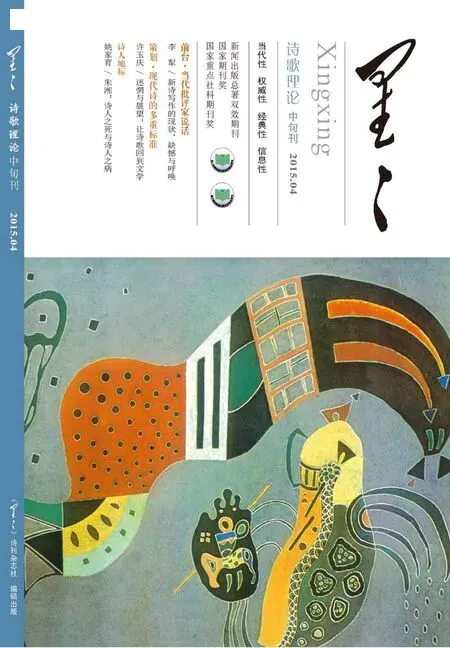耶胡达·阿米亥诗歌中比喻的三层结构
王子瓜
耶胡达·阿米亥诗歌中比喻的三层结构
王子瓜
耶胡达·阿米亥(Yehuda Amichai),1924年出生于德国乌尔兹堡。1935年,在犹太人回归故上大潮中,随父母迁居巴勒斯坦地区。在耶路撒冷中学毕业后,参加了对德作战。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他参加以色列军突击队,战后在希伯来大学求学。毕业后在中学教授希伯来文学和《圣经》,后在希伯来大学任教。2003年逝世。
阿米亥从四十年代后开始发表诗作,一生写有1000余首诗,出版了25本诗集,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他不仅仅是诗人,还是小说家、剧作家、随笔家,甚至儿童文学作家。作为第一代以色列作家,阿米亥开创了希伯来语文学的全新世界。一方面,他让古老的希伯来语焕发了青春,另一方而,又以自己的方式肢解和重构着古老的希伯来习语。他以十足的个人化和口语化语言,与希伯来诗歌数千年来面对民族苦难时的集体声音决裂。
作为世界顶级的诗人,他的作品至少在写作技法与内容两个方面十分值得我们关注。在内容上,他的诗歌主题丰富,涉及宗
教、传统、战争、爱情、时间、日常生活等等,诗所表达的思想也纷繁复杂,笔者还未能有所把握。因此,在这篇随笔中,我将自己的野心限定在分析其写作技法的层面上,仅就阿米亥诗歌的皮毛进行一些探讨。我相信,尽管仅是在这个层面上,他的诗歌仍然足以让我们许多人学习和赞叹了。
在将诗人的写作意图和诗歌的整体暂时搁置之后,初读者往往会发现阿米亥的比喻十分精妙,并且这些比喻往往是进入阿米亥诗歌的捷径。比喻是人们最熟悉的修辞之一,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比喻都常常被使用。在经历数千年的历史、经由数千种人类语言的反复咀嚼、锤炼之后,比喻仍然具备鲜活的生命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场浩大长久的文学进食仍将继续下去。可以说,比喻的技巧是诗人的基本功:如何将两个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从中产生更大的张力,进而获得诗意。对这一基本功的把握能力是评判诗人创作能力的标准之一。阿米亥在这一方面可谓登峰造极,他的作品中精美、贴切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比喻随处可见:
我的双眼想彼此流通,
像两个相邻的湖泊。(《六首给塔玛尔的诗》)
只有我母亲的话语与我在一起,
就像一块包在沙沙作响的蜡纸里的三明治。(《当我是个孩子时》)
我们的爱在一所孤儿院
穿着孤儿的制服。(《给一个女人的诗》)
完整地离去的人们
傍晚被带回家来,像找回的零钱。
(《一间屋里三四个人当中》)
至于我的灵魂:
那道道褶皱一直存留着,
好像一封你不敢再度展开的
旧信上的褶皱。
这里。
是。
从这里起
开始撕裂。
(《在七十年代前夕》)
你的面容和你的名字美丽,
印在你身上犹如印在一罐
精美的蜜饯上:
水果和它的名字。
你还在里面吗?
(《我们曾相近》)
然后,举起手
掩住哭泣的双眼
就像捧一只水盆
喝呀,喝。
(《带我去机场》)
她回答:我的灵魂像你的一样被撕裂,
但它因此而美丽
像精致的丝带。
(《躺着等待幸福》)
正如时间不在钟表之中,
爱情也不在肉体之中:
肉体仅仅显示爱情。
(《在别的某个星球上你也许是对的》)
可是当肉体死去时,爱被释放,
疯狂地增长,
就像一台自动售货机出了毛病
鸣响着愤怒的铃声一下子倾倒出
所有世代的幸运的
所有硬币。
(《肉体是爱的原因》)
通常而言,比喻往往将一物比作另一物,本体被比作喻体,这一过程是一维的,是直接而简洁的,单维的比喻无论何其精妙,也很难给人惊奇之感。而以上的诗句中,阿米亥将比喻进行了延展,成为了二维的比喻。从形式上看,这并非是一物被比作另一物,而是以这个物体为主体形成的一个句子为本体,被比喻为另一个句子。在这个过程中,比喻不再草草结束,而是在一个平面中行动起来,本体和喻体的联系不仅仅存在于中间的比喻词。延展之后的比喻不仅具备更强的画面感,也为比喻本身的合法提供了诗人自己的证据支持。在现代诗歌中,许多诗作的比喻因为跳跃距离太大,或太抽象,往往使读者感到莫名其妙,这也是现代诗歌饱受责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喻的延展则可以使这一危险迎刃而解。二维的比喻解放了阿米亥的手脚,因为无论跨度有多大,只要本身的确是有效的,延展开后读者总能找到合理的理解。设置的障碍越大,连接的桥梁就越能给人惊喜,“陌生化”在这里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而诗意就在这些联系之间焕发出来。
有时,一首诗由许多个二维比喻串联起来,阿米亥的作品多属此类。如:
当我是个孩子时,
蒿草和樯桅耸立在海滨;
我躺在那里的时候,
我想它们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们全都在我之上升入天空。
只有我母亲的话语与我在一起,
就像一块包在沙沙作响的蜡纸里的三明治;
我不知道我父亲将何时归来,
因为在空地那边还有一片森林。
一切都伸出一只手,
一头公牛用犄角牴破太阳,
夜里街上的灯光爱抚
墙壁的同时也爱抚我的脸颊,
月亮,像一只大水罐,倾俯着,
浇灌着我焦渴的睡眠。
(《当我是个孩子时》)
凉鞋是完整的鞋的骨骼,
骨骼,及其仅有的真正灵魂。
凉鞋是我奔驰的双脚的缰绳
和一只疲倦的、祈祷着的脚上
系经匣的带子。
凉鞋是我所到之处我践踏的
小块私有土地,我的故乡、
我真正的国家的大使,地上
群集的小生物的天穹
和它们的必将来临的毁灭之日。
凉鞋是鞋的青春年华
和在荒野中漫步的记忆。
我不知道何时它们将丢失我
或何时我将丢失它们,但它们终将
被丢失,各在一个不同的地方:
一只离我住所不远,
在岩石和灌木丛中间,另一只
沉入大海附近的沙丘,
像一轮落日
面对着一轮落日。
(《凉鞋》)
另一些时候,一个成功的二维比喻就足以支撑阿米亥的一首诗:
当耶路撒冷的市长
是悲哀的。
太可怕了。
一个人怎么能当那样一座城市的市长呢?
他能把她怎么办?
他将建筑,建筑,建筑。
而在夜间
四周山上的石块
将爬下来
趋向那些石头房屋,
好像群狼前来
冲着那些
变成了人们的奴仆的狗儿嚎叫。
(《市长》)
有时我非常快活,不顾死活。
那时我就深深扎进
世界这只绵羊的
毛里,
像一只虱子。
我就这么快活
(《有时我非常快活,不顾死活》)
事实上,只要多加练习,比喻的延展仍然是较为容易的。单维的比喻常常显得单调且不能准确地传达诗人的意思,延展之后的比喻就是为能指与所指之间千万种可能之间划出了最有效的一
条,给出了另外一个坐标。这时诗歌是平面的,不再是词与词、句子与句子的拼合。然而阿米亥的诗并非到此为止。在少数诗中,他将比喻继续延展,制造了三维的比喻。最具代表性的应当是《自传,1952》、《夏末黄昏在摩査》等。
我父亲在我头顶之上建造了一片大如船坞的忧虑,
曾有一回我离开了它,在我被造好之前,
而他留在那里守着他巨大、空旷的忧虑。
我的母亲像一棵海岸上的树
在她那伸向我的双臂之间。
在'31年我的双手快乐而弱小,
在'41年它们学会了使枪,
当我初次恋爱之时,
我的思绪像一簇彩色气球,
那女孩的白手把它们全都握着,
用一根细线——然后放它们飞走。
在'51年我生命的动作
就像许多锁绑在船上的奴隶的动作,
我父亲的面孔仿佛火车前面的照明灯
在远方愈来愈小,
我母亲把许许多多的云关闭在她那棕色的壁橱里,
我走上街头时,
20世纪就是我血管中的血液,
那在许多战争中想要通过
许多开扣流出来的血液
因此它从内部撞击我的头颅,
愤怒地汹涌到我的心脏。
可是现在,在'52年春天,我看见
比去冬离去的更多的鸟儿飞回。
我从山丘上走下,回到家里。
在我的房间里:那女人,她的身体沉甸甸的
充满了时间。
《自传,1952》
一辆孤独的推土机与它的小山搏斗,
像一位诗人,像所有在这里独自工作者。
成熟的无花果的一阵沉重的欲望
把黄昏的天花板扯到与大地齐平。
火舌已经吃掉了荆棘,
死亡无须做一件事除了
像失望的火焰一般叠起。
我可以得到安慰:一种伟大的爱
也可以使一种对山水的爱。
一种对水井的深沉的爱,对橄榄树的燃烧的爱,
或像推土机一样独自挖掘。
我的思绪总是在擦拭我的童年,
直到它变得像一块坚硬的钻石,
不可破碎,切入
我成年的廉价玻璃。
(《夏末黄昏在摩査》)
在这两首诗中,我们看到许多二维比喻相互交织、相互联系,诗歌的涵义从这种联系中体现出来。比喻在诗中千回百转,纷纷扬扬,每一个比喻都没能完整的表现主题,也没有哪一个比喻真正脱颖而出,但它们都围绕着某个中心在旋转,那个神秘的、没有点明的中心就是比喻的第三维,或者说是整首诗本身。如果说从比喻到比喻的延展只是个技术的问题,那么从比喻的延展到比喻的回旋体现的则是对诗歌的掌控能力、对现实和记忆的体认程度。
《夏末黄昏在摩査》中,二维比喻有这样几组:比较明显的有,“孤独的推土机与它的小山搏斗”-“像一位诗人,像所有在这里独自工作者。”;“死亡”-“火舌吃掉了荆棘”、“失望的火焰”;“思绪总是在擦拭我的童年”-“它变得像一块坚硬的钻石”;“童年”切入“成年”-“钻石”切入“廉价玻璃”。另外,隐藏的暗喻有,“成熟的无花果的一阵沉重的欲望/ 把黄昏的天花板扯到与大地齐平”-诗人垂下头,寻找根基;“荆棘”-成年生活;“像推土机一样独自挖掘”-我可以做和应该做的事。
一开始第一组比喻告诉读者诗人在与某件事物搏斗着,“成熟无花果”两句暗示着某种下垂与回溯,“火舌”三句在讲述死亡在无法吞噬之物面前的失望,“我可以得到”三句是对那不可磨灭之物的猜测,而后又回到最初的意象:“像推土机一样独自挖掘”。第一节的叙事风格沉郁,隐喻层叠,不易解读。第二节则好像完全换了色彩和质感,但这组二维比喻本身使得第一节的所有比喻生效:童年的珍贵、不可摧毁,与成年生活的“廉价”、易碎。读者于是明白,第一节推土机在挖掘的,正是这样一些珍贵的、不灭的事物,连死亡也不能带走的事物。整首诗的层层比喻各有着逻辑的或内在的联系,使它从平面中竖立起来,形成了一个更加精妙结构,其中所呈现的诗歌的张力、意境,是平面的诗歌所不能比拟的。
《自传,1952》是阿米亥最早发表的诗歌之一,这个早熟的诗人在这时就已经开始了三维比喻的尝试,并且是一次十分完美的尝试。诗中主要有如下几组比喻:父亲给予我的忧虑-建造很大的船坞;“我离开了它,在我被造好之前”-船离开船坞,在它被造好之前;“母亲”在“伸向我的双臂之间”-“一棵海岸上的树”;“思绪”-“彩色气球”;“那女孩的白手把它们全都握着,用一根细线——然后放它们飞走”-思绪紧跟着一个女孩儿,又忘了她;“我的动作”-“奴隶的动作”;“父亲的面孔”“愈来愈小”-“火车前面的照明灯”;“云关闭在她那棕色的壁橱里”-一个自我封闭的过程;“战争”中的“20世纪”-血管“开口”中的“血液”;“血液”“撞击我的头颅”、“心脏”-战争使我狂热。
这首诗的第一节是一个总述,描述一切开始时的忧虑状态,第二、三两节则是故事的展开,最后一节是一个突变和沉淀。前三节各自的一组或几组二维比喻已经构成了三个小的相互联系、相互印证的整体,而通过语调的平稳、醇厚、意象选择上的沉郁色彩、“父亲”、“母亲”、“船”、“海”等意象的多重比喻、明确年代的顺次出现,这些小的整体被悬起,开始环绕着同一个中心不断回旋:时间。
从以上两首诗中,我们能发现比喻的回旋中各个二维比喻是如何实现联系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方式:
1、比喻自身的方式:在一个比喻建造完成后,其喻体在接下来的比喻中作为本体出现,继续延展。如在《自传》的开头,忧虑被比作船坞,紧接着我就像一个未造好的船一样离开船坞,在这里船坞就已经是一个实指的本体了;或针对同样的本体,使用多种二维比喻,将其本身作为喻体。如《夏末黄昏在魔査》。
2、比喻之外的方式:如通过明显的提示词将各个部分串起来;通过意象、语言风格的有意选择;同样意象的反复出现等。
种种方式可以造成比喻重章叠唱、千回百转的效果。这并非易事,因为比喻的回旋绝非毫无意义的技法。在大部分现代诗歌中,比喻本身就是一种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或将陌生事物可感化的过程。诗歌要求经验,因此比喻要求诗人至少对本体与喻体其中之一有所体会。对事物的体会愈深入,诗则愈真挚、愈美妙。单维的比喻因为所包含的内容太少,往往显示着作者体认程度的不够深刻,因此价值不高。二维的比喻要求诗人在简洁的比喻基础之上进行延伸,这本身就是一个体认的过程。不过这种体
认仍然局限在事物个体之上,这个个体仅仅是整首诗的局部。想要制造比喻的回旋,其难度远远超越前两者。除了做到比喻及其简单延伸之外,整首诗的各个部分都要联系起来,并将隐藏的环绕中心提示给读者,这需要诗人对他所要表达的主题本身的深刻体验,毕竟这将是一个可以独立运行的世界。这事实上是一个追求穷尽的过程:从小处讲,你的想象力究竟能走多远,你对事物的体验究竟有多深;从大处讲,你所表述的主题究竟有多少种合适的表述方式,你的思想究竟能显现出多大的价值,以及你——诗人本身,是否具备创造另外一个世界的能力,是否可以成为夏弗兹博里所谓“第二造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