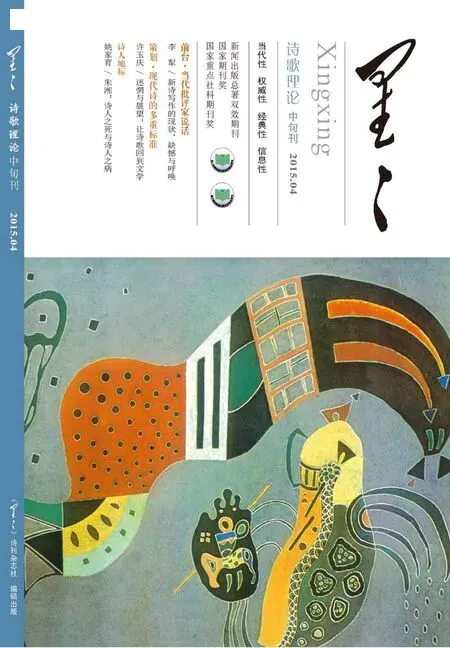走向“文学广场”的诗人们
——《中国诗人随笔序列·福建卷》序
曾念长
走向“文学广场”的诗人们
——《中国诗人随笔序列·福建卷》序
曾念长
就文学体式而言,散文与随笔可并成一大类。若要一言以蔽之这类体式之特性,我斗胆说:公共性。它是众多文学体式的公约数,也是无数社会性言说的公约数。所以,诗人、小说家往往要附带写写散文或随笔,学者、医生、演员、商人和官员,数不尽的各行各业的人,都会跑到散文或随笔这块领地上卡遛[1]一番。它是文学的“公共广场”,无论你是专业的文学写作者,还是其他社会领域的各路神仙,只要来到这个广场,大家就享有同等的“文学身份”,就可以以文学的名义说话,甚至聊聊文学本身的问题。
作为社会物理空间的广场,天然具有两种功能属性:抒情性和议论性。在农村,村庙就是广场。每逢佳节,村民在此狂欢;但逢大事,族人在此定论。在城市,广场的双重属性在聚合,在放大,还变幻莫测地相互转化着。君不见,三十年前广场批斗小兵横行,三十年后广场歌舞大妈扰民。而我想说的是,散文和随笔,作为纯粹精神空间的“文学广场”,也有这双重属性,并且它们在这个时代发生着复杂的转换关系。
一般而言,散文亲抒情,而随笔亲议论。这种天然分化与中国古代的文章学传统并不相符,而是现代文学体式发生流变的结果。这里面不得不提鲁迅的特殊贡献。通过他的海量写作,杂文从广义的散文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纯议论为要义的文学体式。显然,在这个体式茁壮成长的背后,隐含着特定的诉求:对社会公共问题的介入。其结果是,散文中的抒情性和议论性分道扬镳了。不过,自1990年代末以来,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杂文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快速衰变为两个支流:一支最大限度地删除了杂文的文学性,发展为大众媒体时评;一支则向文学性回归,重新融合散文的大统,发展为随笔写作。于是,散文的抒情性与随笔的议论性在慢慢靠拢,“文学广场”上的两种声调正在汇合。让议论变得更加柔软,让抒情变得更加有力,这是世纪之交发生在“文学广场”上的交响曲。
这套丛书名为“中国诗人随笔系列·福建卷”,其中对随笔这一文体的界定,必须放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广场”中给予具体的考察。随笔不仅仅是一事一议,而是在与散文大统的重新融合中走向新的“文学广场”,走向辽阔的精神世界。似乎有人说过,21世纪的写作是随笔的写作。我希望那些有考证癖的人能够考证出这句话出自何人。如果“查无此人”,那就当是我说的好了。就文体的普适性而言,我以为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随笔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章”,可长可短,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可写一己之私亦可言天下之公。它有其他文体不可比拟的精神容量,因而往往承接了从各种狭窄、僵硬的言说空间中溢出的话语。它是怎么都可以的一种言说体式,唯独如此,它才能够呈现言说者的真诚品质和精神形状。诗人于坚认为存在一种“散文
化的写作”,它是“各种最基本的写作的一种集合”,其“出发点可以是诗的,也可以是小说的、戏剧的,等等”。我理解于坚所说的“散文化的写作”,就是接近于已被我们的文体观念接受了的随笔。它是一种最公共的写作,也是一种最自由的写作。这种写作本身,就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有效结合。
有一种传说试图指出,福建是一个“诗歌大省”。如果仅仅是指诗人的数量和影响力,我以为这种传说言过其实。哪个省域不是诗人成群?又有哪几个省域举不出若干有影响力的诗人?但我以为,如果是指诗人在一个特定时代中的精神境遇,福建的诗人及其写作是极具典型性的。从历史上看,闽人文学长于诗文,而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至今尚未完全走出这种宿命的循环。其中的原因,很难给出一个实证性的定论。一个较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闽地方言制约了闽人的大众化写作,因而也就失去了进入白话小说领地的优势。这一说法或许不假,但我以为还有一个因素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那就是闽人精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内排遣”传统。闽人是习惯于自我言说的。他们往往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向外部世界寻找人生问题的答案。在依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气息的乡村地区,拜神依然是许多福建人极具日常化的行为。他们习惯性地在神像前喃喃自语,实则是在与自己的心像一问一答。这种向内延伸排遣路径的精神构造,也正是诗歌和散文的天然形式。相比之小说指向社会的丰富性,诗歌和散文更直接指向了个人内心的细密纹理。闽人对诗歌、散文以及散文诗的偏爱,或许正是缘于此。他们的天然节奏不是东北人的唠嗑,不是北京人的段子,而是以沉默为外部表征的内心絮语。这种精神特征也让闽人背负了一项无端的罪名,那
种通往内心的诉说与自救,往往被假想为深不见底的心计。我以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人们对自我言说的恐惧与排斥,在“早请示、晚汇报”的时代一度达到极致。如果我们不理解自我言说是人类话语结构的重要基石之一,也就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反驳那场极端化的话语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以郑敏、杜运燮、蔡其矫、舒婷为代表的福建诗人,凭着对自我言说的时代性觉悟,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新诗潮中成为一面旗帜,也为福建诗歌赢得了至高的荣誉。
作为一种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存在,今天的福建诗人(也包括批评家)依然保持着如隐士般构建自己的内心世界的精神传统。如厦门的舒婷、陈仲义,福州的吕德安、鲁亢等等,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公共话语似乎缺乏志向,因此也很少像文化中心省份的诗人一样甚嚣尘上。与其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刻意姿态,不如说这是诗人的一种心灵隐喻。诗人就是这个时代的隐士。他们是一种逃遁式的存在,真实地辐射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却很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太阳来到了隐士的家/隐士却不在家”。这是江苏诗人胡弦的诗句,在此我愿意借它来阐明这个时代的诗人的心灵志。但我还想说的是,现代诗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存在,不可能完全隔绝于世。他们往往还借助诗歌之外的形式,介入公共事物,与外部世界进行对话。在此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不乏有令我们素然起敬的国内同行。比如于坚,这位自称“在散文写作中向后退”的云南诗人,实际上是通过随笔这条言说通道重新抵达时代现场,将文学的态度和立场带入大地与环境、建筑与城市、本土化与全球化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再说王小波,他不是诗人,却在小说中前所未有地开辟了自我言说的路径,因
而比许多诗人更早抵达诗性的精神国度。即便如此,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直面时代议论的随笔写作,并称这是知识分子在承担应有的道义和责任。我想诗人写作随笔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诗人不仅仅是诗人。他首先是个人,具有每个人通常都有的两面性,以及由两面性拓展开来的多面性。当诗歌在表达一个人的多面性时变得言不及物,诗人就会借助另外一种表达形式,以探求诗人与世界之关系的多种可能性。写随笔就是诗人延展自己的精神空间的一种有益尝试。正如前文所言,随笔是“文学广场”,是个体言说与公共言说的交汇地带,也是诗人出来卡遛的绝佳场所。
我想这套丛书的多数作者是以诗人为身份自觉的,因此才有“诗人随笔”一说。这么说来,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些随笔作品看作是诗人的“副产品”。一个成熟的诗人对自己的作品是极为苛刻的,我想他们对自己的“副产品”也应抱有同样的态度。至于这些随笔写得如何,实无由我评说的必要。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再费口舌也是多余的。我更想借这个机会,谈谈对写作的两种精神向度的看法。呈现在我眼前的这些随笔作品,更多是延续了福建诗人的自我言说的精神传统。这种“路径依赖”是一种常见现象,也符合诗人的自我期待,以及多数人的阅读期待。一位学者来到广场,未必就能抛弃书斋里的习惯,遇见新鲜事恐怕要寻根究底一番,甚至与自己“死磕”。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合乎常理的。依此类推,诗人出现在广场,也有自己的习惯性方式。他们左顾右盼,略带神经质,却不愿参与任何“群众聚会”,就像传说中的“打酱油”者,一溜烟又飘走了。我作此类比,仅仅是想说明,诗人自有诗人的专注精神。诗人最关心
的,终究还是自己的内心世界。即便是写随笔,他们还是习惯于将文字的光亮照向自己的心灵空间。这本无可厚非,但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时代的声音牵扯着人心,我们又岂能充耳不闻?但我并非是要主张诗人们去做单刀直入的社会时评家。诗人自有表达时代经验的独特方式。像安琪一样立誓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将诗人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和左冲右突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字面上。或像鲁亢一样写留学往事,写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度凝视,并将它们与读万卷书的知性体验融为一体,再和盘托出。凡此种种,都是诗人介入公共言说并借以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不同尝试。
我之于这套丛书的不少作者而言,算是老读者了。这里我指的是他们的诗歌。对于他们的随笔作品,我却读得较少。我愿意将这一次的集中阅读,当作一次发现之旅,去看看我似曾熟识的诗人,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更为丰富的一面。
(注:“中国诗人随笔系列·福建卷”拟于2015年10月由宁夏阳光出版社出版,共收入安琪《女性主义者笔记》、鲁亢《被骨头知道》、老皮《知天命》、何奕敏《去远方寻找自己》、深蓝《在春天或者在梦里》等五部随笔作品。)
(作者单位:福建省文学院)
1. 卡遛:福州地区方言,也通行于台湾马祖等地,意指闲逛、遛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