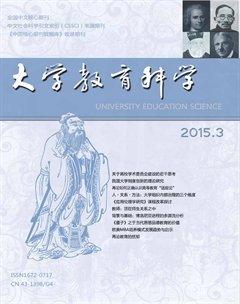再论教育的忧郁
摘要:为我们的教育而忧郁的人可谓有识之士。忧郁代表着一种觉醒,一种责任。我们把这种忧郁引伸到哲学上来,教育与哲学如此密不可分,兴盛教育需要同时从哲学和教育那里寻找出路。哲学的成长和繁荣离不开批判,教育及其他事业的兴旺需要深深的忧虑和深刻的批判。现在,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严重地妨碍着我们,我们太崇尚感性,缺乏理论兴趣和哲学兴趣在妨碍我们深入反思教育改革。
关键词:教育;忧郁;哲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3-0125-03
收稿日期:2015-03-25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名誉校长,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的研究。
教育是如此壮丽的事业,有什么可忧郁的?这是不是杞人忧天?教育如果无可忧郁之处,又为何需要改革?是谁看到了需要改革?这个“谁”是不是杞人?杞人的存在,在今日已经不是故事,许多人为我们自己的教育忧郁,这些忧郁的人可称之为有识之士。这种忧郁代表着一种觉醒,一种责任。
从19世纪后期以来,全世界可以看到美国的长盛不衰。它为什么会长盛不衰?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时刻是忧郁着的。它不是很兴盛、很繁荣吗?为何要忧郁?是杞人忧天吗?然而,一点也不假,他们真的忧郁着,真的常常做着检讨,自我检讨,没有旁人的督促,他们真诚地检讨而少见莺歌燕舞一类的颂词。当然,制度设计是很重要的。可是,制度怎么设计出一个忧虑来呢?
我特别仔细地读过博克校长在哈佛大学建校35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这篇演讲让人感动,当然也就让我难以忘怀。这个长篇的演讲中,竟对哈佛取得的成就只字未提,例如,它培养了多少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培养了多少位总统,均未提及,他所提到的是哈佛面临的危机与挑战,这篇演讲的开头就说到哈佛最初的校长夫人往学生稀饭桶里放羊屎的故事。由此,我能确切地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哈佛能成为常青藤大学,美国为什么成为常青藤国家?
在苏联于1957年把人造卫星送上天之后,科学技术本已全面领先的美国,却陷入了深深的检讨之中,并从这些检讨之中获得了众多理论成果,包括教育领域里的许多成果。
美国当然也有它引以自豪的东西,首先就是制度设计,另一个就是他们发达的高等教育,还有就是他们的NBA。社会制度的设计从华盛顿那里就开始了,一直保持着,议会,两党,常常争论不休。然而,正是这一点,他们很难有影响全局的战略错误。
发达的高等教育,则是从德国那里学来的,有虔诚的检讨,才有虔诚的学习。
篮球虽起源于英国,从19世纪末以来,经过了许多次的改革,才有了今天如此之高的观赏价值。它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运动员,包括中国的姚明、王治郅、巴特尔等球星。什么叫改革?什么叫开放?看看NBA就明白了。
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过大清洗、大镇压,有位中国人说,这在西方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在60年代发生了“文革”,又有一位中国人说,这在西方是不可能发生的。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么大的举动是必须经过议会的,那些议员们会赞成你大镇压、赞成你把全国都搞乱吗?他们连总统也可弹劾的啊。
中华民族亦必需有长治久安、长盛不衰,不能再折腾了。然而,也必须创造相关的条件。民主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却又是最不可少的。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就有民主与自由。我们有理由对自己有更多的期待。这众多的理由中,包括我们也正在学会检讨,学会忧郁,否则,为何还要改革?
自我检讨亦即自我批判,个人的、团体的、一个社会的自我检讨和批判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十分需要在充满自信与充满怀疑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恰如在骄傲与谦虚之间找到某种美妙的融合那样。可以有所偏颇,却不可只见其一。
对于教育的忧郁,不少人已有所提及。现在,我们把这种忧郁引伸到哲学上来。这种联想的产生是必然的。教育与哲学如此密不可分,无论在古希腊,还是古中国,哲学与教育都是同生同长的。后来的历史继续在说明,它们的盛衰是那样的难以分割。为了兴盛,也就需要同时从哲学和教育那里寻找出路。
当然,我们更可忧虑的,是哲学;哲学的成长和繁荣离不开批判。批判的事业不兴旺,哲学能兴旺吗?哲学不兴旺起来,教育及其他事业能兴旺起来吗?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有过大批判,但那不是哲学意义下的批判,而是意识形态下的批判,那时的大批判是与大整人连在一起的。只有批判,没有批批判的。这种历史,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批判事业难以繁荣的一个历史包袱呢?卸掉它吧,可是,谁来卸?只有批判者自己来卸,批判是与发展同在的,与繁荣同在的,而且可以与友谊同在。这都属于学术,而学术批判,是学术的生命之源。都知道“真理越辩越明”的道理,那就辩起来吧,否则,真理怎能“越明”?
我国古代有过哲学的辉煌,近代,我们也有过王国维、陈寅恪;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也有过贺麟、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这样的世界级哲学家。哲学是智慧的科学,中华民族不缺智慧,因而,我们对自己哲学的未来不必太悲观。
尽管我们可以乐观,然而,又不能不忧郁,这种乐观不能不与应有的、深深的忧虑连在一起。眼下,我们太崇尚感性了,太缺乏理论兴趣,太缺乏哲学兴趣了。学术上的功利主义严重地妨碍着我们。这可不是杞人忧天啊。
有关“实践出真知”的观念是诸多不利于我们学术事业的观点之一。2014年12月31日,省委党校的常务副校长张国骥(我多年的老朋友),和我在一起聚会时,他谈起最近自己读到的一些天文学知识,天文学家们所说到的一些天文奇观,哪里是从实践来的?实践怎能知道银河有多宽?宇宙有多大?
岂只是天文学,爱因斯坦的理论是从实践来的吗?非歐几何是从实践来的吗?全世界的艺术的各个种类当有千种万种了吧,是从哪千种万种实践中来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哲学是从什么实践来的?康德的大爆炸学说是从什么实践来的?
哲学辞典把实践界定为感性的、物质的活动,我相信我的众多的论著,绝大多数与这种实践无关。比如我的《哲学是什么》、《人论》、《数学方法论》、《数学文化》、《人是美的存在》等等就不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什么呢?这些著述大多源自于我的心灵感应,对人对天的感应。我坚信,人最伟大的方面莫过于其思想和想象力,可以穿透几乎所有的事物而入木三分。人还有支撑这些东西的无限情感和意志。
为什么原理性的发现极少出在我们这里?为什么我的哲学十分贫乏?为什么哲学难以成为我们全民族的事业?为什么我们很难有成批的哲学家出现?为什么北大这样的大学在蔡元培之后就再难以有教育家?为什么近60年来大陆没有出现过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为什么我们的高等教育连亚洲一流的水平也还达不到?为什么昔日的北京大学比东京大学强而今却是后者大大强于前者了?为什么以色列这样的国家在短短的时间里创建了世界一流的希伯来大学而我们难以企及?全世界把大学当做政府机构对待且赋予其官级的,为什么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两三个国家?为什么改革开放已30余年了,教育的改革还收效甚微?为什么教育被人们视为改革要攻破的最后一座堡垒?为什么我们的教育科学也十分落后?
再细一点,应当还可以问更多的“为什么”,更多地问问我们自己的教育。我们该不该多问问呢?所谓多问问,也就是忧郁,我们该不该忧郁呢?能不忧郁吗?
近20年来,政府搞了“211工程”,还搞了一个“985工程”,拿出了大量资金,谋求办出一批高水平大学来。有一個“2+7”的计划,这个“2”就是北大、清华,希望把这两所大学办成世界一流,投资也相当大。可是,世界一流大学还真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当今的中国已经不缺钱了,缺的是什么呢?缺改革,缺深入的教育改革,缺从根本上、从体制上进行的改革。我们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希望就在这里。若要动真格的,就从这里做起。
有谁比生活在大学里的人更懂得大学?有谁比大学自己更知道怎样办大学?有谁比大学里的人更有可能把大学办好?尽管“旁观者清”之说有一定的道理,大学也别忘了听取来自社会评价的声音,然而,这仍然只是辅助性的。看得清楚的,还是自己,尤其是那些清醒的大学及其管理者们自己。身临其境究竟还是不一样的。
以上所言,似乎是十分浅显的,几乎就是常识的问题。为什么也存在呢?站在大学外面的人,可以去评价它、质疑它,但若明智一点的话,就不要去管它,不要去插手其内部事务,让大学自己去忧郁自己吧!它所必需的忧郁,谁能从外面给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