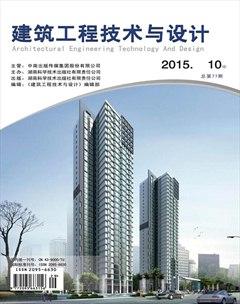回到未来
王颢霖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城市发展迅速,国外建筑师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建造了一系列或追求建筑高度,或造型体量戏剧的“标志性建筑”。此类建筑盲目追求新奇,为与众不同而求新求异,脱离了建筑本初的原则,单一的建筑语言使建筑的民族性难以为继,也使城市与城市之间,面容渐趋相似。与此同时,在当代建筑的浪潮中,以王澍、张永和、刘家琨、董豫赣等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建筑师,试图从历史经验中抽取传统精神作为未来创作的源泉,积极寻求中国当代建筑自我的道路。
【关键词】实验建筑;本土;建筑精神
回溯上个世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之间,建筑的差异还极为明显。然而,新世纪的今天,随着社会的变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筑的民族特色却在现代化建筑的浪潮中,渐渐消解。国内城市多高价聘请国外建筑团队,建造了一系列或追求建筑高度,或造型体量戏剧的“标志性建筑”。单一的建筑语言使建筑的民族性难以为继,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面容渐趋相似,城市价值的认同与判别,错误的被引导向依靠视觉冲击性的地标建筑中,忽视了适合城市自身的建筑叙事方式。
从国家大剧院的建设到奥运场馆的“鸟巢”方案、CCTV的新办公大楼,对国外建筑师在国内进行的大型建筑工程,国内各界一直存在著议论。此类建筑动辄花费十几亿或是几十亿的高昂设计费用,同时因其对新奇形式的追求而做出一定功能上的妥协,建成后城市居民的接受度并不乐观。建筑是承托着社会生活,城市历史文化的物化场景,此类建筑的设计并没有很好地考虑其与城市历史文化背景的衔接,及与周围环境空间的协调性。以央视新办公大楼为例,单纯从建筑设计,技术角度来看,不失为一件优秀的建筑作品,但将其放置于北京这样一座传承千年文明的城市中,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究其根本,国外建筑师的作品,缺少的恰是当代中国建筑中应存续并探索的本土建筑精神。
与国外建筑师在国内的“大手笔”相对,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国内对国外建筑师迷信的现象正被打破。以王澍、张永和、刘家琨、董豫赣等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建筑师,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当代实验建筑的道路上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近年来,如王澍、李晓东、马岩松等中国建筑师纷纷走向台前,在国际舞台上展露,摘取诸多建筑奖项。中国建筑当前正处于一种多元化的局面,中国本土建筑师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标示着中国当代实验建筑的前途与方向。他们对于自身建筑风格的追求本身所反映的是“中国知识精英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和建设所持的理念” 。如王澍先生倡导的“诗意城市”的情怀与“回到未来”的构想,是其作为一名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也是其作为一名“哲匠”建筑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从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宁波博物馆、南宋御街改造项目,以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的瓦园,都体现了王澍先生富于中国传统精神的建筑叙事方式。以宁波博物馆为例,其建筑通体坐落在灰瓦色的高台之上,主体部分以开裂的方式完成空间的高度;这种开裂使观者感受到一种张力,一种执拗的对冲与盛大的抗衡;恣意而秩序,随心而不逾矩。同时,瓦爿墙与竹模板砼墙的运用,更于自然与人工的对话中演绎了意趣盎然的和谐,营造了“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氛围。采用几何叙事的构筑手法,合围成以建筑写胸中丘壑的内向自省,建筑整体以一种既回望传统又自由于未来的姿态存在于自然中,重新收集并记忆着这片土地曾经存在与即将拥抱的时间。
中国当代实验建筑带来的是富于本土性的传统建筑精神。本土的精神见证着代代相传的品位、情感,见证着公共、个人的事件与发展,身处祖国大地上的人们更容易被这种本土精神所感染,也就更容易在此类空间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 建筑不仅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它亦承载着城市的历史,凝结着社会的变迁,为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提供一种身份认同的方式。当代中国城市与建筑需要能够承载、传承中国记忆和精神的城市与建筑,其应是城市记忆的延续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诠释。近代以降,中国建筑师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归属两难,许多建筑师将传统与现代对立,全盘否定传统或现代,或在其间摇摆不定,致使中国建筑产生了一定的身份焦虑,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具有集体性认同的建筑范式。传统与现代的问题,“本质上是文明(裂变)问题而非建筑(形式)问题” 。面对当代中国实验建筑可以看出,传承并非一味的追求过去,更不是对传统建筑形式的模仿,追求传统精神更不是要“复古”,“而是把将来折射为过去,通过对某种遗失的形象的回忆、追溯和融合实现一种当代的艺术理想” 。我们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中国性的现代建筑,建筑的中国性亦不是依靠表面的形式或符号来支撑,其彰显有赖于建筑师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意识和传统生活方式所包含的精神性的认同。从冯纪忠先生的方塔园,汪国瑜先生的云谷山庄,到刘家琨先生的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王澍先生的宁波历史博物馆、瓦园,冯先生“与古为新”的概念一直伴随着当代实验建筑的发展,“所有的设计中——从格局、到结构、到细部——都隐隐地呈现着源自中国传统的古意,也都有着经由现代建筑之后的二度创作和阐释” 。是用现代的“型”,写传统的“意”。诚如刘家琨先生对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的阐释,“从总的追求方面,它显然是一个当代性的追求,但是它跟自然的关系,是一个东方式的传统的关系”,归去来兮,我们仍会心于千百年来与自然共生的辩证关系。
回望过去,可以寻到未来的路,一代又一代中国建筑学人都在其存在的时代为中国建筑的事业播撒下理想的稻种。当前中国实验建筑师正在行进的路,是对现下中国城市建设及城市建设中涌现的大批量建筑的反思与超越,是实验建筑师们主动赋予中国建筑发展主体性问题而不断做出的解答。实验仍在继续,也乐见继续,真诚的建筑带给我们切实的美的感受与使用的舒心畅快,还原我们生活里最本质的真实,它是真实而广泛的建筑受众所应得的尊重,也是一代代建筑学人道路的方向。果实的孕育总需热夏的时光,以罗丹的话作结“那由时间所凝结的,必将得到时间的尊重”。
参考文献
[1]赖德霖.《六零学人文集·走进建筑 走进建筑史:赖德霖自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周榕.《不一不异,与古为新——当代语境下对传统文明的批判性认同与包容性建构》【J】,《城市建筑》2014年10月刊,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3]巫鸿:《美术史十议》【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4]刘东洋:《这里也有风格派?》【EB/OL】,http://www.douban.com/people/dyl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