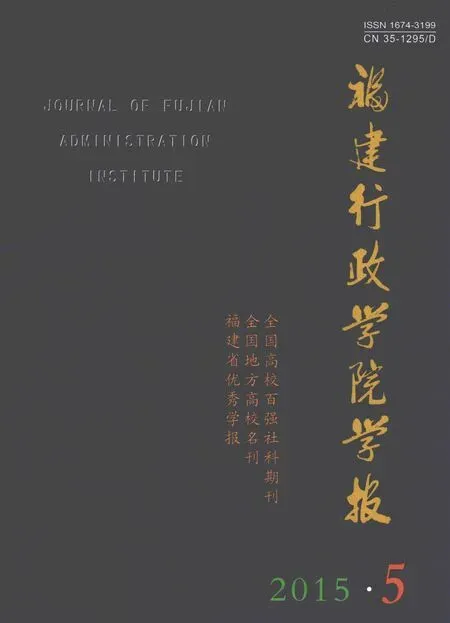家族政治与腐败桎梏——后威权时代菲律宾的民主困境
王尘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一、后威权时代的菲律宾政治状况
就政治制度而言,称当前的菲律宾为“东方的民主橱窗”并不为过。由于在历史上和独立之时深受美国影响,菲律宾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体制基本仿效美国,甚至连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也对美国有样学样。例如,议会实行两院制,分为由全国选民投票选出的参议院和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的众议院;行政体制为总统制,行政权归属总统,其任期为6年且只能任职一届,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由总统提名委任。司法权隶属于最高法院,下设三级法院和一些专门法院和特别法院。完全仿效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14名陪审法官组成,首席法官具备对其他法官的领导权。[1]
最近几十年来,菲律宾经济快速增长,已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新型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人数日益壮大。有鉴于此,政府在社会领域也按西方理论建构本国的社会模式,大力扶助和发展非政府组织(NGO),力图形成“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使“社会”成为国家的对立物和制约者。当前,菲律宾拥有各类非政府组织7万多个,该数量在所有发展中国家排名第三,诸如文化、宗教、人权、农村发展等各种领域中的非政府组织正在该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
经典的腐败治理理论认为,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中产阶层的兴起与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司法程序应当能够对政治腐败起到巨大的约束作用,但现实情况恰恰与此相反,菲律宾非但不是一个清廉的国家,甚至是亚洲地区最为腐败的国家之一。在2014年“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菲律宾只获得38分(0分为最腐败,100分为最清廉),在全部17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5位。[3]猖獗泛滥的腐败现象从一个侧面证明,在西方民主的宪政体制的表象下,菲律宾实际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政治运行程序远非完美。根据菲律宾参议院公布的一份报告,2001年由于腐败和管理不善,政府预算共损失950亿比索。相关人士还指出,从1988年开始,每天大约有1亿比索的公款被贪污[4],前总统马科斯甚至曾“荣登”吉尼斯世界腐败纪录。
二、家族政治与政府腐败
家族政治盛行是菲律宾政治权力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从政治权力结构视角出发,菲律宾国内政治中的各大家族势力组成了官僚体系内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既有政治结构中,这些大家族的成员在担任公职时凭借制度安排,将附着于权力的特殊利益当成职业目的来追求,蜕变为比较稳定的特殊利益主体,并在抗拒对其既得利益的相关政策调整、维护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完成了行为和观念的群体化。
家族政治现象在菲律宾表现得尤为突出,根植于西班牙殖民时期庄园制的庇护关系结构①在300余年的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菲律宾形成了土地高度集中的大庄园制,也由此形成了两大截然对立的阶层:掌握各种资源的西班牙土著贵族阶层,以及永远贫困的佃农阶层。与中世纪欧洲类似,佃农把地主视为自己的恩人和保护人,从而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形成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主从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菲律宾长期以来家族政治的基础。和美国政治模式中的一种典型功能缺陷——政党分肥制,由菲律宾精英家族组成的集团持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获得比其他民众更多的利益。换言之,传统庇护关系使菲律宾民众在选举和改选的过程中倾向于支持他们的政治庇护人。庇护关系使人相信,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政党而是个人和家族。另一方面,这种庇护关系进一步强化了民主政治中的政党分肥问题,不仅执政党领袖把政府官职或其他好处作为酬劳分配给在竞选中出过力的本党党员和个人亲信,党员和个人亲信也更倾向于跟随、效忠领袖而非效忠于国家和政党本身——无论是为了偿还政治人情,还是为了获取政治上的好处。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菲律宾精英家族的规模日益庞大,他们不仅在国内手握大权,而且与更大的国际市场和外国政界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政治精英家族有能力把持他们在地方和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多代不变,并凭借他们对区、省、镇的牢固控制建立起强盛的政治王朝。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北伊洛戈省的马科斯家族、打拉省的阿基诺家族和伊洛伊洛省的洛佩斯家族。在中央层面,各主要家族操纵选举、扶植朋党、扩充权力。例如费迪南德·马科斯能够长期维持其寡头统治,主要原因在于他能够依靠强大的家族势力建立起由忠诚的亲友和技术官僚组成的精英联盟。即使是在进入“民主转型”之后的“后威权时代”,情况也没有根本改变。出生于阿基诺家族的贝尼格诺·阿基诺当年是马科斯的强大竞争对手,而他的夫人科拉松·阿基诺最终完成了丈夫的夙愿,推翻马科斯继任总统一职。时隔多年,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则又是科拉松·阿基诺的独生子。总统的这种沾亲带故关系并非巧合,其历史上所产生的15位总统中有12位存在亲属关系。另外,以1986年民主转型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为例,169名众议员是精英家族成员或是与各个家族具有某种特殊联系,而众议院总议员人数也只是200名而已。
植根于东南亚地区的传统荫庇关系和西班牙殖民时期的阶层固化,菲律宾的家族政治并未在后威权时代的民主化转型中自然消弭,而是愈演愈烈,导致政治权力在几大家族中分配的权力结构固化现象更为严重。“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难以被制约的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所握有的政治权力使腐败问题难以得到根本好转。据世界银行统计,菲律宾大约40%的国家预算由于腐败而流失[5],为了在激烈的政党竞争中胜出,这笔巨额资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家族政客用来买通电视台、电台和报纸等媒体,炒作各种与自己有关的话题以提高知名度和关注度。
三、菲律宾的腐败治理困境
就西方腐败治理理论而言,完善的反腐败法律机制是实现政府清廉的必要保障。吊诡的是,拥有相当完备的廉政机构设置和廉政法律法规体系的菲律宾却长期深陷腐败泥潭,在腐败治理过程中手段频出却鲜有成效。
菲律宾的廉政机构主要包括反贪污法院、审计委员会、独立调查处以及监察专员署;从1960年颁布实施《3019号反腐败行为法》迄今,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廉政法律体系。在《宪法》第十一条中明确规定公职人员问责制,要求公职人员和政府雇员需要全面问责和绝对诚实,正副总统、内阁成员和最高法院成员等如果出现违反宪法收受贿赂的情况应当被立即弹劾并通过正规司法程序起诉。《3019号反贪污行为法》则进一步界定了腐败内涵,明确了相关腐败行为的惩罚措施,还要求公职人员每两年向政府诚实申报财产。进入后威权时代,各民选政府又相继颁布了各类反腐败法律法规,如阿基诺夫人任职期间制定的《6713号共和法令》《6770号反贪调查员法令》,进一步要求所有政府官员必须诚实准确申报财产、公布净资产和财务关系,新任官员必须在就任前30日内剥离与任何私营企业的关系以避免利害纠纷,同时设置功能性极强的专职反贪机构——反贪调查局,遏制政府腐败。为了保障反贪机构的独立性,使其成员不必担心因履行职责而遭报复,相关法律条文还赋予了这些机构财政独立的地位,它们的行动只需向最高法院负责。[6]此外,后威权时代的菲律宾并未实行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制度,而是力保新闻自由,努力发挥大众传媒和民间组织在反腐败中的作用。阿罗约总统甚至将手机短信作为民众举报腐败嫌疑的媒介以期充分发挥反腐败的公众参与。
但是,制度反腐的努力并未受到应有回报,更确切地说,在家族政治现象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国内政治权力格局没有发生本质转变的情况下,这些廉政法律和政策大多无法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廉政机构也无法发挥应有作用。政坛腐败有增无减,甚至总统本人也在高呼反腐口号的同时因为腐败丑闻被掀翻。全盘仿效美式民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上层政治权贵以合法性,打着民主选举上台执政旗号的政客和掌握权力的公职人员能够通过荫庇关系与政商结合的寻租手段不受约束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轻易获取非法利益,分享本已稀少的社会资源并强化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意图对腐败问题进行治理的政治家本身又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代理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反腐举措绵软无力且无法被落到实处的问题也并不令人奇怪,反腐败成为了各大家族争权夺利、清除异己、夺取政权的政治手段,甚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本身也与政治权贵家族关系复杂。
1986年上台的科拉松·阿基诺发誓要与各种腐败行为作斗争,但在她任期内,国家每年大约有30%的预算因腐败流失。[7]1998年,出身草根的明星总统埃斯特拉达在选举打出的竞选口号是“振兴经济、消除贫困、发展教育、严惩腐败”,但埃斯特拉达本人却深陷腐败丑闻,在众议院弹劾他的8项罪证中,6条涉及权钱交易和官商勾结,另外2条直指其任人唯亲。在透明国际2004年世界10大腐败领导人排行中,埃斯特拉达榜上有名。2001年,埃斯特拉达被阿罗约发动的“第二次人民力量运动”推翻,但就在埃斯特拉达被控腐败且被判终身监禁的同时,以反腐败为名上台的阿罗约也因选举舞弊深陷腐败泥潭,随后阿罗约对全国民众正式道歉并表示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2010年下台后,阿罗约又被选举委员会旋即指控涉嫌与安帕图安家族共谋操纵马京达缁省的参议员选举,从而使12名阿罗约的亲信候选人全部当选,同时,反贪检察官还指控阿罗约及其丈夫收受某电信设备制造公司的巨额回扣。
那么,为何拥有完善的廉政法制体系和美式民主制度架构的菲律宾无法抑制各大权贵家族的势力扩张,有效治理精英阶层的腐败顽疾?
四、美式民主的桎梏
在很多西方学者的眼中,民主选举、多党竞争等一直被视为实现权力监督、遏制权力腐败的灵丹妙药,这些制度还能保障一国较强的自我纠偏能力,使当政者及时调整国家政策。此外,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础的美式民主在历史上也曾深受政治精英权力膨胀之苦。由于基本照搬美国政治制度与民主模式,因而也难以摆脱美式民主精英治理模式的桎梏。换言之,即使是在美国这个自诩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几大家族轮流当政和政商结合、甚至是学界与政界剪不断理还乱的“旋转门”模式时至今日仍是一种常态。
根本而言,美式民主精英治理模式的合法性依赖精英与民众之间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即政府作为民众的代理人,接受民众委托并对民众负责。这种关系赋予了美式民主正当性,也使位居上层的政治精英与民众结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契约关系。从历史看,这种“委托—代理”模式最早出现在经济领域。在西方资本主义公司制度中,产业财富的“所有者”仅仅剩下象征性的所有权,而权力、责任以及财产的真正所有权正逐渐被让渡给一个手中握有控制权的独立集团[8],换言之,股东们将财产委托给职业经理人进行经营,经理们作为代理人对股东负责。当西方各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委托—代理”模式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各类组织形式的核心,并逐渐成为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精髓和人民与政府的普遍关系模式,其在政治学领域的表现则是经典的契约论原理。
“委托—代理”模式的主要优点在于,政治精英可以完全以代理人角色行事,而不必在每件琐碎的事务处理中过多考虑委托人的具体意见,以此有效提升政府效率和政府的治理能力。但这种模式的缺点也很明显,亦即无法保证作为代理人的政治精英不会背叛作为委托人的普通民众,换言之,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代理人可能因为委托人的无知而采取机会主义行动为自身谋取利益。①“理性无知”(rational ignorance)指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无法追究真相,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内部人”对民众刻意隐瞒真相,以及了解真相的成本太高。而作为委托人的普通民众要想发现代理人的行为真相,可能将耗费很高的监督成本,于是代理人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就会有空可钻,违背委托人的意志或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则是政府的寻租行为和官僚腐败。因此,在民主理论中,普通民众如何防止精英的治理行为不会偏离公共利益,如何制约精英的权力就成为了一个长久争论的关键问题。在美国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这也成为了所谓“大众民主”②“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并非是一个规范的政治学概念,事实上,它是一种价值取向,一种与精英立场形成鲜明对照的底层立场,也就是大众主义取向的民主。正是认识到现代所谓的民主为少数精英所得,变成少数人操纵的工具,“大众民主”概念才被针锋相对地提出。在历史上不断推进的一个主要动因。
如果说西方国家能够通过完善的大众民主体系和充分的阶层流动性对上层统治精英实现有效制约,那么按照美式民主依样画葫芦的菲律宾则是只学皮毛不识本质,严酷的荫庇关系和家族政治现状使阶层固化现象严重,例如历史上全部的15位总统中,只有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出身平民家庭,其余皆来自奥斯梅纳、洛佩斯、阿基诺等各大家族;历届众议院中也有大约2/3的议员来自各地政治家族,而这些家族多数也是叱咤经济界的大财阀。少数政治精英凭借家族权力执掌政权、公职人员自利自肥等问题反而愈演愈烈。在政治、经济领域执掌权力的精英阶层不想、也没有必要与普通民众分享权力,因而植根于“委托—代理”模式的美式民主顽疾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当权的精英阶层难以受到普通民众的有效制约。可以说,菲律宾实行的只是“形式层面的民主”,一些学者甚至将其作为“民主失败”的典型案例。[9]
五、经验与启示
首先,西方民主制度并非遏制腐败的万金油。在缺少足够的大众参与、家族政治根深蒂固、传统政治文化大行其道的情况下,以“委托—代理”模式为核心的西方议会民主的政治架构本身难以实现对政治权贵和上层官僚的有效制约。与此同时,“委托—代理”模式还以代表社会各阶层利益为基本要义,而这也为各种政治势力提供了生长和张扬恣肆的政治环境,结果易使政府陷入纷繁复杂的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的泥潭,加剧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另一方面,即使菲律宾拥有比较完善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和反腐机构设置,民主制度所固有的审慎特点又可能造成政府在制定反腐政策、采取反腐行动过程中出现拖沓不决、效率低下的问题。由于治理腐败意味着政府需要对既得利益集团和大量内部机关开刀,因而也使相关政策的出台尤为困难,各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影响政府决策,使得有效的反腐制度难以实施。
其次,从菲律宾的案例中可以发现,由于腐败治理困境源自美式民主的“委托—代理”模式,权贵家族与普通平民的利益需求分化严重,因而提升政治阶层流动性、扩大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是高效整治腐败的必要前提。在大多数成功治理腐败问题的西方国家,大众民主已经成为常态,各个阶层参与政治并发挥影响力意味着对政治资源的进一步分化,即声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分离。在这些国家,声望意味着选票,选票意味着公共职位,而公共职位则意味着影响力。因此,社会不同阶层的流动直接导致从以累积性不平等为基础的旧式寡头统治模式向以分散性不平等为基础的新式精英治理模式的转变,而后者又成为了消除官民信息不对称、实现民众对政府有效监督的关键。
再次,构建负责任政治文化和平等的民主理念是廉政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菲律宾腐败屡禁不止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纸面上的廉政法律与反腐机构设置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荫庇制传统和家族政治观念。根本而言,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产物,而政治文化又需要政治制度的支撑才能够得以长期存在。由于西方民主制度并非亚洲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产物,因而难以完全适应本地区的基本国情。许多照搬西方民主的亚洲国家,如菲律宾、印度等,由于过度分权普遍存在家族势力和地方政府尾大不掉的现象,“委托—代理”模式的弊端表现的更为突出,也更容易受到腐败的侵蚀,反倒是日本、韩国等中央集权较强的发展型国家能够对导致腐败的既有分配机制进行严格控制,自上而下抑制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并通过加强监管等途径有效狙击腐败。
最后,对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努力而言,植根于家族政治和民主制度缺陷的菲律宾腐败问题更能对我国的相关实践有所启发。菲律宾各大权贵家族的本质是既得利益集团,而美式民主的固有缺陷使菲律宾在治理既得利益集团腐败的过程中暴露出国家能力和政府效能不足的问题。因此,遏制既得利益集团,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也就成为了我国在廉政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环节。当前我国的廉政建设要有开阔视野和长远眼光,不仅需要通过民主化、法治化、公开化的改革制约已经形成或可能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建立一个规范化、法治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法治基础上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与公众参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等的关系,建设具有透明性、回应性、责任性和开放性的服务型政府。
[1][澳]约翰·芬斯顿.东南亚政府与政治[M].张锡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房宁,许利平,郭静.菲律宾:一座政治博物馆——对菲律宾民主政治的实地观察[J].文化纵横,2014(1).
[3]透明国际.2014年全球清廉指数调查报告[EB/OL].(2015-02-19).http://cpi.transparency.org/cpi2014/results/.
[4]瑞军.总统的特权与悔过[J].政府法制,2011(27).
[5]Simon S.C.Tay,Maria Seda.The Enemy Within:Combating Corruption in Asia[M].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2003.
[6]李文,王尘子.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J].政治学研究,2014(3).
[7]季正聚.菲律宾三任总统与腐败[J].中国经贸导刊,2003(1).
[8][美]阿道夫·伯利,加德纳·米尔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M].甘华鸣,罗锐韧,蔡如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9]颜武.菲律宾:家族政治与腐败成灾[J].检察风云,20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