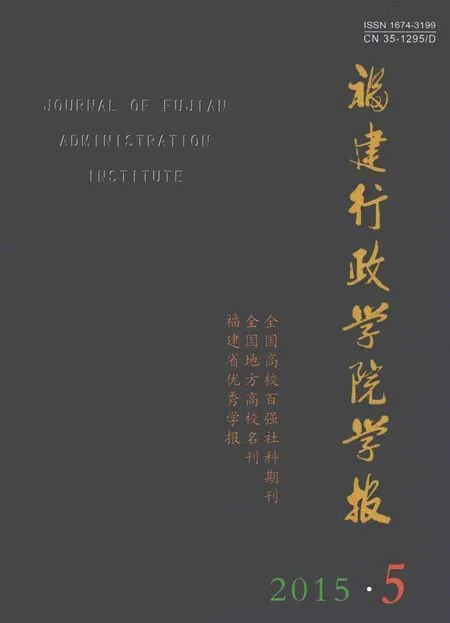传统节庆文化记忆的巩固与传承
——以泉州市元宵节为例
李双幼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市情研究所,福建泉州362000)
社会与文化
传统节庆文化记忆的巩固与传承
——以泉州市元宵节为例
李双幼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市情研究所,福建泉州362000)
元宵节庆历时久远、内容丰富。泉州市祭祖祀神、祈利求福、祈育示丁、文娱喜庆等各种节庆传统,既保留了重申宗族伦序和地缘秩序的身份认同功能,又发挥了世俗的娱乐性和彰显家庭亲情的亲缘纽带维系作用。从时间维度和组织化情景两方面来考察,元宵节庆的集体行为在加深人们对有关记忆的沟通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传统节庆文化记忆的建构过程中,记忆的主导主体明显发生了变迁,而文化认同的实现脱离不了地方性场景的作用。
文化记忆;元宵节庆;泉州市
自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集体欢腾”、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集体无意识”等理论基础上,提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记忆”之后,记忆研究角度便从个体转向集体,也由此带来一种新的诠释个人及其所属群体的视角,进而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兴起了社会记忆的研究课题。在这场关于过去、记忆和历史关系的探讨中,德国学者夫妇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厘清了各种记忆形式的内涵后,在文化社会学的框架下概括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沟通记忆——文化记忆”的基本过程,认为通过客观化的文化型构载体(文字记载、礼仪仪式、文物、建筑等)和机构化(或制度化)的交流渠道(朗诵、庆祝、观看等形式),可以把过去的内容保持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从而在时间维度和组织化情景中赋予文化记忆以经验和意义。本文从“定期举办的纪念仪式是使过去得以存活的最早手段”和“有些记忆只有不断地通过新的行为一再地重现它们,才能得到巩固”[1]出发,在文化记忆的理论视角下,探析传承久远、盛演不衰的泉州元宵节庆活动所呈现的记忆内容和文化传承等问题,考察其中的历史变迁和借鉴意义。
一、记忆的视角:泉州的元宵节庆传统
不同的习俗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内涵,也寄托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愿景,承载的却是生活其中的人群共同的文化记忆。泉州的风俗历来繁多,而元宵更为隆重,从官府到民间均参与其中,并再次掀起贺喜新春的高潮。具体而言,泉州的元宵节庆习俗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祭祖祀神
不管是认为元宵节来源于汉家王朝正月上辛日的祭祀仪式,或是来源于汉唐时代的燃灯敬佛,其与祭祀敬神息息相关是基本可以确定的。
1.祭祖。元宵祭祖包括家祭和祠祭两种。元宵节的家祭虽不及中元、冬至和除夕的家祭隆重,但接春纳福的祭春意义使各家都不敢掉以轻心,连灶君、土地等在内的家神也被纳入祭祀对象,其中,煮熟的元宵丸是必不可少的祭品。祠祭的规模则依据宗族的大小而不等,春祭的时间不同于冬祭之固定在冬至日举办,有的在正月十五,有的在正月十八或其他日子。调查发现,为了将祭祀活动与新正节日结合以示隆重,也为了便于在固定的时间尽量多地召集到事务繁忙的宗人参与,在元宵节当天进行春祭成为越来越多宗族的选择。
2.祀神。历史上,在元宵节祭祀地方保护神在各地均是重要的活动,一般伴有巡游(绕境)的迎神活动。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之风俗十八记载,迎神前,先穷极珍贝,妆饰神像,再“择其境之齿德而裕财者首其事,鸠金订期设醮,然后迎神,周其境内人家置几椟焚香楮者甚恭”。迎神巡游往往能掀起祀神活动的高潮,甚至有的境铺、村落之间为了争夺巡游的边界而起争端。建国后,在扫除封建迷信的大环境下,除了乡间偶有为庆祝神诞或新址落成而进行的“刈香”外,奢靡鼎沸的迎神赛会早已销声匿迹,而“杂牌”的民俗表演队伍因其娱乐性,被文化部门利用改造为“文艺踩街”活动,并美其名曰“歌吹漫步”。偶尔有台湾信众遇神祇诞辰奉尊回祖庭祭拜时,当地为照顾其信俗需求,也允许其举行“巡境”。
(二)祈利求福
1.吃元宵丸、润饼菜。饮食最直接地实现了节日习俗的现实意义,泉州元宵节庆有元宵丸和润饼菜两种最主要的应节食品。在元宵当日,全家以供祀过的元宵丸作为早餐,并且以此招待客人,预示着家庭团圆和睦,圆满吉庆。而润饼菜既发源于泉州,又流行于闽台,寓意团圆美满,有包金包银之吉兆,是海峡两岸新年、尾牙和清明节祭祀祖先的应节食品,也是家族成员聚会的重要饮食。
2.孝敬“代人”。所谓“代人”即人的代替之身,由薄纸篾和五色纸糊成人的模样,预示由这些“代人”替主人祛祸消灾,以保一年的好运。
3.听香。主妇或年轻女子为求解难决之事,在自家厅堂或宗祠或寺庙,向神明焚香求告指点迷津,然后卜出听香方向和走路步数,到达目的地后窃听他人话语,据此判断大致意向,再返回卜问,确定所听之话是否即为答案。如果不是,则重新卜问。过去泉州“听香”之俗极为普遍,有“正月十五听香小仙梦”的谚语,如果错过了元宵夜,还可以在中秋夜继续听。
4.乞寿龟。寿龟寓示平安长寿、生意兴旺,寿龟的样式各异,大小不同,由米粉或面粉蒸制而成。乞寿龟要通过向神佛卜信杯,取得允许后方得拿去,且一般要许愿来年将奉还比今年规格大、数量多的寿龟。自2007年开始,泉州天后宫与台湾澎湖天后宫每年元宵联合举办“乞龟祈福”民俗活动,很受大众欢迎。
5.祭祀“棕蓑娘”。棕蓑娘,即厕神紫姑,未成年女孩为祈求心灵手巧、精于女红而祭。
(三)祈育示丁
“灯”在闽南语中与“丁”同音,每一盏灯就是一个具体家户或是一位男性成员的象征,因此同时具有光明与添丁的意思。
1.上灯。凡是过去一年有得子之家,都要在族内宗祠里挂灯,得多少子挂多少灯,如此族人可据此得知添丁人数。
2.数宫灯。这是晋江东石镇特有的习俗,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元宵,新婚男子都要在镇里的嘉应庙(也称三公宫)悬挂宫灯,以示新婚祈子并贺新春。移居台湾嘉义县的东石人将此俗照搬过去,形成了“闽台两东石,共数一宫灯”的特殊风俗。
3.送灯。相传起源于南安丰州傅氏家族的做法,元宵前娘家送新嫁女红、白莲花灯一对,元宵节点燃双灯,如果白灯被烛火所焚,则预示生男丁,红灯被烛火所焚,则预示生女婴。
4.接龙灯。此风俗多见于山村。龙灯的龙头和龙尾是事先备好的,而龙身则由各家各户自备的灯笼连接而成,全村组成一条龙,灯龙越长,表示该村人口越多。[2]此俗与祭祖中的迎灯有异曲同工之意。
5.钻灯脚。元宵入夜,当年的新妇各执一根带尾的甘蔗(预示着夫妻和睦的吉庆含义),由婆母带领到祠堂,从厅堂的彩灯下穿行而过。早些时候,有好事者会将点燃的鞭炮扔向正在钻灯脚的新妇们,增添喜闹气氛,是为“戏新娘”。
6.抢佛仔。此俗亦为晋江东石镇所特有。元宵夜,新郎新娘同到宫中观灯,新郎用红蜡烛向庙祝或执事换取泥塑做成的佛仔,以祈新娘早生贵子,新娘担心佛仔不够,不待庙祝动手就径自去抢,从而形成抢佛仔的热闹场面。
(四)文娱喜庆
元宵灯会相传始于隋唐,盛于宋,明时全面复兴,民间对灯会的热情也渐渐高于官府,且融入了杂技游艺与戏曲表演,增加了许多娱乐的内容。[3]
1.赏灯、游灯。是日入夜,家家点上元灯,小孩则手提各式各样的“鼓仔灯”,呼朋引伴形成游街闲逛的队伍,给节日增添不少童趣。而每逢元宵,泉州城内不仅沿街挂花灯,还先后在开元寺、府文庙、后城街、文化宫、威远楼、新门街等场所设灯会展,吸引远近市、县的游人前来观赏。泉州闹元宵习俗、泉州花灯、泉州花灯制作工艺之一的李尧宝刻纸均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安英都镇的拔拔灯俗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将古时纤夫的“拔船”融入游灯闹春民俗活动中,并间以南音管弦乐队等民艺表演。[4]
2.戏曲表演。既娱神又娱人的性质使戏曲具有聚拢人群的舞台魅力。作为一种成熟的表演艺术,它在明代开始融入传统节庆活动中,至清代成为民间娱乐的最主要方式,并且与传统节庆形成了互相推动的影响关系。[5]有趣的是,在全国各地的戏曲中,元宵节成为不少剧目的故事背景或剧情要素,而且大致可以分为“元宵闹剧”和“元宵爱情剧”两大类,凸显了元宵节的娱乐和情感色彩。泉州元宵节庆中展演的地方戏有梨园戏、高甲戏、傀儡戏、布袋戏等,其中元宵闹剧多为水浒剧,而爱情剧则以梨园戏《陈三五娘》最为脍炙人口。
3.游艺杂耍。“妆人”游艺包括装阁、火鼎公婆、踩高跷、骑驴子等,杂耍有弄龙舞、刣狮队、宋江阵、车鼓阵等,至今在元宵游艺和丧葬队伍中还存留。此外,攻炮城、戏相贡(手旁)等习俗现今已鲜少见到。
二、节日的意象与记忆的巩固
以上所述各种元宵节俗在泉州各地的普及程度不一,在历代移风易俗的变迁过程中,有的仍存留,有的已发生蜕变,也有的不免式微甚至消逝。为了具体观察泉州元宵节庆的现代表征及其内在隐喻,本文结合调查问卷和个别访谈的方式,分别对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对元宵节的认知、对元宵节庆活动的参与和评价等方面进行调查。问卷分别于2015年元宵节前后在泉州府文庙、仰恩大学、丰泽广场、美食街等地发放。本次共发出问卷300份,回收275份,有效问卷266份,有效率96.72%。从调查问卷和访谈内容的结果可以看出,随着年代和时态的更移,元宵节作为重要的传统岁时节俗,其原有的宗教和政治意味渐渐让位于民间大众的娱乐趣味,各种活动事象在民间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
(一)仪式中的记忆:重申宗族伦序和地缘秩序,构建身份认同
扬·阿斯曼认为:“在节日最初的功能当中,最为原本的莫过于帮助参与者与宏观时间取得联系并调整自身的方向。”[6]无独有偶,在法国人类学者阿诺尔德·范热内普看来,岁时节庆作为人类对于年、月、季等时间变化做出的反应,与人生礼仪、首次礼等一样是一种过渡礼仪。[7]问卷调查中,关于“您觉得过元宵节有什么意义”的选项中,“参加传统民俗活动,加深年味和儿时记忆”“与家庭成员团聚,增进感情”“延续新春之喜,庆祝一年之始”分别以32.45%、28.99%、25.80%的比例排名前3位,“年味”“家庭团聚”“新春之喜”等词语,说明在人们的心理层面,过元宵节这一行为具有共聚家庭成员,完成岁终年首的过渡礼仪的意义。
从除夕到元宵这一跨年度的过渡期中,人们打破日常生活秩序,通过家庭团聚、迎神祭祖、祈育趋利、观灯娱乐等活动演绎自己的年令过渡礼仪,表达对祖先和神灵所施予的既往利益的谢忱,进而重申既有的宗族伦序和地缘秩序,进一步强化身份上的认同。
对宗族伦序的重申表现在祭祖尤其是祠祭仪式上。祠祭涉及整个宗族,讲究遵循一套完整的礼仪,越是显贵的家族越重视遵守上下尊卑伦序,以示仪式的庄严。祭祀仪式由族长率领,各房份依序备办各类供品,在祠堂中按各自的位置摆列,祭祀自开基祖以下的列祖列宗。也有的采取按房头轮流提供贡品的方式进行。礼毕后,往往会举行丰盛的团拜宴饮,族人仍“依序次宴会”,宗族伦序马虎不得。
而对地缘秩序的重申则表现在迎灯和迎神仪式中巡游路线的确定上。迎灯巡游本身也是祭祀的仪式过程。[8]正月十五傍晚,迎灯队伍在总祠举行出发仪式,由事先挑定的男性成员手持点燃的红灯笼,锣鼓乐队和本村保护神的木刻神像尾随于后,在预先选定的大小房支祠堂和村落边界外围巡游,最后回到总祠结束。巡游村落边界不仅意在通过灯显示“丁”的强盛,更以此进一步确认了自己村落的权力范围。而迎神的巡游(绕境)活动,往往由境内或村里有一定声望和经济实力的年长者负责,巡游区域一般限于本村或本境,以此划定境主神的管辖范围。与迎灯巡游一样,迎神巡游也是向其他铺境或村落显示自身势力不容侵犯的一种手段,因此往往成为铺境和乡族冲突对抗、甚至发生械斗的一个导火索。泉州历史上有名的东西佛之争,涉及面域广、时间长,其冲突即起因于祀奉各自境主的迎神、妆人、镇符和接香等活动。
(二)世俗机制作用:宗教和祭祀意味弱化,娱乐性上扬
在文化的记忆功能中,宗教占据核心位置,但在宗教色彩退位的现代社会,文献、艺术等世俗机制明显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为。在“以下泉州的元宵习俗你参加过哪些”的选项中,迎神/拜佛明显排在吃元宵丸、逛灯会、游灯之后,而祭祖更落后于看戏、吃润饼菜的排名。
在“以下哪些活动您觉得应该在元宵节期间多提倡”的问题中,灯会不出意外地位列首选,其后分别是文艺作品展览,南音、梨园、高甲等演出,美食、小商品展销,文娱踩街等,而祭祖的响应比例只有5.81%。
而在回答“元宵节期间您是怎么参加祭祖活动”的问题时,“在家里简单祭拜”和“都是家里老人操办,自己不参加”均超过“参加在宗祠里举行的祭祀仪式”,而“没听说过”的人甚至占23.66%。
可见,在吃元宵丸、逛灯会、观看文艺展演、品尝美食等文娱活动面前,无论是迎神拜佛还是祭祖都远占不到大的市场。在访谈过程中,几位访谈对象也都表达了“元宵节是‘人节’”,“灯会是‘人会’”的意思。可见,节日的仪典性渐次退位,娱乐性成为人们的首选。
其实,元宵节的娱乐性上扬并不是现代才有。从唐代允许在元宵这天开放宵禁,到宋代兴起市民游玩之风后,在城市夜游生活和朝廷粉饰太平的鼓励下,元宵灯会的娱乐气氛日渐上扬,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游乐活动。赏花灯、品小吃、看游人等活动热闹纷繁,张灯结彩、火树银花、一夜鱼龙舞年年上演,好诗擅赋的文人们在宋朝以后又加入了猜灯谜的竞玩趣味。在中国几大传统节日中,唯独元宵节同时兼具全民性和娱乐性,又因它弥补了宋朝开始式微的上巳节男女相会之俗,人们在七夕之外,又找到了另一个过“中国情人节”的机会。《陈三五娘》的男女主人公就是因元宵灯会而结缘,这种关于爱情的美好印象经由民间故事的口耳相传和历年元宵活动的不断搬演,已经在人们的记忆深处逐渐巩固,每年的梨园戏展演单上均少不了这出剧目。
(三)亲缘纽带维系作用:彰显家庭亲缘关系的意象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元宵节在人们的心目中仍是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家庭亲缘在人们对元宵节印象中是丢不掉的传统。而在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结构单一的趋势下,通过祭祀和巡游强化宗族伦序和地缘秩序的仪式感也逐渐被淡化,节日的意象更多地转化为家庭成员的亲情表达。
在“以下传统节日中,您认为哪三个比较重要”的选项中,元宵节以38.9%的比例紧追除夕、中秋节、清明节之后,排名第四。元宵节与除夕同属春节、时间间隔仅15天,38.9%的比例与清明节42.0%的比例相距也不是很远,可见,元宵节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
在回答“您一般是怎么过元宵节的”时,“跟家人一起在家里吃团圆饭”和“跟家人或朋友一起逛灯会、看踩街”分别占了32.50%和29.17%。家庭聚餐和观看灯会直观表达了元宵节的节日特色和喻意。元宵节不仅是个家庭团聚的日子,寓意团圆吉庆的元宵丸是这一天必不可少的食品和供品,一起团聚的不仅包括家庭成员,连先祖也被邀请来一起共飨美食;也是举行祠祭的重要节日,通过举行祠祭仪式,增强了宗族成员的情感联系,强化了共处一地的命运感;更是万象更新的时节,生殖、繁衍的时候也马上开始,送灯、钻灯脚、抢佛仔表现了添丁的愿景。
三、记忆的建构与文化传承
在大脑和神经学领域的研究中,个人记忆并非原封不动地长期保存在人的大脑中,人的回忆是受主观经历、客观记录的事实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再现和建构过去的过程。[9]个人记忆尚且如此,具有广泛的时间维度和社会属性的文化记忆更体现出重塑的特征。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参照过去并根据当下的需要来塑造自己的,塑造的过程就存在着主体的范式问题,也即文化记忆的过程受占主导地位的主体因素所左右。因此,描述历史、开展记忆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框架下进行,比如民族、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就是通过学校教育、社会仪式、公共媒介等渠道进行强化的。
(一)元宵节庆的集体行为沟通了人们的有关记忆
对记忆的沟通和文化的传承有赖于有组织的、公共性的集体交流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吸引群体成员在场并亲身参与某些重复性行为的元宵节庆,以其公共的时间、空间以及特有的节日意象,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记忆的场。置身于元宵节庆及其相关仪式氛围中的人们,超越了日常循环的生活秩序,找到了所谓的历史意识,完成了文化记忆的过程。
在回答“以下哪些因素更能影响您参加元宵节活动”时,“娱乐性”和“重温过节的记忆”均占23%以上;而“是否空闲”和“是否有伴”分别以17.65%和16.93%位列第三、第四,集体的沟通和交流成为必不可少的行为。
元宵节预示着春节接近尾声,新的一年即将开始。人们在此节日展示美食、才艺和情感,展现民间的生活形态,使个人情感在传递、沟通和相互影响中引起集体的共鸣,使信仰需求和文化情怀得到正常的抒发,从而具有一定的心理和行为渗透性,既加深了记忆的沟通,又发挥了文化传承、情感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社会效益。
从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狂欢理论看,节日与日常生活构成了批判的节律化关系,节日的狂欢式生活与日常生活相交替,构成了人在现实社会生活的重要节奏,这也是世界各国不厌其烦地设立各种名目之节日的原因之一。来自不同阈限的人们聚在一起赏灯、游艺、看戏,本身就是一种美好的人生体验。游艺展演也因为再现了丰富的民间生活场景而深受游人喜爱:火鼎公婆抬着火鼎三进三退,打诨笑谑,斗篮两侧贴着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的红联纸,体现了安平吉利的节日意味;骑驴子中的老夫牵着老太婆骑着的“驴”,假装因为彩礼的事带着女儿和“憨女婿”要到男方家评理,举手投足惟妙惟肖;装阁中“阁旦”经常扮演成“八仙”等民间传说人物,弄龙舞、台(刀旁)狮和宋江阵等综合了舞蹈和武艺,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而车鼓阵中的乐器都为闽南人所熟悉。热闹的表演、愉悦的场景气氛,冲散了日常生活的平淡感,使大众百姓获得了普天同乐的欢欣和情感的交流,从而实现个人记忆与沟通记忆的融合。
(二)文化记忆的主导主体发生了变迁
如果说在古代传统社会,文化记忆的主导主体是民间的神明系统和乡绅阶层,现在的主导主体则转移到官方的行政机构了。从迎神巡游到文娱踩街的过程,集中体现了文化记忆主导主体的变迁。确定“巡游边界”时,不免各方力量暗中较量与妥协,实际则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基层政权区位体系的组织运作过程。农村“迎灯”队伍巡游前,由公众协议祖厝祭祀点的顺序以及整个巡游路线;府城内,迎神队伍的巡游路线则由各铺份事先商定,有“借道”有“还道”,互相标明势力范围和亲善不和;现今的巡游则蜕化为文艺展演队伍的踩街,队伍成员由各街道组成,所走路线则是综合传统以及主办方、负责安保工作的公安部门的意见而定。
泉州市区元宵灯会的举办经费动辄以百万计,如果没有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支撑,没有哪个机构敢承担这项耗资巨大的工程。每年元宵前,泉州市政府会下文对时间安排、灯会地点、花灯数量等做出部署,并对有关协办单位提出具体工作要求,确保交通、消防、卫生等安全和医疗保障的到位。而市政府每年大费周章地张罗元宵灯会,除了出于遵循传统做法和传播传承“非遗”文化的考虑外,更意在借机宣传各类城市建设主题。比如2002~2009年连续七届的海丝文化节、2010年和2013年的闽南文化节、2014年的东亚文化之都开幕式等,集中在正月十五前后几天举办文艺汇演、南音大会唱、摄影展览、泉商大会、学术论坛、闽南语歌赛、台湾特色庙会等各类特色活动,均取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关注度,参与的群众有逐年增多之势。2015年的元宵灯会由于受上海跨年庆新踩踏事件的影响,市政府决定降低举办规格和规模,主办单位由地市级转为区级行政单位,举办地点分散在城区三个地方,举办经费也相对缩减。一位常年在文化部门参与组织元宵灯会的工作人员道:“前几年,实际上是政府在包办。为什么说是政府在包办呢?你看,选址圈定在固定的地方,所以选址是政府包办的。花灯制作也是政府包办的。刚才说过,任务发下去,需要每个县(市、区)30盏你就要弄30盏,每个企事业单位、市直单位,(比如)机关一盏、企业两盏,这都是用指令性的。连挂灯都是艺术馆组织的,请干部职工去挂,撤下来也是。(所以)变成高度组织性。其实参观也有点组织的意味,比如有事先公布路线,(实施)交通管制,发信息组织车子停在哪里,还有公交公司免费运送人员来观灯,体现了计划经济的特色。其实,现在我们不把它(指元宵灯会)列入民俗的范畴,我们还是列入政府组织的大型文化活动这个范畴,如果用这个来理解就豁然开朗了。”将灯会定义为“政府组织的大型文化活动”,充分说明了行政机构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而泉澎两地天后宫的“乞龟祈福”活动,脱离不了闽台深厚渊源和两岸融洽关系的考略,明显是在政府的允许下愈演愈烈,也充分体现了行政机构在重塑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主导意志;而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研究会等社团对民俗大舞台的支持、以“歌吹漫步”的名义坚守文娱踩街,则体现了社会组织在这一主导格局中日渐显出张力。
(三)文化认同脱离不了地方性场景
文化记忆的内容是某一群特定文化主体共同拥有的过去,“对于集体文化认同来说,共享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一样,对其生存非常重要。”[10]泉州元宵节庆活动中的祭祖祀神、有关灯的活动、“歌吹漫步”等较为完整地保存和延续了传统的内涵和形式,主办机构又在活动中着意充实和扩展本土文化特色。对本土文化元素的运用,民众显然十分受用,并赖以自觉地树立起一种自我形象或者说是独特意识,从而形成群体和文化的认同。
泉州的元宵灯展区经历了几次变迁,从开元寺,到文化宫,到府文庙、后城街、威远楼,到新门街。在“如果在以下几个地方设元宵灯会,哪几个展区您比较喜欢去”的选项中,文化宫、后城街占24.94%,开元寺、承天寺占22.80%,府文庙17.34%,新门街占12.83%,而侨乡体育馆仅占7.36%,威远楼6.41%,还有8.314%选择了其他。
而在回答“您比较喜欢以上所选展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时,“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和“花灯比较好看”的比例分别以33.87%和22.27%成为最主要的两大原因,“交通便利”占17.40%、“人多比较热闹”占16.01%。
综合以上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文化宫、后城、开元寺、承天寺均举办过元宵灯会,但考虑到人流的安全,后来挪到府文庙举行,并且出于同样的考虑,从2012年起挪到相对开放的新门街举办。在主办单位看来,2014年新门街的元宵灯会从电力隐患、人群分流、场地容量、活动内容等方面来说,是历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内涵最丰、影响最大、也是最成功的一次,不出意外的话以后也将固定在这里举办。但民众的看法显然并不一致,他们更喜欢到古色古香的闽南传统建筑空间里观赏花灯,他们认为那里的传统文化氛围更加浓厚,观赏花灯更加应景。“重构过去的活动得以发生,道德感情必须具有柔韧性,易于变化。”[11]换句话说,越是传统深厚的社会,文化的特质越稳定,越容易对重构产生抵制。因此,建构记忆和文化只能在在地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认同离不开地方性场景。
四、结 语
综上,泉州元宵节庆活动内容丰富、衍播久远,并且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具体表现在核心内容由宗教和祭祀让位于娱乐,主导主体由神明系统和乡绅阶层让位于行政机构等方面。公共的时间性、空间性和特有的节日传统使其构成了一种公共文化空间,完成了个人记忆向集体记忆转换的过程,并进而发挥了构建身份认同、传承文化传统、加固乃至重构文化记忆的作用。在这其中,传统文化元素、地方性场景是传统节庆活动发挥文化记忆功能价值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
[1]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G]//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57-74.
[2] 陈垂成.泉州习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3] 赵婕.中国元宵灯俗的审美人类学泛谈[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
[4] 周婷婷.泉州地区古村镇的历史文化考察[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9.
[5] 孟祥路.节庆传统与民间戏曲的互动影响探析[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4).
[6][9] 陈新,彭刚.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7] [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过渡礼仪[M].张举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8] 钟建华.“迎灯(丁)”:一个闽南宗族村落元宵节的田野解读[G]//萧庆伟,邓文金.闽台文化的多元诠释(一).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240-248.
[10] [英]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1] [美]巴里·施瓦茨,福冈和也,泷川石井幸子.集体记忆:文化的重要性[G]//马克·D·雅各布斯,南希·韦斯·汉拉恩.文化社会学指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17-233.
[责任编辑:林丽芳]
Consolid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Cultural Memory:Taking Quanzhou Lantern Festival as an Example
LI Shuang-you
(Institute of City Situation, Quanzhou Party School, Quanzhou 362000, Fujian, China)
Lantern Festival has lasted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rich contents, such as Quanzhou’s ceremonies of ancestor worship, praying, blessing, amusements and so on. These traditional festivals retain the identifying function by restating clan and geo orders, and also play a secular role in entertainment and a role of genetic link in family consoli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ime dimension and organized situations, the collective actions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of people’s memory,further more realize the traditional culture’s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memory, the dominant subject of the memory has changed obviousl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local scene.
cultural memory;Lantern Festival;Quanzhou
2015-07-07
2014年泉州市社科规划项目(2014E14)
李双幼(1981-),女,福建泉州人,中共泉州市委党校市情研究所讲师。
G122
A
1674-3199(2015)05-0051-07
——泉州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