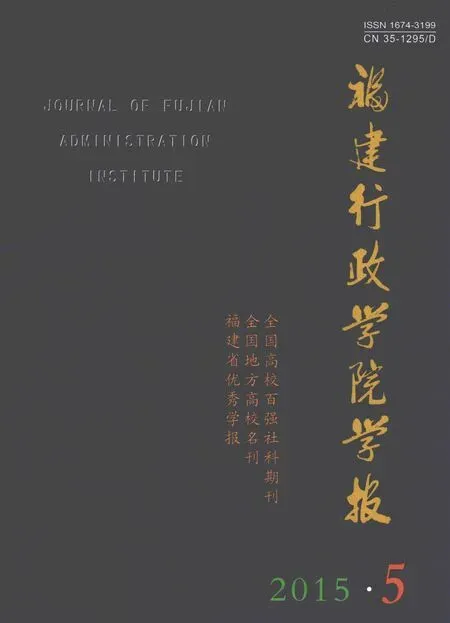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现状与发展趋势——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王少泉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福建 福州350001)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爆出的县级权力家族日益增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检索到的涉及家族政治的外文文献不多,研究中国家族政治的文献则更少。伯纳德·弗里德曼(Bernard Friedman)针对家族政治对纽约议会选举的干扰进行了研究[1];琳达·列文(Linda Lewin)对巴西东北部家族政治的影响展开研究[2];瑞莎·W·沃妮克(Retha M.Warnicke)对亨利八世时期的安妮·波琳家族[3]、芭芭拉·H·罗森文(Barbara H.Rosenwein)对意大利国王贝伦加尔一世时期(888~924年)的家族政治[4]、穆雷·斯科特·坦纳(Murray Scot Tanner)和迈克尔·J·菲德尔(Michael J.Feder)对后毛泽东时代的家族政治、精英招募和政治继承展开研究等。[5]上述外文文献所研究的对象大多为上层政治权力“家族化”,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县级权力家族化现象)存在较大差异,无法直接借鉴,但这些文献中的一些观点值得本研究借鉴,如商品交换与家族政治存在相关性。[6]
国内学术界对权力家族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已有的成果不多。宝成关和胡锐军从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体制性障碍角度分析了基层权力家族出现的成因[7];杨彩利从历史视角、文化视角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分析了基层权力家族化的成因,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基层权力家族化的避免机制[8];陈天祥分析了基层权力“家族化”的危害、成因及治理之道[9];张喜红不仅分析了基层权力家族化的成因及对策,还分析了其发展趋势。[10]这些研究由于缺少理论视角,对我国权力家族的现状分析不够深入,也难以对未来发展态势做出有说服力的描述。
县级权力家族的出现与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①存在于社会组织之中的信任、互惠规范和沟通网络三种特征能够强化其成员之间的合作,并在这一基础之上提升社会效率,由社会组织的这三种特征整合而成的即社会资本。参见:[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密切相关,而且,与公众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有所不同:县级权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多种领域发挥作用(某一批公众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通常只在某一领域发挥作用)、归属于小群体(公众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归属于大群体)、发挥的是负面作用(公众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发挥的是正面作用)。鉴于此,在展开研究之前,有必要对社会资本加以分类:第一,根据社会资本所属领域,可以分为政治社会资本、经济社会资本和文化社会资本;第二,根据社会资本所属群体的大小,可以分为小群体社会资本与公众社会资本;第三,根据社会资本属性,可以分为正社会资本和负社会资本。县级权力家族借助其内部及之间存在的社会资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利用掌控的资源谋取私利,给我国各领域造成危害。从宏观视角来看,县级权力家族的出现是我国党政系统中极少数精英异化的表现,这种异化影响我国党政系统的运作效能,而且,县级权力家族的出现及运作会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这将削弱存在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公共社会资本,当这种公共社会资本削减到一定程度之时,国家会面临存亡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对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向展开研究,为消除这一现象提供理论支持。
二、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现状
(一)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表现
1.东中西部省份均存在县级权力家族。已发现的县级权力家族(见表1),属于东部省份的如广东省揭阳市的江中咏家族、河北省馆陶县的闫宁家族;属于中部省份的如湖南省湘潭市的王茜家族和徐韬家族、安徽省宿州市的张治淮家族、山西省运城市的孙太平家族;属于西部省份的如云南省A 市的资某家族。从归类情况来看,我国东中西部省份都存在县级权力家族,可见:县级权力家族是否存在不受限于地域,东中西部省份某些地方都受到了县级权力家族的影响。
2.县级权力家族的出现与经济发展水平无明显相关性。县级权力家族并非只出现在欠发达地区,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方都有存在。根据2012年县域人均GDP可以将这些县划分为三类:经济发达的县域,如湘潭市的两个县区,人均GDP约为4万元;经济水平居中的县域,如馆陶、运城、揭阳等地,人均GDP约为2万元;经济欠发达的县域,如宿州的人均GDP只有1万元左右。这表明县级权力家族化现象的出现与出现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没有直接相关性。这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的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县级权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换言之,某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是否出现县级权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没有直接关联。必须注意到同等规模的两个县级权力家族,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县级权力家族能够凭借所掌控的社会资本获取大量私利,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级权力家族凭借所掌控的社会资本获取的私利会较小,但是,前者对所在地造成的危害有可能小于后者,其原因主要是:同等数量的小群体社会资本(负社会资本)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所造成的危害大于在经济发达地区所造成的危害。
3.爆出县级权力家族的地方不断增多。近年,我国爆出县级权力家族的地方逐渐增多。其成因:一是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政府的内外部监督日益增强,政府组成人员的背景日益透明化,被爆出的县级权力家族也就随之增多;二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同一领导职位上能够运用的资源日益增多,县级权力家族借助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能够获取的利益也日益增多,这意味着县级权力家族所拥有的负社会资本能够造成的危害随之变大,受到关注并被爆出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三是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使公众更容易获知政府部门的用人信息,当县级权力家族借助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谋取新的公务员岗位或采取其它违法举措之时,很容易被公众查知,继而爆出整个县级权力家族。
(二)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县级权力家族具有扩张性、流动性、浮沉性、历史性,这些性质存在于县级权力家族的萌芽、发展、稳定、衰落和消亡过程之中。
1.扩张性。从县级权力家族本身来看,在被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遏止或县级权力家族本身失去扩张潜力之前,县级权力家族的成员数量会不断扩大,所掌控资源的涉及面会不断扩张,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会不断增加,对当地公务员群体声望的破坏度也会不断提升。
通常情况下,县级权力家族从萌芽到发展再到稳定的过程即这些家族扩张的过程,也是这些家族增加所拥有社会资本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县级权力家族成员的数量一般都有所增加,且所掌控的资源总量、资源范围及社会资本也逐渐增加。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自身的升迁及扩大能够获取的私利,权力家族的核心成员会寻求增加家族中担任公务员(及准公务员)的成员的数量,而且还会借助已经掌控的公共权力扩大掌控的资源总量、资源范围和社会资本。资源总量、资源范围、社会资本的扩大主要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担任公务员(及准公务员)的家族成员职务的升迁或实权的扩大;二是将已经是公务员的家族成员转任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职务,或借助掌控的公共权力让家族中的某位“平民”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担任某职务,从而在扩大掌控资源范围的同时增加掌控资源及社会资本的总量。 县级权力家族进入到衰落和消亡阶段之时,其扩张性随之消失,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党政系统中的影响力也随之逐渐下降直至消亡。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县级权力家族的扩张性在某一时期消失之后,会在另一时期再次出现,即某一时间点之上,家族中担任正处级或副处级领导的成员卸任且不再升迁,这一权力家族的扩张性随之消失,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党政系统中的影响力也随之逐渐下降,但这一时间点之后,这一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开始担任正处级或副处级领导,实现了这一权力家族的复兴,其扩张性再次出现,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党政系统中的影响力也随之逐渐上升。
2.流动性。从横向来看,某地的县级权力家族会因领导者的变换而出现更替,这种更替是县级权力家族具有流动性的表现。县级权力家族的“流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因同一个县权力家族的“浮沉”引起的县级权力家族流动。某个县级权力家族因为不再有担任正处级或副处级领导职务的成员而“浮沉”为其它级别的权力家族,另一权力家族开始掌控或扩大原先已经掌控的公共权力,成为新的或更强的县级权力家族,党政系统中存在的负社会资本的掌控者也随之变换。二是因不同县之间权力家族的迁移引起的县级权力家族流动。即这样一种情况:某个县级权力家族中担任正处级或副处级领导的成员得到升迁或职务下降,引至该权力家族成为其它级别的权力家族,继任其职务的是原先就职于其它县的公务员,而且,继任者已经在其它县构建起权力家族并逐渐将家族成员逐渐“迁移”到新任职的地方,并将县级权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带到新的任职地。这种情况使权力家族及其社会资本实现了不同县之间的流动。当然,这种流动并非好事——这种流动会将县级权力家族的危害带至新的任职地而且有可能延滞铲除县级权力家族的进程。
3.浮沉性。从纵向来看,县级权力家族与上下层级的权力家族化现象密切相关:县级权力家族一般是由下一级(乡镇级)的权力家族发展而来,而且有可能发展为更高一级的权力家族或重新“沦落”为乡镇级权力家族。当县级权力家族上升为更高层级的权力家族之时,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随之增加,对我国公务员群体所造成的危害也随之增加;当县级权力家族下降为乡镇级权力家族之时,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会有所减少,更为重要的是,其核心成员不再归属于公务员群体,因此,对我国公务员群体的影响力会急剧下降。从宏观视角来看,县级权力家族的萌芽、发展、稳定三个阶段属于“浮”这一大阶段,衰落和消亡两个阶段则属于“沉”这个大阶段,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县级权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行政层级中“浮沉”的表现。
尽管都属于“浮”这一大阶段,但必须注意其变化:在萌芽阶段,权力家族中没有担任正处级或副处级领导职务的成员,因此,权力家族并非县级权力家族,但在这一阶段,权力家族已经将家族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运用于党政系统之中——借助这种社会资本谋取私利。当县级权力家族的某位成员开始担任正处级以上的领导职务且没有任何一名成员担任正处级或副处级领导职务之时,权力家族继续“上浮”——由县级权力家族升级为厅级(甚至部级)权力家族,权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开始在党政系统中的更高层级发挥影响力,其对我国公务员群体声望的损害度也会加深。当县级权力家族的某位成员开始担任正处级以上的领导职务且至少有另一名成员担任正处级或副处级领导职务之时,这一权力家族具有双重“身份”——厅级(甚至部级)权力家族和县级权力家族,这种权力家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县级权力家族,不在本研究的分析范围之内。
县级权力家族的“沉”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自然“沉”的县级权力家族。如果县级权力家族在萌芽、发展、稳定三个阶段中所造成的危害并不严重,党和政府没有采取严厉举措直接将其铲除之时,这些县级权力家族会自然消亡,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及所造成的危害也会逐渐消亡。自然“沉”的过程包括衰落和消亡两个阶段,衰落过程通常表现为县级权力家族中不再有成员担任正科级以上领导职务;消亡过程通常表现为权力家族中公务员的数量日益减少直至完全没有。在这两个阶段中,权力家族成员所担任的领导职务逐渐变小,家族成员对核心成员的信任度随之下降,家族内部的互惠规范的约束力逐渐变小、沟通网络的效能也逐渐降低,权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就逐渐减少。二是非自然“沉”的县级权力家族。在某些情况下,县级权力家族的发展历程不存在“衰落”这个阶段,而是由“稳定”阶段直接进入“消亡”阶段,这种情况一般归因于我国党和政府对县级权力家族的铲除。当县级权力家族的核心成员因违法、违纪而被查处之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会得到提升,进而增加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公共社会资本。同时,权力家族普通成员对核心成员的信任会迅速消失,存在于家族内部的互惠规范会因无人监控、实施而难以发挥效用,沟通网络则会因为有可能危害普通成员的利益(监察部门会根据沟通网络对权力家族的成员进行核查)而迅速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县级权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会迅速减少直至在党政系统中消失。
4.历史性。从历史角度来看,县级权力家族不是天然存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它随着历史发展而出现,也将随着历史发展而消亡。党政系统中也并非天然存在权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在权力家族构建之时由这些家族的成员带入党政系统之中,并随着权力家族层级的“浮沉”而在不同层级发挥其影响力。县级权力家族都会经历从兴起到衰亡的过程,其萌芽于家族中第一位担任公务员的成员就职之时,发展于担任公务员的家族成员逐渐升迁和逐渐增多过程中,稳定于家族中某位成员开始担任正处级或副处级领导之时,衰落于家族中担任正处级或副处级领导的成员卸任且不再升迁之时,消亡于担任公务员的家族成员逐渐减少且公务员的层级不断下降之时(自然“沉”),或消亡于被相关部门铲除之时(非自然“沉”)。值得注意的是:县级权力家族的兴起并非绝对意味着其在党政系统中“创造”了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这种情况不常见)。一般情况下,党政系统之中出现归属于权力家族的社会资本是因为权力家族成员将原先存在于家族之中的社会资本“移入”党政系统之中。与此相似,县级权力家族的消亡,并非意味着这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完全消失,而仅仅意味着这种社会资本从党政系统中消失,但依然存在于并非权力家族的家族之中。
三、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发展趋势
对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究,有助于为消除县级权力家族献言献策,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发展趋势主要如下:
(一)由单一型向全面型发展
县级权力家族在掌控一定的公共权力之后,为了获取更多的私利,往往将所掌控的公共权力运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等等(实质上是将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扩展至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从而使单一型的权力家族发展为全面型的权力家族。县级权力家族从单一型发展为全面型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将家族中的某位或某几位成员“提携”成为经济领域或社会领域中的领导者。政治权力通常对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有重要影响,因此,掌控一定公共权力的县级权力家族有条件将家族中的某位或某几位成员“安插”进经济领域或社会领域,并协助这些成员成为这些领域的领导者,从而使这一县级权力家族从单一型发展为全面型。相对于其它两种方式,这种方式见效较慢,因此,被县级权力家族采用的概率不高。二是将家族中的某位或某几位成员转入经济领域或社会领域担任领导者。政治领域的领导者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通过“转任”的方式进入经济领域或社会领域并继续担任领导者,县级权力家族通过这一方式能够使其从单一型发展为全面型,进而谋取更多私利。与前一种方式相比,这种方式见效较快,能够直接使县级权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中的较高层级发挥影响力,因此常常被县级权力家族采用。三是与某个全面型的权力家族(不一定是县级权力家族)联姻。权力家族常常为了有效地维持或扩大自身实力而与其它权力家族联姻,当某个单一型的县级权力家族与某个甚至某几个全面型的权力家族联姻时,这种联姻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县级权力家族在政治领域实力的增强,还会使这一县级权力家族从单一型发展为全面型,从而有效地增强双方的实力,并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基于某些互惠规范、通过相互之间网络谋取更多私利。《中县干部》一文中,张泰康家族通过与张保彬家族的联姻实现了从单一型发展为全面型——张保彬是张泰康的大女婿,张保彬家族是全面型权力家族。[19]这种方式与第二种方式一样见效快,但是,县级权力家族采用这种方式从单一型发展为全面型,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实力的增强和私利的增加,还有风险的提高:采用联姻方式容易使权力家族过大、借助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造成的危害过大,进而引起党和政府的注意,势必增加县级权力家族的生存风险。基于此,县级权力家族在采用这种方式扩展其实力之前,往往会慎重考虑,一旦预估到有较高风险,县级权力家族的成员就会迅速放弃这一方式转而采用其它方式扩展实力,因此,这种方式被采用的概率低于第二种方式。
无论县级权力家族采取哪一种方式从单一型发展为全面型,都会将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由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等领域之中,这意味着县级权力家族不再仅限于压制政治领域的精英,而开始对经济、社会等领域之中的精英也形成压制,这种压制会引致真正的精英对权力家族甚至对政府产生不满,从而削减了这些精英对政府的信任度,他们与政府之间的互惠规范、沟通网络的效能也会随之下降,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精英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公共社会资本被削减了。另一方面,县级权力家族由单一型发展为全面型之后,其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中谋取私利,这一情况会使归属于县级权力家族的社会资本的负面影响迅速扩大,随之出现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公共社会资本被进一步削减。
(二)两代型所占比例将增加
权力家族的萌芽,一般源于家族中的某位成员开始担任公务员,这位成员担任公务员之后会在家族内部形成“示范效应”,提升家族中其他成员通过考试等方式成为公务员的积极性。当家族中不仅仅有一位成员担任公务员之时,权力家族开始形成并将存在于家族中的社会资本“移入”党政系统之中,而且,这一阶段的权力家族一般是单代型权力家族——在权力家族形成之初,通常情况下,第一代公务员年龄都不会非常大,凭借掌控的公共权力“提携”家族中晚辈的概率不是很高,通常是协助家族中的同代成员进入党政系统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将家族中的社会资本“移入”党政系统之中。
当权力家族中担任公务员的人数逐渐增加或某位成员开始担任领导职务(掌控一定的公共权力)之时,为了扩大权力家族在党政系统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以谋取更多私利,权力家族的成员开始采用不正当手段“提携”家族中的成员进入党政系统,这一过程中,权力家族的成员将家族中存在的社会资本“移入”党政系统之中,同时,他们还通过强化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完善互惠规范及沟通网络等方式增加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这些被“提携”者在权力家族中的辈分通常晚于权力家族中的第一代公务员,因此,当权力家族发展到这一阶段时,从单代型发展为两代型的可能性很大。
从已经爆出的县级权力家族的类别来看,单代型的县级权力家族所占比例很小,多代型县级权力家族的数量稍多于单代型,比例最大的是两代型。这是我国当前县级权力家族的现状之一,也是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发展趋势之一。为了谋取更多私利、保证长期获益,单代型县级权力家族中的成员通常会寻求将下一代的家族成员“提携”进入党政系统,从而使县级权力家族的类型由单代型发展为两代型,在党政系统之中实现权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两代传承”并在公务员群体之中实现“世袭”。值得注意的是两代型县级权力家族发展为多代型的难度较大、风险较高。原因在于:一是从代际的年龄差距来看,祖孙三代同时担任公务员的难度较大;二是两代型县级权力家族常常因带来的危害较大而引起各界关注甚至引致党和政府的查处,在尚未发展成为三代型之前就消亡。三是县级权力家族中较有“远见”的成员会考虑到连续多代担任公务员所带来的风险,因而在家族成为两代型县级权力家族之后,主张家族成员尽量进入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工作,将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和社会等领域之中,从而有效地降低家族覆没的风险,这种举措也阻滞了县级权力家族由两代型发展为三代型。
(三)中型权力家族所占比例将增加
从规模来看,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发展趋势呈现梭形(橄榄球形),这一趋势与上一个趋势有相关性,但不完全相同:在某些情况下,单代型县级权力家族发展为两代型之后,并不必然导致县级权力家族规模的扩大——由单代型发展为两代型的过程中,有可能伴随着家族中担任公务员的总成员数量减少。中型县级权力家族在全部县级权力家族中所占比例增加的原因在于:
一是小型县级权力家族为了维持或扩大所获私利,通常会想方设法寻求担任公务员的家族各成员职务的升迁,但是,县级权力家族左右其成员职务升迁的难度较大,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家族成员的职务甚至会下降,这一情况的存在迫使县级权力家族的成员采用另一种难度较小的方式实现家族利益的维持或扩大,即扩大担任公务员的家族成员的数量。这种方式的采用,使小型县级权力家族在全部县级权力家族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中型县级权力家族所占的比例逐渐上升,权力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也随之被大量“移入”党政系统之中并得到进一步增加,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公共社会资本也被进一步削减。实际上,从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情况(尤其是《中县干部》一文所述县级权力家族的情况)可以看出,县级权力家族中,中型县级权力家族所占的比例最大。这是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现状之一,也是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发展趋向之一。
二是近年我国逐步强化了监察制度,这一举措有效地降低了我国大型县级权力家族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大型县级权力家族中担任公务员的人数较多,所掌控的政治、经济或社会资源较多,借助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造成的危害较大,极易引起各界的关注并随之引致党和政府的查处。一旦被查处,大型县级权力家族将步入衰落甚至消亡阶段,其在全部县级权力家族中所占比例随之下降,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县级权力家族对我国公务员群体声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各类公共社会资本会随之得到增加。
三是很多中型县级权力家族在发展成为大型县级权力家族之前已经被查处并随之消亡。中型县级权力家族中较有“远见”的成员熟知我国古语“日中则昃,月满则亏”,为了维持或增加家族所获私利,必然想方设法降低自己所处家族的生存风险,基于这一考虑,这些成员会注意在监察制度完善之后展开风险评估,为了规避风险而开始考虑适度控制家族规模及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因而不再吸纳更多家族成员进入党政系统,而采取将家族成员安插入经济领域或社会领域(实质上是将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移入”这些领域之中)等方法来维持或扩大家族所获私利,甚至满足于现状,连这一举措都不采取(如云南省A 市A 县资某家族的情况)。这些举措的实施有效地降低了大型县级权力家族的出现率,同时也就降低了县级权力家族对我国公务员群体声望的损害度,提高了增加各类公共社会资本的可能性。即使中型县级权力家族的总数量不变,其在全部县级权力家族中所占的比例也会因为小型和大型县级权力家族的减少而增加。
(四)实际存在数量将减少
近年,被查处的县级权力家族不断增多,但这一情况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总数量在大幅度增多——我国县级权力家族的主要增长期是转型时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最初十年),这一时期,我国逐渐构建了市场经济体制,政治制度也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完善,但是,政府在某些方面依然对市场有过多干预,极少数公务员得以利用这一点在党政系统之中构建权力家族并谋取私利,同时将家族中的社会资本“移入”党政系统之中并进一步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县级权力家族逐渐出现。最近几年,随着我国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各界已经注意到少数县级政权中的部分公共权力被某些权力家族掌控、党政系统之中存在归属于权力家族的社会资本等现象,并采取一些措施开始遏止,使得县级权力家族的实际总数量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的三种趋势,实质上主要是现有的县级权力家族在演变,而非全国各地在不断大量出现县级权力家族并持续演变。
政治制度的完善能够有效减少县级权力家族的实际数量,清除党政系统之中归属于权力家族的社会资本,提高我国公务员群体的声望。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我国的公务员录用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日益严谨,掌控一定公共权力的公务员利用公务员录用制度的不足之处将家族成员“吸纳”进党政系统的可能性不断变小,权力家族的出现率随之降低。二是公务员监察机制的完善(如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20]),增加了发现并铲除县级权力家族的可能性。除政治制度的完善之外,社会组织和公众问责能力的增强及随之不断完备的问责文化的存在等等,也使我国实际存在的县级权力家族不断减少。这些情况的存在都有助于减少党政系统之中归属于权力家族的社会资本,且有助于塑造我国公务员群体的形象,为公务员群体与公众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公共社会资本的增加创造条件。
四、结 语
作为权力家族中的组成部分之一,县级权力家族通常由乡镇级权力家族发展而来,且在具备某些条件之时会发展成为更高级的权力家族。县级权力家族的出现意味着其核心成员进入了地方精英阶层,并由此造成或加剧地方精英阶层的分化,降低了我国某些地方精英阶层的素质,阻滞了我国构建高素质的精英阶层的进程。值得欣慰的是,县级权力家族只极少地存在于我国极少数地方,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的持续推进,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县级权力家族会不断减少,这一情况的出现能够为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健康、快速发展创造条件。
[1]Bernard Friedman.The New York Assembly Elections of 1768and 1769:The Disruption of Family Politics[J].New York History,1965(1).
[2]Linda Lewin.Som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Kinship Organization for Family-Based Politics in the Brazilian Northeast[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79(2).
[3]Retha M.Warnicke.The Rise and Fall of Anne Boleyn:Family Politics at the Court of Henry VIII[J].Lehmberg Renaissance Quarterly,1990(4).
[4]Barbara H.Rosenwein.The Family Politics of Berengar I,King of Italy(888~924)[J].Speculum,1996(2).
[5]Murray Scot Tanner,Michael J.Feder.Family Politics,Elite Recruitment and Succession in Post-Mao China[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3(30).
[6]Margot C.Finn.Colonial Gifts:Family Politics and the Exchange of Goods in British India(1780~1820)[J].Modern Asian Studies,2006(1).
[7]宝成关,胡锐军.基层权力“家族化”危机及其现实根源[J].人民论坛,2013(7).
[8]杨彩利.探析基层权力家族化现象[J].经济研究导刊,2013(25).
[9]陈天祥.干部管理制度漏洞检视——基层权力“家族化”的危害、成因和治理[J].人民论坛,2013(7).
[10]张喜红.基层权力“家族化”的治理之道[J].学习与探索,2013(12).
[11][19]冯军旗.中县干部[D].北京:北京大学,2010.
[12]刘立民.29岁县长的飞升之路[J].政府法制,2011(11).
[13]宋坚刚,赵宬斐.由“湘潭神女”事件谈干部选拔问题[J].领导科学,2012(6).
[14]张灵霞.“腐败父子兵”的警示[J].先锋队,2012(10).
[15]易国祥.徐韬小恙仍是“举之过”[N].长江日报,2013-05-09(5).
[16]宁新春.“房媳”是基层政权家族化倾向的产物[N].东莞日报,2013-06-25(2).
[17]达海军,揭组宣.撤销江中咏副区长任命[N].南方日报,2013-05-11(1).
[18]王少泉.服从与抗命:公务员两难困境分析[D].上海:复旦大学,2011.
[20]王东.让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具体化[N].学习时报,2014-12-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