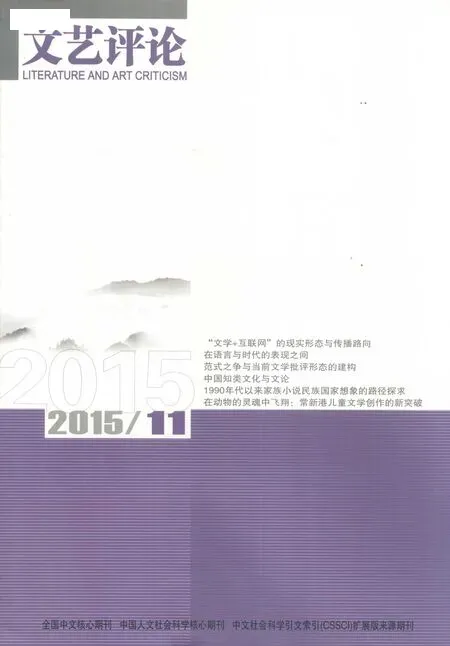中国知类文化与文论
○王 澍
一、知物与以类知物
除了重德,中国古人也很重“知”。《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其实,动物虽亦有知,但远不如人的知;因为动物的知,仅限于感知;而人的知,既有感知,更有理知和理性。按现代人的说法,人有两种理性:即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荀子所讲的“义”,主要指道德理性。工具理性是知,道德理性也属知。所以,人贵有知。知是人和动物的区别。
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中国古人重知的特点是顾大体、崇尚全知全识。所谓“辨雕万物,智周宇宙”,还有宋明儒所说的“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皆是此意。而且,全知还不够,还要“高”知。知的最高境界是知“道”。但是,要知“道”,须先知物,尽可能多地知物。欲知物,须先格物,即“格物致知”。凡物皆参透了,才有可能知“道”。万物皆通,又能“知道”,这样的人就是完人,就是圣人。所以古代的优秀君主常被誉为“有道之君”;而孔子不仅是大仁大义的“德圣”,同时也被标举为全知全能的“知圣”。
但是,一般人的经历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而外物是无限的、也是不断发展演化的,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那么,人如何才能全知全识呢?这就必须靠“知类”。知类,实际上就是“以类知物”。知类是一个提纲挈领、以少总多的好方法。同时,知类也是知“道”的前提。无类的知识是零碎的、杂堆的,知的再多也免不了“不伦不类”,很难上升为规律,更难以触及“总规律”(即道)。“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荀子·解蔽》)。物的个体无法一一尽知,但物类基本上是可以穷尽的。此之谓“以道观尽”(《荀子·王制》)。万物万类皆通达了,就是“知道”;知道是人的最高境界。所以,古人很重视“知类”。
“类”是中国古代理性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本质”、“规律”等意义。具有相同相近本质、规律的事物为同类,反之为异类。“类”字最早见于《尚书》;但真正在“本质”意义上使用类这一概念的,是春秋末年的墨子。墨子自觉地把“类”概念作为论辩的武器,时时斥责论敌“不知类”、“不察类”的逻辑错误。后期墨家进一步完善了“类”思想。他们明确了“类”和“不类”的意义,提出类同是“有以同”,不类是“不有同”;他们运用具体事例说明分类不是随便根据事物的某一属性,而是根据事物的本质属性;他们还提出,类是确立和进行名、辞、说(即概念、判断、推理)的依据和前提。除了墨子和墨家,先秦时期的其他诸子如鬼谷子、荀子、吕不韦、孟子等也较重视类和知类,从而共同完善了知类思想。如《鬼谷子》讲“知类在穷”,《礼记·学记》云“知类通达”,《荀子·王制》提出“以类度类”、“类不悖,虽久同理”,《吕氏春秋》提出“类固不必可推知”,等等。
可见,中国古代的“知类”文化,不只是讨论分类问题,实质上是强调逻辑思维,它涉及概念确立、外延辨析、规律与个案、演绎与归纳以及推理、判断、预测等等抽象理论问题。诸如以少总多、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纲举目张、遗形取神、触类旁通、以此类推、不伦不类、有教无类等等说法,都是知类文化的显现。对整体上偏于感性、重视情感的中华民族来说,这些理性之光自然显得弥足珍贵。
当然,与西方的科学话语系统相比,中国的知性文化言说总也让人有一种“隔”的感觉。这是因为其中既有理性成分(是非),也有非理性成分(对错)。但大体上可以说,或至少在知性文化领域,理性是大于感性的,逻辑是压倒文艺的。当然,这个话题,学界尚有争议。本文不以此为目标论题,所以不作深究,只以折中的态度处之。
另外,中国古人的类型论还常常与等级说交叠,在儒家话语体系里尤然。如《论语》中的“子曰”动辄就是君子如何好、小人如何差。这是在“类”人,也是在褒贬人。儒家本来就喜言等级贵贱,所以他们讲的类型大多兼有等级之意。这是我们应注意的。
还有一点——这点经常被一般论者所忽略——即中国古代知类文化与神秘术数说或数字迷信也时时有染。分类必用序数字,用序数字本应视实际需要而定,但古人有时考虑得更多。如古人发现,阴物多偶数,如六出雪花等;再加上其他一些不明就里的原因,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奇数,禁忌偶数,尤其是“4”、“6”等。这样,古人在分类时就有可能有意无意地歧视或回避偶数。所谓“事不过三”、“不着四六”、“六道轮回”、“胡说八道”等等说法,即有此意。中国传统节日也多选单数。如春节、上巳、端午、乞巧、中秋、重阳等。中国古代数人、数物合称的叫法很多,如三曹、竹林七贤、九僧,以及三才、五行、十三经、三请孔明等,一般奇数远多于偶数,而且凡是偶数,一般带有一定的否定倾向或悲剧意味。如二十四友、大历十才子、戊戌六君子,以及四书、八股文、六出祁山等。如此,一方面为知类文化增添了趣味性,另一方面也为其附丽一层神秘之光,增强了非理性成分。
二、知人与作家类型论
古人认为,人生活于天地之间,天、地、人构成“三才”。天地万物构成“物”的层面,人本身构成“我”的层面。人要知物,也要知人——其实人亦物也:人是天地之子,是特殊的物。《老子》第33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如何知人?仍然是以类知。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规定人的社会类属性。《西游记》中,唐僧经常训斥孙猴子的话是:人有几等人,物有几等物,如何不分个贵贱。此语实际体现了儒家以等级类人的思想。还有,在《论语》里,从知的角度,孔子实际上把人分为三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下愚。这个分类具有强烈的道德偏见,不完全是科学的,但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无论如何,其说影响很大。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也都很注重研究人。诸子百家都各有一套系统的理想人格模式。①有学者甚至认为国学主要就是人学,或以人学为核心。②其最大特色就是高度推崇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实际就是教人做什么样的人的。
魏晋时,曹丕、陈群等在孔子“三等人”论的基础上,增衍而提出了“九品论人”说。汉唐人化繁为简,揭出“性三品”③说;宋明儒则提倡“两重人性说”④。
文化是水,无缝不入;思想如风,无孔不钻。人类的思想文化本就是互通互促、动辄“串味”的。其中,有的影响是显性的、有意的,有的影响则是在主体无意识或潜意识下进行的。后者的情况可能更多。因为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的显意识犹如水的表面,而潜意识犹如深层。表面当然远不及深层。且,中国古人同时还大都较缺乏严格明晰的学科区分,所以意识观念的走穴串门应当如风起云涌,自然蓬勃,经常不期然而然地发生。所以,同样是论人,人论与作家论倘风马牛不相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事实上,这些人等说或人类论影响于文艺,即造成了中国文论富于作家论和作家类型论。如梁代钟嵘《诗品》虽曰“诗”品,实系“人”品,即诗人品级论。而且,钟氏的诗人三品说的大构架与孔子三等人论、曹丕九品官人说之间有直接借鉴和移植关系。而且,自钟氏《诗品》出,中国古人的诗品、诗话类文论著作如雨后蝉蛹,竞相破土,代有其作,文明昌盛的宋代甚至号称有“千家诗话”,以至于成为中国文论领域一道独特的风景。这些诗品、诗话类著作正是我国作家论的主要载体,此类著作的持久繁荣则说明了中国文论作家论的偏盛。虽然,后来的诗话类著作一般较为低调,不愿或不明采用钟嵘《诗品》的品级论架构,但春秋笔法,抑扬难掩,善读者自可从字缝里看出端倪来。为什么都要有品级呢?还是唐僧那句话,物有几等物,人有几等人;一般人鱼目混珠尚可,理论家岂可不分轩轾!理论著述存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要显优劣,寓褒贬,辨明良莠。
《诗品》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在钟嵘之前,作为中国文论的开篇之作,曹丕的《典论·论文》的核心部分也是作家论——建安七子论。此文以此见长,见重。细读此文,还可以发现曹丕实际上把作家分为三类:即通才、文艺型偏才和理论型人才。曹丕视自己为“通才”,王粲、刘桢等是文艺偏才,徐干则属于理论型人才。这里,曹丕的三等文士论简直是孔子三等人论在文论领域里的“复制粘贴”。
而在曹丕之前,汉代的刘向、扬雄、班固、王充等也曾发表了或体现出很好的文人类型论。刘向、刘歆的《别录》和《七略》分书籍为六类,实际上同时也就把文士分为六类了。⑤扬雄提出“诗人之赋”、“辞人之赋”的说法,这样说当然是在划分赋的类型,但是请注意他是通过划分作家类型来划分赋的类型的。班固的赋类观基本继承了扬雄说,体现了汉人共同的重讽谕之旨;其《汉书·艺文志》又继承刘向说,分书籍为六类,实际同时也分文士为六类。王充是中国古人中极具理性的一位,他早就赢得了“士君子之先觉者”⑥的雅称,所以他的文人分类更精细、更概括,《论衡·超奇》把文士分为四类、四等:“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这四类中,王充最推崇“鸿儒”;鸿儒即指作家,包括辞赋家和作子书者。
当然说到汉代的作家论,屈原是不能不提的。屈原和他的创作在汉代影响至巨。汉人起初的作家论就是围绕着屈原而展开的。从西京到东京,从贾谊、马迁到班固、王逸,屈原的冤魂附体于一代代文士身上。几乎所有的人类学、作家论都曾被用于对屈原的评价上,或褒或贬,见仁见智,讨论相当热烈,深入,持久。汉人的作家论方面的理论蕴藏与创造都被冤屈的屈子充分激发出来了。而正是在这样的话语场中,涌现出了上述扬雄等人的文人类型论。
上述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作家论、作家等级论在中国文论中的发达和繁盛。
当然,这些作家(类型)论大都寓含了一定褒贬倾向,带有划分等级的意味。不过,也正是由此,学者们发现了汉魏间人的以类论文人(以及以类论文)时所体现出来文学自觉意识。魏晋或汉魏时期,中国文学始渐自觉。这是学术界共识,兹不论证。这里要点出的就是:很多学人正是从彼时的作家类型论中窥探出彼时的文学自觉意识的。
现将知类文化对作家论的影响概论或补论于下,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重视作家论。文学就是人学;中国古代尤然。中国文化重视人;先作人,后作文;所以中国文论重视作家,作家论很发达。文学自觉后,作家论更劲。中国文学何时自觉?对此学界尚有争议。或先秦,或汉代,或魏晋。一般认为是后者。堪称文学自觉宣言书的《典论·论文》,首先昌论七子,褒贬作家,并完成了对作家类型的初步划分。钟嵘《诗品》及以后的诗话类诸作等则代表着中国作家论、作家类型论的总体规模和主要成果。另外,总集类著述也有以人叙次、各体作品系于作家名下的,如《河岳英灵集》《宋文选》《古文关键》等,这也体现了对作家的重视,是另一种形式的作家论。
第二,重视作家类型论。作家类型论既有形而下的研究,也有形而上的探讨。如《典论·论文》论建安七子时较偏于形而下,而《文心雕龙》已偏于理论概括。《文心雕龙·知音》有下面一段话:“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这是论人的“知”的,既可看作是论读者,同时也可以看作论作者,两者本不绝缘。当然,作家论和作家类型论的主要载体是为数很多的诗话、词话、曲话类文论著作。
第三,作家类型论指涉个人风格论,所以中国文论中的文学风格论也很发达,且文风论大都比照人格论。孟子说,他的雄辩源于他的“浩然之气”。曹丕《典论·论文》最早把“人气”(作家之气)和“文气”(作品风格)联系起来。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则从作家气质类型的角度把风格分为“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八体”是指八种风格。“八体说”是我国最早、最系统的风格类型学。八体说的提出,显然与作家类型论有一一映射关系。唐僧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则提出19种风格,哪19种姑且不论,笔者关注的是,这19种风格几乎都是从作家性情气质特点的角度立论和命名的。很明显,没有作家类型论,焉得有如此精细之风格类型说!与皎然同时的书法家窦蒙在《语例字格》中甚至提出有90种“字格”——这似乎也过于苛细了;唐末司空图《诗品》有24诗品说;宋代严羽《沧浪诗话》提出“九品”说,等等,这些说法也大都源于作家性情气质类型学。至清代,桐城派文论的集大成者姚鼐则把诸种风格浓缩为两种:阴柔,阳刚。⑦这当然是化繁为简的意思。他的分类依据,仍然来自天地阴阳男女等天人相通、人物交感的中国“人学”。
三、知文与文体论
中国古代,儒家基本上一直都是社会主流思想。儒家重视文化、文学。魏晋文学自觉后,文学更受重视。重视文学,就要知文学。什么是文学?文学为物多姿,属性繁杂喜变,内涵至难厘定。至今世人也没能搞出一个普适的关于文学的定义来。中国古人弃难就易,不孜孜于文学概念本身,而是把更多的心思花在文学外延的研究上。外延搞清楚了,内涵自在其中。所以,中国古代文类学或文体学一向非常发达。
第一,中国古人重知文类或文体。“重视文体形式研究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学术传统之一。”⑧《尚书·毕命》早就提出:“辞尚体要。”刘勰认同此旨,《文心雕龙》“征圣”、“序志”两次引其言。《文心雕龙》共49篇,有20篇属文体论,足见刘勰是如何贯彻落实“辞尚体要”四字的。唐宋人评文章,喜欢讲“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⑨。宋末严羽也很重视文体问题。《沧浪诗话》有五大部分,其二曰“诗体”。他认为宋诗之所以不好,一个原因就是“体制莫辨”⑩。明代吴讷宣称:“文辞以体制为先(《文章辨体·凡例》)!”此言更明确地强调了识类、辨类的重要性,也引起了文士们的广泛共鸣。总之,“‘体制为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学观念之一,历代均有广泛影响”⑪,“‘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⑫。
重知文类或文体的观念落实到操作层面,即体现于文论和文集中的文体论和分类论。提出中国文论“开山纲领”的《尚书·尧典》就已从分类的角度区别了诗与歌:“诗言志,歌永言。”《周礼·春官·大祝》有“六辞”,谓六种文体:辞、命、诰、会、祷和诔。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把诗歌分为“风”、“雅”、“颂”三种,《诗经》就是这样编纂成书的。汉代文体大备,因而有关文体的论述也较多。如刘歆《七略》、班固汉志、王充《论衡》、蔡邕《独断》、刘熙《释名》等。其中刘歆《七略》可谓我国文类学的发端。毛传《诗·鄘风·定之方中》也提到卜、命、铭、誓、说等几种文体。我国第一篇文论专论,曹丕的《典论·论文》提出了“四科八体”的划分。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是“我国文体论的开山之作”⑬;东晋李充《翰林论》也是较早的论述文体的专著。另外,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肖统《文选》、任昉《文章缘起》等都有各自的文体划分或文体分类观。其中《文心雕龙》不仅重视文体论,还为文体论开创了一个“周详的体例”⑭,也就是搞出了一个较系统的文体论方法论。唐宋时出现了很多种诗文集,这些集书在编纂时大都按一定标准先划分文类,再依类编文。明代更出现了多部著名的偏重于文体辨析的著述,如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徴《文章辨体汇选》⑮、杨慎《绝句辨体》、许学夷《诗源辨体》、符观《唐宋元明诗正体》等;明代还有一些著述虽不冠以“辨体”之名,而实也以辨体为主要内容,如《唐诗品汇》《艺苑卮言》《诗薮》《唐音奎签》等。上述这些著述的分类都难免繁琐,也各有其不合理处。“因而从清代开始,文体论者则注意到文体的归纳问题。其一般作法即将文体首先分门,然后系类,以克服列类繁琐,而取得纲举目张的效果。”⑯此之谓“分门别类”也。其中做得较好的是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虑及篇幅,不一一敷述。
第二,重视“辨体”。中国文类繁杂,文类之间的混融或文类互文也很普遍,所以非常需要辨体,对写作者而言先辨明体制尤为重要。否则,就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如上所述,辨体工作秦汉以前就已开始了。秦汉以后,辨体日愈:“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⑰宋代,辨体意识普遍高涨。“辨体批评,成了这个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坚持文各有体的传统,主张辨明和严守各种文体体制。”⑱辨体精微莫过于明代,上引明代多部辨体论著可证。朱迎平说:“传统文体论以辨体为核心,而且重点在个别文体的辨析,”“由于中国古代文体研讨的根本目的是指导写作,因而‘辨体’成为其核心”⑲。
所谓辨体,就是辨析相近文体或同一文体的不同亚体之间的细微差异和各自特点,以免混淆。辨析相近而不同的文体的情形最多,如文笔之辨、诗文之辨、文史之辨、文子之辨、文经之辨、经史之辨、文言之辨,以及古今之辨、正奇之辨、雅俗之辨、骈散之辨,等等。辨析相近文体或同类文体的亚体的细微差别的,如雅与颂、赋与颂、辞与赋、诗与赋、诗与词、词与曲,等等。上述明代的多部辨体著作,即既有辨不同文体的,也有辨同一文体的亚体(或变体、子体)的,这些辨别工作常常表现为分类后的再分类(子类)、甚或再再分类。如贺复徴《文章辨体汇选》分文章为132类,“论”类属其一,然后在卷390“论”类下又分为8个子类:即理论、政论、经论、史论、文论、讽论、寓论、设论等。
辨体的目的是“分开”。但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和合,所以古代文学史上总有一些作家意搞文体浑和或混融。如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词为诗、以诗论文、诗体小说、骈体小说等,这样做,虽然似乎只是形式上的翻新出奇,但其实也是文学创新,自有其价值。当然,文体混融既有有意为的,也有无意而为的。就像植物、动物的杂交一样,文体的“杂交”当然也可以自然地发生。曹丕云:“夫文,本同而末异。”所以,文体间本来就彼此互有。
另外,围绕《诗经》风、雅、颂三体的辨析工作也一直在进行着,此事自汉代开始,一直到唐宋,浸淫及明清近代,延续很久,若总结下来,可自成一小部“三体辨别史”。其中辨得较好的如唐人孔颖达(其《毛诗正义》主要从内容上为三体辨体)、宋代朱熹(从音乐上分辨)等。
不消说,辨体工作是古人“知文”意识的集中体现。
第三,重知每种文体的特征和属性,亦即知“势”或“体势”,简称“势论”或“体势论”。
如果说,文体辨析重在标明不同文体间的差异;那么,“势”或“体势”论就是旨在发觉某一文体自身的内在属性。前者是告诉作者不要怎么做,以免混体;后者是告诉作者要怎么做,以保纯粹。两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保持文体自身的质的规定性,通过唯一性和独特性来确保文体的存在和延续价值。
“势”或“体势”是《文心雕龙·定势》篇提出的:“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学界对刘勰的“势”或“体势”仍有争议。一般认为,他讲的“势”是指“作品的风格倾向”;“势”与“体”(文体)是连言的,“体”决定着“势”,作者应顺体而为,遵循其规律性;“势虽无定而有定,所以叫做‘定势’”⑳。《定势》还明确指出:“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定势》还批评了那些“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穿凿取新”的做法,认为若能“以意新得巧”尚可,但若“失体成怪”就不好了。当然,在刘勰之前,蔡邕、曹丕、陆机等在各自的论述中都已经述及体势问题了;在刘勰后,论述此问题的也很多,尤其在文体辨析类论著中;但以刘勰的论述最集中。限于篇幅,兹不再一一敷述。
中国文体论地位重要、程度发达的原因非一,主要有四:一者,欲重文,须知文;欲知文,须知类,知类当然要先分类了,这是根本原因。当然,中国文体分类的直接动力源是文集的编纂。二者,文体学本应是文艺学或文学学中的“显学”。文学史往往就是文体史,而文体史往往就是文体的(动态)分类史。文学史往往就是文体的兴衰轮替,文体的兴衰轮替必然要导致文体学的重新构架和再书写、再定论。三者,中国实际文类本繁多,相应地文类学亦繁多。徐复观《〈文心雕龙〉浅论》之七:“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同点之一,在于西方文学只顺着纯文学的线索发展,而中国则伸展向人生实际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以西方文学的种类少,而中国文学的种类繁,因此在作品的整理与把握上,中国文学分类的重要性过于西方。”㉑四者,文体混融或文类互文的时时发生和永恒存在,使知文体、识文体很难,作者分不清,论者也难搞明白,读者更易糊涂。这就非常需要经常的、大量的文体辨析工作,从而倒逼了文类学(和辨体论)的繁荣。
四、知书与目录学
《汉书·艺文志》:“书以广听,知之术也。”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但也可理解为一般著述。人们求知的最主要途径不是直接经验,而是间接经验,即读书求知。为满足此项文化需求,我国历朝历代,只要政有余力,一般都会组织人马,编书出书,而且部头和规模越整越大。
书多了,自然要分类,“以类知书”。以类知书是治学关键。南宋郑樵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㉒。在我国,书籍分类早已成专门之学,此即“目录学”。我国目录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编写历史和编写传统。先是西汉刘向、刘歆编成《别录》和《七略》;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因之;至西晋荀勖编《中经簿》时,弃“七略”而创“四部”:即经、史、子和“丁部”;梁代目录学家阮孝绪编撰《七录》时,已有“文集录”,正式开启了《隋志》之“集部”;《隋志》正式确立四分法;至清代,四部、四库囊括众籍遂终定局。
书籍分类有利于分类知书。欲知理,看经子;欲知事,看史部;欲知情,看集部。按清代叶燮《原诗》中的说法,天下万事万物,不外“理”“事”“情”三字。三字通,万事明。
当然,古代目录学虽全,但仍有一大人为的疏忽,即以小说、戏剧为代表的白话通俗文学不在收纳范围,此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