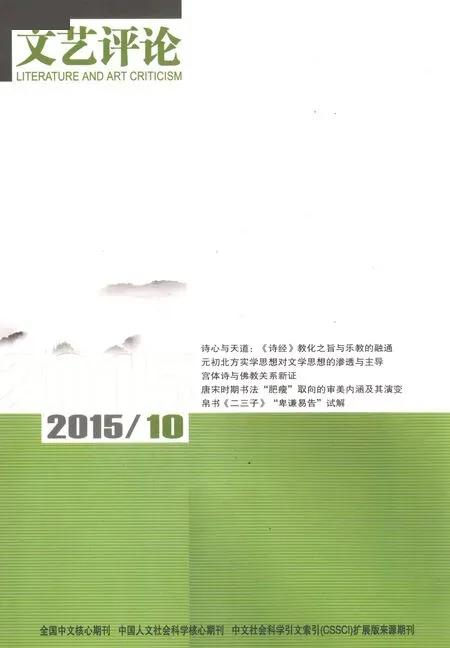《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的艺术比较
王 延
《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的艺术比较
王延
小说到明清两代,具有讽刺意味的作品逐渐成熟,其中以《聊斋志异》中的部分作品和《儒林外史》在这方面造诣最高,《儒林外史》是一部纯粹的讽刺作品,讽刺的是封建科举制度和与之有关的文化思想统治,描写了当时士林的病态。《聊斋》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揭露了这方面问题。两书从艺术上有一些同异,若从这方面作以比较,可以发现古代讽刺小说中的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题材与内容的选择
讽刺小说的题材和内容关系到作品是否真实可信,主题是否有深度,所以两部小说里都体现了对这方面的重视,具体作法却又各有不同。
《儒林外史》中将八股取士作为中心题材,在作者看来正是因为朝廷推行了八股取士制度,才使许许多多读书人为了谋求功名利禄,做出啼笑皆非的事,于是他把八股取士作为主要的揭露、讽刺与批判的对象,强调它是导致士林轻视文行出处的根源。这一点,在小说的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就已经点出来,该回的后面写秦老从城里带回一本邸抄,写有“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指给秦老看,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里王冕就是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借他的口将全书的主要思想说了出来,他的重视行文出处、轻蔑功名富贵等行为,更是对小说中“品地最上一层”的名流行为的隐括,全书就是围绕这一回中透露出的中心思想展开,通过认真体味我们还可以发现,吴敬梓有意识地在描写过程中将儒家的道德伦常看作了他的思想基础,即通过正反两种人物的描写,一方面指责道德的颓败和沦丧,另一方面又寄托重振道德伦常的热望。在客观上起到了批判当时文化思想统治和整个世态人情的作用。①
在《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讽刺科举及有关士人的作品,大约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作者没有认为科举制度是士林诸恶的根源,相反,还对这一制度抱着希望。他的讽刺所向是某些科举机关和主考官员,对于讽刺一般士人的作品,也不把过错或罪责归到科举制度本身上,主要归到人物自身的道德修养之上,如《雨钱》、《沂水秀才》、《苗生》等篇都是如此。在题材的广度与深度以及所带来的社会意义而言,《聊斋志异》比之《儒林外史》还是有所不及的。
对讽刺小说而言,体现其艺术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实,在小说史上有一些所谓的讽刺小说,虽然内容在讽刺,但实际并无讽刺艺术可言,主要原因就在其内容往往出自作者的“造谣和诬蔑”,因此往往给人以脱离实际、远离生活的感觉,在这方面《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就是其它讽刺小说所不及的。《儒林外史》的题材虽是假托明代,实际都是清代社会的真实写照,如《儒林外史跋》中所说书中人物都实有其人,“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不仅如此,甚至将作者家世写入书中,如严贡生谋吞弟弟家产,即是作者族人欲侵其祖遗的缩影。虽然有相当的情节是采自他人的著述,但是对这件事已作了艺术的表达,总之,全书的取材正如清人邱炜萎所说的“纯从阅历上得来”。也正因如此,鲁迅先生对吴敬梓表达出“身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态,就能格外详细。”的评价,从以上情况来看,《儒林外史》在内容与题材上具有真实性也具有托讽性。《聊斋志异》有关科举和士人的讽刺性作品也具有托讽性,只是他的托讽性是除了假借真人真事之处,还假托志怪式的虚构故事,因此作品内容往往较为庞杂,这是它的特点。
从主、客观角度来看,《儒林外史》的取材和内容是偏重于客观的,全书有讽有揭,写正写反,作者有意识的保持着局外人的态度,这使整部作品地冷静、深沉、稳健,因而在具体描述中能表现出秉持公心,指擿时弊,区别对待。如,同样是讽刺,写王惠到任搜刮有批判性;写汤奉故作廉能有谴责性;写范进喜极而疯有嘲笑性,写权勿用硬充名士有揭露性;写王玉辉鼓励和羡慕女儿殉节有哀婉性,总之全书的艺术格调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流露出作者对当时国家政教倾颓而忧心忡忡的情感。《聊斋志异》中有关这方面题材的作品虽也有讽有揭,有正有反,但总体上来说比较主观,因为作者本人是局内人,迷恋着科举和功名利禄,所以态度上有明显的严刻、激烈和热切,有些作品尽管也带着戚谐与婉讽,但总的来说,更多的是露骨的鞭笞和嘲骂,从思想境界上逊于《儒林外史》。
二、结构情节和人物塑造上的不同
在结构上,《儒林外史》它采取短篇勾联成长篇的体式,即在集中写一人或少数几人横面的基础上兼及较少层次的纵面,然后逐渐地转向另一个或另几个人的横面与较少层次的纵面,这样不断地更换,推演,最后罗织成长篇,小说家曾朴在其《孽海花》修改本中,把这种结构比作“珠练”,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这种结构能够充分包容社会生活的各个横面和纵面。《聊斋志异》全是短篇,每篇写一个人或几个人,也是取横面兼取较少的纵面,而且每篇都有模式,胡适在其《胡适文存》中就指出它们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朗,……好事多磨,……遂为情死”等等。
从情节上看,《儒林外史》是近乎开放式的情节结构,不太重视情节的完整性,讲究情节的真实性、典型性、生动性和丰富性,其中生动性的情节中以“计谋”式的情节更为突出,所谓“计谋”式的情节,是指对于某种支配事件全局的计策、智谋或手段的过程给以描述。《儒林外史》十分巧妙地运用了这类情节的艺术,所不同的是,其并不写“计谋”的全过程,亦即不完全遵照传统话本小说中所运用的事事人人皆从头说起的叙述方式,它往往没有明显的起承转合,也没有突出的高潮。它的主要组成部分都是人物最具有本质特征的、尤其具有戏剧性的一个或几个生活的片段。而且这种片段又常常是悲剧性和喜剧性相互交融、相互照应的。《聊斋志异》在情节设置上,也注意真实性,但更多的是幻想的真实,当然它也注意情节的典型性、生动性、精彩性、曲折性、新奇性和完整性。特别是完整性,更受传统小说情节特点影响,喜欢从头说起,所以它大致属于封闭式的情节结构。
在人物塑造方面,《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无十分强烈的悲和喜,反面人物多是可笑可鄙之人,可憎者较少,是悲喜剧相融合式的,各种人物之间身份、地位的悬差并不是十分大,因为大体都属于士林的范畴。各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则比较复杂,真真假假,明明暗暗,总是交织在一起,但各自出场及主要行动方式却十分灵活,根据剧情临时的需要来决定来去,随兴随灭,自然起伏,不太重视交待人物的最后结局。《儒林外史》在人物塑造三种基本关系上(人物与环境的对比、人物与人物的对比、人物本身的对比),其更注意人物与环境的统一性和矛盾性,而不在意人物之间的强烈敌对冲突,尤其是人物的性格自我表现,在这里,环境、事件和性格紧密联系起来,不通过堆砌事情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点,也不通过情节的变化来理出性格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以前传统写法的创新。②
《聊斋志异》中有关科举和士人的讽剌性作品中,人物类型不算多,多是正与反两方面的,有时也有一些处于中间类型的人物,其中正面人物以可悲者居多,反面人物可鄙、可憎者多,可笑者较少。总的来看,悲喜剧融合式的人物较少,较多的是交错和转化式的人物。人物的悬差一般也不大,但出场的方式及其走向却异于《儒林外史》,它的主要人物都是先出来,并且人物走向很清楚,有完整的性格和明显的发展过程,结局也都交待得比较明白。在人物塑造三种基本关系上,《聊斋志异》更强调人物与环境及人物与人物间的矛盾关系,特别是人物与人物间的激烈、敌对矛盾,为了突出这种矛盾和感受,常常侧重人物的不被赏识和自身感受,有意的堆叠事情,直至事件的高潮。如在《司文郎》中,既写了考生与考官之间的矛盾,又写了考生与考生之间的矛盾,表现了考生自身的情绪起伏。为了突出王生的怀才不遇,而着重安排其与余杭生之间的对比情节,并将其再次落榜作为高潮。这就把人物的主要性格表现得较为完整,发展过程也较为清楚。
三、艺术技巧方面比较
在严酷的封建统治下,为了避开文字狱之类的迫害,讽刺作品相较其他作品更需要讲究艺术技巧。《儒林外史》主要通过夸张手法来具体描述人物,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肢体夸张,如严监生在咽气前伸出二根手指示意嫌费灯油;二是言语夸张,如匡超人在牛布衣面前自吹;三是心理夸张,如范进见中举喜帖后心理失常发疯。不过全书最为常用的是白描手法。书中的白描丰富多彩,其中最有典型、最基本的有两种:一是反映人物精神、心理和性格本质特征的,如第六回严贡生为儿子娶媳妇,雇两只民船,自已坐在船上忽然患起头晕病,吃了几片云片糕,将吃剩下的云片糕放在一边,被掌船的船工吃了,船靠码头后,他寻起云片糕来,发现被吃了,于是他说这糕花了几百两银子,用上等的人参、四川的黄莲配制的救命药,非要把船工押去送官,结果赖下了船费。通过这段白描,把他吝啬、无赖、仗势欺人的嘴脸与本性刻划得入木三分。二是揭示人物言行矛盾或身份与才识的不相衬,如第四回举人出身的张敬斋将宋初赵晋与赵匡胤的故事安在了刘基与朱明璋头上,而范举人和汤知县竟信以为真。这段白描,有力地嘲讽了许多士人身份虽然提高了,但是学识却贫乏的可笑。《聊斋志异》中的讽刺作品不太使用白描,有时主体的部分使用了这一手法,但在篇末又加上了断语,使白描显不够纯粹,虽然较少使用白描,但同它的作者处于局内,多作主观描写也是相协调的。③
对比手法也是讽刺作品中常用的手法,它不仅能使相互映照的人物形象更鲜明,而且能带出作者的褒贬之意,《儒林外史》不仅喜用相背式的对比,即正反人物的对比,又常使用相助式的对比,即相同或相近人物的对比。相助式对比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周进与范进,二是王德与王仁,三是娄玉亭与娄瑟亭,四是严贡生与严监生,五是牛浦与牛玉圃等,作者之所以多用这种相助式的对比,显然是出于主题的需要,强调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并非少数,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反映出科举制度给整个士林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聊斋志异》较多地使用相背式的对比,包括人物与人物、情节与情节、人物本身以及人情与人情之间的对比,而且这些对比里还带有浪漫与夸张的色彩。如《辛十四娘》中单纯直率的冯生与奸诈阴险的银台公子对比,《叶生》中叶生前“所如不偶”与死后得中功名对比,作者大量使用这种相背式对比,同作者对社会的孤愤不平有直接关系。④
通过《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书都抓住了讽刺艺术的关键,即都能根据人物与事件本身所具备的矛盾性、荒唐性以及可鄙、可笑、可憎的特点,加以白描、夸张和渲染。
【作者单位:河南工程学院发展规划处(451191)】
①陈美林著《儒林外史人物论·“隐括全文”的“名流”王冕》,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1页。
②刘伟编《蒲松龄研究集刊》,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121页。
③王枝忠编《国际聊斋论文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④杨义著《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