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萨,索穷和朋友们
周翔
就西藏的每个人而言,对拉萨这座城市的理解,大概与对自身的理解是不可分的——在这里,人们会遇见一切。
藏族小伙子用汉语说:“他,哪里来?他……”
美国人仍用藏语说:“糌粑没有吗?”
汉族商贩严肃地用英语重复着:“中国。美国。”
这是索穷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在《西藏文学》上的一篇小小说的结尾。隔了快30年,当年《西藏文学》的编辑央珍和索穷以及几个朋友一起坐在一间传统藏餐馆的房间里,央珍还记忆犹新地提起这篇“特别有意思”的小说。阳光透过窗格照着索穷有点花白的头发,他脸上有种羞赧的神情。通过小说和这些朋友结识的年代,转眼已过去这么久,而在这时间的慢慢酝酿中,当年写作时不甚明了的意味,倒一点点咂摸了出来。故事很简单,一个藏族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汉族人在西藏一个小县城里相遇,都拿自己不擅长的语言去沟通,又得不到说话对象的理睬,形成一个循环的怪圈。“就是写他们互相拧巴着,都要跳出自己的文化,但是又跳不出去的那种感觉。”这像多年前的一个隐喻,虽然那时候索穷并不那么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我就觉得是要发生的一种事情,要有新的事物进来,要有新的改变发生——好与坏,并不知道。”
被他们的谈话勾起了兴趣,我向索穷要他的小小说想读一读。他为难地搔搔头说:“我这里都找不到了。”他不保存自己多年前的作品,而且,他也很多年没有写虚构的作品了。但在80年代,在阿里措勤县唯一的学校里,用教课之外大把的时间,不断地写一篇又一篇的小小说,将它们寄往拉萨的报刊杂志,却是索穷最大的快乐、最好的“抒发自我的方式”。
80年代: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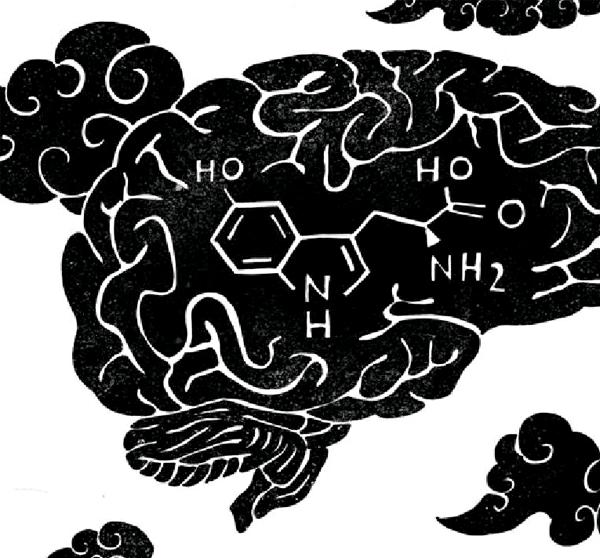
拉萨市内的一家茶馆。到茶馆喝茶聊天是藏民喜好的生活常态
措勤县是阿里的东大门,是阿里地区离拉萨最近的县城,但邮车也要半个月才来一次,带来一个月以前的书信、报纸和杂志,那是当时获取外界信息唯一的通道。1965年出生在阿里噶尔县门士乡的索穷算是当地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在乡里上了几年小学后,他考到位于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读了三年预科之后又读了两年初中,最后的第六年进入边境地区小学教师培训班,毕业后分到措勤县完全小学,成了县里不多的“有文化的人”。1984年,从民族学院毕业分配回乡时,索穷第一次路过拉萨,他意识到内心强烈的渴望,一定要到这里生活。“拉萨太好了,是藏族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中心,我是西藏人,我就要来这里。”
在广袤的高原上,“文化的绿洲和生态的绿洲往往是重合的”。阿里地区除了普兰、扎达、日土这几个县城,其他地方在索穷的眼中都缺少文化和历史。措勤县以牧民为主,历来居无定所,除了帐篷,“连一间房子也没有”,只有门东寺这一处古物,“文革”时期成为粮食仓库,才得以保留下来。七八十年代四川的建筑队在这里修了校舍和住房,只有一条街的县城就固定了下来,住在县上的人口只有百来人,其他仍然在牧区过着迁徙的生活。索穷就在小县城里施展着自己的想象力,幻想着、勾勒着会发生在生活里的变化、冲突、异于自身的一切可能。攒钱,每个暑假搭上三天邮车去一趟拉萨,是最快乐的事情。“没有一定的目的,就是觉得要去有人、有文化的地方。在八廓街附近找个招待所,逛书店、画廊,看寺庙和古建,跟陌生人聊天。”
不过索穷当时看到的景象,在老拉萨人央珍的眼中已经变化了模样。60年代生活在拉萨的央珍和姐姐玉珍对这个城市的判断是“洋气”,因为地缘的关系,西藏与印度联系密切,而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而备受其影响。西藏贵族中多年来的传统就是前往印度甚至英国留学,因而西方的生活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西藏尤其是贵族阶层的生活。60年代这种影响的延续性仍在,央珍记得那时的拉萨往往比内地物质更丰富:“英国的巧克力、呢料,印度的泡泡糖,都可以买到,看电影、跳舞,也都是平常所见的情景。在西藏待了几十年的廖东凡1961年从北京大学毕业来拉萨,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当时内地因为自然灾害物质很匮乏,没想到来了拉萨看见八廓街上商铺特别繁荣,他就推着自行车东张西望地看,一路上还有许多身着艳丽服装的藏族妇女在卖香,装在印度进口的铁箱里。”
那时拉萨的城区只有从西面布达拉宫到东面大昭寺一带,在今天的北京东路和与之平行的宇拓路上住满了城市居民,八廓街上满是商铺,但是不同于今日,“店铺里面是放着印度的音乐,有淡淡的香气,商人静静地坐在店铺里,没有靠吆喝招徕生意的”。藏族所需的一切物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要买内地商场里的东西,则去宇拓路。幼年的玉珍和央珍姐妹俩有时候还会被父亲带去甜茶馆。今天走进任何一家甜茶馆,大都是人声鼎沸,除了藏民在里面打牌、下棋、聊天,还有很多游客。但60年代的甜茶馆在央珍姐妹的记忆里“安静极了,大都是一家人在喝茶,或者男人们在低声地谈论新闻”。而且极少有女性会去甜茶馆,这些都是拉萨人的老规矩。在央珍眼中,过去的拉萨社会,所有的特质可以总结为“优雅”:“重视礼节,歌舞的动作幅度不会很大,说话嗓门不会很高,穿衣服也不会特别艳丽,房子的颜色绝对不会大红大绿……”
这些记忆因为“文革”的开始而中断。当1981年央珍成为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西藏学生时,这座城市又慢慢开始从“文革”的单调中醒来。跟内地一样,拉萨的文化艺术活动也掀起了热潮。有不少大学生怀着理想主义与浪漫情怀来到西藏工作,从事文学艺术创作,马原、裴庄欣、于小冬以及更早到来的马丽华、韩书力等外来者与当地的知识分子一起,构成了规模不大但异常活跃的文化圈子。如今的布达拉宫广场一带,当时全是居民聚居区,不少拉萨市民把房子租给外地的艺术家,这一片因而成了颇有名气的画廊。南边的拉萨河则是青年们聚会聊天的天然场所,仙足岛和太阳岛一带都是茂密的树林,外来的青年也学着闲适的拉萨人一样到那里去“过林卡”(郊游)。
1981年,初中刚毕业的阿旺扎巴以画画的特长考取了西藏师范学院(1985年改为西藏大学)艺术系,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从小就被家里的宗教氛围熏陶长大的阿旺扎巴,一到拉萨立刻去了大昭寺朝圣。但进入学校不久,按照他的说法,却“很快转换了信仰”。那时正是陈丹青《西藏组画》声名大噪的时候,学校里所有的美术杂志、丛刊都是相关的介绍。在昌都长大的阿旺扎巴所受的启蒙教育来自在当地教书的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生夏和中,他教给阿旺扎巴最基础的素描,但这一次油画产生的震撼效果确实是前所未有的。“那种色彩、人物和生活的方式,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画西藏的。”阿旺扎巴从此立志要画好油画,“画画成了我的信仰。”因为当时是被当作师资力量来培养,他们所上的课程包括了各个门类的绘画,但是阿旺扎巴却并不喜欢画唐卡。“我总觉得它拘泥于过去陈旧的模式,我在学校学中国美术史、世界美术史,那些艺术家都是在不断超越当时的艺术巅峰,才造就出伟大的作品。唐卡好像复古一样,不是跟当下相对应的艺术形式。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时代的烙印,你是这个时代的,你的艺术就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氛围。”
作为粗犷的康巴汉子,阿旺扎巴内心深处总觉得和拉萨的优雅、从容有一点“隔”,在那个逐渐升温的年代里进入藏地文化的中心,他喜欢拉萨的氛围,但画笔下的冲动总是指向遥远的昌都。1985年毕业,阿旺扎巴拒绝了去天津进修然后留校的机会,告别了学校里的李津、于小冬等师友,回到了昌都。同样在1985年,上学期间四年没有回过拉萨的央珍又回到故乡,在文联下属的《西藏文学》当编辑。当时的这座城市,正经历着她记忆中最有活力的时期。民族的与外来的事物,统统像地下的潜流重新接上了过去的余脉,或者打开了新的空间。“以前机关单位里极少有人穿藏装,现在有人穿了。老建筑上抹的灰泥都去掉了,民族的色彩回来了。”
80年代末,央珍和索穷在拉萨看到了阿旺扎巴的成名作《等待》,他们也因此认识了阿旺扎巴——拉萨的文化圈子,历来是“特别小的”。这幅后来更名为《无题》的画,在1988年中国美协西藏分会在北京举办的西藏当代画展中得了一等奖。它是一幅康巴人的群像,红褐为主的色调,并不完全写实,人物和空间的组合有一种抽离感,康巴地区的强悍气质就更加凸显;天空上诡异地挂着一个时钟,上面的指针指向完成这幅画作的时间。人们都问阿旺扎巴,等待什么呢?“我就说等待未来啊,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才画了这张画。”
90年代:分歧
小说和绘画成为80年代对西藏赋予想象的主要方式,不管是外地人还是当地人。马原和扎西达娃以西藏为题材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风靡全国,这种新的叙述方式与西藏的传统相遇,较之内地而言,更能为天马行空的瑰丽幻想提供适合的表现题材。当然,外来者的审视意味和想象性会更加强烈。在宗教范围浓厚的传统藏族那里,往往不是线性的时空观念在支配他们,前天、昨天和今天并不一定遵循着单一的逻辑,循环往复和重叠错乱恰恰为叙述的多重维度提供了空间,放进写作者自己的想象。但并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如此。
央珍不这样写。“我没有他们那样奔放的想象力。”她说,“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作家对西藏有一定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但是我从小生在拉萨,在十分熟悉的环境中,无从产生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种熟悉让她的写作更多指向对过去的追忆,她要通过虚构的方式呈现真实的过去。1994年,央珍出版了小说《无性别的神》,这是第一部藏族女性所写的长篇小说。小说的叙述时段主要集中在1940到1951年,小说中关于当时贵族的家庭生活、礼仪规矩、饮食习惯、文化风俗的素材,大都来自她听到的祖辈的描述,以及她自己在60年代拉萨生活的直观记忆和感受。“拉萨的生活在‘文革之前是有延续性的,虽然贵族、商人、平民之间的阶层差异消失了,但是人与人的相处模式、生活方式很多还保留着。”央珍的写作里因此充满了真实的追忆性质,不同于魔幻现实主义,她的写作更注重于通过客观的真实性来让人们了解这片土地和生活的细节。
这种写作上的定位,要依靠她较之其他人更丰厚的拉萨记忆,这是不能通过想象力替代的东西——既是对自身记忆的发掘,也是重新梳理、诠释、理解它们的结果。“我小时候淘气,下雨天麻雀飞来,我们去逮,家里老人就会立刻阻止。”她后来意识到,这是藏族根深蒂固的佛教传统的一种表现,“见了动物不能杀生”。她小时候上汉语班,教育里没有传统的内容,她说“书里会告诉我们哪些是不好的,我们也没有地方去了解”。而到文联工作以后,她一面当编辑,一面跟着民间艺术研究会到处下乡。“重新了解民族文化,也更有自觉要把自己身上缺失传统的那一部分补回来。”那是她记忆中最好的时光,她说,“那是我最喜欢的拉萨,丰富,充实,满是希望。大家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感情而去了解和保护民族文化,不像90年代以后到现在有很多商业的考虑。”
同样感觉到90年代带来的变化的,还有1992年终于下定决心辞职来到拉萨的索穷。离开措勤之后,他进入拉萨的《西藏文化报》,辗转“在很多媒体干过”,直到2007年加入《西藏人文地理》。索穷本来打算到拉萨继续写小说,然而他自己也没想到,来到拉萨以后他开始了纪实性的写作,从文化调查类的小散文开始,到系统地研究八廓街、研究西藏近代史上的教育。当年上私塾的老先生、曾经的留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些大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成为他口述历史的对象。“以前在措勤,只能通过虚构和想象来支撑写作,但是到了拉萨,遇到的一切都变成了我的素材。”
索穷之所以对西藏的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因为他觉得教育是改变人生最根本的途径——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央珍,或是历史上的西藏人,都是因为所受教育的不同,而改变着自己,以及自己与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关系。“你会发现几类人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比如早期留学印度、英国的留学生,他们所接受的是西方那种自由、民主的观念,回到西藏以后一腔热情要改变这里的社会制度和秩序。留学生们大多有过在西藏接受私塾教育的经历,但相比起他们,只接受私塾教育的老先生则更加保守,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有非常丰厚扎实的学养,但又相当谨慎。而后来去内地上学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现在西藏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更紧密地联结着西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不过索穷更感兴趣的还是普通藏族人的“言传身教”,那些形形色色人们的经历,是他们更本质的教育。喜欢跟陌生人聊天是他最大的特点,也是有助于他成为一个“记者型作家”的原因。“我特别喜欢跟拉萨街头的人说话,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那些朝佛过来的,那些沉浸在声色犬马里的……随便什么人都可能是一个传奇。有时候人家也来劲儿了,觉得找到了很好的听众,就掰扯上大半天。”索穷最喜欢去的还有拉萨街头随处可见的小酒馆,在街角、在路口、在树荫下,随处可见,拉着布帘,远远地在外面就能听到里面轰然的笑声。“一般都是一圈人在那儿玩骰子,又唱又跳。玩骰子的人口才都很好,嘴里念念有词,从一开始唱到数字十二,每个数字都能唱出一大堆故事,像诗歌一样。曾经有人还编了本书就叫《西藏骰子说词》。”这是民间文化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比试口才中的灵光乍现、突发奇想,都是从小耳濡目染的结果,充满了俗世的谐趣和智慧。
索穷用对他们的记录和观察,代替了小说写作。如今回头看来,央珍夸他做了一项抢救性的工程。“我们生活在拉萨,倒想不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反而索穷怀着对拉萨的热情和想象记录下了缺失的这一段历史。否则,今天的拉萨已经不同了,过去也就找不到了。”1994年,央珍的工作从拉萨调到了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此后每年只有尽可能找时间回到那里。而距离的遥远,更让她觉得这个城市充满了越来越快的变化,她对于拉萨的追忆,充满了老拉萨人“追忆似水年华”的味道。在八廓街的中心区域,她觉得甚至很难再找到一个传统的拉萨人了。而当初来到西藏的大学生和艺术家也大多纷纷离开,曾经热闹的文化圈子逐渐风消云散。
“80年代的一阵风吹完了。”索穷说。不仅是知识分子圈,民间松散、惬意的文化氛围也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而逐渐消失。街头的酒馆茶肆在逐渐消失,他并没有一丝要离开的念头。“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就要在这里生活。”他仍然觉得拉萨是一个“传奇”,只有在这里故事才能有更精彩的继续。“西藏最好的与最坏的肯定都在这里。”
阿旺扎巴也重新回到了拉萨。1990年他调进了西藏美术家协会,从此有了条件专心从事创作。但他没有停止内心的“不安”,他安慰自己这里是一个窗口,也会提供给他更好的审视昌都的角度。“其实离开一个地方,再从很远的地方来看这里,会真的不一样,那是非常深刻的。身临其境的时候说不定很多东西你看不到,容易钻牛角尖拔不出来。所以我想,来拉萨也许是幸运的。”不过90年代中期以后,他变得有些苦闷起来,曾经的油画技法对他而言不再能够满足表现力的需求,而走出门外,他总是听到人们问他,你的画卖得怎么样?
焦虑和张力开始在离开故乡的他身上变得明显起来。属于传统的唐卡、国画在这个时期重新进入他的视野,他意识到这是躲不开的传统。“我开始想把现代绘画介绍给他们,当个中间人。”阿旺扎巴说,“传统是你的灵魂,但要不断地提炼,像两块石头碰在一起产生的火花。这支撑着我从油画转向尝试新的画法。”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他在自己的小空间里开始做一件更基础性的工作,借鉴西藏传统绘画材料,调配新的颜料、新的油,他说:“我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话。”
2015年:重逢
这一次他们的相聚是在阿旺扎巴的家里,休假回来的央珍想去他家里看画,同时也会会许久不见的老友。9月初的拉萨白天阳光依然灼热得像夏季,家家户户的窗台上和院子里都种满了花。央珍说,这也是拉萨人的传统。以前的拉萨人,不管多穷,连家里的桶和盆也要拿去种花。
2004年以后,阿旺扎巴重新开始大量作画,他已经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绘画语言。10年的试验,他把西藏传统绘画中的植物颜料和矿物质颜料加入油画所用的颜料中,研究伦勃朗调制油时所用亚麻仁油和核桃油的比例,并加入西藏过去织地毯染色所用的桐油,“研制”了一套自己所用的特殊材料。他也重新吸收了80年代曾经排斥的唐卡的风格,吸收那种“以线当面”来描摹的技法。“油画的色彩、国画的线条、唐卡里的技法,融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我今天的画。”阿旺扎巴说,“也许有点狂妄了,我给它们起名叫作‘康巴艺术,我还是画这个地方的人,画这群人怎么生活,我怎么感受他们。别人怎么解读,那是他们的事。”
比起80年代的画作,阿旺扎巴新世纪以来的画虽然仍有油画的质感和技法,但是风格和画面上有了传统壁画的神韵,想象和画面组合也更加奇崛,唐卡里的宗教人物和佛经故事有的变成了画中的元素。而他所画的一组康巴人的肖像,国画的画风更加明显,色彩的呈现又是油画式的。
央珍仍然记得当年看到《等待》时的震撼,“一下子就能感觉到拉萨以外的藏族的气息”。而如今眼前的画作,在一贯的强悍、爆发式的状态里,又多了些内在的从容。过去的圈子消失了之后,阿旺扎巴每天的生活就变成了独自作画,“画画的时候不抽烟了,和人聊天高兴起来才抽烟喝酒”。他的画里有了更多清醒的审视和有意识的创造,他习惯了热闹之后独自一人的状态。“八九十年代大家的群体意识很浓,搞艺术的全都从早到晚在一起谈天,现在都是各干各的。但我觉得对于艺术的认识,大家都在提高。其实一高了,人就独立了,个性化了。这是一个过程,并没有绝对的好坏。”
虽然他们记忆中的拉萨在变化——古老建筑的消失,城市的扩张和改变,曾经的朋友各自散去,但是拉萨还是存在一个“解释不清楚的无形的气场”。阿旺扎巴内心和拉萨之间存在的疏离感,那种既近且远的张力终于处在一个刚刚好的关系之中,如今他找到了最舒服的作画状态,一个能够在熟悉的地方“跳进跳出”、随时变幻审视距离远近的位置。“不想画的时候就可以跑到八廓街转一圈,那种氛围一下子就会带给我画画的冲动。”今天的八廓街上反而是康巴人居多,他们轮廓分明的五官、脸上深深的皱纹,都和阿旺扎巴的画里一样。
从阿旺扎巴家告别,索穷又准备去八廓街。不同于阿旺扎巴来这里找绘画的灵感,索穷像是在这里找故事的续集。过去的拉萨景致消失之后,央珍不太常去那里了,相反,索穷却越来越多地泡在八廓街一带,在他看来这里仍然是“所有可能性的所在”。传统的冲赛康市场盖起了新楼,但楼前的一片空地仍然每天进行着传统的冲赛康“站市生意”,来自西藏甚至全国各地的商人带着他们淘到的古董、珠宝,进行着一场场关于文化、商业、经验上的较量。
索穷在那里一待就是半天或一整天,很多时候他并不说话,只在人们交谈的时候静静地听着,或者细细地看他们手中的古物。他常常会站在市场上年纪最大的阿觉爷爷身边,让他教自己如何通过观察一件青铜挂饰的孔道来分辨它的年代,买水獭皮如何观察它的绒毛,什么样的玛瑙石和绿松石才最好。他常常会记混了昨天和前天遇到的人事,在时空之间跳跃。他教我如何不讲逻辑地交谈:“这里跟人们说话的好处就在亮堂堂。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要一万块钱,你可以还价一块钱,他不会生气。”在传统的藏族人那里,大概一切语言和事物都可以直达它的核心,并不需要中间的层层递进。我看着他想,似乎拉萨把索穷变得更像某一种西藏人了;但同样是在这里,索穷和他的朋友们是多么既相似,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