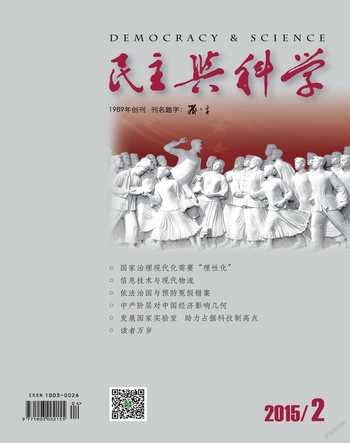当前冤狱防范面临的问题和出路
易延友
这些年纠正的冤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被冤枉的人都被刑讯逼供。归根到底,冤案发生是因为制度建设、权利保护不到位。
冤案发生的频率和制度设计的水平体现了社会、尤其是政府、执政党对冤案的容忍度。我们应该树立一个观念——不能够办一个冤案,把疑罪从无观念贯彻到底。
有一些制度是可以预防冤假错案的,如沉默权原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犯罪嫌疑人在被询问时享有律师在场权、关键证人对质权。
一方面通过制度完善,尽可能从源头杜绝冤案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司法人员努力,严格遵守司法程序,遵守当事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建立冤狱防范、冤案及时纠正的机制。对这个问题,我想谈三个观点。
古今中外都有冤案,但是中国的冤案略有不同
古今中外都有冤案,中国的冤案略有不同。在于中国的权利保护不到位、制度设置不到位。这是主因。
香港首席大法官李国能说香港没有冤案,这个我相信,因为香港地方小。但是像中国内地这么大地方,不可能没有冤案。英国很小,也有冤案,法国也有冤案,美国更有冤案,中国古代也有冤案。哪一个稍微大的国家说没有冤案?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就目前来看西方国家的冤案有个共同的特点,例如《错案》所论述的那样,冤案发生是由于DNA技术等科学技术不够发达造成的。以前没有DNA这项技术,现在有这项技术纠正了很多冤案错案,如果更早一些就有这个技术,冤案就会少了,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同样地,人们以前比较容易轻信目击证人证言,以为证人既然亲自在场,他说的怎么可能会错;现在我们通过科学研究尤其是反复实验,发现目击证人犯错的比率很高,因此不再那么轻信目击证人的证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冤案。所以现代西方社会冤案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科技不够发达。
中国冤案发生的原因和西方不一样。最近这些年纠正的冤案,像佘祥林被指控杀妻,最后他妻子活着回来了;赵作海被指控杀害其邻居,最后邻居也活着回来了;杜培武被指控杀害他的妻子和妻子的情人,最后真凶被发现了。这些冤案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被冤枉的人被刑讯逼供。这和西方国家披露的冤案发生的原因是完全不一样的。科技不发达不是通过侦查人员的努力可以避免的事情,刑讯逼供则通过主观努力完全可以避免。
刑讯逼供不是说法律不禁止,1979年刑诉法就明文禁止。但是我们在禁止刑讯逼供方面制度不到位。我认为刑讯逼供是可以禁止的,只要愿意下决心去禁止。那么多年的顽疾,从1979年恢复法治建设以来,我们几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讲刑讯逼供,难道是不可治愈的癌症吗?其实是可以治愈的,就看愿不愿意下决心治愈它。有一些制度我们明明知道是可以防止冤假错案、可以防止刑讯逼供的,如沉默权、讯问时候律师在场权等,但我们不去确立,在法律上不去规定。我想,这是中国大陆冤案发生的最根本原因。
任何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逮捕拘禁必须要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聘请律师,如果没钱请律师可以帮他。这是1966年米兰达案件宣布的规则。当年米兰达案最高法院法官一判完,全国媒体一起声讨,甚至尼克松总统也反对他,说这个制度太严厉了,让很多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尼克松之所以能上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帮助他登上总统宝座;他极力反对当时联邦最高法院颁布这个规则,并承诺选举胜利后一定设法改变这个规则,所以赢得了选民信任。他上台以后又促使议会通过了新规则。但是联邦最高法院颁布的规定,他没有办法改变,一直实施到现在,对于保护嫌疑人权益发挥了巨大作用。香港也是这样,香港为什么没有冤案,跟权利保护到位有关。
冤案发生的频率和制度设计水平体现了社会、尤其是政府、执政党对冤案的容忍度
我从无罪推定谈起。无罪推定其实在中国古代就已经作为一种观念形式存在。《尚书》说“与其杀不故,宁失不经”,就是说与其将可能无辜的人判处死刑,不如离经叛道将其放了算了。这说明在中国历史的源头无罪推定是有依据的,有丰厚的文化资源。西方也实行无罪推定。但是最开始起源于一些谚语,比如说布莱克斯通说“宁可错放10个也不错杀1人”,后来有人说“宁可错放20人也不冤枉1人”。有没有说宁可错放1万个也不错杀1人的?有没有说宁可错放100万也不错杀1人?如果宁可错放100万也不冤枉1人,刑事案件就没有冤案,就可以宣传中国大陆没有冤案,因为中国大陆每年刑事案件大约是八九十万件;如果宁可错放100万,就用不着刑事审判了。但是这不可能,任何一个社会除了特别小的像梵蒂冈可以做到这点,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做到。
刑事审判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所有有罪的人都被定罪;一种是所有无罪的都不被冤枉;还有一种情况是大多数有罪的人都被定罪;最后一種情况是大多数无辜的人都不被冤枉。第一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所有有罪的人都定罪那就得把所有的人全部抓起来。有人建议说把15岁以上65岁以下男子全部抓起来大约可以做到所有有罪的人都不被放纵,我看即使这样也未必。第二种情况也不现实,你完全不起诉不定罪大约能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在第三种、第四种之间进行选择,是宁可冤枉更多的无辜者,还是宁可放纵更多的有罪者。制度是选择放纵更多的有罪者(无辜者被冤枉的可能性相应降低),还是选择冤枉更多的无辜者(有罪者逃脱惩罚的可能性相应降低)?我认为我们的制度选择了冤枉更多的无辜者。我们不能容忍一个有罪的人被放纵,所以只好在制度设计的时候选择冤枉更多的无辜者。
我们制度建设能不能到位,体现的是执政党、政府对冤案的容忍度。不是说明知道一个被告人是冤枉的还要冤枉他,事实上办冤假错案的那些人也都是好人。呼格案件的办案警察并不比别人更欠缺正义感,他可能比一般人有更强烈的正义感,他把这个人抓起来也是朴素的正义感,这个人强奸杀人不应该抓吗?而是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有罪者、可能的有罪者被放纵,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可能的无辜者被冤枉。换句话说,我们会在冤枉可能的无辜者和放纵可能的有罪者之间到底选哪个?我想包括中国古代以及上世纪80年代之前,甚至包括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我们一直选择的是宁可冤枉更多无辜者也不放纵更多有罪者。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如果这个观念不解决,说再多也是无用的,接下来要讲的制度建设,也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只有当我们接受了宁可放纵更多的有罪者也不冤枉一个事实上的无辜者,只有我们确立了这样的观念,我觉得接下来的探讨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应该树立一个观念——不能够办一个冤案。怎么才能够做到这点?我觉得应当通过两方面努力。一方面通过制度建设的完善,尽可能从源头杜绝冤案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司法人员努力,全面树立办冤案可耻的观念,每一个案件尽量遵守法定程序,尽量尊重当事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在被告人有罪无罪之间仍然心有疑虑时不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尽一切可能避免办冤案。当然,即使这样做,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避免冤案,但那是我们认识能力和意志因素不能掌控的原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科技发达水平是时代决定的,而制度设计水平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在制度设计方面,要在观念上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当一个被告人事实上可能有罪,也可能是无辜的时候,宁可放纵有罪者,也不要冤枉无辜者。也许案子可能会犯错,但是坚决不能冤枉一个事实上可能是无辜的人,把疑罪从无的观念贯彻到底。
在确立了这样的前提之后,提一些防范冤假错案的建议
这些建议都是有助于防范冤假错案的,也许不一定能够防止所有无辜者不被冤枉。现在还谈不到说通过科技防范冤案,当务之急是制度建设问题。
一是明示的沉默权规则。1979年刑诉法、1996年刑诉法都明文规定,“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要如实回答”,2012年刑诉法已经明文规定不准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是“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的规定,依然放在2012年刑诉法里,这本身是有矛盾的。因为,第50条规定不准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然后第118条又说嫌疑人对侦查人提问要如实回答,而且第50条还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威胁、引诱、连欺骗都不行。如果说他保持沉默能把他怎么样?不能怎么样,连威胁引诱、欺骗都不可以。所以说118条是道德劝说,是没有法律意义的。从法律上讲,真正的义务要有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惩罚性规范,没有惩罚性规范不构成真正的法律规范。
二是赋予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时享有律师在场权。这两年我作为兼职律师做一些法律援助。去年我办理一个案件,被告人1992年被指控故意杀人、放火,1994年终审判决他罪名成立,因为证据不充分判处死缓。证人证言都证明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案发时他在一个地方搞装修,装修工人和公司的几个人都证明案发时他在吃饭,7点以后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以后打麻将,包括吃完饭以后证人证言都说新闻联播时他在场给大家端茶到水,打麻将时也在端茶倒水。证人都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但是判决书里,把这些证人证言都当做他有罪的证据来对待,法官还解释说他有空档,6点吃完饭说不定中间出去20分钟别人没怎么注意呢。所以我去年见被告人,他一见到我们就哭,详细讲述自己被刑讯逼供,拿铁棍打、绳子勒、撞他的头,威胁他说你今天叫“一日游”,还想不想“三日游”“七日游”,看看你能熬到几日游?如果有律师在场,我相信不会有刑讯逼供。上世纪90年代,我们对这样的制度还不敢奢望。但是今天,我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有要求律师在场的权利。
三是对质权。那些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人,应当让他们到法庭上作证,让被告人和指控他犯罪的人当庭对质。南昌中院审判周文斌案,100多个证人就1个证人出席,而且这个证人到庭还翻供了。正是因为连这1个证人到庭都翻供了,所以法院才不愿意传唤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但是不传唤证人到庭作证就属于权益保障不到位。不要害怕证人翻供,翻供了公诉人通过业务知识、业务能力驳斥,向公众证明这个证人翻供是不对的;然后应当举出证据证明为什么证人今天在法庭上说的不对,之前向侦查人员说的是对的。除非公诉人明知证人在法庭上说的是对的,之前在侦查机关说的不对,才不敢让证人出庭作证。只要证人提供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言,被告人对证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这样的证人都要传唤他出庭作证。证人不出庭作证、背后放冷箭,最后被冤枉谁负责任?
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确实没有赋予被告人与不利于己的证人当庭对质的权利。我主张并非所有的证人都必须出庭,只有必要证人需要出庭作证。必要证人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当事人对证人证言真实性有疑问;第二,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影响。只要这两个条件满足就应当出庭作证。可是2012年刑诉法采纳了我前面的建议,基本说法和我的文章文字表述一样,但是它在后面又加一句话,“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出庭作证”。既然这两个条件都满足就应当出庭作证,后面这句话绝对画蛇添足。非要让法院对立法上已經确立为必要证人的证人还拥有是否让他出庭的自由裁量权。这完全没有道理。
最后,是要有更加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们现在只排除根据刑讯逼供获得的直接证据,不排除间接刑讯逼供的证据,这个规则不仅无助于刑讯逼供,而且助长了刑讯逼供。比如说刑讯逼供获得了供述,根据供述获得了杀人武器,再根据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获得了别的供述。这里涉及到二次供述、三次供述是否必须要排除的问题。如果只排除刑讯逼供直接获得的证据,之后再讯问获得的供述都不排除,那这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如果我是侦查人员,我在第一次讯问时候就将嫌疑人打到永远也不敢翻供,打到他一见到我就哆嗦,这样我刑讯一次就能无数次获得他的供述,而不必担心这些供述被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如果实施成这个样子,将不是有助于防止刑讯逼供,而可能会助长刑讯逼供,程度会更加严厉,所以要实行更加严格的证据排除规矩。对于二次供述、三次供述,都应当予以排除。另外,只要是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取得的证据,也都要予以排除。
补充一下,我认为第一,反贪和其他任何犯罪一样,事先预防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民主选举和财产公示;事后打击都是最不得力的办法。明太祖下令官员贪污五两银子就要剥皮实草,自以为从此天下无贪,结果仍然是无官不贪。说明严刑峻法对于肃贪并无实质效果。第二,不是不要事后打击,我也主张严厉打击,但是贪官也是人,对于他们的基本人权,也应当予以保障。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