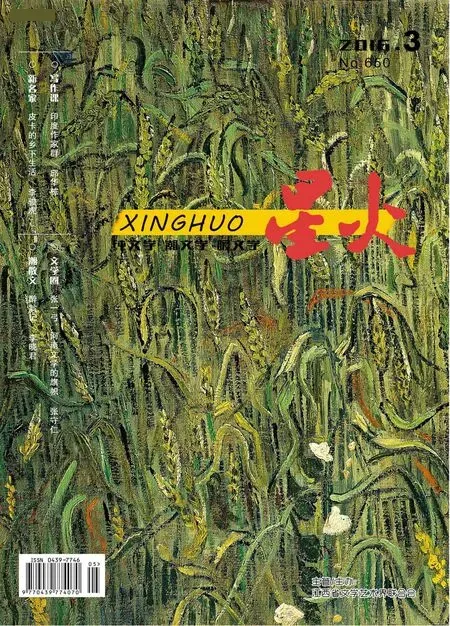与树取暖,老何所依?(创作谈)
文//罗聪明
与树取暖,老何所依?(创作谈)
文//罗聪明
一直想用文字唱赞一下生养过我的乡村。摸着心底的小路返乡,发现乡村需要的已不是赞。
在乡土文学里构造了“乌山”和“野人国”的野莽,从北京的电话那头狠抽我一鞭说,要写就写别人没写过的独一无二,不然没意思!自知没这个本事,只想把脑瓜里腾冲已久常令我站在现实的路口不知所向的炊烟水汽泄放出来。一还是二,明星脸还是大咖秀,不问不求。唯一能把握的是,经我心地走出的这个乡村,即使模样类同别处,却只是我自己的乡村,住着我自己的祖辈父老。
湖南老家的小山冲有个习俗,喜欢在亲人坟前栽一棵树,是给逝者的魂灵纳凉避暑遮风挡雨的。葱绿的坟山,有多少棵树就有多少个魂灵站在那里,鬼怪神灵与山冲的古往今来在树林里深藏。朝着坟山打一望,熟识的邻居与未曾谋面的祖宗都在那里招手。少时上山打柴,累了随意靠靠某棵树,似能感觉地下主人的体温。树,占满了我的乡村记忆。
被一年年“新”过的村庄,路修得树根一样密,楼房比着竹竿往上蹿,确是光亮了,齐整了,便利了,丰裕了。年轻人在奔小康奔富贵的路上忙转,在孝老敬亲的礼数里热闹。山上的树仍在古风里倍加繁盛。而离树越来越近的老年人,他们的舒适快乐,体面与尊严,跟楼房马路无关,跟身上的衣服新旧无关,跟存折上的金额无关,跟饭桌上香的辣的无关。曾被养儿育女的重担挤压到角落的愁苦烦闷,担子一卸就疯长蔓延,扭曲了那些脸、肢体与心肠。这些,却被掩盖,被无视,被认命。我的父辈老了,我的乡村也出了点毛病。
业余时间零打碎敲地写。冗长的会议成最爱,如同拣到一根枯枝,即刻想纵火一把取点暖。心思擦着悄然裂开的地缝就地遁逃潜回乡村,穿过坟山挤密的树,触摸楼房窗口里阿公阿婆们的精神孤寒。偶一,在会议圆满成功的掌声里哗哗泪下。
夫子早有训导,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我的意思,还是这套陈词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