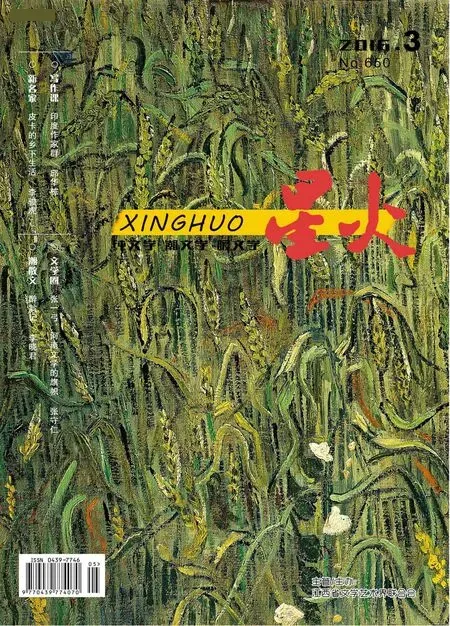奔跑在文学暴雨之路上
——武歆访谈录
访问者:周凡恺(《天津日报》社高级记者,著名作家)
受访者:武歆
奔跑在文学暴雨之路上
——武歆访谈录
访问者:周凡恺(《天津日报》社高级记者,著名作家)
受访者:武歆
周凡恺(以下简称周):现在谈文学或者生活,真有白驹过隙的感觉,转瞬之间,我们都快成老头儿了。有时晚上睡不着,我常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在一起相互鼓励、大做文学梦的那些情景,尤其是坐在南戴河的海边儿,被大雨淋着,谈论的依旧是与文学有关的问题。那时的人多么清纯且有理想。几十年过去,我们应该怎样去评价那段生活以及对我们人生走向所产生的影响?
武歆(以下简称武):我们相识那么多年了,想一想,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坐下来,清茶一杯,面对面地说文学和生活。要是没有《星火》杂志提供的这样一个契机,匆忙的我们大概还不会坐下来聊天吧?我是一个伤感的人,尤其最近几年,泪腺仿佛旺盛的泉眼,稍不小心,就会泪眼涟涟。你也是,只不过你的泪腺不在眼睛里,在心窝子里,很深的地方,像宝贝一样藏着,从不示人。但还是在我这里“露出马脚”,否则你不会把访谈的开端,一下子拉到那么遥远的过去,只有年岁大了并且感伤的人,才会以回忆当作交谈的“导火索”。年轻人不说过去,都畅想未来。我们都五十多岁了,说未来会更加伤感。那就说过去吧。你说的八十年代末,那时候我刚调去天津作家协会,准确时间应该是一九八八年的三月份,正是北方乍暖还寒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穿着一件高领红毛衣,在我至今五十三年的时光中,我只有那么一件红毛衣,以后再也没穿过。我不喜欢热烈、鲜艳的颜色,可能跟内心伤感有关。进入作协后,我先在办公室做出纳,接着很快去新成立的文学院搞函授教学,跨度大吧?八十年代是文学的年代,人们无论什么职业,都向往文学。当然,我在文学院也没有耽误本行,同时兼任会计、出纳的工作,文学院成立了好几个实体,好几个账号、好几本帐,都是我一个人忙碌。另外,我还和另一个女同事编辑一本内部刊物,虽说是双月刊,但也要编稿、校对,所有的办刊过程都有呀,当时我年轻,又是小伙子,所以干劲儿冲天,连刊物的版式都画。哦,还要跑印刷厂,出刊后还到邮局寄送,我曾经一个人把三千多本刊物从办公室搬下来、装上车,送到邮局后再卸下车。有时候还要给邮局工人帮忙,帮助盖邮戳、装袋子,现在想来,哪来的干劲儿?就是因为做的工作与文学有关。只要跟文学沾边,上刀山、下火海都成!那时下班后,我还要坚持写作。当时我刚结婚,孩子小,多少年以后妻子跟我讲,那些年她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夜晚台灯下写作的背影,孩子晚上哭了、尿了,都不会影响我的写作,说起来也够狠心的,妻子一个人那么忙乎,我连头都不回,继续趴在那儿写作。是呀,那时候觉得天下最大的事情就是文学、就是创作,做任何别的事都没有意义,都是在浪费时间。后来改革开放,许多人“下海”做生意,对我来讲,最向往的事还是读书、写作。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生活,一点儿都不后悔,相反充满了回忆的甜蜜。我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我是懦弱的人,生活能力极差,也不自信,甚至还很自卑,要是没有“文学”这把镇尺,我早就向生活缴械投降了,“稀里哗啦”的早就变成了一地的碎骨头,还得麻烦大家打扫。文学就像看不见的钢筋骨架一样,支撑起了我单薄的身体,重新锻造了我脆弱的神经,让我拥有了生活的热情。我这样讲,可能现在的“80后”、“90后”不理解,显得比较矫情,显得比较“大条”,可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讲,就是这样的情况,没有丝毫的夸张。我想念八十年代的“文学大雨”,将我们浇了个透,从外到里,幸福无比,至今难忘。南戴河的大海可以作证。
周:你的文学之梦是从天津的工厂里开始的,我的艺术之路则起步于长白山大森林,所处的环境虽截然不同,但对艺术的领悟或感知却有共通之处。我读过你几乎所有的作品,包括“延安、北京、天津、重庆”几大“爱情”长篇,但最喜欢的,还是你写工厂的那些中篇和短篇,我认为与其他工业题材的作品有所不同,似乎更加得心应手,更加充满感人的魅力。为什么?
武:看过你那么多的画儿,现在想起来,最喜欢你画东北长白山的作品。我想,每个人都有出生地,写在户口本上的。写小说、画画儿一样,也有出生地,只不过称作“艺术出生地”。一个人的“艺术出生地”,决定了他未来的艺术之路,注定了艺术血型,有可能亘古不变。“艺术出生地”往往充满着泪水和惆怅,我相识的大多数作家,其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没有一个内心充满幸福感的。自信心爆棚的人,大概不适合当作家。我的“小说出发地”来源于一九八○年的高考。落榜后的我进入一家国营大厂当工人,干的是铆工,天天抡大锤,又脏又累。我那时脸皮儿白,走在车间里,穿件破棉袄,像个蹩脚的乞丐,我师傅望着我,总是唉声叹气,说我命不好,应该进科室当干部。我在工厂度过了八年的青春时光。我是在高考落榜那一年开始小说创作的。那时,我每天下班后都去一家区级图书馆看文学杂志,只看头条,记下地址和编辑名字,然后回家去投稿。那会儿我最大的理想就是离开工厂,我不想当工人,想当作家,还要当不上班的专业作家。我经常请事假,回家写小说,而且跟组长讲明了,所有的奖励我都不要,只要能给我时间就成。说起来不好意思,想要离开工厂的原因,除了热爱文学要当作家之外,还因为三次爱情受挫和一次人格受辱。记得有一年,有人给我连续介绍对象,一个是画家的女儿,一个是“少管所”的警察,最后一个是大企业的“厂办”秘书。三个女孩都亭亭玉立,长得好看,家庭出身也好,自身又都是干部,她们每一根迎风飘扬的发丝都是骄傲的……最后她们都向我告辞了,在半年之中,我先后被这三个姑娘抛弃了,她们的铮铮爱情誓言,全都随风而逝,她们告别时,都没有和我见面,只跟介绍人讲,最近工作很忙,没时间见面了。那时姑娘们很含蓄,不像现在女孩子,直接标明择偶条件。其实说来简单,事后介绍人告诉我,她们对我本人没有任何意见,就是因为我的“工人”身份。再说那次人格受辱。我们工厂四千多人,那年要从年轻人中间招十名会计,所有适龄青年都可以报名,然后参加集体考试。当时我上“夜大”,学的是财务会计专业,所以立即应聘,在几十名考生中,我考了第六名,应该没问题。党办、厂办和劳资处的干部们组成面试考官,东拉西扯,看看本人的情况和基本素质。其中有人问我,业余爱好是什么?我说,读书、写小说。问我读什么书?我说了《红与黑》和《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个黄眼珠子的“党办”领导,勃然大怒,竟然拍了桌子,问我为什么不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竟然看黄色小说?随后对我进行了暴风骤雨般地“教育”,并且撂下一句话,像我这样看黄色小说的人,将来不会有好下场的,一辈子都当不了干部。我吓坏了,委屈得差点当场哭出来。事后我理所当然不被录取。再后来又因为熬夜写小说,导致上班打瞌睡,当着全车间四百多人的面,被车间主任罚站、批判。我知道我再也当不了干部了,尽管后来我在全厂演讲中,自己的稿子、自己演讲,影响广泛,得了百人演讲的第二名,厂工会主席特别欣赏,点名要我当脱产工会干部,可是车间主任不放我,说我不务正业,整天写小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干部呢?这些经历都是我“小说出发地”的“美妙景观”。你说我的“工厂小说”有特点,都是因为这些“屈辱”。现在想来,这些所谓的“屈辱”很可笑,可在当时确像大山一样压着我。所以我写工厂、工人的小说,里面始终有着隐忍的东西,有青春的仇恨,有内心的发泄,但是这些仇恨和发泄不在表面,都在文字深处,在每一个文字的背后,每个文字的后面都有着层层包裹的血泡,只要稍微用力,就会捅破了,就会鲜血飞溅。那些血泡都是人生体验。

诺言-武歆作品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陕北红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

树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延安爱情,作家出版社2010年

重庆爱情,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
周:几年前,你跟我说要读些书了。我觉得作家的阅读,不能局限于文学艺术类,越杂越好,由高古而到前沿,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的“思想发动机”,或者说建立一个“思想的培养基和温床”。
武:说到读书,我感慨很多。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整整十年,完全放弃了小说创作,写散文,写随笔,写专栏。那十年,我在放弃小说创作的同时,几乎放弃了读书,当然所谓的放弃,只是相对而言,也不是一本书不读,只是读得很少、很少。现在想来,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说到这一点,我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现在定居英国伦敦、当年的“朦胧派”诗人杨炼。记得七年前,杨炼回国,我们在天津一起吃饭、聊天,他跟我说起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说起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说起那么多的外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眉飞色舞的杨炼,看着我漠然的脸,立刻换了话题。那次交谈,给我冲击力很大,我下定决心,沉下心来,要好好的认真地读些书了。套用美国作家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来比喻,读书也要永远“在路上”,绝不能停歇。最近这些年,我每年都会读上十几本经典之作,受益匪浅。二○一四年的岁末,《小说月报》的执行主编徐晨亮告诉我,他们想在《小说月报》刊登三十五位作家的“2014年作家阅读书目”,被邀请的作家,每人向读者推荐三至五本书,我应允推荐后,立刻整理自己这一年的读书篇目,发现竟有十几本之多,许多书读完后,我还写了读书笔记。你说读书的种类越杂越好,我同意,但还是要有选择的,还是要读经典的,不管哪类书,都要选择经典。所谓经典,都是经过岁月的淘洗,经过几代人检验的作品才成经典的。读书的收获是潜移默化的,就像种庄稼积肥一样,用你的话说,就是“思想的温床”,书籍就是“床”。但也有人跟我说过,读书是用别人的马蹄践踏自己的疆域,并且给我讲了不少不读经典、照样写出好作品的实例。我觉得这种观点有些牵强,还是要读书的,不仅写作者要读书,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是要读书的。我尊崇大多数人的观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留着以后再说吧,反正关于读书的话题,永远说不完。
周:我是主张作家们要学学绘画、书法、音乐等,古人讲“琴棋书画”,这是一种修为,不图有成就,但求自身艺术素养的提升。不知你还记得否,那年我们作家代表团去韩国,在南怡岛,多么美丽的夜晚,韩国人备好了笔墨纸砚,想让大家一展身手,可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作家,一不会做律诗,二不会写书法,签个名字都歪歪扭扭,只得草草收场,丢人丢大了!
武:那个场景我记得,只是羞于提起。我在你的影响下,也想练练字,去年炎炎夏日,流着大汗,买了纸墨笔砚,还买了刻刀和石料,结果只操练了几天,便鸣锣收兵了。写字画画儿,需要心态,可能我现在心态不在这上面,或是没有书法和绘画的细胞吧,总之坚持不下来。但是听音乐还是不错的,我那天偶然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大提琴协奏曲和弦乐四重奏,一下子就迷上了,感觉就像与一位智者谈心,或是抒发自己内心的苦楚。这位一生都在等待枪毙的作曲家,在生命的惊悚中完成了那么多充满想象力的感人的音乐作品,尤其是在夜晚写作时,听着他的音乐,在他忧伤沉郁的旋律中,仿佛看到了阴霾天空中的微弱亮光。肖斯塔科维奇有一句名言,我的音乐就是我的墓碑。我记得特别清楚,永远忘不了。我想,听听音乐,也是在心里绘画吧。
周:有时我给你打电话,问问你的近况,说实在的,我是怕你坚持不了。为何要这样说呢?我知道你是一个孝子。有一次你跟我谈起,九十多岁患病的父亲,认为晚年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你抱着老爹说,你只给我添了几年的麻烦,我可是给您添了一辈子麻烦呢!当时,我泪如雨下。我一直在想,一个人无论做什么,有没有成就,首先他应该是儿子、父亲、丈夫,连这一点都做不好,妄谈其它,就是瞎胡扯了。孙犁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他生前曾跟我说过,一个作家,第一是做人,其后才是作文。我一直坚信他说过的那些话,比如:莺歌远去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旧是莺歌,彩云流逝了,留在记忆里的也仍旧是彩云!
武:我父亲是去年八月份去世的,九十五岁。我写了一万多字的怀念父亲的文章,给了宁夏的郭文斌先生,给了他十天,郭文斌先生就回信定下了,很快发表在他主编的去年第十期的《黄河文学》上。我父母年岁很大,母亲至今健在,已经九十岁了,患阿尔茨海默症,不认识人,一身的病,每天要吃大把的药,还要打胰岛素,做过好几次大手术,死里逃生好几回。早些年,我长期住在父母家,一个礼拜要住四天,买菜、做饭。父亲脾气倔,死活不雇保姆,后来我实在顶不住了,父亲才答应雇了保姆。你总是说我孝顺,其实许多时候,我不是一个孝顺的人,爱着急,有时也跟父母吵架,急得我用手捶墙,那样子你都想象不出来,可是每次吵架回来,当天晚上就后悔。父亲教给了我许多的人生哲理,他是一个坚定的人,但他又是一个怕死的人,总是跟我讲,“那边”啥样子?人怎么还得死呀?后来心绞痛折磨得他不行了,整夜坐着,洗脸、漱口,只要一有动作,就得吃硝酸甘油片,一次最少要吃四片,最后有一天他跟我讲,他不想活了,想死。父亲不想死在家里,要死在医院,想法很简单,担心死在家里,对我母亲影响不好。我父母吵吵闹闹,别扭了一辈子,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和蔼地坐在一起说会儿话,可是父亲还是惦记着母亲,这就是那代人的爱情和婚姻。父亲走的那天晚上,保姆打来电话,说老爷子不行了,我赶去后,叫来救护车,把父亲送去医院。父亲这口气一直憋着,直到救护车停在急救室门口,父亲这口气才断了。父亲死在我怀里。那天晚上下大雨,趁着短暂雨歇,我和妻子趟着没过脚踝的积水,把父亲的遗体推进了太平间。我在那篇文章里说,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推着父亲遗体前往太平间的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死亡时间的人,是不是坚定的人?要想理解自己,先要理解父母。我至今还没有完全理解他们,慢慢来吧。孙犁先生讲的话,我特别赞同,我从内心里尊敬那些人品好、作品又好的作家,从心底尊敬。那些总是昂着头、总是自以为是、总是认为自己高于别人的家伙,我的处事原则就是,不争不吵,掉头就走,让他们自恋去吧。
周:前几年,还有人跟我谈知识分子的良心,现在已经没人再谈了。但社会毕竟需要头脑清醒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他们存在的意义。作家应该抒写有温暖的作品,现在社会上呈现“后宫风格”,到处都是争斗,外人之间争斗,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也争斗,存在一种要把旁人置于死地的阴暗心理,有些文艺作品更是对此推波助澜。作家如何面对这样的社会氛围,如何把握自己的写作立场,如何抒写自己的作品?
武:知识分子的良心,这是一个永远在谈论的话题,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话题。当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解读。但无论怎样的解读,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知识分子的良心,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社会精英这个阶层。这个阶层人不多,但却是社会的脊骨。知识分子的良心,首先来源于知识分子思想的独立性。而所谓的独立性,必须要有自己的思考,前瞻的思考,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能人云亦云,不能随波逐流,而且要有担当的勇气和责任。前一段儿社会上讲,真正的知识分子太少了,还有吗?也就是“识字分子”,比老百姓多认识几个字罢了。这话说得尖锐,但也很实际。确实如此,现在让人感动的有风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当年的“五四运动”,走在时代前沿的是知识分子,他们勇敢地呐喊,不怕杀头,不怕流血,捍卫正义。可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下真是少之又少。关于这个话题,说到多深,都不会终结,而且永远在探讨。还是回到抒写温暖的文学作品这个话题吧,抒写温暖,需要拥有温暖的内心立场,要有冲破阶层的悲悯之心。说到温暖,可能就会说到关于“审美”的话题。当然文学不仅存在“审美”,也存在“审丑”,但是文学的“审丑”,也是“审美”的一部分,并非简单地展示丑恶。鲁迅先生说过一句名言,原话我忘记了,大意是“我们要拷问出来洁白下面的龌龊,还要拷问出来龌龊下面的真正的洁白”。我想,这似乎就是对“审丑”的最好注解。单纯揭露所谓的黑暗,抒写人性的恶,并不完全是文学的使命。去年去世的获得一九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戈迪默,写了许多抨击种族隔离制度的文学作品,但是她的抨击并不是一味的咒骂,一味的哀叹,一味的哭泣,而是抒写人性之美,抒写种族、肤色之上的人的尊严。她一直生活在南非,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没有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之前的南非生活,身处那样一个严酷的社会环境中,却写了许多优美的童话作品。她获得“诺奖”后,面对采访的记者,她说那些获奖的作品,是写给大人们看的。我想,戈迪默的内心肯定是温暖的,她更注重人心深处最柔软的那部分。我们这样讲,不是说让作家逃离现实,而是要站在人性的高度,要拥有宽广的胸怀,要走出狭隘的世界,不是一味地抒写黑暗。去年南非作家代表团来到天津,在与南非作家交谈时,无论黑人作家还是白人作家,他们总是说起戈迪默,他们的目光充满敬仰、尊崇。我想,戈迪默的写作立场,是对作家如何面对社会氛围、如何把握写作立场和如何抒写作品的最好诠释,也是作家最好的榜样。其实拥有这样写作立场的作家还有很多,特别是美国当代作家,比如菲利普·罗斯,还有唐·德里罗等等,美国作家其实最充满正能量,他们面对黑暗时,常常看到了光亮。抒写黑暗,但是黑暗的后面,紧紧相伴着希望。
周:我真的希望,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自由的。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陈述自己的主张,构建一个没有恐怖袭击、没有宗教冲突、没有仇恨的和谐世界。
武:你所描绘的那种画面,是那样的美好,是所有人所向往的。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依旧存在仇恨、袭击、恐惧,但是无所谓,这些东西肯定不是社会的全部,就像昨天还是雾霾,今天不就是阳光灿烂吗?你看,天空多么明净。要不,我们不喝茶了,出去走一走,如何?在蓝色天空下说会儿话,继续着我们的话题,我想那会更加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