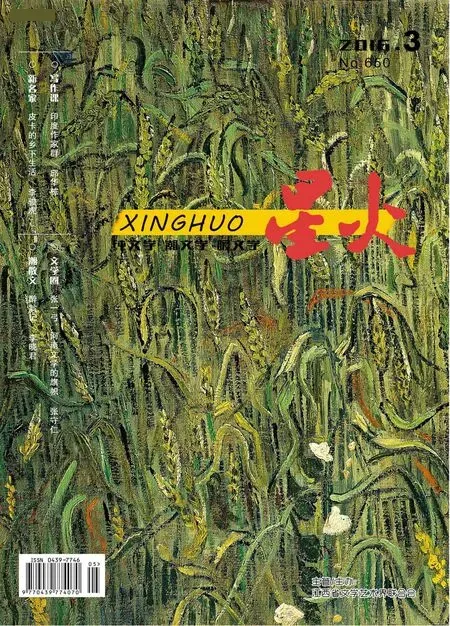湖上鼓手
文//文非
湖上鼓手
文//文非
文非,江西进贤人。做过期刊记者、编辑,现为上市公司职员。二○一○年正式开始写小说,偶有小说发表。

出校门往东去七八里就是鹿儿湖,鹿儿村灰白的房子像落了霜的牛粪散落在湖边。
经过多年的开发,鹿儿湖已彻底变了样,湖边酒肆商铺林立,原本清新的鹿儿湖边终日弥漫了一股市井烟尘。卖荸荠的、摇棉花糖的、兜售纪念品的商贩往来不绝,这些商贩大多是附近像鹿儿村这样的村民,他们被禁下湖捕鱼,上岸做起了小买卖。湖面上,三三两两的花船、梭子(两头尖细的船)、竹排在落霞粼粼的湖上穿梭往来,热闹得很。人们兴致盎然,在船上喝茶下棋观景。相对而言,漾在堤边快艇的生意就要冷清许多,好不容易等来顾主,早已疲乏的船老板铆足了劲,犁开水面贴着花船狂飙而过,水花四溅,像戏谑更像是发泄不满,惹得花船上的人泼了茶乱了棋而高声喊叫。
远处岸边,一阵激越的锣鼓声传来。
咣咣咣,咚咚咚——
咣咚咣咚咣咣咚——
循声望去,蟹黄色的湖面,一个着黄袍戴面具四肢短促的小丑站在梭子上正在为即将开始的耍鼓做最后的准备。小丑腰别两枚小红鼓,一件短袍几乎罩了整个身子。那面具也甚是滑稽,卓别林式的胡子,弥勒佛般的笑,脸颊两团胭红,铜铃眼,八字眉。正打量,他已纵身跃到水面的浮鼓上,借助梭子上跛脚汉子伸出去的竹篙,脚蹬鼓背,和着跛脚“镗镗”的锣声摇摇晃晃走了起来——锣声愈紧迫,脚下的红鼓转动得愈快。几分钟后,小丑掌握了平衡,双手稳稳当当离开了竹篙开始轮番敲击小鼓——脚下大鼓翻转,腰间小鼓咚咚——岸边和近处花船上爆发出阵阵喝彩声。声音未落,小丑却又借竹篙纵身跳到了水面一只比圆桌还大的红鼓上,和着愈加激扬的锣鼓,小丑变脸成了矮个孙大圣,手持竹篙抓耳挠腮,在鼓面上击鼓翻腾,金色的水波从红鼓的四周一圈圈荡漾开去……。我看得呆了,不禁近前鼓起掌来。小丑看上去更得劲了,一别脸又成了一个笑容可掬的短脚老太,捏着蒲扇在鼓沿扭捏走了几圈,随后撅起屁股冷不丁掀起短袍,半拉子不白不黑的屁股露了出来。游客稀里哗啦笑倒一片。小丑回头朝岸上望了望,脚下的动作刹那失去了连贯性,一个趔趄仰面从鼓面跌落水中。随着人群发出一阵惊呼,我的心也“咯噔”提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表演的一部分,眼见小丑趁势抓住跛脚伸过来的竹篙脚一搭翻身上了船。
游客渐散,我沿着鹿儿湖快步向鹿儿村走去。
背山面湖的鹿儿村,这里三间那里五家,高高低低随山就势。房舍全部被粉刷成灰白两色,倒有几分醒目。我向几位散着手在墙影下闲聊的老人打听马小陶,老人琢磨了半天说你找的是晃球家吧,然后往山腰间一处矮房点了点。
我不知马小陶为何又叫晃球,马小陶个头矮小但并不胖,不至于用“球”来形容。据我所知,学生们私下给马小陶取了不少外号,睡虫、机器猫、两段……但晃球还从未听闻。也是因为这些外号,马小陶愈加变得孤僻,还是因为外号,马小陶才和武大脑动了手,这可是件不寻常的事。“两段”竟然敢动武大脑,纯粹是自取其辱。“两段”是武大脑送给马小陶的外号,武大脑煞有介事说正常人都有脑袋、身子和下肢三段,就像写作文的三段式,开头中间和结尾,一样都不可缺,但马小陶偏不是,总像是少了那么一段,具体哪一段也不好说。总之,马小陶是他父母仓促间弄成的一篇并不成功的文章,是半成品,是机器猫。武大脑说完这番话后,为自己的想象力很是得意。马小陶用袖子擦了擦布满眼眵的脸,迷瞪瞪地望了望众人,两眼一闭趴桌上又呼呼睡去。等着起哄的同学倍觉无趣,看来马小陶这颗大脑袋已经彻底沦为武大脑的尿壶了。
在我的印象里,马小陶是一个骨头缝里都爬满睡虫的矮小子,偏执甚至有些憨呆,坐在教室最后排,总是一副低头塌眼恍恍惚惚的样子,只要停下来眼皮子就掐上了。一个月前的音乐课上,我被马小陶无所顾忌的鼾声和武大脑放肆的笑声彻底激怒。课后我把他们留了下来,罚他们每人抄写二十遍五线谱。离开教室后,我也就把这事给忘了。傍晚,有学生跑来说武大脑和马小陶打了起来,起因还是武大脑的“两段”说。我赶到教室,实际情况和我预想的情景有些偏差:两人抵在墙角,马小陶犹如猴子一般吊在武大脑背上,两手从后死死箍住武大脑,可怜平日骄横的武大脑竟被箍得面红耳赤,动弹不得。那副模样,令人忍俊不禁。我沉下脸喝令他们立即让家长来学校。
马小陶紧张了。武大脑意味深长地笑说等你的“媳妇姐”(据说是他父亲捡养的,预备着给他做媳妇。有点可笑,也不知真假)来救你吧。马小陶被激成了疯牛犊,兜头撞了过去。我怒不可遏顺势给了马小陶一脚。马小陶猝不及防扑倒在地,爬起来时啐出一颗血牙。我自知失手,挥手说滚吧滚吧。马小陶强忍泪水瞪了武大脑一眼,恨恨而去。
好几个礼拜的音乐课,马小陶的座位都空着,听说已经辍学了。为发泄不满,马小陶用小刀在他无数次酣睡过的课桌上留下了“绝笔”:我不是两段,我不是小丑、机器猫,总有一天我会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高大!!马小陶的委屈和愤怒令我不是滋味,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偏袒了武大脑,谁让他的爷爷是老校长呢。
风波过后,从班主任口中我无意得知马小陶的父亲意识尽失常年卧床,一直由马小陶和他的“媳妇姐”日夜照顾。我顿感讶异,明白了马小陶上课为何总是输给了两片眼皮子。
马家低矮的房屋建在山腰上,白墙灰瓦。我站在坡上四下逡巡,并没有发现有人。进了院门透过空窗才见一个肤色白皙身形清秀的女孩正在为躺在床上的中年男人擦身,女孩的脸被垂下来的一绺黑发遮挡,看不清楚面目——想必是马小陶的姐姐马芳和他的父亲。马小陶的父亲几近皮包骨头,嘴硬硬地斜张着,凹陷的双眼空洞地望向空无一物的墙壁。马芳似乎并不避讳,低头利索地褪下父亲空荡的裤子,赫然露出胯间耷拉着的物件。一股尿骚及陈腐混合的异味随即从屋内飘了出来。这股气味我太熟悉了,马小陶身上就散发着这种特殊的气味。没人愿意和他同桌,他也没什么要好的朋友。我将提来的盒饼放在窗台上,正欲张口,马芳却端了一盆擦澡水出了房间,我抬脚向大门迎了过去。
“我找马小陶……你是他姐马芳吧?”
“高老师?”马芳冷着脸,上下打量我。
我扶了扶眼镜,笑笑说:“……他有些日子没去学校上课了。”
话才落,那盆脏水“哗啦”应声泼下,泥点子溅了我一腿。
“与你何干,你走。”马芳说完扭身回屋,“哐当”一声把大门给关上。
我愕然呆立,刚刚生发的一丝感动和怜悯荡然无存。转身欲离开,门却又打开了,“东西拿走。”说着一包塑料袋“哗啦啦”飞了出来。我拎起地上的盒饼,气冲冲地出了院门,差点和进门的人撞了满怀——马小陶的母亲回来了,像是出了远门,挎着一只蓝碎花的包袱。马芳叫了一声“娘”便飞奔了过来。
马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看我,又看了看马芳。
马芳白了我一眼,解开包袱,一堆蓬乱的干草药露了出来。
“我是学校老师,来找马小陶。”
马母把我让进屋,掉脸问马芳:“他人呢,又去湖边耍鼓了?”
“拦都拦不住,偏要去。”马芳提出一个黑乎乎的鼎锅,开始往里面放草药。
“耍鼓?”我惊讶地叫起来,想起刚刚在湖边遇到的那个小丑,那敏捷滑稽的表演和往日无精打采的马小陶判若两人。看不出来,马小陶还会这一手。
隔壁屋内马父响起急促的“咕咕”声,马芳丢下鼎锅跑进了屋。我朝屋内迅速瞟了一眼,看不清马小陶父亲的脸,一双枯瘦泛黄的长脚板,却也是老茧厚重的皴裂。
“耍鼓回来喝了点酒,摔成这样,好多年了。”马母叹气,“他倒好,睁眼不管事,一大家子。”
我嗫嚅着不知该说些什么,马家的情况出人意料。
“这两天痰却是多了。”马芳声音里透出担忧。
“鱼汤喝着么?”
“一直没断哇。”
……
我局促地站在门外,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下来。
一直等到天黑,马小陶才回来。先是听见村路人语响,举目细看,并未见人。近前了,进了院门,才看清马小陶夹在鼓间矮瘦的身影,腰带上还用柳枝栓了几尾闪着白光的鱼,坠得本就显长的裤脚臃塞在脚跟。我上前帮助他把背上的鼓卸下,有一只小鼓骨碌碌滚落,马小陶躬身趋前捉了回来,然后叠放在大鼓上。马芳接过鱼,瞟了我一眼,冲马小陶努努嘴,然后矮身钻进了厨房。马小陶一径向檐下的水缸走去,舀了一瓢水坐着喝了一气。我在他身边蹲下。月朗星稀,清冷的虫声在夜色中浮泛而起。
“是不是不想见老师?”
“我在鼓上看见了你哩。”
“所以才落水?”
马小陶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
“不回学校?……上次的事情是老师不对。”
“他们欺负人。说我是小丑、两段。”
“你说的是武大脑?”
“还有贺桂、陈松、刘俊志……我不想念了,我已经答应了蒋瘤开始耍鼓,但比和爹在一起时少拿三成。”
“蒋瘤是谁?”
“湖上的老板,可有钱哩,湖上的花船多半是他家的。”
我们没有再说话,马小陶的瓢中,月亮在云层穿行,仲夏夜清凉的晚风把阵阵鱼香送了过来。马小陶响亮地噏了噏鼻子,低头继续喝水,瓢中的月亮顿然漾开散尽。搁下瓢,马小陶靠着墙壁塌了眼坐着。
“你看上去很睏。”
“停下来就这样。得干些什么。”
右手侧的厨房里,一灯如豆,马芳母女窃窃的私语和被压抑的轻细的声响,在静谧幽暗的夜晚显得格外幽沉。我正欲起身告辞,马小陶却提起墙角的小红鼓钻进了父亲的房间。月下,马小陶浓重的大脑袋在墙壁上晃动——其实马小陶的脑袋并不大,和武大脑比起来相形见绌,只是他愈发短粗的身子使他的脑袋看起来特别大——最终定格在墙壁某处,片刻,鼓声响起,轻柔温婉,但床上的马父依然无知无觉,空张着嘴,目光僵直。
离开马家前,我悄悄用面具将三百元钱压在窗台上,然后乘着稀朗的月色向湖边走去。身后的鼓声,慢慢趋于激扬,被温热的夜风送出去很远很远。
几天后的一个晌午,我正在宿舍调琴,马小陶捏着那三百元钱来找我,半颗大脑袋在窗户上刚升起来便又沉了下去。我搁下琴出了门,马小陶拎着柳条串着的几条鱼躲在门外。几天不见,马小陶更黑了,颈脖处露出一圈明显的细白。
马小陶塞回来的三张票子已被汗水濡湿,我进屋拿出一个鼓鼓的信封,连同那三百元递给马小陶。
“虽然不多,但是大家的一片心意……同学们等你回来。”
马小陶没有接,低声说。
“马芳让我向你道歉,那天不该那样……对你。”
“马芳是谁?”
我觉得很有意思,打趣地问。
马小陶低了头,羞涩地笑。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怪异,那个蛮横无理令我难堪的马芳,现在想起来竟然没那么可气。我琢磨不透,在马小陶的眼里,马芳是“姐姐”多一点,还是“媳妇”多一点呢?这也许是个无聊甚至有点邪恶的问题,但我忍不住自己的好奇。
“这也是她让你送的?”我瞅着鱼问。
马小陶点点头,又摇摇头,迅即把鱼挂在门把上,哧溜转身跑远了。我喊了几嗓子,五月的阳光下,马小陶黑瘦的身影已跑过长廊,越过操场,在校门拐角处一闪便消失了。
马小陶终究还是没有返校,倒是经常有一两条活蹦乱跳的鱼挂在我的门把上。剖开鱼,总能发现鱼肚子里马小陶写给我的纸条。这些巴掌大卷好的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三言两语歪歪扭扭,多半是他父亲的病情和耍鼓抓鱼的趣事。我被马小陶的描绘所吸引,只要有空,我就会去湖边看马小陶耍鼓。偶尔,持篙敲锣的跛脚忙不过来,我便自告奋勇顶了上去。你是知道的,我一介书生,在狭长的梭子上站都站不稳,那伸出的惊慌失措的竹篙自然毫无力量。马小陶也只是象征性地抓住我的竹篙,奋力翻腾,好多次有惊无险。敲锣我自然在行,和着马小陶的鼓点,敲得风生水起。
一场鼓耍毕,马小陶摘下面具脱掉衣服一个猛子跃入水中,水面绽起簇簇浪花,旋即复归平静。我坐在船上,静候马小陶出水。可过去了两三分钟,水面不见动静,我双手卷筒扯嗓子呼喊,空旷的湖面水光潋滟,无声无息。惊慌间,身后砉然水响,马小陶高举着两条鲶鱼冲出水面。我长舒了一口气,手忙脚乱按住被抛进梭子的鱼。
“谁教你的?”
“我爹,他可能了,早先我耍鼓,他就潜在水下稳住。”马小陶有些得意。
“他会徒手抓鱼么?”
“咦,从不落空,嘴里还咬一条哩。”
“也会杀牛做鼓?”
“嗯,力气可大……可现在他什么都干不了,我都在他床前敲了两年,以前他听到这鼓声就会来劲。”
马小陶耷拉下脸,看上去有些沮丧。
“会醒来的。”我用手摸了摸马小陶湿漉漉的头,“他是好男人,好男人怎么会舍弃一家子呢。”
马小陶眼泪汪汪仰起头,将套在头上的面具扯下戴好,给了我一个夸张搞怪的笑脸。
岸上已经聚拢了一群游客,跛脚在高声催促。
临近中午,马芳提篮子给我们送来了午饭,马小陶将大鼓系在水下面的暗桩上,然后收拾好家什向岸边摇去。满身酸汗钻进树下,马小陶四仰八叉躺在草席上,看上去累得很,耍鼓毕竟是高强度体力活。马芳从鼎锅里给我们每人舀了一碗绿豆汤,然后把满满两碗饭搁在我们面前。
“晚上给你们烧酸菜鱼,高老师一定要去。”
“可不敢,别泼我一身酸水。”我揶揄道。
马芳满脸绯红,嗔怒道:“能不提这出么,你怎么不记得人家的好哇?”
我一时语塞,找不到合适的话,只得埋头往嘴里扒饭,扒到一半,两个滑溜的鸡蛋露了出来。我觑了一眼马小陶碗里,头埋得更低了。
吃完饭扯了一会儿闲话,马芳哼着歌去湖边洗碗。我目送着马芳清秀的身影穿过树林弯弯绕绕向湖边走去,然后消失在湖堤后面。远处刚刚离岸的快艇风驰电掣驶了过来,船上的人挥手打着尖锐的唿哨。马芳站了起来,咯咯笑地也朝快艇舞动着手臂,银铃般的笑声如波光洒满了水面。我暗自唏嘘,真是个不简单的女孩,生活的重压和愁苦并未泯灭她那蓬勃的朝气。我扭过头,马小陶已经靠着树打起了盹,花花搭搭的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落在他身上。我起身将马小陶慢慢放倒在篾席上,然后挨着他躺下。……我怎么会睡得那么沉呢,连马小陶和马芳什么时候离开的都不知道。远处湖面上,马小陶的表演就要开始了,马芳坐在梭子上,举着槌拼命向我挥手。
有一段时间,我带领校合唱团去市里参加比赛,回来时,门栓上挂了好几条已干瘪的鱼,我剖开鱼肚取出了几张纸条,字迹已漫漶,没有注明时间,也无法判断出其先后顺序。
高老师:
今天很难过,娘冲爹又发火,马芳也和娘吵了起来。娘总是这样,动不动发火。娘说爹就是一块叫不醒焐不热的石头。我知道娘并不是真的嫌弃爹,她只是心里难过。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这块石头叫醒呢。
纸条字迹较为潦草,还有一张字迹较为端正的大纸条引起我的注意。高老师:
今天,有个戴墨镜的人在湖边找到我,说是遥远的兔儿岛的主人。岛上有游乐场,有五彩的水母,会飞的鱼和会捕捉昆虫的树叶,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像我现在一样和游客逗乐。他开出了高于蒋老板三倍的钱要我跟他走。三倍的钱是我想要的,我们需要钱,很多钱,可我不愿意离开爹娘离开马芳。还有,我离开后,谁来为爹敲鼓呢?高老师,你能帮我出出主意吗?
最后一行字特意加粗加大,甚至将纸条划破。我撂下纸条,在愈来愈暗淡的残阳中匆匆向鹿儿村走去。湖边终日漂浮在水上的大鼓不见了,远处,悬于湖面的太阳“哐当”一声坠入湖底,砸得湖水一漾一漾地冲刷着堤岸。我心里跟着陡然一紧,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在快接近鹿儿村时,一阵隐约的鼓声传来,那是我所熟悉的节奏。我收住了脚步,在一棵树下长时间凝望着山腰上那一点豆黄的灯光。
鼓声渐息,我在习习的夜风中转身往回走。
闷热的夏季很快就过去了,湖面上吹来的风有了点点凉意。
从夏天走到秋天,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马小陶依然每天去湖边耍鼓,马父的病也未见好转,马芳依然里里外外操持家务照料父亲。这期间,我托朋友请来一个权威的神经内科专家来马家走了一趟,专家并没有给出令人鼓舞的结论。“不排除会有奇迹发生。”专家拿起马小陶的红鼓,勾起指头敲了敲,最后丢下这句模棱两可的话。
从夏天走到秋天,也有一些内心的东西在悄然改变——我和马芳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马芳并不是很漂亮,但神态里有一种沉静的东西吸引我。我不知道事情会这样,竟对一个初中尚未肄业的女孩动了心,说出来会被那些油滑的老师笑死,他们曾经热心地给我撮合过镇上条件优越的女孩,他们甚至怂恿老校长的胖女儿向我献媚。我也不知道马芳内心的真实想法,现在的事实是,她已经不叫我高老师了,她碰到我的目光就脸红。还有,她总是刻意地躲着我,我知道她不是不想见我,而是在避免某种尴尬。显然,马家糟糕的现状并不允许我们做出任何不合时宜的举动,我们似乎都在回避。马家我自然去得少了,但适得其反,越是不见越想见。这对一个单身寂寞的乡村老师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
在犹豫和不安中,我小心翼翼地向马芳伸出那敏感脆弱的触须。
鹿儿湖成了我们约会的绝佳地点,我们悄悄荡舟湖上,经历了白天的喧嚣和骚动,秋夜笼罩下的鹿儿湖一派静穆。我们一桨一桨将船划至湖心,我为马芳一遍一遍拉老帕的《卡农》。这是马芳最喜欢的曲子,甜蜜、宁静而忧伤。悠扬的琴声随着湖波流淌、回旋。
我们的交往似乎被马小陶察觉,只要我们在一起,总有可疑的人如影随形。我敢断定就是马小陶,那身影我太熟悉了。但马小陶看上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依然每天悄无声息背着梭子和红鼓去湖边,回来后便坐在父亲床前敲呀敲,只是鼓点听起来有些凌乱,不如初听那般清越激扬。
我有些担忧,“媳妇姐”传言虽荒唐,但也并非空穴来风。马小陶就像一个古怪的幽灵,潜伏在不知名的暗处,窥视着这一切。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事,我转弯抹角向马芳道出我的忧虑,马芳“扑哧”一笑,抬手作势要“撕了我的嘴”。
这天黄昏耍完鼓,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冲毁了通往鹿儿村的路,风停雨住后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我们背着梭子和小鼓绕道向村子走去。雨后的空气中有一股好闻的清新气味,路很泥泞,我们一前一后,“呱哒呱哒”的脚步声显得有些黏稠。
“你好像有心事?”我边走边说。
马小陶没有吭声。他当然明白我指的是今天耍鼓的接连失误。游客都喝起了倒彩。这是很少有过的事情。
“别这样丧气,一切会好起来的。”我又说。
身后没有脚步声,我扭过头,马小陶一言不发地站在路上。
“喂——”我叫了起来,“我们得抓紧赶路,又要下雨啦!”
僵了一会儿,马小陶追了上来,短促的双腿走起路来令他像极了一只笨重的鸭。
“老帕是谁?”在接近村庄时,马小陶问我,像是憋了很久。
该死,马小陶早就知道了我和马芳的事,他竟然连我给马芳拉的曲子都清楚。
“帕赫贝尔。教堂里的一个琴师。”我故作轻松。
“还有呢?”马小陶并没有放弃。
“他深爱着的妻子和孩子患鼠疫离开了,他无法停下对妻儿的怀念,就有了这么一首曲子。”
“……听起来很不错。”
“是的,这是爱情的力量。你不会懂的。”
“你能教我拉琴么?”马小陶伸长了脖子,“我天天给你抓鱼。”
“我教过,可你总是在睡觉。”
马小陶没有出声,我感觉到了他的失望。
“也许可以考虑,”我换了一副口吻,“只要你为我们保守秘密。”
马小陶站住,颠了颠背上的鼓,提了提裤子,默默地越过脚下的水洼快步赶到我前面去了,不多会儿便隐入魆魆夜色难辨身形,只能凭借他身上的鼓发出的越来越快的“嚓嚓”声,判断出他在急促向前,那“嚓嚓”声之下,是从更幽暗的深远处传来的,村子里朦朦胧胧的喧闹声。我停了下来,把梭子的绳索从左肩换到右肩,快步追了上去。
时间一天天向前推移,我对马芳的感觉也在分秒升温,原来的顾虑和拘谨统统见鬼去了,晚上只要有空,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在湖面上约会。我坐在船头拉琴,马芳躺在船尾,双手在初冬温暖而沉静的湖水中滑动。“多想永远在这湖水中睡去!”马芳喃喃自语。……我们就那样躺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任凭船悠悠地漂游。我们沉醉在满天的星光和天地镶接处繁星般灯火所点缀的秋夜里,直至寒露打湿了船舷,才慢慢向远处群山的轮廓漂去。
当然并不是每个夜晚都如此美妙,更多的时候只是匆匆见一面说上几句话,马芳不是总能找到恰当的理由在外面待上大半夜。
半年后的夏天,马小陶开始在蹭蹭长个头,声音开始变得又老又粗,犹如嘎嘎老鸹叫,唇上也冒出了细细的嫩须。这是令马家欢欣鼓舞的事情,大家都以为,一百一十公分的马小陶将永远停留在这个高度直至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侏儒。令人没想到的是,在停滞了若干年的发育后,马小陶宛如春雷后的竹笋,开始舒舒展展拔节生长。
那些日子,除了马小陶的父亲,马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久违的笑容。马母拉着儿子在街面上一遍遍招摇过市。人们奔走相告,马家的小子竟然开始长个了,听上去多么有意思。喜悦激荡的日子,烦恼也随之而来——鼓上的马小陶耍得越来越吃力,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灵活和流畅,一场鼓耍下来累得气喘吁吁。这是不可阻挡的严峻的事实,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水上的红鼓将慢慢承受不了马小陶的身重,马小陶终有一天会耍不动。
马小陶听从了我的建议,减少了水上蹬鼓、空中翻腾的动作,增加了鼓沿打马、鼓上矮子功的表演。所谓鼓沿打马就是模仿戏曲小丑在漂浮的鼓沿打马快跑,也是难度较高的技术活,没把握好速度和平衡容易落水,但比起鼓上翻腾体力消耗少一些。鼓上矮子功表演起来不费力,马小陶有先天的条件,且有喜感。虽然如此,马小陶依然耍得面红耳赤,跛脚的脸阴得都能拧下水来。
这天我在上课,马芳打来电话说马小陶在鼓上晕倒跌落水中。我赶到马家时,马小陶刚刚醒了过来——马小陶一直在瞒着我们缩食,据说连续四天没有正常进食了,他以这种近乎残忍的方式来抵抗身体的生长。
众人散去后,一直守在马小陶身边的马芳突然中弹一般“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她捶打着马小陶,好似在捶一面小鼓。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马芳痛哭流涕的样子,我没有上前抚慰,我担心马芳因过度悲伤而扑倒在我怀里。
马家毅然决然阻止马小陶再去耍鼓,蒋老板不得不决定取消这个项目。
马小陶在争取无望后,只提了一个条件——让他最后耍一次。我们不明白马小陶为何要这样做,多耍一次又能怎样呢?也许他是在抓住最后的一线机会证明自己,也许他根本舍不得耍了几年的鼓。为了这一次,马小陶做了充分的准备,短袍短裤重新洗了一遍,选了一个笑脸佛的面具和一根更称手的竹篙。
要我说,这次耍鼓和往日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的目光被马小陶牵着跳蚤一般在鼓面上跳跃,我们关心的不是他翻腾得有多高,而是担心他每一次落下时是否会跌倒。谢天谢地,总算没有丢丑——马小陶从最后奋力一跃的极限高落下,双手合十盘腿坐在鼓中央——岸上爆发出噼噼啪啪的掌声。马小陶保持着姿势就那样坐着,双耳垂肩,笑口大张,俨然是一尊稳坐莲花台的笑脸佛。我们感觉不对劲,匆忙划船过去把大鼓和马小陶拉回了岸边。马母打落马小陶仍合着的双手,摘下他的面具——普度众生喜气盈盈的笑脸后面,竟是一张泥塑般的木然的脸。
马家的日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迫,不再耍鼓的马小陶话也越来越少,但他依然在不停地忙碌,每天一早背着梭子去湖边抓鱼,通常给我送两条,多则三条,给父亲留两条,余下的拎到集市上贱卖。
濒临绝望的马母将有鱼刺的鱼汤喂给马父,马芳发现后哭着从父亲嘴里抠出鱼刺。这些都是我从鱼肚里的纸条得知的。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马家了。我在慢慢疏远马芳,只是我不敢承认罢了。马家目前糟糕的样子令人心灰意冷,尤其是我们之间还横着一个说不清楚的马小陶。马芳也没有来找我,也许是糟糕的生活让她无心谈情说爱,也许对我心生怨怼和愧疚——我的大部分工资因贴补马家生活而捉襟见肘,我们的感情在学校老师间传播而招致非议。
中秋之夜,我的新女友被贴在窗前的一双眼睛吓得失声尖叫,待我追出去,那双困惑的眼睛如同一对受惊的鸟儿飞离了枝头,矮脚植物后一个瘦小的身影倏然不见踪迹。门把上晃晃悠悠吊了一个小丑面具,它此前一直挂在马父房屋的墙壁上,因为长得过于丑陋,不忍直视,马小陶一直没用过。我捏着面具一步一步登上宿舍楼顶,心潮难平,我的目光越过鹿儿湖望向鹿儿村,目光愈拉愈长,我看到了马小陶和马芳将他们的父亲抬到了院中,马父张嘴耷着头空空地望向浩瀚深邃的夜空,马小陶怀抱着小鼓就坐在他父亲身边,敲呀敲呀……我侧耳倾听,似乎听到了那不绝于耳的鼓声在村子上空飘荡。
打这以后,我再也没收到过马小陶送给我的鱼。
多年后的一个阴冷的雨夜,为生计兼做吹手的我随人去给人吹曲,当我们戴着斗笠顶着细雨途经鹿儿湖慢慢向坡上的马家方向行进时,我的心突突地跳得厉害,我想踅回,可已经来不及了。出人意料的是,马父竟然脸色红润坐在大门边的竹椅上,不时在纷乱进出的腿脚中颤颤巍巍伸出手中的竹杖,拄掉地槛上的污泥。悲怆的马母被人搀扶着委顿在地。灯影里的那个戴着面具耳朵里塞满白棉花的人,应该是马小陶,看不出脸上的表情,头发上闪了一层银亮的雨丝,个头比几年前高出许多……瞬间,我的心窝犹如被人冷不防捣了一拳,眼前跟着黑了一下——躺在篾席覆盖着的红棺里的死者,据说在外面挣了很多钱,但也招来了许多流言,每次回来心情也不好,这次却投了湖。我的双耳充塞了嗡嗡营营的声音,似有群蜂在耳边乱舞。我提着呜咽的笙,趁乱匆匆逃离了马家。
夜色很好的晚上,人们总能看见鼓手马小陶戴着面具背着梭子和红鼓去往湖边。时疾时缓的鼓声被微风从湖上送了过来。人们不知道马小陶在敲什么,但从那深深浅浅的鼓点中,我依稀能分辨出他是在演奏老帕的《卡农》。
责编:朱传辉
题图:程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