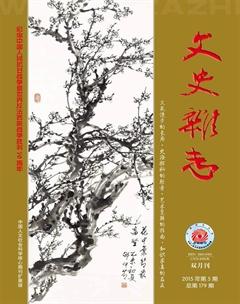论羌族火葬的成因
黎明春

摘 要:羌族的火葬是羌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之所以能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得以逐渐形成,既有外部的原因,亦有民族自身的原因。考察羌族火葬的来龙去脉,或可对当代社会移风易俗、大力推进火葬继而促进丧葬制度的彻底改革,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关键词:自然环境;战争;灵魂观念;图腾崇拜;祖先崇拜
羌族是我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在历史上分布很广,曾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羌族是汉族的称呼,其自称是“尔玛”(x ma)、“日玛”(z ma)或者“尔麦”(x me)、“日麦”(z me),翻译成汉语就是本地人、当地人的意思。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羌族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背景,逐渐发展演变出很多支系。今天西南地区的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拉祜族、基诺族、普米族、独龙族、怒族和土家族等民族的历史,都与羌族有紧密的联系。羌族很早就开始了和汉族的交流融合,他们也是汉族前身“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甲骨文中,就有不少有关羌族的记载。前辈学者研究认为,在夏商周三代中,羌族是当时中华大地主要民族之一。
关于古代羌族的分布活动范围,西晋时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五·武都郡》记载:“西羌自赐支以西,至河首左右,居今河关西,可千余里,有河曲。羌谓之赐支,即析支也。”这是古代的文献里第一次对古代羌人分布区域中心的记载。河关在今天的兰州西南,以西千余里皆称为河曲。“黄河自西来,至大积石山脉东南端,曲而西北行;经小积石山的东北麓,又曲而东北行;至曲沟,又曲而东行,凡千余里,皆称河曲,羌语称之为‘赐支’。”[1]《后汉书·西羌列传》:“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2]其也提到西羌诸种分布在河曲附近以及以西以北。因此可见古代羌族分布在青海东部的河曲及其以北,甘肃以西的广大地区。
另外,笔者近年来多次进入今天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茂县、理县地区作田野调查,多次听到释比[3]讲述的羌族释比唱经《择吉格布与王位》,里面讲到“很久很久以前,大部分羌人由黄河源头徒步迁徙来到了松潘草原……”这也证明古代羌人的主要生活地区是在黄河源头,即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
那么,羌族火葬的成因是什么呢?换言之,是怎样的因素促成羌族在历史时期最终选择了火葬呢?
一、自然环境因素
古代羌族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少土、多石、狂风、寒冷的环境让他们的生活十分困难,迫使羌族无法选择“入土为安”的土葬,只能采用简单、易行的火葬。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在甘肃以西、青海以东的湟水一带,虽然土地广阔,但自然环境一直比较恶劣,主要以高山草地为主,葛剑雄认为:甘肃地区“以往两三千年间其总体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今天视为不利因素的沙漠,戈壁,盐碱地,植被稀少的黄土高原早已存在。”[4]“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5]土地难以为生活在这里的民族提供实际上的依赖价值,也就难以成为人们维系情感的纽带。因此,“入土为安”的意识从未成为羌族丧葬文化的组成部分。羌族很早就是一个游牧民族,“羌,西戎牧羊人”,放牧必然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单纯的人丁以及牲畜数量的增加,成为提高生产力简单易行的方式。这样带来的必然是过度的放牧,又造成了植被的破坏。大量的植被破坏,又反过来制约羌族的生活生产。西北又是大风天气的集中地区,植被的破坏以及大风的侵蚀使得土壤层很薄。根据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一地区的土壤沙化现象自古十分严重,如下表所示:
西北地区土壤侵蚀量[6]
年均土壤侵蚀量(亿吨) 自然加速侵蚀率(亿吨)
距今6000—3000年 10.75
公元前1020—公元1194年 11.6 7.9
这说明人类历史时期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是在不断加剧的,使地表更趋近于岩石层。这样如果选择土葬,那挖掘起来必然十分困难, 特别是在远古时期,靠简陋的木器、石器更是吃力。因此,开掘地穴埋葬尸体的行为很难形成风气。这就从客观上注定羌族无法为死者提供“入土为安”的丧葬方式。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形成了古代羌族代代沿袭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游牧生产完全不同于农耕生产。农耕生产以土为本,一切庄稼,一切植物的生命均来自泥土。春种秋收,从土地里获取所有生活资源,决定了农耕民族有地则生、无地则死的强烈的“土地崇拜”意识。土地是母亲,土地是生命,土地是希望,强烈的“恋土”意识,最终转化为农耕民族“众生必死,死必归土”[7]的所谓“入土为安”的丧葬习俗。
与农耕民族截然不同,羌族人所从事的游牧生产,必须逐水草而居,“所居无常,依随水草”[8],经常迁徙流动,不断转换地域空间。这一种流动性极强的生产方式,使得羌族人难以常年世代定居一地,形成浓厚的“恋土”意识,从而也不可能像农耕民族一样,为逝去的亲友择地安葬,并定期进行扫墓祭祀。于是羌族人用另一种丧葬方式慰藉死者的灵魂,让灵魂尽快离开肉体的庇护“登遐”(升天),这种方式就是火葬。换句话说,自然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流动性生产方式,是羌族火葬习俗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战争因素
羌族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制,不仅导致内部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和生存环境而发生争夺,也让中原政权在处理羌族问题的时候,无法和一个代表羌族的领导者进行交涉,于是更多地采用各个击破的强硬政策。这就导致了长期的、不断的战争。而羌族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在战争中必然会有很多族人死去。活着的人连自己都无法保护,何况死者,但是民族的情感也无法让他们视族人的尸体于无睹。于是简单的火葬成了他们的选择。
羌族与中原政权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商朝和两汉。这两次大规模的冲突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羌族与商王朝的战争主要和祭祀传统有关。因此商朝主要是以俘虏羌族为主。而汉朝是害怕羌族和匈奴联合起来威胁自身的安全,采用了比较强硬的政策。在现在可以看到的商朝的文献中,涉及羌是比较多的。甲骨文中“羌”字写作:“”,从字形来看就像是一个人被绑着的样子。
现在可以知道,商朝是一个对祭祀十分敬重的国家,并且人牲和人祭制度在商朝发展到了极致,那在祭祀活动中的人怎么来呢?位于商朝西边的羌方成了最好的来源。最初的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取得祭品,但是商人发现征伐羌方可以获得大量的战俘,而这些战俘就成为祭祀鬼神最好的人牲。
有学者统计“商代用羌民作为人祭共七四二六人,另外还有三二四条卜辞未记具体人数……占了总数的一半。”[9]
在中国古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口的数量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实力的象征。而在冷兵器时期,抓住八千名战俘,那意味着死去的羌族人只会更多。值得注意的是,成为“人牲”是没有太多的条件,老人、成年人、小孩都可以,我们可以从商朝的祭祀坑中看出。频繁不断的战争,羌人不断死于战场,每次都会留下大量的尸体。对于如此多族人的尸体,任其在野外被野兽吃掉或者自然腐烂,这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客观上,尸体腐烂还会传播各种疾病和瘟疫,影响活着的人,因此具有清洁功能而又较为易行的火葬成为最好的方式。
这一时期,火葬并不是羌族唯一的丧葬方式,土葬和火葬是并存的。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初,青海循化阿哈特拉发掘卡约文化的墓葬中除了土葬,也有火葬的痕迹。[10]阿哈特拉2期早段的12号墓距今3555+130年,5期晚段的158号墓距今2800+140年,相当于商周时期。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一时期,羌族的丧葬是火葬和土葬并行的。
而到了汉朝,火葬逐渐成为羌族主要的丧葬方式,这和汉、羌更大规模的战争不无关系。
汉朝时期,出于中央政府的自身安全考虑,羌人又遭到了汉朝统治者的大规模镇压。到了东汉,羌族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而与起义相伴随的,则是更大规模的屠杀。
汉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11]时,又恃强大肆屠杀,“召先零羌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12]。
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至金城,先零羌受重创。据赵充国奏:“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13]
从这两段材料可以看出,这时的战争中羌族作为弱小的一方,伤亡是十分巨大的。在长期的战争中,死去的主要是青壮年,剩下的老弱病残,则无法也无力去处理更多的尸体。据《后汉书》关于羌族“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14]的记载,羌族是一个以战死为荣的民族。因为战争而死去的英雄,他们的尸体必然得到族人的尊重与崇拜;但是客观的战乱与自然环境又不能让他们采取复杂的丧葬来处理,于是既省时省费又简洁快速的尸体处理方式——火葬,便成为羌人普遍采用的丧葬方式。
在长期被压迫被镇压的遭遇之下,羌人原本就已经松散的组织更加涣散。人口的大幅锐减和被迫四处迁徙的境遇使得羌人产生漂泊苍凉的心境,他们难以对现世生活产生希望,而把心思放在对死后世界的憧憬上。让灵魂随着跳跃的火焰、游离的风和升腾的烟雾到达理想的世界,也正与羌人心中有关灵魂、图腾和祖先的崇拜理念相契合。
三、灵魂观念因素
灵魂观念可以说是一切丧葬活动产生的一个共性,和灵魂相对应的就是肉体。肉体是灵魂的一个载体,而人死以后,为了让灵魂能够尽快地去另一个世界,不再干扰活着的人,于是人们把这个载体给“藏”起来。依赖土地的农耕民族采用“入土为安”的土葬,而四处漂泊的游牧民族,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长期的战争动乱,于是采用了“灵魂升天”的火葬。
古代的羌人和其他民族一样,由于对自然现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无法理解,对天灾人祸的恐惧,自然地就把人本身以及人以外出现的自然现象等同相看,把他们接触到的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自然物人格化。他们认为人有灵魂,自然物也有灵魂,“羌族是信鬼神的民族,他们认为无论什么地方都有鬼神的寄托……总之,羌族之信仰还在灵气崇拜(万物有灵)和拜物的阶段。”[15]因此,便产生了“万物有灵”的灵魂观念。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认为,世界上的生灵万物都是外壳与灵魂的结合体。人和自然也是肉与灵的结合体, 而肉体只不过是灵魂的载体。死亡只是灵魂和躯体的分离, 是灵魂脱离这一躯体投入到另一个躯体的一种转化。
羌族不仅相信人有魂,人死了,魂魄不灭,而且在死后几天,还会回家,要“回煞”,要祭奠,这和汉族的某些观念是一致的。在“方子”(棺材)里面要放猪膘、酒肉、杂粮、小刀、烟斗等供死者的灵魂享受。这个时候来吊孝的人也得自带食物,陪死人说话、吃饭,和活着的时候一样。这些丧葬中的表现,都说明了在羌族人的观念里,灵魂不仅不会死去,在离开身体后,还和活着一样,只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如果灵魂无法尽快地到达另一个世界,那就有可能成为“鬼”,就会作祟降祸,对活人造成威胁危害。火葬习俗受灵魂因素的支配,是基于这样的观念意识:人死后,其灵魂迷恋肉体,久久附于尸体不愿离去,给活着的人造成巨大的心理恐惧。要使死者的灵魂不再迷恋肉体,要让灵魂尽快升天而不变成“鬼”,同时也为了尽快消除生者对死者的恐惧,必须想办法尽快“处理”死者的尸体,使其灵魂摆脱尸体的束缚,早日升上天堂,到另一个世界去。而“处理”尸体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火焚尸,实施火葬。史载“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16]这里的“登遐”就是灵魂升天之意。随着焚烧尸体袅袅上升的青烟,灵魂也升上了天空,去到了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羌族的火葬虽然和其它民族的丧葬方式如土葬、水葬、树葬、崖葬等大相径庭,但不同民族的各种丧葬行为,却有它共性趋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把死者从活人群体中尽快排斥出去。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在他的学术名著《原始思维》中,对包括火葬在内的各种丧葬行为,作了这样极其经典的论述:“不管尸体以什么方式处理——土葬、火葬、树葬、崖葬等等,都是把死者从活人群体中彻底排斥出去的仪式。”[17]通过焚尸火葬的行为仪式,把死者从活人群体中彻底排斥出去,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活着的人对死者灵魂的恐惧。火葬焚尸,对羌族人而言,则是解除这种心理恐惧最有效的方式。
四、图腾崇拜因素
仅仅是灵魂崇拜让羌族选择火葬还是不够的,火作为羌族的图腾,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火在羌族心目中,不仅是取暖、吃上熟食的生活必须,而且还是圣洁的象征。对火的崇拜,不仅体现在对火神的敬重以及火塘的重要性上,还直接导致了羌族人在自己生命结束的时候,采用火葬的方式处理尸体。火葬意味着让自己的灵魂在圣洁的火焰中得到升华,让灵魂干净、清白地回到另一个世界,去到祖先的身边。
图腾崇拜在羌族宗教信仰中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旧时,不少前辈学者根据《说文·羊部》关于“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的说法,认为羊是羌族的图腾。但笔者认为《说文》只是从“六书”的角度来解释“羊”,并未涉及图腾问题。羌族的图腾并不是羊,而是火;或者说火至少是羌族的图腾之一。对火的图腾崇拜,促使羌族选择了火葬。
在今天阿坝州汶川县史志办公室里,笔者看到了2002年8月当地政府搜集到的《蒙格西送火》的传说:
在古代,人神共世的时候,大地一片荒凉,没有火种,人饿了就吃树果树根,冷了就穿树叶兽皮。蒙格西是天上的火神,与如布西本有私情,后来如布西被贬到凡间当地母娘娘。有一次,蒙格西悄悄和如布西相会,送给她鲜红的仙果,并对她说:“以后有了娃娃,就叫他到天上找我,给人间取火啊。”蒙格西和如布西私会的事情,让恶煞神知道了,就使用魔力,下起了铺天盖地的大雪,使凡间变得天寒地冻,想把如布西和凡人全部冻死。凡人们冷得只好躲进了山洞,据说这个就是冬天的来历。后来如布西生了一个娃娃,名叫燃比娃,浑身是毛,从小就聪明伶俐,长大以后更是机智勇敢,武艺高超。有一天阿妈就把她和阿爸相爱的事给他讲,并叫他上天去找阿爸,给人间取火种。燃比娃经过了三灾八难,才找到蒙格西,又经过九死一生,才战胜恶煞神,把火种藏在白石间带回了人间。后来人们在取火的时候只需要两块白石碰撞下就可以发出火花。从此人间有了火,才可以吃熟东西,冷了也可以烤火。[18]
这个传说在今天阿坝州的汶川县、茂县、理县以及松潘县、黑水县羌族的聚居地区流传得十分广泛。剥去它神话的因素,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包括羌族在内的人类在没有懂得使用火之前,如果饿了,只能吃“树果树根”;如果冷了,只能穿“树叶兽皮”。其二,后来人类获得了火种,对之十分珍惜。其三,火对于远古的人来说十分重要。其四,因为火来之不易和火的重要性,人类于是对火产生了一种敬畏,特别是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大西北的羌族,更认为火是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便使火逐渐成为羌族的图腾。羌族各村各寨信奉的神灵虽有所不同,但是火神蒙格西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位。
对火的崇拜也反映在火塘上,羌族认为架于火塘上的三角架就是火神的象征。火塘是羌族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设施。在羌族堂屋中央的火塘是用木头或者石框镶成,四边形代表着地方,火塘上方有个圆形的天井,代表天圆。上面置放一三角铁架,三角象征着天、地、人。火塘上方挂链,可自由升降。火塘既是取暖做饭的地方,也是家庭休息、议事的中心,对火的崇拜随着火塘这一生活必需品而融入了羌族的生活。火塘上的三角架更是火神的象征,任何人都不准移动或去碰三角架,更不能踩、蹬或者跨越——那样做被认为是对火神的不敬。火种长年不灭,叫作“永不熄灭的万年火”。
可以看出,在羌族长期的民俗养成过程中,火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于是火的重要→火的崇拜→火成为图腾→火神的敬畏(火塘的重要)→采用火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关于火之成因的链条。
五、祖先崇拜因素
每一个创造文明的民族,对于自己的祖先都有一种天生的崇拜感,而祖先的典型行为或者突出性格,则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人。羌族的情况便是如此。羌族火葬习俗的产生形成过程,与其两个祖先的影响作用密不可分,一个就是公认的羌族始祖——炎帝,另一个是第一个在史书中出现名字的羌族祖先无弋爰剑。
炎帝是中国上古时代神农部落首领的名称,有关史籍中炎帝及记载如下:
《国语·晋语》:“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南宋)罗泌《路史·国名》:“炎帝后,姜姓国,今宝鸡有姜氏城,南有姜水。”
(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名女登;为少典妇,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
《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研读以上四段有关炎帝的史料,有两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分析。
其一,炎帝出生并长于姜水,其作为姜姓部落首领,与羌族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明代天顺五年(1461年),李贤等人所撰《大明一统志》对姜水作了考证,其在第三十四卷《凤翔府·古迹》中记载:“姜氏城:在宝鸡县南七里,城南有姜水。”[19] 距今四千多年在陕西宝鸡姜水一带生活的,只有羌族,没有其他民族。显然,炎帝作为姜姓部落的首领,实际上也就是羌族一个部落的首领。因此,炎帝毫无疑问应是羌族的祖先。关于这一点,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有这样一段精辟的阐述:“‘羌’从‘羊’从‘儿’作为部族之名,‘姜’从‘羊’从‘女’,作为羌人女子之姓。”[20]顾氏之说,为炎帝是羌族的“始祖”作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论证。
其二,“炎帝”这一名号的由来,是因为“以火德王”,这与羌族“尚火”以及选择火葬有重大联系。战国末期的阴阳家邹衍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附会王朝的命运,称为“五德终始”。炎帝受命为部落首领,在“五德终始”运行中被归属于火运,故称“以火德王”。由于炎帝被羌族人尊为始祖,其“火德”之运势必对羌人产生重大影响,羌人崇火尚火习俗世代传袭,以示不忘祖先之功德。也正是因为对祖先“火德”之运的崇尚,成为羌人选择火葬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考察祖先崇拜与火葬关系的因素中,除了炎帝的影响之外,对羌族火产生重要作用的,还有第一个在史书中出现名字的羌族祖先无弋爰剑。
《后汉书·西羌列传》:“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21]“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22]“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23]无弋爰剑本来只是一个秦国的奴隶,被秦国的人追赶,躲在山中的岩穴,秦人没有办法,只好放火烧山,逼其出来;但是由于某种巧合,无弋爰剑并没有被烧死。这个时候,羌族的先民们认为无弋爰剑是天神的使者,因而得到火神的庇护才被焚不死;也正是火的净化作用,才使他洗净身上的罪孽,摆脱冤魂的勾摄,成为神所庇佑的人,所以推举他为羌族部落的首领。正是这种火崇拜观念,羌族先民认为只有经过火化才能去见自己的祖先。
除了这两个共同祭祀的祖先外,羌族每个家庭还把死去的先人奉为神灵,称为祖宗香火,神位在火塘的一角。不管是从名称还是供奉的位置都可以看出,后起的祖先崇拜和火这一图腾崇拜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只要看到火葬焚尸的烟火升起,羌族便感觉祖先的灵魂已经与之相伴随,死者已经追寻祖先回到另一个世界。
通过对羌族火葬的历史起源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对羌族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和发现。羌族采用火葬这一方式,不仅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自然环境的恶劣以及战乱的因素,还有其内部的原因,包括灵魂、图腾和对祖先的崇拜。我们可以说,每一种风俗文化的起源必然有着其丰富的原因与内涵,虽然十分纷繁,但是历史的研究正如顾颉刚先说所说是“层累的历史”,我们只要一层层地剥开迷雾,就会发现最真实的历史。今天我们人口众多,土地狭小,实行火葬是利国利民、干净环保、移风易俗的优良民俗,这对于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1]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1页。
[2][5][8][14]《后汉书》卷八十七,列传第七十七,《西羌传》,2869页,2869页,2869页,2869页。
[3]释比是羌语,翻译成汉语就是端公。
[4]葛剑雄:《从地理看长时段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5页。
[6]转自朱士光:《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基本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7卷第三辑,7页。
[7](汉)戴圣:《礼记》卷四十七,《祭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6册第275页。
[9]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与人祭(下)》,《文物》,1974年,第8期,57页。
[10]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近十年考古工作的收获》,文物出版社,1990年。
[11][12][13]《汉书》卷六十九,列传三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2973页,2973页,2992页。
[15]胡鉴民:《羌族的信仰与习为》,《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16]《墨子·节葬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48册第67页。
[17]法国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306页。
[18]以上是2002年8月,汶川县县志办在汶川克枯乡,根据苟释比、余释比的讲述,形成的文献《汶川县羌族古籍·释比的故事》所载。
[19](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四,《凤翔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27册第850页。
[20]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121页。
[21][22][23]《后汉书》卷八十七,列传第七十七,《西羌传》,2875页,2875页,2876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