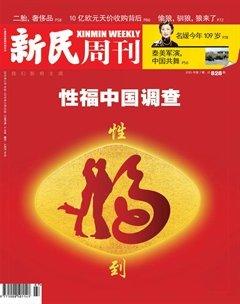直面衰老,理解生命
夏学杰
过了三十五岁,我就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老之将至了,“岁月不饶人”,古人的这句总结真是精准。白头发悄然增多,眼角纹真的深了,记忆力大不如从前,总是丢三落四。不怪乎约翰·亚当斯三十七岁时就以老人自居,有人请他赴波士顿演讲,他说:“年事已高,不克复作大型演说。”
面对自己的衰老,我们很无辜。而面对亲人的衰老,我们又很无助。前几日,我父亲左手不太听使唤,我和妻子软磨硬泡,他好歹听话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是,才两三年的光景,已从腔隙性脑梗变成双侧脑梗,更要命的是CT显示有小脑萎缩症状。尽管大夫告诉我这是老年病,但我还是无法接受父亲一点点衰老的事实,泪水直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想明白秦始皇为何那么热衷于长生不老药。我越来越长吁短叹,妻子说,最反感我叹气的样子。可是,我叹气,并不代表泄气、放弃,我从没有停止过努力,只是觉得世间之事并非努力就都能做到。
步入中年,人愈发敏感起来。《流放的国王》一书,看得我几度落泪。“我如同在慢动作电影中看着父亲慢慢滴着血,生命一点点从他身上渗漏出去,整个人的品质和个性一滴一滴从这个人的身上渗漏掉。”这样的描述,有多少当儿女的会感同身受?作者阿尔诺·盖格尔的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虽然依然充满活力,拥有不失幽默的智慧,但是疾病让他慢慢丧失了记忆和理智,他逐渐失去了他的生活。他就在家里,可“要回家”的渴望无时不在。“父亲就像被流浪的国王一样,不知所措没完没了地四处乱窜”。其实,就是不得老年痴呆症,老人亦是如此。陈丹青记录木心最后时刻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终于,到那一刻,他很乖,被扶起后,凛然危坐,伸出手,签名有如婴儿的笔画,‘木’与‘心’落在分开的可笑的位置,接着,由人轻握他的手指,沾染印泥——先生從来一笔好字啊,人散了,我失声哭泣……”
据《世说新语》,谢安对王羲之说:“人到中年很容易感伤,每次与亲戚朋友别离都会难受好几天。”王羲之说:“晚年光景更是这样呀,只好靠丝竹管弦娱情养性,排遣胸怀,还总怕儿女发觉,破坏了他们的兴致。”老人不仅是易感伤的,更可能丢掉原有的品质。同事说:最愁放假孩子没人带。我说:不是还有她姥姥在家吗?她说:我母亲陪孩子,就是一人一台电视。她的母亲当了一辈子教师,按理说,应该懂得孩子常看电视的危害。阿尔诺的父亲的生活就已“散发出的是麻木淡漠的霉味”,“他觉察到自己已经失去控制能力,无法把握事物,便索性摆脱一切的责任。整天玩纸牌或者看电视,而不去给园子里的西红柿浇水。”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想想我们的生命在不停地老去,的确挺可怕,虽说生命正因为有限才有意义——正如作者所言:“我觉得生命之所以有吸引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死亡。死亡让我对世界上很多事物看得更清楚。”不过这个“有限”实在是太短了。
昆德拉说:“我们称之为生命的那无可回避的溃败,在它面前,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理解它。”阿尔诺写道:“我想,挺住就是一切,这比战胜病魔更加重要。”诚然,未来你我不可获知,你我又不能掌控世界,别说世界了,就是自己的命运又几时掌控过。有时,除了挺住,我们别无可做。
有人说:爱父亲,为他朗读这本书。这本书,在我看来,不只是一本忆述亲情的书,更是在试图思索“人之存在”。作者说:“如果人类长生不老,那么人类将思索得更少,当人类少思索时,生活便不妙了。”人,在思索中珍惜地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