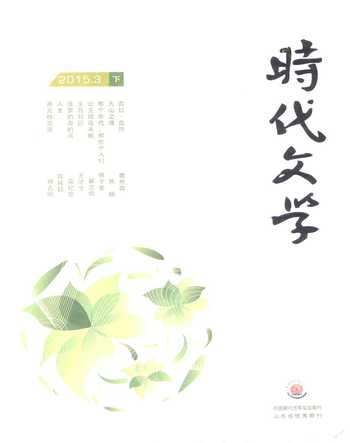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诗歌的雕塑美与艺术性
梁媛
摘 要:康斯坦丁·卡瓦菲斯是希腊现代诗人,卡瓦菲斯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少年时在英国待过七年,后来除了几次出国旅行和看病之外均生活在亚历山大。笔者主要从两方面分析卡瓦菲斯的诗歌,卡瓦菲斯的诗歌从其发表的154首正典来看,主要分为描述现代此时此刻当下的感官情诗,神话诗以及涉及政治历史的诗歌。笔者认为,从卡瓦菲斯的感官情诗和涉及神话和历史的诗歌当中尤以感官情诗为主,体现出一种对美的追求,而这种美所涵盖的不仅仅是男人纯粹的感官肉体性,而是一种简练带有雕塑特点的纯粹艺术美,而这种充满浓郁贵族气息的感官欲望和对情欲的描写也与卡瓦菲斯对待历史的态度如出一辙。论文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卡瓦菲斯平淡而隐忍的一生,对诗人的生平做一个大致地概括。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卡瓦菲斯诗歌中的雕塑美感,第三部分探讨卡瓦菲斯诗歌中艺术性与历史主义之关系。
关键词:卡瓦菲斯;雕塑美;历史主义;感官性
“我给艺术带来了
我在沉思冥想中坐着
我给艺术带来欲望和感觉
一瞥而过的事物
面孔或线条,对于不圆满的恋情的
一些模糊回忆。让我顺从艺术:
艺术懂得如何构造美的形状,
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使生命圆满,
把各种印象混合起来,把日子和日子混合起来。”
——卡瓦菲斯(C.P Cavafy)
康斯坦丁·卡瓦菲斯是希腊现代诗人,二十世纪诗人,又或者称之为历史诗人。这是卡瓦菲斯为自己下的定义,在随后的讨论中我们会详细分析这一点。卡瓦菲斯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少年时在英国待过七年,后来除了几次出国旅行和看病之外均生活在亚历山大。由于诗人是用希腊语创作,在这里笔者从黄灿然版本的卡瓦菲斯诗集出发,对照蕾·达尔温, 基利和谢拉德的英译本对卡瓦菲斯的诗歌进行分析。主要从两方面分析卡瓦菲斯的诗歌,卡瓦菲斯的诗歌从其发表的154首正典来看,主要分为描述现代此时此刻当下的感官情诗,神话诗以及涉及政治历史的诗歌。笔者认为,从卡瓦菲斯的感官情诗和涉及神话和历史的诗歌当中尤以感官情诗为主,体现出一种对美的追求,而这种美所涵盖的不仅仅是男人纯粹的感官肉体性,而是一種简练带有雕塑特点的纯粹艺术美,而这种充满浓郁贵族气息的感官欲望和对情欲的描写也与卡瓦菲斯对待历史的态度如出一辙。卡瓦菲斯说,“艺术懂得如何构造美的形状”,这形状的构成有边界有形体,甚至有欲的味道,它如同亚历山大海港旁的一座白色雕塑,高傲而凛冽的站在远处,漂亮而触不可及。
一、卡瓦菲斯平淡而隐忍的一生
C.P卡瓦菲斯的父母是P.J卡瓦菲斯和哈里克莱雅福蒂亚迪的儿子,两人都来自君士坦丁堡富裕家庭,C.P卡瓦菲斯是家中第九个孩子。P.J卡瓦菲斯经营一家进出口公司,做谷物,棉花和未加工水牛皮生意,其子公司在英国的利物浦,曼切斯特和伦敦均有子公司,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小卡瓦菲斯前往英国待了七年,于1879年重返亚历山大。卡瓦菲斯十六岁进入墨尔赫斯商校学习,求学期间对古典作品和希腊古代文明产生浓烈爱好,1882年反外国热,反基督教的暴乱导致很多欧洲人被杀,也导致英国炮轰亚历山大各要塞,哈里克莱雅带卡瓦菲斯前往君士坦丁堡避难,也正是这一次离开,卡瓦菲斯错过了一生中唯一一次亲眼目睹亚历山大遭受重大创痛。逗留君士坦丁堡期间,卡瓦菲斯对希腊俗语发生兴趣,接触了用雅语和俗语写的希腊现代诗。1882年,卡瓦菲斯重返亚历山大,当时英国的炮轰只是一个开始,埃及在当时实际上已经属于英国的附属国,希腊社区的商业生活也被摧毁,用蕾·达尔温在《卡瓦菲斯小传》中的话说,卡瓦菲斯生活在一个普遍悲惨和颓废的时代,亚历山大的希腊人很难重建他们的生活和制度。”卡瓦菲斯的传记作家特拉斯提斯.齐尔卡斯也说“卡瓦菲斯家所熟悉的埃及的道德和物质外貌已模糊难辨。” 29岁的卡瓦菲斯在水利部找到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做了三十年的临时职员,据卡瓦菲斯在水利部的档案了解到,卡瓦菲斯除了通晓古代和现代希腊语,还通晓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通过蕾达尔温的传记可以了解到,卡瓦菲斯每年写约七十首诗,而这些诗中他只保留四到五首,其余全部毁掉。卡瓦菲斯对公众意见有一种病态的恐惧,而其惯常的做法是把这些诗作副本寄给朋友,在朋友赞赏其有价值后才愿意刊印。1907年卡瓦菲斯对一个叫‘新生的文学青年团体发生兴趣,该团体致力于推广希腊俗语文学和促进希腊俗语。佩里迪斯曾说,“卡瓦菲斯有一种战斗性的语言良知之美,他常常谈到俗语现象和种种问题。”从后来刊印出的卡瓦菲斯诗歌中可以发现,卡瓦菲斯不仅常用俗语,也未忘记雅语,反而二者兼容并用,把二者的微妙和敏感混合起来。1922年退休之后,卡瓦菲斯仍然会去咖啡馆和朋友聊天,仰慕他的人会与他共享土耳其咖啡和聆听他那“管风琴语调”的声音。1948年,卡瓦菲斯因喉癌逝世,在G.莱乔尼蒂斯在他未发表的《卡瓦菲斯自谈笔记》中,卡瓦菲斯说:“很多诗人都是只做诗人……我,我是一个诗人史学家,我写不了小说或者戏剧,但我感到自己身上有一百二十五个声音在告诉我,我可以写历史。但是现在来不及了。”
卡瓦菲斯是诗人史学家,或者写历史的诗人,但实际上,从他这一生大致的勾勒即可以看出,卡瓦菲斯所钟爱的神话历史和他所写短小简洁的感官情诗有着紧密地联系。从中我们可以描绘出一幅幅色彩强烈,线条丰富,我们甚至可以感触到他所塑造的美,那些肉欲的躯体在字里行间隐忍而压抑地透露出来。
二、卡瓦菲斯诗歌中的雕塑美
W.H奥登有一篇著名的论CP卡瓦菲斯的文章,在文中他写道,正是卡瓦菲斯影响了他的创作,倘若不认识卡瓦菲斯,奥登所写的诗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奥登在随后谈到了一个和笔者所面临同样的问题,卡瓦菲斯用希腊文的雅语和俗语进行创作,而要理解卡瓦菲斯的诗歌特点,只能通过中译本和英译本进行对照,这就涉及到诗歌翻译的问题。奥登强调,在诗歌的诸要素中,肯定有一些可以直接从原文翻译过来而有些部分由于和原语言不可分割而不能翻译,而诗作中可以保留的部分要素即是明喻和暗比喻。奥登指出,这两种比喻并非源于地方性的措辞习惯而是源于全人类共同熟悉的经验。然而这两种情况在卡瓦菲斯的诗歌中都不可用,卡瓦菲斯习惯用松散的短长格诗行创作,兼容希腊的俗语和雅语,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成英语或者从英语翻译到中文的可能性很低,同时卡瓦菲斯也不用比喻或者纷繁的各种修辞手法。众所周知,在隐喻当中通常可分为两种要素,也就是说隐喻通常由这两种要素构成,一是描写的对象也即‘要旨,另一种是描写对象所体现的载体。卡瓦菲斯直接略过描写对象即‘要旨而反复描述载体(布罗茨基论卡瓦菲斯),布罗茨基认为,卡瓦菲斯对描写对象地忽略而对载体地强调,实际上是一种简练的同义反复,他松开了读者的想象力而不建立暗喻中描写对象和载体之间明显的链接。布罗茨基最后总结到,对卡瓦菲斯而言,载体对应埃及的亚历山大,而描写的对象也就是要旨就是卡瓦菲斯所经历的人生。
那么是什么让卡瓦菲斯成为希腊诗歌中的特立独行者,给后来如布罗茨基,奥登,米沃什等人强烈的影响?奥登认为是一种独特的语调,不管是任何版本的译文,都能够轻易地辨识出这是出自卡瓦菲斯。在福斯特1923年的随笔《法罗斯和法里隆》收录的关于卡瓦菲斯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卡瓦菲斯“……一位戴草帽的希腊绅士,绝对静止不动地站着,从一个稍斜的角度看世界,他双臂张开,很可能……”“一种倾斜的角度看世界,在卡瓦菲斯的诗歌中,这种‘倾斜的角度,也就是奥登所谓的独特的语调,而这种独特的语调和风格也就是笔者所要描述的如雕塑一般的对美的追求,哪怕短暂也在所不惜。下面几首诗歌,都属于卡瓦菲斯所写有关情欲的诗歌,他在追求欲,年轻的朝气蓬勃的欲望,带着身体冲动的欲望,然而在这欲望的回忆中也带着美的追求,或者换一种说法,真是感受到了这种美,激起了诗人强烈的欲望,如飞蛾扑火,它是真实存在的也是虚幻而模糊的,我们抓不住它,它似乎只降临在年轻男子紧绷的肉体和鲜红的嘴唇上。
欲望(1904)
就像那些早夭者的美丽身体
悲哀地禁闭在豪华的陵墓里,
玫瑰在头边,茉莉在脚边—
欲望似乎也这样,它们衰竭了,
从来没有满足过,没有得到过
哪怕是一个欢乐的夜晚,或一个绚丽的早晨。
卡瓦菲斯在描述美的时候,用到了‘早夭和‘身体,对身体的迷恋是卡瓦菲斯情诗一向的主题,在卡瓦菲斯传记里,我们不难看出,欲望的对象性别模糊,并且从大量关于卡瓦菲斯的生平或者仅仅从这些诗歌里面,可以体会到这些性别模糊的对象其实都是年轻的男子,快乐的纵欲往往发生在诗人年轻时候的幻想或者真是存在的一夜情当中,可也总是那么一闪而过,让人回味却短暂。比如在这首诗中“哪怕一个欢乐的夜晚,或一个绚丽的早晨”,时间是短暂的,对诗人来说,这种短暫的激情从来不曾满足也从未真正得到过。是某一个男人的爱情?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卡瓦菲斯虽然是同性恋,但是并未聚焦在某一个人身上,诗歌中所体现的都是没有来由的一夜欢愉,它们存在在诗人脑海中,而正是短暂带来了压抑和隐忍,对这种美更强烈的渴望和追求。又比如1912年的这首《回来吧》
回来吧
经常回来并占有我吧,
我所热爱的感官,经常回来并占有我—
当肉体的记忆复苏
而一种古老的渴望再度贯穿血液,
当嘴唇和肌肤想起
而双手感到仿佛又在触摸
经常回来吧,在夜里占有我,
当嘴唇和肌肤想起……
卡瓦菲斯诗歌中,多次反复而单调地出现对情欲的渴望,它们总是发生在对年轻的回忆当中,诗人享受感官的快乐,对肉体有强烈的迷恋,奥登曾提出卡瓦菲斯在诗歌的创作当中做到了极度简化,这是他的个人风格,可以说是‘贫乏的选用词汇来描述原本可以丰富多彩的场景,和聂鲁达在《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所描绘的关于爱情的诗相比,卡瓦菲斯的诗歌虽然也极具感官色彩,但是并不会用让人眼花缭乱,情绪四溅的方式来展现,聂鲁达的爱情诗像一首首探戈,激烈,炙热。相比之下卡瓦菲斯显得压抑而向内生发,他迷恋肉体,迷恋美男子的头发,眼睛,身体和嘴唇,对他而言这就是美。但是这种美的表现方式并非通过各种绚烂的明喻和暗语,而只仅仅似乎如同描述似的近乎理智地呈现出来,形成一种简单,深刻而压抑的姿态,似乎是一个人在勾勒一出线条,仅仅几笔,空出了大量留白。但笔笔深刻力透纸背。
少有之至(1913)
一个老人— 已经耗尽,驼着背
被时间和纵欲弄瘸—
缓慢地沿着狭窄的街道走着。
可当他踏进他的屋子,掩藏起
他那年老的蹒跚,他的精神就转向
那份仍然属于他的青春厚礼。
现在他的诗被年轻人引用。
他的奇思妙想活现在他们眼前。
他们健壮而放纵的精神,
他们标志而绷紧的肉体,
立即唤起他的审美直觉。
卡瓦菲斯的诗歌中多次提到年老对年轻的回忆,比如这首《少有之至》,于是一个旬旬老者对年轻的回忆就跃然纸上,他老了,被纵欲弄瘸,但心里有着曾去青春的放纵,那些少年的脸匆匆掠过,留下的是抹不去的美,审美直觉,于是什么是美?在诗人的作品中,美是通过回忆慢慢侵蚀出来,但却以直接的方式表露,美就是欲望,就是年轻,就是肉体,就是放纵而快乐,卡瓦菲斯渴望这种美,却并未要求它长存,也不可能长存。于是我们看到少年们健壮的四肢,带着希腊人高昂的头颅,微卷的头发,笔直的鼻梁,深邃的眼神,眼神中全是欢愉的欲望,这其实正是卡瓦菲斯作为希腊人对泛希腊的一种诠释,感官的,纵欲的而智性的,这种对美的诠释正像一座雕塑,在读者面前矗立,栩栩如生。
这种雕塑般的美的描述在《在咖啡店入口》(1915)也有体现:
他们在我旁边说了些什么
使我的目光投向咖啡店入口,
这时我看到那个可爱的身体,它似乎是
经验丰富的爱神可以制作的,
喜悦地塑造它优美的四肢,
筑构它高大的身材,
温柔地塑造它的脸庞,
最后手指一触,把一种细微的气韵
留在那眉,眼,唇上。
一个美男子的形象被雕刻似得简单明了,充满了魅力。在这里不做过多赘述。卡瓦菲斯除了关于感官的情欲诗,在众多描写神话题材的诗歌中也爱对神话里美男子的形象做描述,尤其是在希腊神话中有着同性情爱关系的神之间,进行抒情和再现,或惋惜或幻想。
在恩底弥翁的雕像前(1916)
我从米勒托斯来,要到拉特莫斯去,
乘一辆由四头白色骡子拉着的白色马车,
它们的装饰全部都是银做的。
我乘一艘三层紫色船从亚历山大来,
要去主持神圣的仪式—
祭祀和祭酒—纪念恩底弥翁。
这就是他的雕像。现在我陶醉地凝望
恩底弥翁那远近闻名的美貌。
我的奴隶们把蓝里的茉莉全拿出来,
吉祥的贡品恢复古代日子的快乐。
希腊神话中恩底弥翁是人世间最美的人,月亮女神塞勒涅爱上他,并让宙斯把他保存在永恒的睡眠中,好让她每夜都可以去探望他。这个神话中的美男子,牧羊人在卡瓦菲斯的笔下,静默地伫立在那里。诗人化名一个虚构的亚历山大人前往探视,在这里卡瓦菲斯提到了美和雕塑,它们融合在恩底弥翁这个神话人物上,带着对恩底弥翁的迷恋,压力山大人在作者笔下不辞千里赶来欣赏,美凝固成了雕像,诗歌凝缩成了雕像,它们都在诠释卡瓦菲斯对优美地爱恋,恩底弥翁在卡瓦菲斯的诗歌中也多次出现。
亚西斯之墓(1917)
我,亚西斯,躺在这里—我的美貌
尽人皆知,在这个伟大的城市。
智者赞赏我,凡夫俗子也如此。
两方面的赞赏都使我快乐。
但是鉴于经常被视为纳克索斯和赫尔墨斯,
我被放纵累死了。游客阿,
如果你是一个压力山大人,你就不会责备我。
你知道我们生命的步伐—它的狂热,它无与伦比的感官享受。
亚西斯也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在神话和历史题材中加入想象和杜撰的人物是卡瓦菲斯诗歌的特点,这一点和葡萄牙诗人佩索阿有着相同之处,佩索阿甚至用塑造不同人物来完成诗风看似变化的诗歌,正因如此,后来Stelios Haralambopoulos 拍出电影《佩索阿遇上卡瓦菲斯的那个夜晚》 Τη ν χτα που ο Φερν ντο Πεσσ α συν ντησε τον Κωνσταντ νο Καβ φη (2008)中以伪纪录片的形式,讲述卡瓦菲斯和佩索阿两人在去美国的船上相遇并互相谈论诗歌和创作,对二人进行了各自的书写。我们回到这首亚西斯之墓,诗歌中纳克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河神基菲索斯的儿子。仙女厄科绝望地爱上他,但遭到拒绝,香消玉殒,最后只剩下声音。阿芙洛狄特为了惩罚纳克索斯使他自恋自己水中的倒影而死。诸神遂将他变为水仙花。在这里卡瓦菲斯仍旧运用神话传说和杜撰人物来说明亚历山大人,生命的步伐是对美的追求,而美的一部分就是无与伦比的感官享受,它由亚西斯这个虚拟人物以静态的方式展现。
在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卡瓦菲斯的情诗和神话题材诗歌,在描述爱情或者情欲的作品当中,不论是题材还是诗风都明显呈现如雕塑一般简约深刻的特点,而它们指向的就是对美的向往,这种对美的向往和渴望以年轻美男子作为载体,带着希腊人骨子里特有的享乐情怀,在诗歌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读者在感受到诗人凝练的诗风,简单的话语和内心压抑而强烈的冲动,他感受希腊曾经坚不可摧的情怀,感受美无处不在如爱琴海上的风,感受年轻时候欲望和感官带来的享乐,和享乐背后一去不复返的时光流逝。随即凝缩成各式各样的雕塑在诗人头脑中永久地封存。
三、卡瓦菲斯诗歌的艺术性与历史主义之关系
译者黄灿然在《卡瓦菲斯诗集》2012年版的前言里提到,卡瓦菲斯的诗歌分为现时的,和历史题材的。在前面部分笔者着重分析了以情诗为主的现时题材诗歌中体现对美的追求和如雕塑般凝固的特点,但是很显然,卡瓦菲斯的历史题材诗歌占有相当重要的篇幅,作为一个亚历山大人,希腊人,卡瓦菲斯总是从大致两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选材进行创作,即公元前三个世纪的希腊,和公元初四个世纪罗马统治下的希腊,而在这两段时期间来回摆动。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国崩溃后由罗马建立起来的希腊附属国时代和基督教刚征服异教徒成为官方宗教的康士坦丁大帝及其继承者的时代。历史题材看似和现时部分毫无关系,但是笔者认为,卡瓦菲斯现时性的感官诗歌和历史题材诗歌是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画等号的,它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一种感官美与逐渐夭折的关系。而亚历山大这座在二十世纪看起来颓败的城正如卡瓦菲斯笔下旬旬老者,在回忆和声色犬马中煎熬。我们首先从《城市》开始。
城市(1910)
你说:“我要去另一个国家,另一片海岸,
寻找另一个比这里好的城市。
无论我做什么,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而我的心灵被买埋没,好像一件死去的东西。
我枯竭的思想还能在这个地方维持多久?
无论我往哪里转,无论我往哪里瞧,
我看到的都是我生命的黑色废墟,在这里,
我虚度了很多年时光,很多年完全被我毁掉了。
你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家,不会找到另一片海岸。
这个城市永远跟着你。你会走在同样的街道上,
衰老在同样熟悉的地方,白发苍苍在同样这些屋子里。
你会永远发现自己还是在这个城市。不要对别处的事物
报什么希望:那里没有你的船,那里没有你的路。
就像你已经在这里,在这个小小角落浪费了你的生命,
你也已经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毁掉了它。
诗人的作品中有实际的城市,隐喻的城市,感官的城市,神话中的城市,更有希腊主义的城市。埃及的亚历山大建于公元前332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在公元前305年至前30年成为埃及托勒密王朝首都,一时间成为地中海和东方各国贸易文化的中心,公元前48年罗马统帅凯撒率兵占领了亚历山大,这座希腊名城经典被付之一炬,成为浩劫。7世纪阿拉伯人进入后亚历山大城彻底衰落,现在的亚历山大城几乎已经无任何古迹,希腊和罗马时期留存的文化遗产似乎都已成为过去,正如导演保罗·索伦蒂诺所拍摄的《绝美之城》所示,虽然拍摄地在罗马,但其实质却如出一辙,卡瓦菲斯生活在这个残存如废墟一般的城市,写下了这首诗歌,亚历山大在卡瓦菲斯眼里都是“生命的黑色废墟”,“虚度了多年时光,很多年完全被我毁掉了”,这种感慨如老人衰老发皱的皮肤,亚历山大就像这个面貌丑陋的老人,徒劳的回忆曾经的光辉和蓬勃,想起年轻时候的感官享乐,而此处的享乐也许正是卡瓦菲斯历史题材诗歌中那些微妙的反思和感叹。他说:“我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家,不会找到另一片海岸,这个城市会永远跟着你。”布罗茨基在评论卡瓦菲斯的诗歌中说道:“一个人惟一可以用来对付时间的工具,是记忆,而正是卡瓦菲斯独一无二、感官的历史记忆使他如此与众不同。卡瓦菲斯与其说是比较感官与历史,不如说是把感官与历史等同起来。”卡瓦菲斯不会选择离开这种城市,除了从人本身存在的角度理解這首诗歌,表达生活在别处的徒劳之外,更重要的一点便是对亚历山大城虽然颓靡但仍旧对其曾经的生机勃勃所存有的依恋,而这一切之存在在神话传说和史册当中,唯一仅能够留存下来的美是希腊主义的精髓,希腊语。
在卡瓦菲斯发表的154首诗歌中,历史主义题材的诗占了几乎一半,前面已经提到,卡瓦菲斯称自己是诗人的史学家,主要聚焦于公元前三个世纪和公元初四个世纪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以1918年发表的《凯撒里翁》为例,具体说明卡瓦菲斯在历史题材中所倾注的亚历山大城的爱,亚历山大人的爱,以及这种历史絮语中隐含的对泛希腊化的渴望和推崇,那个曾经伫立在地中海如年轻人青春正茂的肉体的城市,以及城市的落败。
凯撒里翁(1918)
既是为了了解某个时期,
也是为了消磨一两个钟头,
昨夜我拿起一卷
有关托勒密家族的铭文。
对于他们每个人的赞美和奉承
都相差无几。全都英明,
荣耀,强大,慈善;
他们每做一件事都充满智慧。
至于他们家族的女人,贝丽奈西们,克娄巴特拉们,
也全都非凡能干。
当我找到了我想核查的事实,
我本想把书丢开,但是有一段
并不重要的文字提到凯撒里翁国王,
突然引起我的注意……
你就在那里,焕发你不言而喻的魅力。
因为我们在史书上
对你的了解如此少,
我可以更自由地在脑中想象你。
我想象你英俊又敏感。
我的艺术赋予你的脸孔
一种梦幻般慑人的美。
而我是如此完全地现象你
以至于昨天晚上
灯光熄灭时—我有意任它熄灭—
好像你走进了我的卧室,
好像你站在我面前,用你在被征服的亚历山大会有的那种方式瞧着,
苍白而消沉,悲伤中更见完美,
仍然在希望他们会可怜你,他们,
那么渣滓,悄声说:“太多凯撒了。”
恺撒里翁是克娄巴特拉的十五岁儿子,名义上是托勒密王朝最后一个国王,也就是托勒密十六世,尤里乌斯.凯撒与克娄巴特拉的大儿子。公元前被马克.安东尼封为“众王之王”,他在“被征服的亚历山大”遭罗马人奉屋大维皇帝之命处死。卡瓦菲斯在某一天看有关托勒密家族的铭文时,注意到了这个很少被史书详细描绘的凯撒里翁国王,于是开始幻想他是一位英俊健壮而美丽的少年,走进他的卧室,带着一种‘梦幻般慑人的美,在这里诗人说“好像你站在我面前,用你被征服的亚历山大会有的那种方式瞧着,苍白而消沉,悲伤中更见完美。”这首歌在众多卡瓦菲斯历史题材的诗歌中最为典型地体现了卡瓦菲斯笔下感官主义和历史的等同,少年俊美而作为一个少年,带着年轻的气息出现在诗人幻想的夜里,明显的情欲氛围渲染出来,美丽而被征服,这是冲动的欲望在诗句的字里行间被体现出来,不由让我们想起卡瓦菲斯关于现时性诗歌中的简练和纯粹的享乐主义。同时‘苍白而消沉似乎眼前有弥漫出一个微型的亚历山大城市,在历史的战火中硝烟四起,落败而颓靡,最后被罗马人的铁蹄踏过,最后在基督教地入侵下逐渐毁灭。卡瓦菲斯并不排斥基督教,但是正如布罗茨基所说,“导致希腊世界终结的,并不是罗马的征服,而是罗马本身落入基督教手中那一天。在卡瓦菲斯诗歌中,异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互相作用。”他就像是钟摆,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来回荡漾。从其本身来说,卡瓦菲斯就是一个独立的带有人文主义光辉的诗人,宗教和卡瓦菲斯诗歌的关系值得一写在这里不过多赘述。
四、总结
也許我们可以这么说,卡瓦菲斯笔下的众多历史素材,纷纷指向那个曾经辉煌又落败的亚历山大,作为一个希腊人,卡瓦菲斯一生都在不遗余力的从诗歌中来体现希腊的美好和美妙,如感官的放纵,声色的欢愉,对美的追求以年轻男子为载体,这一切也等同于亚历山大这种城市本身。它就像一个曾经风华正茂的俊美少年,被历史撕裂,被岁月蹉跎,年老色衰之后剩下的唯有回忆,智性的回忆,用唯一残存的精华—希腊语来填补,最后凝缩成卡瓦菲斯笔下带有强烈感官情欲色彩的雕塑,呈现纯粹高贵而宁静,简练而悠长的美。
参考文献:
[1][希腊]卡瓦菲斯.卡瓦菲斯诗集[M].黄灿然 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
[2]C.P.Cavafy,The Complete Poems of Cavafy[M].
Mariner Books. 1976.
[3]C.Th.Dimaras,“Cavafy's Technique of Inspiration”[M](1932).translated by Diana Haas, Grand Street, Vol. 8 No. 3 (Spring 1983).
[4]Edmund Keeley,“The Universal Perspective”.In
Cavafys Alexandria. Study of a Myth in Prog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5]J.A.Sareyannis,“What was most precious―his form” (1944), translated by Diana Haas, Grand Street, Vol. 8 No. 3 (Spring 1983).
[6]W.H.Auden.“Introduction”.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C.P. Cavafy[M].translated by Rae Dalven, Chatto & Windus, 1968.
(作者单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
——《魂系历史主义——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