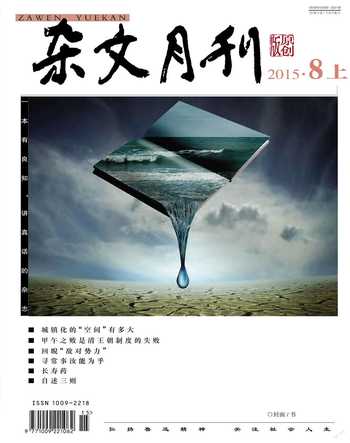青年、利益及其他
郁土
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对学生们说:“这些工作(指政治与现实生活)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能力,各阶层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致使我们精神上的内心生活不能赢得宁静。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日耳曼民族已经把他们的国家,一切有生命有意义的生活的根源,拯救过来了,于是时间已经到来,在国家内,除了现实世界的治理之外,思想的自由世界也会独立繁荣起来。”(《黑格尔对听众的致辞》,刊《小逻辑》)而他对青年抱有莫大的希望:“但我要特别呼吁青年的精神,因为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同样青年人也还没有受过虚妄性的否定精神,和一种仅只是批判劳作的无内容的哲学的沾染。一个有健全心情的青年还有勇气去追求真理……精神的世界就是自由的世界。举凡一切维系人类生活的,有价值的,行得通的,都是精神性的。而精神世界只有通过对真理和正义的意识,通过对理念的掌握,才能取得实际存在。”(同上)
读到这儿,不禁废书而叹。就想到了大学教师钱理群先生。钱先生不能忘怀于中学教育,他从北大退休后,就一直致力于改善它,而结果却是失望。他说:“我对它有两个总结:第一就今天的高中教育来说,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处;第二,就今天的大学教育来说,一切不能为就业服务的教育也似乎没有立足之处。”(《钱理群“告别教育”》,《南方周末》2012年9月9日)
黑格尔认为,青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可钱理群先生却感叹,我们的高中教育就是应试教育,大学教育就是就业教育,这全是“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所以也就没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了!不禁要问,今日之中国青年,難道还不如二百年前的德国青年么?是环境使然,抑或是青年本身发生了蜕变?而青年便是一个国家未来的主人,由现在的汲汲于应试与就业等功利目标的青年,我们不得不为自己民族的未来担忧!
刚读到《西田几多郎简略年谱》([日]中村雄二郎著《西田几多郎》)。有研究者认为,在西田之前日本无哲学,现代日本哲学是从西田几多郎开始的。1945年6月7日西田几多郎去世,1947年7月,“《西田几多郎全集》开始由岩波书店陆续发行,自发行前三天起出版社人行道上就露宿着购书者的长队”。《南方周末》曾刊登过反映购书场景的照片。战败之后两年不到,就有这么多日本人,带着铺盖卷儿,排上三天长队,来购买一位哲学家的全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追求?我不知道。当时,作为战胜国的我们,又在干什么呢?我们现当代的哲学家们可曾享受过如此的尊荣吗?我们有排队购买高考复习资料、纪念邮票与纪念币的盛况,但排队购买哲学家著作的,似乎闻所未闻。1957年的“反右”,1959年至1961年的饿死人,及长达十年的“文革”,是否与缺乏上述这一切有所关系呢?所谓的大和民族,本来一直是紧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行路的,但进入20世纪后,他们跑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兴致所至,乱想一通,乱写一通,如此而已,幸勿见怪。【阎广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