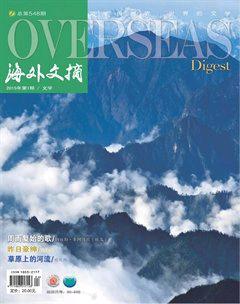送灯
林春山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是人们给故去的先人“送灯”的日子。
这古老的习俗不知是从何时流传下来的。至于“灯”的材质、形状已从我记忆里的形态各异的“豆面灯”,变成了今天的“蜡烛灯”,有圆形的、莲花样的、菊花状的……这些都不足为奇,时代的变迁、生活水平的提高、审美观念的提升,这一些都可以理解。然而,人们行为、心态的改变,让我实在不敢苟同,也让我有一种悲哀的感觉。
近年来,每到正月十五下午两点左右的时候,“送灯”的人们便开始忙碌起来,穿着五颜六色的奇装异服,三三两两地向墓地走去。扛着一箱箱的鞭炮,抬着一箱箱的烟花,挈妇将雏,一路谈笑风生像是去参加一场庆典,去领大奖一般。墓地上,鞭炮齐鸣,烟花竞放,谁也不甘落后,大有攀比夸富之意。这简直是对先人的一种亵渎,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侮辱,是对“百善孝为先”的一种莫大的讽刺。也有一部分人身着素装,在先人的墓前或肃立、或鞠躬、或磕头,显得庄严而肃穆。唉!世间万象,何以评说?
我每年仍是遵循着先人的教诲,不敢有一点造次。
金乌西坠,夜幕降临。此时,热闹了一个下午的山间墓地一片寂静,只有远处的村庄不时地传来腾空的烟火、炸响的鞭炮。我独自来到先人——姥姥的墓前,敬上一炷香,点上一盏灯。伴随着潸然而下的泪水,我长跪不起,记忆的闸门也徐徐打开——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朴素而闪光的形象清晰地展现在面前。
姥姥生于1919年农历八月二十一,卒于2003年农历七月二十一。她18岁来到婆家,28岁守寡,84岁离开了人世。56年寡居,56年坚强度日。56年来,透过亲人和村人乡邻对姥姥的敬仰之情,我看到了她平凡人生中的不平凡。
我从小生活在姥姥家,在我的记忆里,姥姥从来没跟人吵过架,她始终如一的微笑是她一生留给人们慈祥的符号。姥姥走的那天,全村人不分男女老幼自发地为她送行,哭声一片。这哭声绝不是装出来的,这是村人对姥姥一生的肯定。
姥姥一生与人为善,一生循规蹈矩,对上孝敬公婆,对下善待子侄,妯娌和睦,街邻融洽。记得我9岁那年的正月初二,我穿上了唯一的一件打了两块补丁的条绒袄,兴高采烈地要跟大人们去“出门”(走亲戚),这时邻居过来找我姥姥商议借我的条绒袄给她儿子穿着“出门”,姥姥一口答应下来,又反过来做我的工作。这下我可不高兴了,却没办法,只好不情愿地脱下衣服,委屈地哭了一天。
姥姥的父母英年早逝,是在兄嫂的照顾下长大的。姥姥待兄嫂如父母,十三四岁时便帮嫂子织机、做女红、料理家务。姥姥的勤劳、听话,感动了兄嫂,出嫁时,兄嫂给了姥姥最好、最全的嫁妆——楸木的对箱对柜、小柜以及座钟、毛筒等。
来到婆家后,姥姥更是重活累活抢着干,用勤劳和善良感动了婆家人,同时也感动了全村人。侄子要外出上学,姥姥连着几个夜晚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赶做棉鞋,并把自己出嫁时带来的被褥送给了侄子。面对偌大的家庭,姥姥省吃俭用,代替长辈支撑着整个家庭。姥姥又是有名的巧手,她是全村唯一会剪裁衣服的人,90余户的小山村,几乎家家都让她裁剪过衣服。每年的“腊八”过后,刻窗花(剪纸)、做饽饽成了姥姥的“专利”,几乎半数人家的木棂窗上都贴有姥姥精心剪刻的纸花——虫鱼鸟兽、人物形象等,栩栩如生。将近一个腊月都在为别人忙碌,直到将近年关,才抽空忙自己的事情……
我曾聽姨姥姥(姥姥的妹妹)告诉我,我出生后,母亲因患有肺结核病,不能给我喂奶,姥姥便养了一只奶羊,白天我睡觉时,姥姥便去放羊,有一回放羊回来,见我从土炕上掉到地下跌得哇哇大哭,姥姥自责地狠命抽打着自己,并躺到炕上滚到地下,试一试疼到什么程度。这不是故事!我想起来就泪流不止。
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是“农业学大寨”兴修水利的年代,家中没有男劳力,姥姥和男劳力一样,整天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整大寨田,修水库,搬石头,抬泥土,样样不落后,年年得奖状,收工后还要拾草、拔猪菜……
姥姥撑起的岂止是“半边天”!
我12岁时,母亲因病去世,为了攒粪挣工分,家里养了头猪,养猪要吃食,那时,人都吃不饱,猪更不能吃粮食,除了拔猪草外,就是去离村十里路远的县城酒厂买酒糟,每筐一角五分钱。别人家里有大人,能用手推车去推,没办法,姥姥借了一辆独轮小车,让我跟着别人一起去县城。那一天,当我吃力地将酒糟快要推回家时,一声炸雷,大雨骤至,突然手推车翻了,我大惊!恰在此时,姥姥戴着斗笠出现在我面前,我们一老一少,赶紧用手将撒了的酒糟捧到筐里,艰难地推回家。回到家里,我和姥姥抱头大哭一场。从此,我好像忽然长大了,理解了姥姥的艰辛和坚强。
1974年或是1975年,村里要修建一座“过江闸桥”,当地驻军出动车辆,帮忙运来了花岗岩石、黄沙、水泥等,大队安排姥姥做饭招待部队驾驶员,蔬菜和肉、虾仁等都是大队派人去县城买来的。记得有一天中午,客人吃完饭走了,我看着剩下的凉拌菜中有十几个虾仁,不由地咂吧着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虾仁,其实就是海米。只见姥姥用筷子仔细地将虾仁一个个捡到一个碗里,黄瓜片捡到另一个碗里,分别用清水冲洗了两遍,然后放到一边的桌子上,用白纱布盖上,见我那个馋相,姥姥将盘子里的菜汤递给我,说了一句普普通通却意味深长的话:“这是公家的东西,我们不能占便宜,自己吃了填坑,给别人吃了扬名。”姥姥的这句话,令我至今难忘,砥砺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严格恪守做人的准则。
姥姥临走的那天早上,我喂了她一颗剥了皮的葡萄,她却再也没有咽下去。84年人生的苦辣、生活的酸甜,都在那一刻画上了句号!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