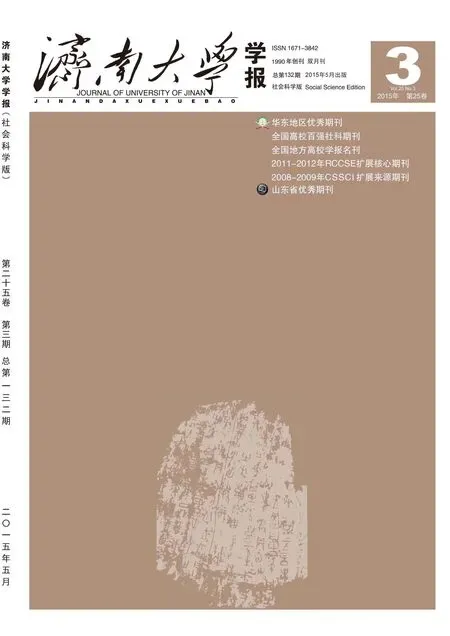拉康学说中的“精神病”
陈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
拉康学说中的“精神病”
陈剑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
在拉康学说中,大他者欲望是符号界的空缺,但它必须以能指的形式支撑符号界。在儿童心理发展上,这可以理解为父名对母欲的命名或隐喻替代。精神病正是拒斥父名的结果。父名的雏形是父亲的禁令,这一能指的隐喻功能建立了语言的第一个意义。精神病由于“父禁”的缺失,语言结构无法内化只能模仿,由此语言成为异物,意义处于漂浮状态。另外,精神病只有遭遇符号父亲才会触发病情,父名从实在界回返,打开一个大他者欲望的空洞,使其不得不以幻觉来填补这一深渊。
拉康;精神病;大他者欲望;“父名”;“父禁”;“纽结点”
精神病(psychosis)涵盖了精神医学领域许多种临床疾病。最为典型的是妄想症、精神分裂、忧郁症、狂躁症等。其病因往往分为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学因素。前者诸如遗传、神经问题,后者诸如家庭、社会环境。[1](P381-384)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破天荒地从符号学的角度解说精神病,认为它无关生物学因素,而是由父亲符号功能的缺失导致的一种心理结构,有一个最关键的能指“父名”(Nom-du-Père)被排除出了符号界。另外,精神病结构也和任何病理症状无关,只有在特定的遭遇下,精神病才会从潜伏导向爆发,“父名”便以幻觉的形式从实在界回返。那么,这个父名能指到底是什么?
一、符号界的空缺:大他者欲望
齐泽克(Slavoj Žižek)曾指出我们这个世界的建构是不完整的,总有一部分是以空缺的方式存在。就像电脑3D屏幕上的一匹马,马的鬃毛、姿态、喘息也许栩栩如生,但如若我们用鼠标点进马的身体,就会发现其内部器官是空白的或未完成的编程。在拉康学说中,这一空洞的存在是符号界(the Symbol)或我们现实生活得以存在的基石,如同一个原始的黑洞奠基着整个宇宙的运行。
对于幼儿而言,最早的不可把握的东西是母亲的欲望、原初大他者的欲望。母亲不能时时刻刻表达对孩子的爱抚,满足其需要,她属于另一个父亲为代表的广大世界。孩子的小小世界总不能明白母亲到底在渴望什么:为什么母亲不看我而要看向无人的窗外?为什么母亲紧紧抱住我却不断哭泣?母亲的欲望代表一个谜,一个深渊,一个幼儿永远看不见的东西。
当幼儿慢慢长大,学习父母教给他的语言及其中包含的各种生存法则。他依然不明白父母的欲望是什么以及如何满足他们。妈妈大声呵斥我,要我洗手系鞋带;父亲看着我,对我微笑或皱眉。他们表达了法则,但他们到底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如何才能让他们满意?这仍是无解的问题。即使我今天令他们高兴了,那明天呢?后天呢?在父母欲望面前,孩子永远是失败者。父母不断变化的表情、语气只能昭显一个难以定形永不满足的混沌深渊。孩子因此感到焦虑。他试图在父母的声音和凝视中捕捉这一不可能的欲望,使其成为一个可把握的客体。这就是拉康学说中著名的“客体小a”(object a),其本质是空无或创伤,是引发焦虑的不可能(确定和满足)的大他者欲望。但它又总是作为对这一欲望的回答,显现在具体的客体上,引导着主体自身的欲望①小孩子最早对客体的确认和恋物癖的逻辑如出一辙:都是将不可能的欲望转化为不可能的客体。但需注意,客体小a并非具体客体,它总是物化又总逃脱物化,它和实在界一样抵制符号化又是符号化的回溯性产物,它和创伤、大他欲望之谜一样代表人类自身存在之谜,是生命矛盾之化身。。
父母的声音和凝视因此作为具体的客体显现,透露着父母的欲望,暗自表达了他们喜欢这样的小孩而不是那样的小孩。小孩借助这些蛛丝马迹构建自己的幻象(fantasy),成为欲望主体。在此,我们有必要区分客体小a的两个层面:作为大他者欲望的层面和作为回答大他者欲望的幻象层面。前者属于纯粹实在界(the Real),疏离于符号界;后者却是实在界和符号界的平衡纽结,维系着符号界②拉康的众多核心概念,如原质(Thing)、实在界、原乐(jouissance)、驱力、无意识、主体等其实都涉及了这两种区分,要么疏离或冲击符号界,要么维系或归属于符号界,绝不可一概而论。。
当小孩遭遇大他者欲望时,令其焦虑的声音和凝视并不是父母有意义的话语、有情感的眼睛,而是某个不可触及或不透明的点。无论小孩如何努力,父母也不会完全满足,他们的欲望在一个不可听不可见的地方。在当母亲不再说话,父亲扭过头去,这才是深渊般大他者欲望之表达。我们只能用沉默来表示声音,用盲点来表示凝视,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大他者不可定形和填补的欲望之谜。齐泽克也因此说:“客体凝视是可视领域的盲点,而客体声音当然是默不作声。”[2](P135)客体小a的本源总是焦虑,是一个不可能镜像化、符号化,也未附以幻象遮蔽的混沌空缺,代表符号界的起源、断裂和开口。它其实就是大他者欲望,是一个不可测不可解的实在界黑洞,在拉康欲望图表上标记为“A/”,表示法文大他者“Autre”被划杠的形式,意味着大他者或整个符号界空缺的那个部分③这帮助我们理解在拉康思想中,为什么欲望就是空缺。但需注意,作为“纯粹欲望”本身,绝不同于被幻象牵引的“幻象欲望”,两种空缺是不同的。前者接近于作为空缺的实在界“A/”,这一空缺未被命名,也不存于符号界之中,它被拉康借用海德格尔的概念称为“外于—存在”(ex-sistence,ex-ist);后者则是欲望无休止的追逐(换喻)过程,客体只要符合幻象就会激发欲望,却又永远不可填平它。人们只能周而复始去满足那虚妄的欲望之洞。——拉康几乎科学地诠释了佛教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或许,它可称为“原初之空”。
然而,幻象中的客体小a绝对不能写作“A/”,它恰好是对大他者欲望的某种形式化具象化以及内在化。它的作用是安抚焦虑,屏蔽大他者的不一致,将驱力纳入幻象和欲望中,维系符号界的统一感。大他者欲望一旦在幻象中被回答,就成为了主体自身的欲望④此时,客体小a如同不可捕捉的幽灵附身于各色客体上又一触即逝,始终牵引着我们的欲望追寻。,支撑着主体的符号法则运行。
无论如何,“A/”总是优先于幻象公式S/◇a中的小a。我们必须先面对大他者欲望之谜,才能回答这一谜语。因此,作为焦虑的客体小a,作为空缺的大他者欲望,是整个主体生涯的开端。人类的主体和主体法则总以这个“原初之空”为基点而建立。大他者总是欠缺的,我们必须承担这一事实,才能建构出幻象、欲望、法则等一切主体必需之物。而拉康学说中的精神病,恰恰是因为拒斥了这一事实,拒斥了母亲欲望的存在,拒不接受这一欠缺的能指化,它并不算真正的主体。
当然,我们必须知道,对于人类这种语言的动物,面对、承担一个空洞的事实就是给予它一个能指,命名它,而这个能指、命名就是人类整个符号世界、现实生活的开端。“A/”在符号界中因此显现为“S(A/)”,即大他者欲望能指,大他者空缺能指,它标示着一个已被符号化的空缺位置。
二、精神病:拒斥阉割
在拉康学说中,拒斥(foreclosure)、否认(disavowal)和压抑(repression)是不同的,三者是面对阉割的三种不同姿态,分别产生精神病、变态狂和神经症三种心理结构。简单说来,三者从重到轻地代表了对大他者(母亲)欲望及父亲功能的否定。当然,没有人可以完全接受阉割,成为所谓的“正常人”。
阉割在弗洛伊德笔下原指阳具被父亲割除的幻想。小男孩总怀有对母亲的爱欲并把父亲视为竞争对手,父亲代表着禁忌的法律,约束着幼儿的爱欲和快感。当小男孩发现女性没有阴茎,会认为她们已被父亲阉割,这无形中加深了父亲的权威。在阉割焦虑的促成下,小男孩开始放弃母亲认同父亲,这也是男性俄狄浦斯情结的完成。对于女孩,则因为天生没有阴茎而感到生理缺陷,并渴望拥有一个孩子做为弥补。因此,阉割总是一种因父亲产生的匮缺感。
拉康从父亲符号功能的角度重新解说了阉割:无论男孩女孩,母亲都是他们的原初大他者,孩子们最早都把自己当作母亲的欲望对象,即想象菲勒斯φ,并认为母亲没有缺失,没有除自身之外的欲望。但由于父亲的干涉或父亲名义上的存在,孩子们逐渐明白母亲的欲望不在自己,母亲望向父亲的目光显示了她不安的欲望,也引领着孩子的欲望走向外界,走向一个父亲为代表的广大能指世界。孩子们在这个世界直面了作为空缺的母欲,母欲获得了命名①裂大他者欲望并不只是母欲,其命名也不一定和父亲有关系。在小孩眼中,大他者欲望可以是一切重要照料者的欲望,其命名也可以关系任何权威指向。但母亲作为人类的生育者,父亲作为家庭的主宰者,以其为原型描绘一个最重要的能指的诞生,这既方便理解,也普遍适用。,“原初之空”获得了能指,这一能指就是大他者欲望的能指S(A/),也被称为“父名”(Nom-du-Père,Name of the Father)②这一能指有众多头衔或称呼:父名、菲勒斯能指、大他欲望的能指,大他欠缺的能指、主人能指、优势能指、空位能指、没有所指的能指,等等。它本身只是符号界的一个空洞,其原初的命名是(神经症)主体诞生的前提,从而避免了精神病和变态狂的命运,但其实它也可以再度命名,这就涉及到新的主人能指对符号界的重组和革命。。但父名本身并不意味着给予母欲一个定义或内涵,而是引入一个符号之“空”,将孩子由一种实体关系中解救出来获得某种能指的自由。正是在父名对母欲的替换中,在第一个能指的隐喻功能里,在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的表征下,主体获得诞生!父名就是主体能指结构(符号界)中画龙点睛赋予灵魂的奠基性能指,相当于一个电脑编程的“空白启动键”,开动运转了主体的整个能指系统。
拉康所说的阉割正是父名替代母欲这一符号功能的实现,人类因此获得一个关键的匮缺能指。精神病完全拒绝阉割,拒绝母亲欲望的存在,仿佛阉割从不曾发生。它的做法是将这一母亲欲望的能指“父名”逐出符号界,排除在意识和无意识之外,主体的能指结构因此就在中枢地带直接剜出一块空洞,“原初之空”也因为没有能指位置,就留存在实在界中也总从实在界回返,这就是“拒斥”;至于变态狂则部分否定了父名,它遭受了父亲的禁令,知道母亲欲望的存在,但拒绝接受、承认,这就是“否认”;神经症则建立了父名这一能指和主体的法则,却将与驱力有关的想法压抑在无意识(本我)中,这就是“压抑”。三者的区分其实在弗洛伊德的笔下就有了:“拒斥所描绘的并不是(像有时讨论压抑那样)简单地在自我(ego)中或以自我抛弃一些东西,也不是(像有时讨论否认那样)拒绝承认记忆中曾目睹并储存的某物,而是从自身——并非仅从自我中——抛弃一部分现实。”[3](P76)
那么,为什么精神病没有实现父名对母欲的命名呢?我们可以简单地设想父亲没有有效干涉母子二元关系,父亲的缺席或母子的过分黏着使孩子一直把自己视为大他者的欲望客体,因此拒不面对母亲真正欲望的存在,拒斥以“父名”命名之而导致了“缺失的缺失”③阉割就意味着无论你有没有阴茎,你都必须以一个能指承认自己没有。这无关男女!让我们回想一下弗洛伊德笔下的狼人是如何面对“缺失的缺失”的。当他没有遭受阉割,就一直怀疑自己的鼻子有毛病,当医生判定这只是疑病妄想,反而令其不堪忍受的焦虑,觉得自己已无药可救。。但我们必须注意,拉康强调的被拒斥的元素并不是血肉父亲,而是父性功能(paternal function)作用下的父名能指。在学者布鲁斯·芬克(Bruce Fink)眼中,父性功能和父名是等价的,两者决不等同于一个血缘父亲或活生生的父亲。父亲的在场或缺场并不能保证或废除父性功能(对于能指而言,缺场和在场并无区分)。这一功能可能由任何一个代表父亲形象的男人来执行,也可以只是通过母亲的话语来表达,甚至只是借助社会文化的影响而实现。哪怕一个寡妇或老师说“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他定会因你蒙羞”,甚至“如果你再调皮,警察叔叔就来抓你”,父名也可能建立。它只是一个表示权威的功能性位置,并非真正主宰。父亲大他者(父他,Father)扮演的角色只是毁灭了母亲大他者(母他,Mother),将孩子从危险的被视为母亲阴茎的母他关系中拯救出来。因此在本质上,父名只是原初大他者关系——母子关系中的一种痕、空洞或否定性,是一个对母子缠绵爱欲大喝的“不”!孩子大多能敏锐地感受母子关系之中引发窒息的母爱和引发焦虑的母欲,并渴望之外的一个解脱,一个权威保证,一个最终的真,这个就是父名。孩子借此获得母亲之外主体欲望的空的支点,一个超越母亲怀抱、母亲权威的位置,一个摆脱窒息母爱、焦虑母欲的空间①如若母亲的欲望不是空缺,不是母子关系的一个开口,那就只是使孩子无法获得独立自由的窒息母爱。如若母欲不能被命名被超越,那就只是引发孩子无限焦虑的空缺和失落。弗洛伊德的小孙子在玩“去/来”(fort/da)游戏时,他绝不仅仅在用能指平抚母亲离开的伤痛,更多的是渴望摆脱窒息母爱和母欲焦虑。当我们跻身这个符号世界,最初的母爱绝非我们身心的最终栖所,母亲并非一个自在自为的完整天堂,她的欲望打开母子关系的一道裂口,父名命名母欲则使我们走进广大的能指世界。。
当然,拉康并不是父亲传统角色或父权的鼓吹者。即使在单亲家庭,母亲也可以扮演好父性功能的角色。重要的是母亲如何定位某种超越自身的东西(母欲→父名),“母亲如何设法含蓄地向孩子指出,存在一个他们都与之相联系的象征网络,并且这个网络超越她们两者之间的想象关系”[4](P103)。
父名可能以各种方式发生。但对于精神病,窒息的母爱淹没了孩子,焦虑的母欲则从未显现,父名更无从谈起。这往往是因为母亲对父性功能的干扰。即使孩子的父亲在场,阻隔了母子关系,并表达了权威姿态:“你不要和母亲那么亲密。”“这是我说的,你就应该这么做。”但如果母亲总在父亲的背后屏蔽掉父亲,继续保持与孩子的二元爱恋:“不要管你父亲,咱们继续玩游戏吧。”或者“这是咱们的秘密,不要告诉你父亲哟”。孩子就有可能拒斥母亲欲望这一事实,忽略父性功能的影响,形成精神病的心理结构。或许这也可视为对母亲色相最深的沉迷。
三、“父禁”或根本纽结点的缺失
法语的父名“Nom-du-Père”其实有两层意思:“Nom”的意思是名字或名词,意味父亲的符号性存在;但“Nom”的发音又类同于“non”(不),整个单词读出来就是父亲的“不”,表示父亲的禁令,指父亲对母子关系的禁止和否定。当孩子出生后,母亲往往是最初的照料者,她用爱接纳孩子并在自己的世界里给予其一个位置。最早,婴儿和母亲就像一体,他无视母亲欲望的缺失,无视父亲的存在,把自己当成母亲“想象的菲勒斯”、阴茎的替代品,并将母亲(如乳房、怀抱)作为自己的原乐资源而霸占享受。但这一关系往往被父亲的禁令所打破,比如“你够大了,只有婴儿才需要妈妈”。孩子慢慢感觉到母亲的亲吻、拥抱变得矛盾而恶心,曾经那个给予他原欲满足和快感享乐的母亲不复存在了,一个原乐母亲在父亲的禁令中被压抑了。
因此,拉康所说的“父名命名母欲”可分出两个阶段[3](P91-93):父亲的“不”取代作为原乐的母亲是初级阶段,即“原初压抑”,也被拉康称为“异化”(alienation)②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一个东西被拒绝,我们才能看见自己的渴望和欠缺。只有当作为原乐的母亲被禁止,孩子才欲望成为母亲的欲望客体。异化不仅是父亲的禁令实施的过程,也是孩子开始欲望母亲的过程。精神病没有经历异化,他本来就是母亲的附属阴茎,而不是像变态狂那样,欲望自己成为那根阴茎。;父名对母欲的取代则是高级阶段,即“次生压抑”,也被拉康称为“分离”(separation)。对于精神病,压抑根本没有发生,不仅父名缺失,其雏形“父禁”也缺失。

严格说来,人类符号体系中第一个隐喻功能是由“父禁”制造的:父亲的禁令给予人类的原初存在“母子关系”一个意义,一个外在的否定性支点给予了整个宇宙第一个意义联系,这个意义就是你对母亲的渴望是错误的,母子合一是不可能的,你不要再妄想回到子宫里去,在羊水和胎盘的滋润下沦为一团原乐!人类出生后必须继续脱离母体、否定恋母。这本质上是对混沌或原乐的否定,是人类符号世界打下的第一个桩,是其结构固定点,语言和意义的联系因此确立:父禁=存在否定。
在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人们渐渐明白世界只是一个语言化符号化的世界。拉康更指出,能指的意义是在相互联系和差异中产生的,能指之外只是混沌,物(Thing)是不可追寻的,那么意义的支点究竟在哪里?拉康并不如解构主义那样让世界不停晃动,否定一切意义的确定性,他为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支点、一个外在的否定性——父禁,或许可称之为“原初否定”。即使有新的主人能指(如基督徒、共产主义)占据了父名的位置,革新符号界,但“父禁”是不会变化也不可能撼动的,这是一根孙悟空也挪不走的“定海神针”。无论人类和个人的精神世界如何日新月异,生命的第一个意义一旦建立就永不动摇。因此,“父禁”既是生命和语言同化、存在和能指勾连的第一个扣钮,也是生命意义唯一不变的根本保证,是拉康所谓的“纽结点”(button tie)①这个也被翻译成“锚定点”(anchoring point)或“缝合点”(quilting point)。但布鲁斯·芬克指出,能指和所指、语言和存在之间的融合并不借助一个真实的锚定处、一片稳固的大陆或一个绝对的指涉物,而仅仅是相互纽结。之上的“根本纽结点”。不幸的是,精神病恰好缺失了父禁(以及父名与符号界大他者),语言也就失去了其根本纽结点,无法形成一个心理内化的稳定结构。对于正常人而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虽然我们自出生就被抛入语言中被其言说,语言异化了我们,但我们总在语言中为自己发现一个地方,最大程度使语言成为我们自己的。我们总使语言主体化,吸收、同化一个语言子集,内居于其中。但对于精神病而言,语言无法同化,只能模仿,语言作为异物侵占了肉体或存在,语言即使形成一些稀疏、不合格的纽结点暂时固着意义,但意义仍会漂浮不定,也随时可能崩塌。
四、精神病的发作:遭遇符号之父
简单说来,作为一种心理结构,精神病就是母子关系的三角化(triangulation)没有发生,父名(父禁)没有横入其中组建三角关系。而父名的建立有一个年龄的最大限度,一旦过限,也就不再可能。因此,小孩的精神病也许可以通过分析师的干预而转变为性变态或神经症,但成年人的精神病在结构上是不可能改变的,只能缓解其病理特质,防止其发作,使其承担生活。当然,结构和症状始终是两个层面的东西,有许多精神病在很多年来甚至一生中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精神病症状,譬如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就是拉康深入研究的“非触发性精神病”(non-triggered psychosis)的代表。
那么,精神病如何才会发作呢?精神病结构虽是个先决条件,但有此潜质的人往往借助生活的想象关系和模仿角色来调节自身世界的稳定②在病症发作之前,精神病有时甚至比普通人更能适应迥异的文化环境、生存场景,他们借助高超的模仿能力甚至比普通人更成功更顺利,而不必经历普通人在不同角色担当中常遭遇的“转换休克”(transition shock)。,只有当缺失之物“父名”需要在符号界中担负其作用,能指结构中这个空缺被召唤和激发,原有的平衡才会陡然崩溃。拉康的认识是:
导致精神病发作的催化剂是遇到了某种让主体唤起父性观念的场景,例如让一个男人成为父亲,或者让一个女人分娩之后从别人手中接过自己的孩子,当然还包括工作职业的晋升,或者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象征地位的改变。所有的这些情境都会向象征性的父性辖域发出召唤,但是那里什么都没有,主体便面对着一个空洞,一个缺口。[4](P106)
父名在其符号位置被召唤,与原有的心理平衡形成对抗,导致了某种欠缺的直面,拉康将这种情况命名为“大一父亲”(Un-Père、One-father)的在场,每一个精神病的爆发都起源于这样一次遭遇,即遭遇了作为纯粹符号功能的父亲,一个缺失了必要能指的权威性位置。布鲁斯·芬克指出,这既可能是遭遇一个代表符号父亲的他者形象,也可能是自己要占据这样一个符号位置。前者诸如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看见她丈夫怀抱孩子的表情,一个悔罪者面对慈悲而肃穆的神父,一个恋爱中的少女遇见其爱人的家长;后者诸如一个男人要当爸爸了,或者要扮演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公正的”父亲角色。
譬如,弗洛伊德笔下的史瑞伯(Schreber)案例,拉康认为患者精神病触发正是因为他升迁为大法官同时又无法生育,不得不面对实在界的父子关系,因此以上帝要娶他为妻的幻想来填补这一实在界的空缺。这种新的宇宙观当然也是重建意义世界的努力。[5](P260)
对于正常人(神经症),当父名被召唤时,一个能指担当了其职责;而对于精神病人,由于父名缺失,其无法运作在符号界③这就是为什么精神病也有无意识,但它不运作的原因。无意识的运作总和与大他者(父亲)的符号关系,即父名的驱动相关。,只能(以另一种形式)返回于实在界中。病人只能直面一个大他者欲望的深渊,并试图用幻觉来解释这种欲望,用某种类似父子关系的信息来填补这一实在界空缺,诸如“外星人要来抓我了”,“上帝已经选择我作为天使了”。
这和神经症的幻觉不同,因为精神病是如此确信这个幻觉的意义。它告诉病人大他者对你的欲望是什么,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因此,它扮演了父性功能的作用,但不在符号界(现实)而是在实在界中。如果我们忽略这一幻觉和人类符号界的碰撞冲突,可以说它同样是精神病人的自我治疗。
如前所述,意义必须有一个组织能指的奠基点,一个关于人为什么活着的核心旨归。正常人以“父名”纽结点为统帅,它并非一个具体意义,而是一个权威性的位置保证,证明有个东西在宇宙和生命的绝对中心,一切能指都向它效命①齐泽克曾论述《旧约·约伯记》中的上帝正是一个父名纽结点。人为什么要受苦?世界为什么如此混乱?上帝从来不曾回答约伯的问题,他只是以一系列创世以来的骇人图景表达自身的至高无上。不要追问我生命的意义!不要追问我(大他者)要你具体干什么!这世界远比你遭遇的一切更加混乱苦痛!但我就是权威,你必须在我名义下重面宇宙之混沌,只有这样才能确立活着的意义。对大他者欲望之谜,人的存在之谜的回答只能基建于一个绝对的空的主人能指之上。。而精神病发作时因为没有此纽结点,只能由有关大他者的幻觉来暂时保证意义。那些幻觉多半是惊恐、怪异、热狂而飞舞易变的。
那么,有没有一种不和现实冲突的合适幻觉给予精神病人较稳定的生活意义呢?我们不由思考,相信上帝创世末日审判难道不是幻觉?相信因果报应菩萨救苦难道不是幻觉?甚至,相信爱情和事业难道不是幻觉?在拉康学说中,可以纳入并支撑符号界的幻觉就是想像界。如果精神病人可以找到一种“符合现实”的与想像大他者的关系,以此作为寄托和使命,他拥有的就不再是精神病意义上的幻觉,而是符号化的信念。
因此,对于精神病,无论是潜伏的还是显性的,分析师永远不要像治疗神经症那样扮演一个符号大他者(符号之父)的角色②对于神经症治疗,拉康前期强调分析师的父他角色,晚期强调客体小a的角色,这两者并无矛盾,客体小a代表的是大他者欲望之谜,是父他的开口和颠覆,促使患者在符号界中重新定位。,这只会导致病症的爆发或更严重。而只能作用于其想像界,帮助其尽快建立一个新的合适的“妄想隐喻”(delusional metaphor),一种想象界的父子关系,令其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自我感觉,建立较为平衡的意义世界。以稳固的想像关系纽结符号界和实在界,令三界再度平衡是大多数精神病人的治疗方法③以想像界纳入符号界再共同遮蔽实在界,帮助三界平衡。这是精神病治疗的主要方法。另一种特例是三界之外的第四环“圣症”(sinthome)也可以起到纽结三界的作用,拉康曾以詹姆斯·乔伊斯为例进行说明。。
[1][法]尚·拉普朗虚,尚一相腾·彭大历斯.精神分析辞汇[M].王文基,沈志中,译.台北:行人出版社,2001.
[2][斯洛文尼亚]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3]Bruce Fink.A Clinical Introduction to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Theory and Techniqu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4][英]达瑞安.里德尔.介绍丛书:拉康[M].李新雨,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5][英]迪伦·伊凡斯.拉冈精神分析辞汇[M].刘纪蕙,廖朝阳,黄宗慧,等,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
责任编辑:杨旻
B84
A
1671-3842(2015)03-0068-06
10.3969/j.issn.1671-3842.2015.03.11
2014-11-01
陈剑(1981—),男,湖南邵阳人,博士生,主要研究西方文学与西方文论。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及国际传播研究”(12@ZH009)子课题“中国发展道路中价值理念的国际传播方式创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985项目“西方文论题义释读”。
——拉康对《孟子》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