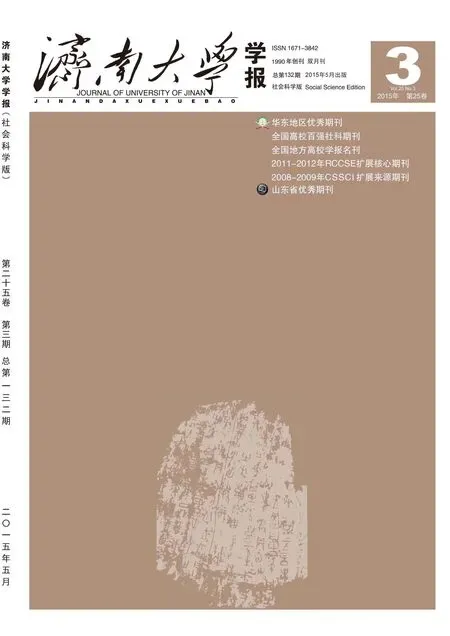上古刑罚与身份
吕利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上古刑罚与身份
吕利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刑罚,通常被理解为通过剥夺权益或者造成身体上的损害而给犯罪者施加一定精神、肉体上的痛苦的制裁措施。然而,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刑罚史上,比财产的损失、肉体的痛苦更深刻的是人格的贬损。犯罪者往往被逐出社会,丧失社会人格,从而改变身份,并丧失附着于身份上的宗教的、家族的、政治的、财产的等各项权益。“刑罚”与“身份”密切相关,构成古代“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中的重要一环。身份是理解中国上古直至秦汉帝国初期刑罚体制的关键起点。
上古;秦汉;刑罚体系;身份;肉刑
“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是梁治平读了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之后,对中国古代社会与法的关系的再一次提炼和概括。然而怎样的身份?何种伦理?在社会历史演进的不同阶段则各有差异。上古不同于中世,中世又异于近代,非笼统的官民、良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及相应的纲常名教所能概括。
刑罚是通过剥夺权益或者造成身体上的损伤而给犯罪者施加一定精神、肉体上的痛苦的制裁措施。在人类社会早期的刑罚史上,除了支付赎金、同态复仇等比较常见的处罚措施以外,这种剥夺往往表现为将犯罪者驱逐出社会,从而使其丧失社会人格,改变身份,并丧失附着于身份上的宗教的、家族的、政治的、财产的等各项权益。在中国古代刑罚制度中,截止到秦汉帝国初期,透过国家制定法,在中央集权的君主官僚制国家的刑罚体制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种身份要素的存在。然其形成与原理,只能从更古时代的追溯中获得。
一、上古刑罚体系
(一)传世文献中的上古刑罚体系
传世文献关于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尚书·吕刑》有“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以穆王训示的形式追述了“五刑”的起源: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①[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这就是囊括了肉刑和死刑的、传统上被称作奴隶制“五刑”或“前五刑”的上古刑罚制度。它源于苗民社会,包括割耳或鼻、毁坏生殖器官、以墨刺面及杀戮。其他文献表述略有差异,有称作“墨、劓、剕、宫、大辟”者,亦有以“刖”或“髌”代“剕”者。绵延至于秦汉帝国初期,于国家制定法所记载的刑罚体系中被规定为黥、劓、斩左右止(趾)、腐以及弃市、腰斩、磔、枭首等死刑。
《尚书·虞书·舜典》记载的舜帝时期的刑罚制度及其实施,似乎已经颇成体系,五刑之外犹有流刑、官刑、教刑、赎刑。曰: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災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①[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由此有“象形”之说,《尚书大传》释作:“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屡,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慎子》则与五刑联系起来解释:“有虞之诛,以幪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屡当刖,以艾畢当宫,布衣无领以当大辟,此有虞之诛也。斩人肢体,鑿人肌肤,谓之刑;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当世用刑而民不从。”荀子反对,讥为是世俗谬说。[1](P5-6)
又,舜帝命皋陶作司法官,其训词中亦提及“五刑”“五流”,曰:
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②[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皋陶作“士”,此处“士”实为主“刑”的官,包括“五刑”“五流”。
如此整齐划一的、体系化的刑罚制度,又见于《吕刑》关于赎刑的记述中,等而下之有“五刑”“五罚”“五过”诸种处罚措施。曰:
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③[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五刑”即前文之“肉刑”和大辟;“五罚”即所谓“赎刑”,由五刑衍生;“五过”或对应更轻微的处罚措施。
又《国语·周语上》“内史过论晋惠公无后”,内史过亦述及古代刑制,曰: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于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蛮夷之国,有斧钺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纵其身乎?[2](P34)刑辟所对为“斧钺刀墨之民”——刑余之人;被流放至边远荒僻地带的族群则繁衍生息聚为蛮夷之国。
另外,在对商代甲骨文的考订中,有学者认为殷商甲古文中已有对应黥、劓、刖、宫、大辟等五刑的文字。[3](P28-30)
上述引文绝大多数出自《尚书》。《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孔子有所斧削、择其雅驯之类不必怀疑,其后辗转流传又有今古文之争,更增加了其不确定性,致使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谦抑的态度。然而在这种必要的谨慎中,从事法制史研究的学者尚居优势。因为法律制度在发展演变中有其内在逻辑,法律的连续性、统一性、确定性、实践性;法律术语与日常用语、学术语言的差别等,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线索,慎思明辨之后,可以寻得更多的确定性内容。《周礼》也是如此。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的问世,也为我们提供了更明确、更可靠的参照系。
(二)“刑”辨
以秦汉以前的中国法制史为背景谈论“刑”,应作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刑”,与“德”对称,泛指一切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措施,即刑罚,为叙述性语言,《尚书》《周礼》行文中常见,如前文中“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狭义的“刑”,则是“斩人肢体、凿其肌肤”之刑,专指黥、劓、斩、腐等残损肢体的肉刑,见于法律文本,也见于《周礼》《尚书》的记述性文字中。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使用的“刑”字,皆指肉刑或毁伤肢体的行为(比如睡虎地秦简中有“父擅杀、刑、髡后子”)。甚至某些“概念”,如“赎刑”,出现于《吕刑》的叙述性语句中(记载赎刑具体内容的正文部分并没有出现),在睡虎地秦简中也有出现,只是其内涵,与《吕刑》及一般法制史教科书中作分析性概念使用的“赎刑”大相径庭。律简中的“赎刑”二字,是“赎黥、劓”和“赎斩、宫”的统称,它甚至不包括“赎死”。这说明在官方正式的法律文本中,直到秦汉帝国初期,“刑”字仍然是在狭义上使用。至于“刑”字何时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把肉刑以外的制裁措施也包含进来,不可确知。在阅读《周礼》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其混乱,《尚书》也是如此。但透过《周礼》的某些记载,我们又隐约可以看到,“刑”和其他一般性处罚措施之间存在的质的区别。根据《周礼》的记载,负责教民的地官司徒之下有掌管“民之衺恶过失”的“司救”,以及维持市场秩序的“司市”,二者都有权对一些顽劣之徒或者有违规行为的人进行处罚。其中司市所施叫做“市刑”,曰:
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扑罚。其附于刑者,归于士。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可见,所谓“市刑”不是真正的“刑”,与其说是“刑”,不如说是“罚”,是类似于今天的“行政处罚”。最轻的处罚是以书面的形式公示、宣布其过恶;稍重的则及于人身,即被强制进行游街示众;最重的“市刑”是对违法者进行鞭挞。有严重的过犯,以致依法规定当处“刑”的,则须提交给专门的司法官(刑官)——“士”来纠治。此处“刑”当属肉刑一类的处罚措施。
《周礼》关于地官大司徒自身的职掌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有按上述思路才能理清。曰:
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②[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八刑”应和“市刑”相类,属于“罚”,不在“刑”的范畴。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但凡涉及到“刑”的适用,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皆自成体系。从皋陶作士开始,至《周礼》之秋官大司寇,到其属官中的小司寇和各级的“士”,皆为刑官。由大司寇“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当然,从行文来看,至少在《周礼》成书时代,“刑”在日常行文当中,已经是广义的了,涵盖了众多的以公权名义施加的处罚措施,而不是专指“肉刑”。这就是所谓“历史语言”问题。有学者试图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的检索来弄清“刑”字的来历。结果确认甲骨文、金文中最早只有“井”字,其原始意义应当是“型”,即浇铸器物的模、范。使用中,多作人名、地名,也有作“遵循、以为楷模”解。西周时期,少数金文中出现了作“法律规范”或“刑罚”解的“井”。而“刑”字,则仅见于东周器,应为“井”的派生字,因从“刀”而更能表达刑罚杀戮之意。[4](P12-13)也许恰恰是这种貌似合理的分野,加之假借等书写习惯,导致上述混乱及对古代刑制理解上的困境。
具备以上识辨能力,反观前述诸引文,不管历来解释上有多少分歧,关于上古时代的刑罚体系,可以确信是:刑罚体系的核心是“五刑”,(即肉刑、大辟)和“流”。至于鞭、扑,所谓“官刑”“教刑”,或许如“市刑”,为一般负责教民的行政官员或家长、族长所用的轻微的处罚措施。至于“赎刑”,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不过是“刑”的派生物,其基本原则是“刑疑从赦”。即在坚持“以刑统罪”的立法传统的同时,开始区分不同的犯罪情节,对那些情节较轻,倘施以“肉刑”明显有违“罚当其罪”的朴素的正义观的行为,则赦免之,改处强制缴纳一定数量的财产。[5]《吕刑》并未严格区分“罚”和“赎”,甚至所谓“赎刑”,实际上就是“五罚”。“赎”是从“刑”中派生出来的,或许仍属于狭义的“刑”的范畴,有别于秦汉时期的“赀”和“罚金”。
二、上古刑罚与身份
(一)刑罚的原始机能及身份后果
身份是个关系的概念,它存在于主体与共同体及共同体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中,用来表明个人之社会属性。罗马法研究者把它定义为:每个人所处的由权力、权利和义务构成的情势,与主体所属的一个更广泛的单位有关。[6]就社会身份而言,在古代,这个与之相关联的更广泛的单位可能是邦国、城邑、氏族或者氏族的联合体。为了公共的利益,这些共同体本能地赋予自身一种权力,就是“谁扰乱了公共安宁,谁不遵守法律,即不遵守人们借以互相忍让和保护的条件,谁就应该受到社会的排斥,也就是说受到驱逐”[7](P66)。这就是滋贺秀三先生所说的,“刑罚的原始意义和机能”,“在于把恶人逐出社会”[8]。被自己所属的共同体开除,对主体而言,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人格的丧失。
驱逐的最直接的表现是“流放”,对古代社会中的人来说,不仅仅是离开故土,更是社会关系的隔绝。
在诗人的口内,曾述及放逐的可怕字样:“命令说:他去吧,他永远不准再进庙内。任何公民皆不准与他谈话和招待他。任何人皆不得准他参加祷祭,或给他洗水。”……法律说:“与同饮食者,近之者,皆须祓除。”[9]
古郎士这样描述被放逐者所失去的东西:
被放逐者的宗教被褫夺了。民权与政权皆出自宗教。被放逐者于失掉宗教时,同时也失其一切权利。被放逐于邦宗教之外,他同时失掉其家族宗教,而熄灭其家火。他再无产业权,其田地与财产皆充公以奉神,或以归国家。既无宗祀,则亦无家族。他亦失去其夫或父的资格,其子不归其管理;其妻亦不再是其妻……[9]
放逐导致被放逐者在该共同体法律人格的丧失,因为古希腊人相信“城邦之外,非神即兽”。换成中国语境,是“名”与“分”的尽失。
就丧失法律人格而言,死刑和放逐的效果是一致的,但相对来说,作为对本共同体成员的处分措施,放逐显得更仁慈一些。因此,在古代罗马的司法审判中,流放和极刑(pena capitetle死刑)就有着直接的关联。“早在民众会议诉讼中,人们就允许在判刑前通过流放来避免极刑,这意味着宣布aqua et igni interdictio(流放),其后果是丧失市民籍和没收财产(publicatio),而且流放者不得返回自己的祖国,否则可能遇到生命危险。有些法律还明确规定被判处极刑的人有权以上述方式自我流放。”因此,“在实践中,这种流放是判处极刑的一般后果”。[10](P275)上古中国也是如此。前文引《尚书·舜典》曰:“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有学者认为,“流”“放”“窜”“殛”都是流放。[8]所谓“流四凶族,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舜流放的“四凶”是四个家族,其被逐,是被联盟所抛弃。这也是内史过所言“蛮夷之国”的来历。另,止国人谤的周厉王也被流放,是为国人和贵族集团所驱逐。滋贺秀三以盟誓为线索对中国上古刑罚制度进行考察,认为上古的流、放,与后世所谓“流刑”是不同的。前者是依据绝交之盟,把受到众人一致非难的为恶者驱逐到共同体之外;而后者则是统治天下的专制君主把版图内人民中的犯罪者强制遣送迁移到同一版图的另一个指定地点居住。[8]
从文献记载来看,除了放逐,中国上古刑罚体系的核心是死刑和肉刑。滋贺秀三先生认为可以也应当从“逐出社会”的角度,一元化地领会死刑、肉刑和放逐刑。死刑、放逐所包含的排斥、弃绝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肉刑。滋贺秀三的“一元化”是针对“中国刑罚起源的二元论”来说的。二元论说在国内外都颇有影响。有日本学者认为:“五刑(即死刑与肉刑)原来是作为对异族人适用的刑罚而产生的,对同族人的制裁,另有一个由放逐与赎刑构成的刑罚系统。”[8]在国内,梁启超先生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梁启超把中国上古时代的国家称作氏族国家、半部落式国家。氏族国家由两部分人组成,即族人和隶民。“族人是享有完全权利的国家共同体成员,隶民是与族人没有血缘关系的被统治者,前者是大夫,后者就是庶人。”而“部落时代之刑律”原是苗民所自创,我族袭用之,专为所谓“庶人”之一阶级而设,而庶人大率皆异族也。而对于贵族中被认为妨害本社会秩序的,则摒诸社会之外,即类似于希腊的贝壳投票制下的放逐。[11]可见二元论与一元论并不完全对立,关键是肉刑问题。
关于肉刑的一元化理解,至少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古书所载的“刑不上大夫”问题;第二,肉刑的意义,驱逐还是报应、残害?首先根据《二年律令·具律》的规定,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公士以上的有爵者的确不适用肉刑。由此可推知,在上古时代至少贵族确是不适用肉刑的。秦汉时期有爵者的特权只是古代社会某个阶段的真实状况的缩影。原本属于整个统治者氏族的特权,随着血缘共同体的瓦解,地域国家的形成,最终演变成新体制下爵位贵族所专有。所以,“刑不上大夫”,确有其事。“五虐之刑”既起源于苗民社会,此后,即使社会结构演进,共同体的范围不断扩张,但社会分层仍然存在,肉刑始终只是用来对付被统治者氏族或平民。其次,肉刑的本意仍只能从“逐出社会”中获得合理解释。中国上古社会,“刑”与“逐出社会”的关系,在《礼记·王制》的记载中也得到完整的阐释:
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塗,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
颁赏赐爵在朝堂(早期往往是宗庙)举行,爵命之施,意味着受爵者被接纳为以君主为核心的士大夫共同体的一员。而行刑则在“市”进行。古代的“市”,是货物集散、权属交割转移之处,也是百族交汇之所。根据《周礼·地官·司市》的记载:“凡万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度量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叙。”买卖者、行刑者各安其位,有序进行。在这样的场所行刑,应带有仪式性,有摒弃之意。对于死刑而言,处死、陈尸示众,一次的弃绝已经结束;而对于一般刑余之人,则是被逐出社会的开始,由此割断与其原有宗族社会的关联。王、公之家不会收留他,大夫之家也不予接纳,士在路上遇到他,也不与之说话。任其四处流离,不享受政治权利或承担义务(赋役不与,不受田宅),不有意创造条件让他活着。显然,受刑者不一定被逐出国境,但确为社会所隔绝。“不及以政”意味着他不再是国家共同体的成员。
另外,从字源意义上分析,滋贺秀三回溯到了“刑”的本字——“型”上。认为“毁伤肉体在上面留下特定的‘刑’(型)”,这就是“刑”字的由来。将“为恶者”逐出社会是普遍公理,“刑”只是被驱逐的标志而已。
传说中的“象形”似乎与此异曲而同工。另,从王制的记载来看,不只是驱逐,确有不问其死活的意思。因此,滋贺氏又认为,肉刑无非是以缓和的方式部分地实现死刑的目的。
与“公家不畜刑人”相矛盾的是《周礼·秋官·掌戮》中的记载:
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从文献记载显示,与“刑人”的身份相伴的是终生的贱役及人身自主权的丧失。对此,滋贺秀三先生的观点是:《礼记·王制》所反映的是流传下来的更古时代的社会实况,在那里,受刑者已经不再被看作社会的一员,任凭他们是死是活,与原始的放逐形态一模一样。让刑人充任贱役,最初可能是一种恩惠性的权宜措施,它能使因被肉刑而为社会所抛弃的人生存下来。后来人们认识到了其劳动力价值,才逐渐制度化。[8]《礼记·祭统》确也有“古者,不使刑人守门”的记载。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设想,古代曾经有这样一个阶段:为恶之人,根据其恶性程度,或者被直接处死,或者被施刑以后逐出社会共同体(包括自己的家族),或者直接被驱逐。被驱逐的人,不再与社会中任何一个阶层发生关系,剥夺一切权利,不再是一个“社会人”,社会也不会有意制造条件,使他们活下去。起初,这种放逐既是政治上的,也是空间上的。后来,随着社会关系的不断复杂化,公共领域不断延伸,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而传统信念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公共领域,对于享有公民权的人来说,除打仗、祭祀以及在庙堂议政或从事农业生产为国家提供军赋以外,其他事项均非必须。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古罗马,那里的警察一度是由奴隶担任的,罗马的公民宁肯被全副武装的奴隶带走,也不肯降低身份从事此类工作。
由此产生的空缺,正好为这些被社会所摒弃的人提供了生存机会。他们在官府从事一些贱役,并获取衣食。但政治上的隔绝仍然存在,他们被视为贱民,穿特殊的衣服,另立贱籍,无资格立户受田,亦不承担徭役、兵役。这就是早期的刑徒,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他们存在的依据,也构成了其身份内涵。进而形成定制,刑徒均丧失公民身份,被官府强制分配到各处从事劳役,除非有赦或者赎、免,终身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至少始于西周,目前已经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有名为“刖足奴隶鬲”的,被刖者扶拐杖负责守门,类似器物还有多件。
(二)于秦汉律中的传袭
秦汉去古未远,汉承秦制,以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为代表的秦汉律简显示,文帝改制以前的秦汉刑罚体系保留了诸多古代因素。表1即为《二年律令》所反映的西汉初期的刑罚体系。
日本学者冨谷至曾对秦汉刑罚体系及各刑种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他认为先秦肉刑中只有“黥”是正刑,劓、斩左右止、腐乃至“具五刑”,并非一味地追求刑罚的残酷与威吓效果,而是有其内在原理和机制——根据犯罪情节或因屡次犯罪多次施加肉刑而逐级附加的结果。[12](P49)这在晚出的《二年律令·具律》中得到证实。
有罪当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斩左止,斩左止者斩右止,斩右止者腐之。[13](P20)
黥即以利器刻刺面部,再填以墨,以留下永久的标志。倘以黥来解释肉刑之全体,则作为区分标志的意义的确更重于施加肉体上的痛苦。联系表1,乃以上诸刑皆旨在施加某种从发肤到颜面、肢体的标志性毁损,并伴以终身的劳役。与此相应的是逐级上升的法律人格的减损,从比平民减半受田宅,到人身为公家所有,到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的不得拥有婚姻、子女、财产。

表1 西汉初期的刑罚体系
司寇、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不仅仅是刑罚中的劳役刑名称,也是表达刑徒身份的概念,其中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在秦汉律简中又被统称为“徒隶”。其存在,说明刑罚的原始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他们是因犯罪而被施以特殊标记排斥在公民社会之外的人,在官府服贱役是其生存方式。
三、小结
古代社会,刑罚可能导致身份的改变。刑罚与身份的这一关联,源自刑罚的原始意义和机能——将为恶者驱逐出社会。被驱逐者因丧失共同体成员资格而失去原有的身份。对被驱逐者,起初是空间隔绝与政治隔绝并存,后来空间隔绝消失,强制劳役成为定制,在劳役的基础上也构筑其新的身份。身份是刑罚的一个要素,甚至是解释上古直至秦汉初期刑罚体制的关键。刑罚中“身份“要素的正式剥离始于汉文帝的刑制改革。
[1]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附寄簃文存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蒲堅.中国古代法制丛钞(壹)[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
[4]叶孝信.中国法制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5]吕利.关于赎刑渊源的考察[J].枣庄学院学报,2006,(6).
[6][意]阿尔多·贝特鲁奇.从身份到契约与罗马的身份制度[J],徐国栋,译.现代法学,1997,(6).
[7][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8][日]滋贺秀三.中国上古刑罚考: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通代先秦秦汉卷)[M]//杨一凡.中国法制史考证(第一卷,丙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法]古郎士.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M].李玄伯,译;张天虹,校勘.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0][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1]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12][日]冨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M].柴生芳,朱恒晔,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3]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陈东霞
K22;D929
A
1671-3842(2015)03-0020-06
10.3969/j.issn.1671-3842.2015.03.04
2014-11-04
吕利(1971—),女,山东滕州人,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