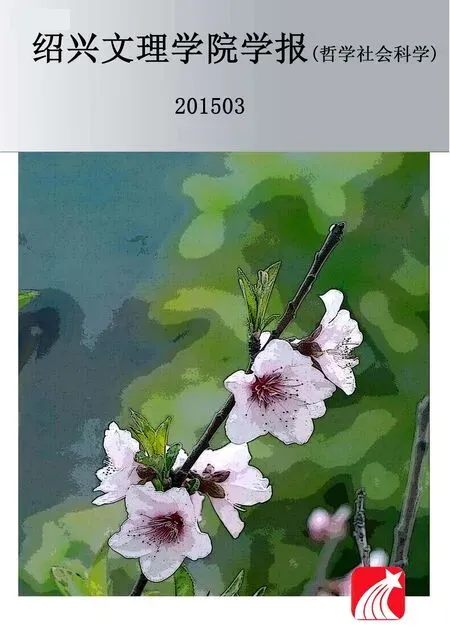禹“修社祀”和“死而为社”考
周幼涛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禹“修社祀”和“死而为社”考
周幼涛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社祀的创设,是大禹的一项重大的政治发明,其目的在于通过召集天下诸侯共同祭祀“共同地域”(九州)的象征——“社”(国土之神)以统一思想(信仰),进而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而通过将“禹葬会稽”的传说与良渚文化土筑高台祭坛及墓葬的考古资料相互印证可知,大禹生前亲自安排自己的墓葬,乃是为了让自己在身后能坐实华夏国祖这个历史宝座。历史地看,社祀是从祭祀生育之神的高禖之祭演变而来。而在后世,作为土地之主的社又与农业之神的稷坐到了一起,“社稷”之名遂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禹;社;禅;会稽;高禖;稷
历来所有的解释都是一致的:社为“土地之主”或“土地之神”。但这个“土”指的不是“田土”而是“领土”即“领地”。这个界定对于本文尤为重要,所以必须先行指明。
“领地”的意识,在动物界就很普遍,人类亦不例外,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并延续至今。城有“城隍”,乡有“土地”,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每个地方都有神灵管着,他们都是“山川之主”“土地之神”,只是“职称”不同而已。
显然,在严格意义上,这个区划地域空间的“谱系”与人类的血缘谱系无关。换言之,它虽然萌生于血缘社会,但却张扬于文明时代,是“以地域划分居民”的产物。征收赋税和以地域划分居民,被恩格斯视为考察国家是否已经出现的两个最核心的指标。据此,“社”的张扬就应在这个历史关节点上。而在中国,处于这个历史关节点上的“领军人物”就是大禹!
一、禹修社祀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禹是“传说人物”还是“历史人物”二者之间一直游移不定。但由于人类早期的历史就是以传说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的,所以这其实并不成为一个命题。退一步说,即使我们遂了传说论者的愿,但古人之所以要塑造出这个大禹,当亦是为了在人类历史的这个关节点上竖立起一个能让后人把握的标杆。
根据传说,禹一生做成了两件大事:一是治平了洪水,二是开创了夏朝。作为治水英雄,大禹在洪水泛滥、民不聊生之际,率领民众疏江导河、治理水患,经过十三年之久的艰苦奋斗,终于“地平天成”,百姓安居,不愧是一位把我们的民族从洪水浩劫中拯救出来的伟大领袖;作为立国之祖,大禹在公元前2l世纪长江、黄河流域万国林立,争夺混战之世,通过一系列战争征服天下和创造发展政治文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天下一统意义的王朝,从而把中华民族带进了文明时代。
这两件事,也可以当作一件事看,因为二者之间是一个单向的因果关系。有一种观点甚至不相信当时真的有一场大洪水存在过,他们认为,大禹治水的传说,其实只是华夏民族向南扩张,征服三苗等南方民族这一历史过程的折光反映。所以等到战争一结束,这场“大洪水”也就销声匿迹了。
这是一个文明曙光在中华大地上喷薄而出的年代,大禹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托起这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创建中国第一王朝!无论是治水还是战争,大禹的一切活动,无不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中心。
国家的诞生,可以有不同的路线图,如内部的阶级斗争、大型的公共工程、对外的兼并扩张等等,当然更多的情况可能是数管齐下。
当时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战争,有着几条不同的战线。如中原地区内部的兼并,与东夷部族的融合,以及向南蛮地区的扩张等等。所以在大禹的传说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不同战线之间难分难解的胶着状态,也因之感觉到分外的扑朔迷离。
绍兴有一则“禹疏了溪”的传说,认为大禹治水就是在了溪结束的,“了”就是结束的意思。而这条了溪就在绍兴的嵊州。
让大禹治水结束于嵊州,是绍兴大禹传说中的神来之笔。或以为大型的公共水利工程也是国家所由产生的一个途径,则关于大禹治水和立国的传说便可以作为支撑这种历史观点的一个相当有力的论据。

图1
大禹的传说遍及全国,这些传说有两个基本指向:其治水的传说,总是将大禹引向神话传说;其立国的传说,总是将大禹引向历史人物。而绍兴大禹传说的可贵之处,便在于都指向他的立国,这是绍兴大禹传说与其他地域大禹传说的最大区别和它的历史价值所在。
绍兴有许多大禹的传说和古迹,但有关治水的故事却只有“禹疏了溪”这一个。显然,安排这个故事的意图,在于为“禹会会稽”作铺垫。治水既已告成,接下去自然就要办建国的大事了。
治水成功之日,大禹在会稽山下召开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诸侯盛会。《左传·哀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文解字》中说:“嵞,会稽山。”许慎当有所据。有理由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君臣、示一体、别远近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会。
这个传说,还见于以下史籍:
《国语·鲁语下》:“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
《韩非子·饰邪》:“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1]:“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会稽。”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2]记载:“(禹)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乃大会计治国之道,内美釜山州镇之功,外演圣德以应天心。遂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
今本《竹书纪年》:“(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
举行这次大会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立国,需要考究的是会议的具体内容。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此时已不用去考虑它了,于是只剩下了“祀”。对于“禹会会稽”,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禹禅会稽”。由此可见,“会稽”的首义,既非计划,也非计功,而是“会祭”。
《史记·封禅书》[3]中说:“禹封泰山,禅会稽。”又说:“自禹兴而修社祀。”祭地叫“禅”,“社”为土地之主。因此这“禅会稽”也就是“修社祀”。
这是大禹的一项重大的政治发明,其目的在于通过召集天下诸侯共同祭祀“共同地域”(九州)的象征——“社”(国土之神)以统一思想(信仰),进而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大禹在会稽山下会群臣,上致群神,二者之间并无矛盾。而这件大事所具有的开天辟地的意义,才是其会址会稽山得以在历史早期一直雄踞于天下九山之首的根本原因。
信仰的统一,是天下统一的思想保证和建国前提。所以这“社祀”,实相当于大禹为华夏王朝所创设的一个“国教”。
公元7世纪时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举措与大禹此举如出一辙。在当时的阿拉伯半岛上,也是“万国”林立,各“国”都有自己的部族信仰。而伊斯兰教要求信教者信仰惟一的真主安拉,认为凡教徒都是兄弟,不分部落。其实质是要各部落放弃各自的崇拜偶像,以求在统一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争取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后来的实际成效也确是如此,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时,阿拉伯半岛已大体统一。
大禹在会稽大会诸侯共举社祭期间,还断然诛杀了一位名叫“防风氏”的诸侯。这个严重的事件,成为这场喜庆热烈的大合唱中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至今在绍兴仍有刑塘、斩将台等地名纪念着这位反叛的末路英雄。后世有人颇不以大禹此举为然,殊不知防风氏的“迟到”其实是一种不合作的政治表态,系故意为之。所以这一杀戮也正是大禹事先就在期待着的一项正中下怀的“议程”。《吴越春秋》一语道破了它的机关:“示天下悉属禹也。”作为成例,我们在《尚书·甘誓》中还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此外,尚有一个发生在绍兴宛委山中的大禹传说需要说明。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记载:“禹伤父功不成,循江泝河,尽济甄淮,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黄帝中经历》,盖圣人所记,曰:‘在于九山之南,天柱号曰宛委,赤帝在阙。其岩之巅,承以丈玉,覆以盘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皆琢其文。’禹乃东巡登衡岳,血白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啸,因梦见赤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闻帝使文命于斯,故来候之。非厥岁月,将告以期,无为戏吟。’故倚歌覆釜之山,东顾谓禹曰:‘欲得我山神书者,斋于黄帝岩岳之下,三月庚子,登山发石,金简之书存矣。’禹退又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发金简之书,案金简玉字,得通水之理。”
这是大禹在绍兴地域中行祭山之礼的惟一一个传说,而宛委山是会稽山的主峰,据此,这个故事实乃“禹禅会稽”传说的一个变文,本与治水无涉。
二、禹死为社
《淮南子·氾论训》[4]中说:“禹劳天下,死而为社。”这里的“社”,指的是社神。而要破释这一传说,则需要用“禹葬会稽”这件大事来加以说明。
“禹葬会稽”的传说,主要见之于以下典籍:
《墨子·节葬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裘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
《吕氏春秋·安死篇》:“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
《淮南子·齐俗训》:“禹葬会稽之山,农不易其亩。”
《史记·夏本纪》:“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或言禹会诸候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集解》引《皇览》曰:“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禹)因病亡死,葬会稽。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上无漏泄,下无即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后曰:‘无改亩。’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
《论衡·书虚篇》:“禹东治水,死于会稽。贤圣家天下,故因葬焉。”
《水经注·渐江水》:“又有会稽之山,……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东巡狩,崩于会稽,因而葬之。”
从以上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到三个信息:第一,大禹葬于会稽之山,其墓就在今浙江绍兴;第二,禹墓的规模形制是大禹生前自己设计好了的,所以历来认为大禹是中国墓葬制度的创始人;第三,大禹遗命不准后人对其墓葬作任何的变动,后人对此举解释为大禹的节俭和爱民。
疑问由之而生:大禹为什么如此重视自己的墓葬,要在生前预作如此周密的安排,而这种安排是否还另有深层的政治意义呢?
研究历史,古人主要依靠文献。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渠道,称为多重证据法。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绕过历史文献所布下的疑阵,从考古资料和文化人类学资料中找到以上疑问的答案。

图2
根据考古资料,在良渚文化的土筑高台祭坛上,均有大墓埋葬。这种大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量的玉礼器随葬。1973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省常州市东北15公里处发现了一处良渚文化遗址,命名为武进寺墩遗址(见图2)。经过多次的考古发掘,发现这里竟然是一座神秘的古国古城。古城中心是一座高20米、直径100米的圆丘形祭坛,四周环以河流,呈方形。其外围又是一条河流,亦呈方形,东西900米,南北1000米。四方居中各有一条河流连结内外河,从而把古城划分为四个象限。
从1978年到1995年,专家在第四象限北部先后发现了4座良渚文化大墓。这四座墓按时间先后自西向东有序排列,其中的3号墓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墓例,随葬器物100多件,其中陶器仅4件,石器9件,其他均为玉器。在玉器中,玉琮33件,玉璧24件,玉钺3件,共60件,占全部随葬物的半数上下。此外,在墓中还发现了燎祭的痕迹。
琮、璧、钺是神权、族权、财权和军(王)权的象征,燎祭则是原始部族中最高级别的祭典。这些都说明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在生前他们是主祭者,在身后又是受祭者,完全具有祖宗神或宗主神的资格,所以,这些墓应该就是祖陵。
大禹具有祖宗神或宗主神的身份,生前握有族权、财权和王(军)权,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他是否还握有神权呢?回答也是肯定的。在氏族社会中,宗教活动的主持人一般都是由氏族长或部落首领来担任的。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才有专职的巫师出现。《海内十洲记》中说大禹“祠上帝于北河,归大功于九天”;《拾遗记》中说大禹铸九鼎,“占气象之休否”;《韩非子》中说“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于内”。说明禹本人确曾主持过祭祀和占卜活动。前面已经说过,“会稽”的第一要义是为“会祭”,大禹就是这次会祭的主持人。
这种宗教活动在当时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禹正是通过这一举措来肯定和巩固他的政治成就和政治地位。大禹自己下令让群臣把他安葬在“会稽之山”,这“会稽之山”实际上指的就是良渚文化时出现的那种大规模的土筑高台祭坛,也就是社坛。大禹还很具体地规定了陵墓的规格,并一再强调“无改亩”,即不许后人更改这个规格。将此事与良渚文化土筑高台祭坛上的大墓相联系,就可明白大禹生前的这一努力乃是为了让自己在身后能坐实华夏国祖这个历史宝座。
大禹生创社祀,死为社神,这既符历史,又合逻辑,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社”的前世和今生
社祀,并不是大禹凭空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通过对以往原始宗教的改造而实现的,所谓“旧瓶装新酒”是也。而这个原始宗教就是高禖之祭,即对生育神的崇拜和祭祀。有人考证,在甲骨文中,“社”字就是女性生殖器的形象。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这就是著名的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恩格斯还说:“劳动愈不发展,劳动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普列汉诺夫在其《艺术论》一书中也曾说到,当时“氏族的全部力量,全部生活能力,决定于它的成员的数目”。
根据这个理论,作为社会生产力之一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即种的繁衍,乃是人类社会早期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类自身的生殖力和生殖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着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人类社会和人类意识形态的基本面貌。
由此,生育崇拜便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发生的第一个宗教因素,生育之神便成为人类所创造的第一个崇拜偶象。
在中国,这个神的名称叫做“高禖”。
对“高禖”即生育之神的祭祀,无论中外,在古代民族中都是非常普遍的。大禹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当时的政治需要,非常巧妙地将这个“以血缘划分居民”的部落宗教改造成一个“以地域划分居民”的国家宗教,无疑更容易得到当时各部落的认同从而减少其推行的阻力。
也正因为如此,高禖之祭的许多功能得以在社祀中传承下来。
这种传承与大禹相关的故事是“禹娶涂山”。
《楚辞·天问》中说:“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欲同味,而快朝饱。”说的是禹和涂山氏之女在“台桑”结合的故事。
“台桑”即“桑台”,桑指桑林,台指社台。但由于“禹娶涂山”的故事应该发生在他将高禖之祭改造成社祀之前,其结合的场所当时还是纯粹的高禖祭地,所以这里的“台桑”一词,当是后世的命名。
要到社祀发明之后,两种祭祀才变成“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浑然一处,所以《墨子·明鬼下》中才会说:“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
再一个是“汤祷桑林”的故事。
《吕氏春秋·顺民篇》中说:“昔者商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
桑林,是殷商的高禖和社之祭地,其地在殷都毫附近。因何祷雨要在此处进行,则是出于古人“天人同构”的观念。高诱在注“桑林”一词时说:“桑林之山,能兴云作雨也。”“云雨”,这是一个人人明白且被广泛使用的隐语,桑林是个行夫妇之事的地方,以夫妇之人事感动云雨之天事,实是一种最质朴的巫术方式。所以《路史余论》引董仲舒《祈雨法》云:“令吏妻各往视其夫,到起雨而止。”据此,后世关于“汤祷桑林”的记载,也可能是一个经过打扫的“洁本”。
当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取代人类自身的生殖能力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导方面以后,社神便不再与高禖为伍,而开始和农神坐在了一起,其标志是“社稷”的出现,并在与“宗庙”的分设中与血缘文化作了进一步的切割。
《淮南子·氾论训》:“禹劳天下,死而为社;后稷作稼穑,死而为稷。”
《礼记·祭义》:“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从此,对于祖宗神和土神、农神的分祭以及土神与农神的合祭制度就被确定下来。
在绍兴的鲁迅故里中有一座“土谷祠”,阿Q常宿那里。这个“土谷祠”,应该就是民间的“社稷坛”。当然,在大多数地方只叫“土地庙”。因为其时的这个“土地”,在很大程度上已有“田土”的意思,所以稷神也就隐而不现了。
文化,是个很不容易丢失的东西。认为人类、动物、植物三者的自身生产具有互渗性的观念,一直被传承下来,并在社祀这个时节中不断地浮出水面。
在汉代的画像砖上,经常可以发现“桑林野合”这个题材。根据交感原理,这可能具有双向的作用。一是用人的交媾巫术来促进蚕桑的丰收,二是也用桑树多籽的特点来提高自身的受孕率。
在浙江湖州与嘉兴交界处的含山,是杭嘉湖盛产蚕桑的中心地带。每到清明前后,周围几十里地的蚕农,会成群结队来游含山,举行祭祀蚕神的庙会,人数最多时可达七八万人。蚕农们怀里藏着蚕籽包,希望在游山人群的相互挤轧中借到蚕气,俗称“轧蚕花”。其中还有“摸蚕花奶奶”的习俗。男女青年故意挤挤轧轧,小伙子伺机动点手脚,姑娘们吃了亏也不恼怒,方言称为“越轧越发”,以此讨彩头,求得蚕花茂盛。
据《礼记·祭法》,在先秦时代,无论个人或群体,凡有领地者皆可立社:“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图3
以上说的是统治阶级,至于黎民百姓,据《说文》引《周礼》,则是“二十五家为社”,但这种“社”,已与最基层的行政区划“村里”结合在一起,成为基层社会组织的名称,名曰“里社”或“村社”。根据秦汉制度,当时农村中的行政建置,是“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其面积,大概是一个亭2.5平方公里,一个乡25平方公里。目前我国“村”的规模大多处于昔日的里、亭之间,而昔日的“里”,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自然村”了。
史籍中多有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之间赠送“书社”的记载。何为“书社”?司马贞为《史记·孔子世家》“昭王将以书社七百里封孔子”作《索隐》曰:“古者二十五家为里,里则各立社,则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名于籍。盖以七百里书社之人封孔子也。”由此可见,所谓“书社”,即是将社员之名籍书于社簿者也。言以“书社”相赠,意在说明是以土地和人民一起相送者也。
综上所述,对于古籍上的“社”字,我们必须根据其不同的语境来区分它的不同指向。一是指社神,二是指神之所依的物质具像,三是指社主所在或社祭的场所,四是指社所拥有的土地,五是指社所拥有的人民,等等。
在以后的演进中,“社”又成为民间团体或业务机构的名称。前者多表现为文化团体,后者则有报社、出版社、新闻社、广告社等。另外还有将经济组织名之为社的,如合作社便是。而这些,当然离开“社”的本初含义已是很远很远了。只有在人们最为熟悉的“社会”一词上,我们仿佛还可以看到禹会会稽,初创社祀时的宏大影像。社会者,会于社、社之会也!
[1]越绝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东汉]赵晔.吴越春秋[M].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淮南子[M].
(责任编辑 张玲玲)
G127
A
1008-293X(2015)03-0007-06
10.16169/j.issn.1008-293x.s.2015.03.02
2015-04-10
周幼涛(1950-),男,浙江绍兴人,绍兴市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退休),现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大禹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