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读、常读常新的文学经典”
张廷佺 徐谙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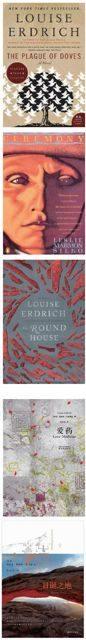
近年来,美国印第安文学[又称“美国本土裔文学”、“美国原住民文学”、“美国土著文学”。]在国内越发受到关注。仅以2014年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年会为例,以美国印第安作家或美国印第安文学整体发展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就有近20篇,其中以研究奥吉布瓦部落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的名著《爱药》(Love Medicine)的论文为最多。《爱药》于2008年由张廷佺首次译为中文,据统计,该译本出版后,国内对厄德里克和美国印第安文学的研究在短时期内呈激增势头。迄今,国内共有5部美国印第安长篇小说被译为中文,其中4部,即《爱药》《日诞之地》(House Made of Dawn)、《鸽灾》(The Plague of Doves)、《圆屋》(The Round House),由张廷佺翻译(主译)。张廷佺是国内较早从事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本文是张廷佺与正从事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徐谙律就美国印第安文学翻译、研究和展望的交谈。
徐谙律:中国读者对美国印第安人[为行文方便,“美国印第安人”、“美国土著人”、“美国原住民”统称为“印第安人”,相对应的部落统称为“印第安部落”。]并不陌生,从库珀的《最后的莫西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中被掠夺土地、被酒精麻痹的命运多舛的印第安人,到薇拉·凯瑟《教授的房子》(The Professors House)和《大主教之死》(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中尊崇自然、聪明智慧的印第安人,再到海明威短篇小说中饱受压迫、备受歧视的印第安人……但以上都是白人视角中的印第安人。您翻译的名著——路易丝·厄德里克的长篇小说《爱药》是首部被译为中文的美国印第安长篇小说,让更多中国读者开始认识印第安人视角中的印第安人。近年来,您对美国印第安小说的集中译介推动了美国印第安文学在中国的“着陆”,让中国读者对印第安文学的兴趣越发浓厚。是什么原因让您如此密集地将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迻译过来呢?
张廷佺:国内读者乐于阅读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我认为原因首先在于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比如《爱药》《日诞之地》《典仪》等都是常读常新的文学经典。美国印第安文学的汉译则进一步扩大了作品的读者群体,帮助读者缩小由语言和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空当”,减少其文本理解上的障碍。我翻译的第一部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不是《爱药》。在那之前,我曾受《外国文艺》和《译文》的约稿,翻译发表了多篇美国印第安短篇小说。翻译过程中,我被印第安文学作品诗性的语言和别具炉锤的叙事方式吸引。大多数当代印第安人不在保留地长大,但他们承袭了祖先尊崇自然、热爱自然的“记忆基因”,许多印第安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对自然细心、敏锐的观察和感受,他们描绘自然诗性、生动的语言赋予文本强烈的画面感和现场感,我由衷佩服他们的这种能力,也为他们描绘家园、书写文化、社会和历史的文字所触动,内心有一种冲动,想将这些文字及其承载的文化用中文呈现。另外,由于继承其祖先古老的口述传统,美国印第安作家在作品叙事方式上表现特殊,有的采用环形叙事,有的采用成套故事叙述,等等。正如莱斯莉·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所言,“每个单词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叙述具有关联性和发散性等特点。通常一个故事是整篇小说立足的核心,发散出打破常规物理时序的众多故事,在逻辑上与核心故事呈现千丝万缕的联系,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不太好懂,在翻译中我时常遇到来自作品的挑战,但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又让我觉得这类作品有必要为更多读者所了解、品读和研究。因此,我在完成《爱药》的翻译后,又接连翻译了莫马迪(N. Scott Momaday)的普利策奖获奖小说《日诞之地》、厄德里克的全国图书奖获奖小说《圆屋》和另一部入围普利策小说奖的作品《鸽灾》。《圆屋》和《鸽灾》的译本将于2015年出版,《鸽灾》的节选部分将先期发表在明年的《上海文学》上。
徐谙律:文学翻译与其他体裁的翻译有一定区别,翻译时难免会因语言差异、文化差异、作者和译者风格的差异等而无法与原作工整对应。您刚才也提到,翻译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时遇到了许多挑战,可否列举一些具体问题,让我们有直观的感受?
张廷佺:由于许多美国印第安作家具有多部落的混杂血统,不同部落有其各自的语言,作家的语言也有混杂性。他们在英语小说写作中时常融入部落语言,或用部落语言的思维和语法习惯表述英语,搭配和意义独特,常让我感到虚脱、失重。比如,《日诞之地》中,作者莫马迪似乎总在挑战英语语法和句法的极限,诸如“alien wind”、“perspective,proportion and design”、“dark and certain shadow”、“pride of discrimination”、“exclusive silence”的表达常让我苦于“贫于一字”;此外,普韦布洛、纳瓦霍、基奥瓦3个部落的神话和传说里特有的神灵、地名、人名都来自各部落自己的语言,如“Tségihi”、“Esdzáshash nadle”、“Dzil quigi”、“Yeí bichai”等,中文里没有现成翻译,而能找到的英文释义更多的是解释,不是对应的翻译,也无法直接为译文所用。另外,印第安部落众多,作品中嵌入或蕴含大量部落文化、历史、政治事件,如不了解这些背景,读者很容易视之为作品情节的跳脱或断层,对文本的理解产生偏差。因此,需添加注解帮助读者理解,但这些事件的细节常常无法在现有资料中直接查找到。再者,许多作品叙事方法独特,呈现出碎片化叙事的特征,且叙事者的轮换和更替大多没有明显标记。译者在翻译前必须完成“侦探”工作,弄清每部分的叙述者,理清不同叙述之间的关系。比如,《爱药》全书故事有20个之多,往往一个故事的叙事者是另一个故事的被叙事者,一个故事的主要人物是另一个故事的次要人物,故事之间相互关联,人物的叙述或相互补充和重叠,或由于叙事的主观性而相互矛盾、相互消解;作品没有中心人物,没有开端、高潮和结局,相关线索或隐或显,若断若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爱药》似乎可以从任何一个故事,也就是任何一章开始阅读。面对由作者和多个人物分别叙述的、时间跨度达50年之久的20个故事,读者就如同进入了叙事迷宫。我充分体会到,文学翻译最重要且最困难的就是要译出其文学性。只有反复研读原文,与其“软磨硬泡”,才能会心况味,体悟到隐于不言、细入无间的意蕴。在文学翻译中,无论是理解和表达都不可用蛮力,而该用巧劲,不可强攻,只可智取,译文的浓淡、繁简、轻重、褒贬、显隐最能显示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的深浅和文字转换的工拙。
徐谙律:虽然我们在谈论“美国印第安文学”,但该名称一直颇具争议。抛开对“美国印第安人”的英语名称“American Indian”、“Native American”或“Indigenous American”的选择不谈,仅是针对可否将美国政府承认的500多个部落及其他未被承认的部落归为统一群体、赋予统一名称的问题,相关学者和部落成员就长期无法达成定论。如今,美国人口统计等表格中,“身份”栏目为便于区分,将不同部落的原住民一致归为“本土裔”(或“印第安人”);学术研究也同样使用这种分类,因此有了作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分支之一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的提法。但名称的统一并不说明上述争议的消除。此外,印第安作家的创作语言并不限于英语,有的作家甚至完全使用部落语言,这种用部落语言书写的文学作品是否能算作“美国印第安文学”也存在争议。所以,如何定义美国印第安文学仍是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您如何定义美国印第安文学呢?美国印第安文学的整体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呢?
张廷佺:要定义美国印第安文学,首先应该扩大对“文学”形式这一范畴的理解。常规意义上,文学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但美国印第安人有特殊的口述传统,其传承也逐渐被融入近代、当代美国印第安作家的书面创作。我们在讨论印第安文学时无法绕开口述传统对印第安人的重要性这一话题,甚至有些人类学、文学研究者将其称为“口述文学”(“orature”)。将印第安口述故事纳入其文学范畴是有必要的。美国印第安文学是来自印第安部落的传统口述文学与具有部落血统的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的总和。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以及部落口述文学与早期书面文学对部落语言的使用,美国印第安文学长期被忽视。直至18世纪,印第安作家陆续开始用英语创作,随着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传播日益广泛、影响力日益增强,印第安文学逐渐从边缘进入美国文学主流的视野。同时,学界出现将美国文学的源头追溯到印第安部落的口述传统的倾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印第安文学视为美国文学的源泉之一。1969年,莫马迪的长篇小说《日诞之地》获普利策小说奖,揭开了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的大幕。自此,美国印第安文坛涌现出莫马迪、西尔科、厄德里克、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琳达·霍根(Linda Hogan)等大批优秀作家。如今,美国印第安文学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书写主题非常丰富,包括土地与生态、印第安性与身份、印第安人与白人形象的颠覆与重塑、印第安历史与政策、战争与后战争影响、生存与抗争、城市与家园、后殖民与反殖民等;叙述特征鲜明、独树一帜,包括成套故事叙述、蛛网模式的关联叙事、叙事时间、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印第安文学与美国其他少数族裔文学相比,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更具个性、特殊性,彰显着独特魅力。
徐谙律:虽然您提到学界出现将印第安文学视为美国文学源泉的倾向,但对印第安文学归属的认定还是个微妙的问题。站在殖民者的角度,在他们对印第安人软硬兼施,采取一系列“去文化”手段之后,印第安人应该逐渐被同化;依照美国主流“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群体的同化观念,部落作家的文学作品理应属于美国文学。然而,如果站在部落成员的立场来看,众多部落坚持自身的民族性,不仅不承认所在部落属于美国,也不认可“印第安人”的提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将印第安文学视为美国文学的分支。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张廷佺:与美国其他少数族裔文学不同,印第安文学与美国文学之间确实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首先,印第安文学和美国文学既包含又不完全包含。虽被称为“美国印第安文学”,但追溯到口头文学,早在美国文学发生前就已形成。“印第安文学”包含各部落(区域)自身的文学,不同部落文学的特征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许多印第安文化、文学研究者都主张印第安文学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平行于美国文学的另一“民族(或国家)文学”。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英语文化强势影响下,印第安人确实在文化、语言、身份认同上被不同程度地同化,当代印第安作家基本都使用英语写作,其作品也因而被视作美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不无道理的。基于印第安人被殖民的历史,印第安文学多被归为属于美国文学的“殖民文学”“少数族裔文学”。其次,印第安文学与美国文学是相互、双向影响的。在以白人为主的美国统治群体话语权占据主流时,英语是殖民时期以来大部分印第安文学的书写语言,这使人们自然会认为印第安文学的萌芽、发展、成熟得益于主流文学的滋养。但要注意,印第安文化和文学传统对美国文学也有同样深刻的影响,比如,印第安口述传统对美国文学的“独立”、美国自由体诗歌和意象派诗歌等影响最为明显,这些影响也已得到公认。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伊沃·温特斯(Yvor Winters)等美国主流作家率先认识到并强调印第安文学对美国主流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作家、学者通过文学作品及论著向人们展示印第安文学对美国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乔克托部落作家、学者莉安·豪(LeAnne Howe)曾指出部落故事讲述的方式使美国主流作家的创作形式发生转向。她说,“本土裔文学、印第安文学、加拿大原住民文学在文学中都起着支柱性作用,我们讲述的故事为主流小说家开拓了创作空间。”豪屡次提出印第安文学和文化对美国主流文学、主流文化的反作用力,认为美国主流作家在逐渐认同印第安人对文学的理解,指出,“美国作家在逐渐学习和适应我们讲述故事的模式,而不是我们接受他们的方式。”豪在提及美国主流作家时,甚至都没有加上“主流”二字,直接将其称作“美国作家”,而将部落作家视为“我们”,将部落同美国区分开。这也印证了我前面提到的两点—二者既包含又不包含、双向相互影响的关系。
徐谙律:您提到莫马迪的小说《日诞之地》,1969年该作获普利策小说奖,让美国印第安作家发出比此前任何时代都强大的声音,拉开了“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的大幕。“复兴”以1968年美国印第安运动为政治历史背景,产生的效应超出了印第安文学创作领域,使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以及整个美国印第安研究也繁荣起来。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专著不断涌现。同年代中期,俄克拉荷马大学英语系教授艾伦·威利(Alan Velie)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美国印第安文学”课程,成为美国大学系统开设此类课程的首次实践;研究美国印第安文学的论文也在美国文学研究刊物上不断增多,后来他们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团体、创办了期刊。但总体而言,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在美国文学研究与世界文学研究中起步还是相对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您能否谈谈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的整体现状和特点呢?
张廷佺: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具有独特的复杂性,除前面提及的文化和语言的复杂性以外,还有印第安部落政治、文化和历史的复杂性。印第安人是美洲大陆的原住民,欧洲殖民者入侵美洲大陆后,他们由主人沦为属下,所以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印第安人比任何一个美国少数族裔都复杂。另外,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有很强的跨学科、跨国别特征。美国印第安人问题涉及面广,包括法律、经济、历史、政治、生态、语言、教育、地理、宗教等,这些在印第安作家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折射或影射,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些,因而印第安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甚至自然科学密不可分。国外对美国印第安文学的研究,除了依照传统文学研究范式撰写的论文以外,更多的是与一个或多个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研究;还有一些研究是将美国印第安文学视为世界原住民文学的一部分,与加拿大原住民文学、澳大利亚土著文学、新西兰土著文学、欧洲、非洲原住民文学一起,进行人类学、哲学、宗教、国际法等方面的跨国别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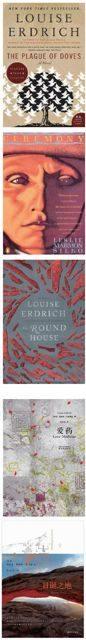
徐谙律:对于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的跨学科特征,我十分认同。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将美国印第安研究单列为以文学、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基础性学科为支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分支。据我了解,自上世纪70年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英语系设立美国印第安研究中心开始,美国许多顶尖高校陆续成立印第安研究机构,如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等,其他在人文学科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大学,如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佐治亚大学等都有印第安研究的专门机构与项目。可以说,在美国,印第安文学、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相比之下,我国在美国印第安研究领域,包括文学、宗教、政治、历史等任何领域,都还处于初始阶段。您可否从文学方面谈谈美国印第安研究在我国的状况呢?
张廷佺:如你所说,美国印第安研究在美国发展很成熟。当下,美国学界对印第安文学的关注度和重视度很高。你也提到,他们有专门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会”,还创办了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期刊,如《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和《红笔评论》(Wíazo a Review)。另外,还有交叉学科综合研究型刊物《美国印第安研究季刊》(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和《美国印第安文化与研究》(American Ind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Journal)。以上都是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的必读刊物。在我国大陆,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方兴未艾。据统计,1983至2013年间,与美国黑人文学、华裔美国文学和美国犹太文学相比,国内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成果总体偏少。现有资料显示,国内对美国印第安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但直到21世纪,研究成果才显著增加。在欣喜地看到印第安文学研究在国内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国内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仍有许多可突破之处。比如,研究对象的范围可扩大,不要限于对厄德里克、西尔科、韦尔奇、维兹诺、阿莱克西等被中国学者热捧的作家,大部分美国印第安作家的研究在我国尚属空白;再如,整体而言,国内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显得单一,研究者倾向于简单照搬西方文学理论阐释文本,却忽视印第安文学文本丰富的主题,忽视其中最“印第安”的一些特质。作品的内涵有待从更多角度、更深程度进行阐释与思考。
徐谙律:复旦大学张冲、张琼教授新近出版了合著《从边缘到经典:美国本土裔文学的源与流》,这是国内关于美国印第安文学的首部史论性专著。您在2012年底承担了上海外国语大学重大课题“美国文学史系列研究”中的美国印第安文学史部分,您的《美国印第安文学史》也在撰写过程中。您能谈谈对美国印第安文学史的书写的想法吗?
张廷佺:大概十年前,我就有过疑问,为什么没有一部“美国印第安文学史”。不仅国内没有,而且国外也没有一部梳理其整体发展历程、概括全貌、同时又深入研究和分析其特质的文学史。那时我就产生了撰写美国印第安文学史的念头。撰写工作于2013年启动。研究印第安文学的学者应该都知道,美国有印第安文学的作品概览,比如A.拉冯妮·布朗·劳夫(A. Lavonne Brown Ruoff)1990年出版的《美国印第安文学:概述、书目评论和文献选编》(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 An Introduction, Bibliographic Review and Selected Bibliography),也有带历时性特征的文学主题研究,比如杰斯·韦弗(Jace Weaver)1997年出版的《民族将继续生存—美国印第安文学与美国印第安社群》(That the People Might Live: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 and Native American Community),还有进行专题研究的导读文集,比如乔伊·波特(Joy Porter)和肯尼斯·罗默(Kenneth Roemer)2005年合编的《剑桥美国印第安文学导读》(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另外,詹姆斯·科克斯(James H. Cox)和丹尼尔·希斯·贾斯蒂斯(Daniel Heath Justice)合编的《牛津美洲原住民文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digenous American Literature)已于2014年8月出版,该手册首次打通美洲国界,以美洲原住民文学整体为对象,对其概貌、发展和部分特点进行专题的介绍。但针对美国印第安文学,目前依然缺少一部全面、连续、具体、深入的文学史。这一现实让我不断思考和论证美国印第安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张冲、张琼教授的新著无疑是国内外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为文学研究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挖掘美国印第安文学瑰宝的大门,也让我更加肯定,书写美国印第安文学史是可能的,而且极有必要。据目前的文字记载,美国印第安书面文学从18世纪开始萌芽,经历了3个多世纪的发展。如果算上其悠久的口述传统而形成的口头文学,印第安文学的历史远远长于人们目前的认识。现存的类文学史著作更侧重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的主题及其体现的政治、历史及社会价值和意义,其族裔特征与政治历史经历使撰史者更加突出作品的“文化价值”。但作为文学作品,美国印第安文学应具有、也确实具有包括叙事形式、声音、语言等方面的“美学价值”。现有研究对美国印第安文学的美学价值关注和论述得还不够。在美国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印第安作家走出最初纯粹的控诉书写套路,转而在写作中运用部落艺术、叙述和思想观念,吸纳现代、当代西方文学的创作手法,形成了有别于主流文学及其他美国族裔文学的美学特征,对整个美国文学图景产生了影响。在唯一“中心”、传统“经典”的概念开始逐渐被挑战,多重中心、经典重塑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代,一部全面、详细的美国印第安文学史能帮助研究者更深入地探索曾是“弱势”、“非主流”的美国印第安文学。
徐谙律:除了文学史的撰写,以及在前面的问题中您提到的拓展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外,您对国内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还有其他的展望吗?
张廷佺:首先,美国印第安文学批评理论是今后值得探索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在思考建立美国印第安文学自身的批评理论体系,比如阿诺德·克鲁帕特(Arnold Krupat)综合人种历史学、历史学和文学而提出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的“人种批评学”(Ethnocriticism)思想;以及莉安·豪提出的印第安文学研究中的“部落书写学”(Tribalography)的概念。另外,艾尔薇拉·普利塔诺(Elvira Pulitano)的专著《转向一种美国印第安批评理论》(Toward a Native American Critical Theory)梳理了鲍拉·甘·艾伦(Paula Gunn Allen)、罗伯特·沃瑞尔(Robert Warrior)和克莱格·沃玛克(Craig Womack)、路易斯·欧文斯(Louis Owens)和维兹诺等人的印第安批评理论观。其次,越来越多的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如《日诞之地》、托马斯·金(Thomas King)的小说《药河》(Medicine River)、韦尔奇的小说《血色冬季》(Winter in the Blood)和阿莱克西的短篇小说集《独行侠骑警与唐托在天堂的格斗》(The Long Ranger and Tonto Fistfight in Heaven)等。对这些文本与电影间的关系及其呈现方式的异同等也有诸多值得探索之处。再次,能否将中国的经典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于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使我们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张廷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邮编:200083;徐谙律: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博士生,邮编:20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