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
〔俄罗斯〕列夫·卡赞采夫·库尔滕著 张克俊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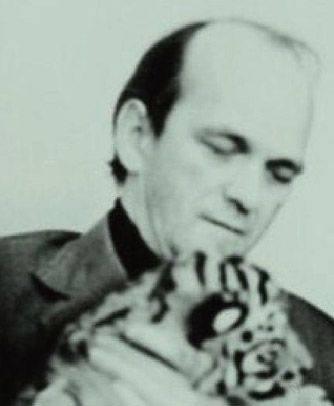
列夫·卡赞采夫·库尔滕
Лев Казанцев-Куртен
1946 年6 月20 日生于俄罗斯伊万诺沃市,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诗人,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时代》、《冒险家》、长篇侦探小说《帝国崩溃》、《入侵》、 《第五纵队少校》、《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科幻小说《筛子里的奇迹》等。
我在宾馆的客房里凭窗而立。城市上空彤云密布,暴雨如注。雨水拍打着金属窗帘架,哗啦作响。硕大的雨点顺着玻璃窗流淌。乌亮的柏油路面闪耀着五颜六色的汽车。热血革命家昏暗的石雕群像点缀着市中心广场。
雨已经连下两天了。据预报,未来一周还将阴雨连绵。我在这个城市里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这一周,我打算用于回忆我的过去,在城里走走。我离开这里已近15年了。离开时,我并不感到后悔。但当火车将我拉到莫斯科5年之后,无尽的懊悔却突涌心头,乡愁与日俱增。按科学说法,这叫怀乡病。自此,故乡以往所有的不好我渐渐地都忘到了脑后,如今浮现于记忆里的就只有这里的好。
身在异国他乡,我常常梦见生我养我的城市,梦见我家所在的街道。上学9年,我走的就是这条街。我还时常梦见我在烹饪商校同窗共读的初恋女友,美女阿霞。正是在这烹饪学校,我掌握了厨师专业。
当时我深深爱上了阿霞,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当我为祖国履行义务,在部队摸爬滚打的时候,阿霞嫁人了。心爱的姑娘嫁作他人妇。每忆及此,我总有锥心之痛。
退役后,我在一家刚开张的饭馆里做厨师。饭馆老板肥头大耳,是阿塞拜疆人。他招我上工的条件是试用期半年,拿最低工资。平素,我总是尽力迎合这位老板,但这却是徒劳的。半年后的一天,他说什么用俄罗斯厨师不顺手,遂将劳动手册摔给我,将我扫地出门,跟他争辩也没用。
第二家饭馆招我做了初级厨师。老板是个俄罗斯女人,名叫杜霞·波利卡尔波夫娜。她40来岁,圆脸,大屁股(大到足以占据两个座位)。杜霞活像是街头小贩儿,没羞没臊。上班伊始,这女老板便邀我到她家做客。整整3个月,我都给她按摩。女老板总是美滋滋地尽情享受,但我却不胜其烦。我决意去另谋新职。
一天,我看见一则广告,招聘俄罗斯专业技术人员到加拿大工作。我随即前去应聘,并很快拿到了签证。
一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我就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前往蒙特利尔市拜见聘用我的“三好汉”餐馆老板。老板已不年轻,名叫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费德洛夫,系白军军官之子。其父当年随俄国白军首领弗兰格尔一起流亡到了加拿大。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尝过我的厨师手艺之后,当即确定给我较高的薪金。不久,他又提拔我做主厨的主要帮手。我的移民生活在蒙特利尔市正式开始了。3年后,我和老板的女儿阿夫多季娅·瓦连京诺夫娜结婚。妻子不太漂亮,还大我10岁,但就因为这场婚事,我得以成为加拿大公民。
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思念祖国俄罗斯,思念我出生的城市。那思念之情时而像恶浪,陡然袭来;时而偃旗息鼓,短暂消退。但未几,这思念之情又奔涌心田。
两年前,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猝然离世。自此,我和妻子阿夫多季娅·瓦连京诺夫娜便成了“三好汉”餐馆的老板。
安葬过岳父之后,我下决心一定要回俄罗斯,到我魂牵梦绕的故乡看看。我到这里已经是第二天了,可这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没完……
近暮,我决定去宾馆底层的餐厅吃晚饭。这时,餐厅的人还不多。纵酒作乐的时辰还不到,但3个半裸的“鸡”已然打坐在吧台旁高脚椅子上守候。她们用浓艳的眼睛紧盯着那些走进餐厅的男人。但我对这些“鸡”不感兴趣。这并不是说我对老婆忠贞不贰。在家里,有时我也会放纵一下自己,做些出轨的事,但通常都是些小小的浪漫,我结交的也都是些渴求情爱的正派的女人。寻花问柳,花钱买爱,我从来不干。
我不理会那些“鸡”挑逗的媚眼,找了个空桌子坐下,招来服务员点餐。等上饭菜时,我环顾了一下大厅。眼前的情景很常见,我也很熟悉:全都是食客。他们有的狼吞虎咽,大快朵颐;有的不慌不忙,细嚼慢咽;有的觥筹交错,推杯换盏。
与我隔桌而坐的是一位女士。她和我年岁相仿,穿件开胸连衣裙。这女士面前只放一杯饮料,几乎一点也没有喝。她兴许是在等人,不时地望着餐厅入口。女士手夹一支细长的,尚未抽完的香烟。我们四目相遇,一次,而后又一次。她撇嘴莞尔一笑。女士的目光久久地盯着我,显然是说她和我似曾相识。我尽力不再朝她那边看。这时,服务员给我上了饭菜。于是,我即埋头吃饭。
“对不起,”我头上方传来女人的声音。我放下碗,抬头看。是那位女士,她手里仍旧夹着那支没抽完的香烟。“对不起,请问您是丹尼斯吗?”
很久没有人这样叫我,这名字我早就忘了。在加拿大,人们都叫我戴恩,或坚尼。
我仔细端详这女人的面容,觉得面生。女子见我认不出她,索性自报家门:
“我是阿霞·霍丽娜。咱们曾一起上烹饪商校……”
“阿霞?!是你?!”我惊叫道。
现在我怎么也不敢认眼前这女人。当初的阿霞还是个小姑娘。那时她身材苗条,辫子粗长,胖脸蛋,樱桃小口。她这樱桃小口我还曾多次亲吻过。
“我变化很大吗?”阿霞问道。“你是不认我,还是把我全忘了?”
“你知道吗,我怎么也没料到现在会在这儿见到你,虽然我不止一次地想起你,”我试图为自己辩解。“屈指算来,咱们已有20个年头没见面了……”
“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你长成了壮汉,但面目却没什么变化,”阿霞说。

阿霞应邀坐到了我桌旁。
“我记忆中的你,还是你在火车站送我去参军时的模样,”我说。“你现在这副扮相和超短发型把我给弄蒙了。”
“不要解释了,”阿霞说,“我知道我变化很大。”
我叫来服务员,吩咐道:“来瓶香槟酒,再看这位女士要什么。”
“不要香槟酒,”阿霞一口拒绝,“我喝这酒烧心。最好来100克白兰地。”
我点了一瓶马爹利酒。
服务员退下,前去给我们上酒。我问阿霞:“你生活怎么样?老公和孩子怎么样?”
“可以说,我活的不成样子,”阿霞回答说,“10年前,我就和老公分手了。从此我成了自由人。我没有孩子。现在一家公司打工……提供服务……你像是结婚了。”
阿霞抿了一口马爹利酒,并向为她斟酒、名叫科斯佳的殷勤服务员道谢。
“是的,我结婚了。我们现在有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2岁。”
“他们在哪儿?”
“蒙特利尔。”
“这在哪儿?”
“加拿大。”
“你跑到加拿大了?”阿霞惊奇地问道。“去很久了吧?”
“1994年。”
“怪不得我起初当你是外国人呢。但后来一看:不对,你还是丹尼斯……在加拿大那儿怎么样?”
“正常。生活还过得去。”
“有工作吗?”
“当然。我和老婆经营一个餐馆。”
“嗯,那就是说你发财了?”
“发财倒谈不上,但不穷就是了。”
阿霞又自斟了一杯马爹利酒。
“为你的幸福,为你的成功干杯……”阿霞起身,举杯说。
“为咱们的幸福干杯……”我纠正道。
阿霞摇了摇头:
“为你的幸福干杯,丹尼斯……而我……一个妓女能有什么幸福?丹尼斯,我现在是妓女……再没什么可说了……我这辈子苦哇……”
我无言以对。阿霞又喝干了一杯马爹利酒,我只抿了一小口。
“你现在喝酒也不像俄罗斯人了,”阿霞冷笑道。
“我不爱这一口儿,”我答道。“而且这酒也糟透了,冒牌货而已……”
这时,3位演奏者走上舞台。这3个人都是细高挑儿,身穿绿夹克。他们一边悄声细语,一边开始调乐器。大厅里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我们吃完饭了。阿霞怕口红弄脏脸,小心翼翼地用餐巾搌了搌嘴,说:
“丹尼斯,谢谢你的晚饭,我该上班了。我不向你推销我自己……我不想跟你做这事……婊子在你们加拿大也有的是……”
阿霞欲从桌后站起身来,我连忙拦住她,说:
“且慢……在加拿大我可是经常梦见你呀……”
阿霞又坐到椅子上,两眼满含晶莹的泪水。接着,眼泪顺着两颊滚滚而下,在脸庞上留下睫毛膏冲出的黑道道。阿霞用餐巾擦了擦眼泪。
乐队奏乐,先是弹起电子琴和吉他,接着便鼓乐喧天。阿霞说了些什么,但她的话我没听清。乐器轰鸣,震耳欲聋,响彻空中。
阿霞用餐巾抹了抹眼,从桌旁站起来,疾步向门口走去。我急忙去追她。在前厅,我一把抓住她的手。
“阿霞,等一等,”我说道。“你去哪儿?你怎么了?”
“对不起,丹尼斯。你快走吧!”阿霞答道。“不要跟着我……回到你的位置上吧……我去卫生间修饰一下,”她笑着补充了一句,“我得有接客的样子。”
我返回大厅。阿霞再也没有露面。我问前厅的保安,看没看见一个身穿红裙子,胸戴黑玫瑰的女子。他回答说,阿霞在衣帽间取走她的外套,就走了。
……清早,我恍然醒来,但见新的一天阳光灿烂,天空湛蓝。气象学家预报说,未来一周都有雨。这次他们又预报错了。
我走出下榻的宾馆时,天已经有点热了。我决定上城里溜达溜达。我先是在我熟悉的那条大街上郁郁独行,迎面走来的全是生人。他们打我身边走过,对我不屑一顾。城里的窗户也都是冷眼看着我。我在这里完全是外人……
3天后,我带着满心的遗憾和惆怅离开了我深深眷恋的这方水土。我再也没见阿霞。她也再没去我俩邂逅的那个餐厅。阿霞原先的住址已由其他人入住,其新址他们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