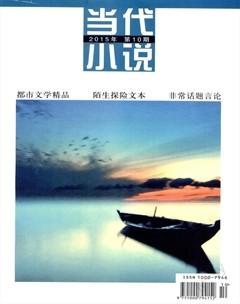中国壁画
许仙
“小仙女!大师!”
“老和尚!七仙女!”
……
我听到外面的大吼大叫声,响彻大殿和僧舍,最后窜到伙房门口;我连忙蹿起身来,后背贴到伙房门口边的墙上,将头探了点出去,露出半张脸和一只眼睛。这只眼睛看到外面有个光头男人,西装革履,四十来岁的样子,他正急匆匆地朝伙房走来;我想回避已经不可能了,我就丢下烧了半顿的晚饭,拔腿往外跑。我们在伙房前的过道上擦肩而过,我穿过大殿,直奔庵大门。
他大吃一惊,停住了脚,喊:“师傅……”
逃命要紧!我可不想落在便衣警察的手上。
他返身朝我追来,边追边喊:“喂!这位师傅……”
奔跑中,我也不忘回了回头,他手上没有枪,没有警棍,有的只是一根折断的树枝;但我还是没命地逃出了昙花庵,往天子岭纵深处窜逃。暮色帮助了我。很快,我就像潜水者那样,湮没在山中提前暗下来的天色里,我安全了。
我想我应该安全了。
我像一只孤独的秃鹰蹲在乱石堆上,我越想越不对劲:那个光头男人,不像是个便衣警察。如果他是,他到庵里来抓我,至于这么大吼大叫吗?如果他是,怎么可能会单独行动呢?庵外早该布下天罗地网了,至于让我这么轻易地逃走吗?我越想越不对劲,我决定下去瞧瞧。
如果他不是,我就立马叫他滚蛋!
这是我的地盘!
我是这儿的当家和尚。不是吗?
山林里时不时地传出索落落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了。自从进入秋天之后,山林里总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不断地掉下来,索落落地响。听久了,让人觉得好像自己的心,也会跟着索落落地掉下来,无端地惆怅。
山里起风了,索落落声就更强烈了。
我摸进庵里。
栖在庵内两棵高树上的那些鸟,在晚风中,在摇晃的枝丛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它们只顾自己像平常那样哇哇乱叫,叫声凄厉,而又悲凉。
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像滴水的冰块一样挂在天际。
只有伙房有些灯光,透过花式窗眼,我看到那个光头男人,正在吃晚饭。
他安静地吃着我才烧了半顿的晚饭,就着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两碟蔬菜,还一脸寡淡的神情,筷头拨在碗里,眼睛却张着门外,他想干什么?他该不会是在等我吧?我是他的什么人吗?我可没有像他这样的朋友。我只有背后插你两刀的朋友。狗日的秦向晚和老五!你们不得好死!
我细细地审视了他良久,决定碰碰运气。
说实话,我也饿了。
伙房门敞开着,我大模大样地走进去;我壮着胆,站在饭桌前,请他滚出去。他从哪儿来就滚哪儿去,我不需要有谁来庵里。我谁也不需要。我只需要一个人呆在庵里,直到老死。我连他是谁都不想知道,我知道他干什么呢?只要他不是便衣警察,那么,请吧,有多远滚多远。
但我说了那么多,说得那么激动,这个傻逼样的男人,竟呆呆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对我的这番话无动于衷到了极点;他在听吗?他长耳朵了吗?他到底想干什么?他突然跑到我这儿来,把我寂静的生活搅得一团糟,他还嫌我不够麻烦吗?我已经无处可逃了,再丢了昙花庵,你让我去哪儿?
去山下找死吗?
他抬起头来,放下筷子,一脸和淡地问我:“师傅是新来的挂单和尚吗?”
他还问我刚才跑什么?
他又问:“老和尚与他孙女哪去了?”
我不知道老和尚与他孙女。昙花庵里怎么会有老和尚与他孙女呢?
我问:“庵里有吗?”
“怎么没有?”他突然站起身来,生气道,“我和他们一起呆过。”
他想干什么?好像他们不见了是我的责任;他不会认为是我把他们赶跑的吧?
“什么时候?”
“五年前。”
“五年前?这么久呀?”
他紧盯着我,目光深远,甚至有些咄咄逼人。
这种目光,我在哪儿见过?我肯定见过。他应该不是一个普通人。
他问:“师傅从哪儿来?来了多久了?”
我转身走到灶头,我饿了,我得先吃点饭,才有力气再跟他理论;但锅里只剩下镬焦了,我一铲就知道焦得不行。什么人嘛,连顿饭都不会烧!我往锅里浇了点开水,然后把可怜的一点镬焦全铲到碗里;我坐到他对面,低头吃我的饭。有饭吃总比饿着强,尽管嚼在嘴里有些苦。我原本早就该吃上晚饭了,但刚才被他这么一折腾,直到现在还空着肚皮。
他不再吃他的饭,只是盯着我看。
我有什么好看的?
告诉我,我有什么好看的?我想知道。
我说:“我来了半年多了,没有你所说的老和尚与他孙女。”
“怎么会没有呢?”
“我哪知道?”
我朝他白白眼。
他不想吃饭了,是吧?我抓过他的饭碗,把他碗底的冷饭拨到自己碗里,我把饭全吃了,我还吃光了两碟蔬菜,一碟青菜,一碟萝卜;我吃光了桌上所有的东西,还不觉得饱。我还饿着呢,他凭什么跑来这荒山野岭抢我的饭碗?我说:“你可以走了。”
我说:“你饭也吃了,人也找了,你可以走了。”
“请吧!”我说,“先生,这儿没你过夜的地方。”
“现在?”他问,“外面这么黑,你要我现在就下山?”
他说:“你才来多久?五年前我就是庵主的朋友,我就住在这儿。”
“你说,”他责问道,“是你走?还是我走?”
呵呵,他倒是跟我杠上了。
但我们就对面对坐着,两个人的胳膊都架在桌上,谁也没有动一下身子。
只有一盏油灯在桌子中央,灯光像个小美人,在晚风中不断地跳舞。
“就是东壁画上那位小仙女呀,”他说,“就在大殿上。”
“你不会没见过吧?”他又问。
“就在大殿上,东壁是天女散花,西壁是八仙过海。”他说,“在东壁画上,身着红裙的大仙女领着六位妹妹,腾云驾雾,飞翔在碧海蓝天,她们手持百花篮,向人间频频散花;其中只有穿黄裙的三仙女回过头来,顾盼着独自落在最后的小仙女。小仙女一身紫裙,她还只是个玩性十足的小姑娘,梳双马尾辫子,长长地挂到腰间;一脸稚嫩,手拈鲜花,笑吟吟地凝视着壁外。”
我越听越糊涂,那不是壁画吗?跟老和尚与他孙女有什么关系?
我笑道:“你不会把老和尚的孙女当做小仙女了吧?”
他拍案叫绝,连声称是;又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会知道的?
听他的口气,瞧他的眼神,连傻子都猜得出来。
他说:“那天,老和尚陪我欣赏东壁画时,我忽然觉得小仙女樱唇欲动,眼波将流,她跟活了一般,我心中便若有所感;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一个女孩跑进大殿里来,稚嫩地叫爷爷,说晚饭做好了。我回头一看,顿时惊呆了。这不就是画上的小仙女吗?”
“嗨!”我说,“这画八成是老和尚画的。”
“可我不知道他会作画呀,”他说,“我也没看见他作过画。”
“人家会作画非得让你知道吗?”
“可我在庵里呆了七天……”
“你来做什么?”
“我那时候焦头烂额,万念俱灰……”
我怎么听着都觉得他是在说我呢?
“怎么啦?”我问。
“不瞒你说,”他说,“我叫顾彼……”
他一说他叫顾彼,我就知道他是谁。我们去过他的办公室。秦向晚总能弄到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她先打电话进去,没人接,我和她再进去,老五在外面接应。给我十秒钟,我就能打开办公室的门。任何锁都难不住我,我有这个本事。我们进去了,我负责打开所有的地方,秦向晚负责搜查一切值钱的东西。她喜欢把搜出来的东西都堆到办公桌上。这个白骨精!搜查结束后,她就在赃物前面放上主人的姓名牌,自己站在边上,摆各种妖七妖八的姿势,叫我用手机给她拍照留念——这是她的爱好。这半年多来,我经常翻看这些照片来消磨时光,想想那些辉煌的日子,还有她上嘴唇的痣。那些东西都是秦向晚独自拿出去的,就装在收破烂儿的巨无霸的蛇皮袋里,她背的背,拎的拎,跌跌撞撞地往外走;那些地方的门卫都是死人,还以为她是收破烂儿的呢!我记得就是去他办公室的那一次,那个傻逼门卫还抢着帮她提东西呢,一对色眼像蚂蟥似的盯着她的胸,问大姐,您哪儿人?并殷勤地送到大门外,吓得我们一身冷汗,事后又大笑不已。每次喝酒,只要谁一说大姐,我们就乐翻天。他办公室里的东西可真不少,有字画、金银饰品、手表、手机、高级烟酒和各种滋补品,秦向晚一个人拿都拿不过来。那些年,我们用这种方法,所向披靡,弄到不少钱;那些丢东西的人,是绝对不敢报案的。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向晚最终还是栽在一个傻逼门卫的手上,她就供出老五和我。老五也进去了,俩人都说我是主谋;幸亏我溜得快,我逃上了皋亭山。
他说:“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烂成这样了?”
“我工作才十多年,就已经烂到芯子里了。”他说,“说出来不怕你笑话,现在中纪委所查的问题,在我身上都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包二奶、通奸、嫖娼……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什么事都敢干,那十几年书全读在狗身上了。我们那个圈子里,有人进去了,有人跳楼了,我就知道我也快了,但我还抱着侥幸心理,我听说龙居寺的菩萨很灵的,那天上皋亭山拜过菩萨后,我不想回去,我怕回去,我长期失眠,我听到警笛声就如五雷轰顶,我就想找个地方,睡个安稳觉。”
“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你能相信吗?我都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套房子?十几套总有吧?家里那么宽广,装修得那么舒适,但我就是睡不着觉,每时每刻都胆战心惊;我跑到这么个荒山野岭里来,只求睡个安稳觉,你能相信吗?”他说,“我是无意间撞到昙花庵的,我想这就是天意吧。我听老和尚说佛法,茅塞顿开。但真正打动我的,还是这位小仙女。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她这样率真、这样纯粹的女孩,我只能这样形容她,我想不出更精确的字眼;她特别爱笑,咯咯咯的,笑得那个脆;世间一切,在她眼里都是乐趣;我们就着一盏油灯,老和尚向我细说佛法时,她就像一头温暖的小猫,在我和老和尚身上爬来爬去,咯咯地笑,露出那颗好看的虎牙。却不知为什么,我听到她的笑声,心情就开朗多了,就把山下的一切都忘却了。老和尚说他的这个孙女是个痴女,又说她喜欢我,她玩累了,就团在我的膝盖上,像猫一样地睡着了。”
“我在山下阅女无数,但从未见过像她这样希罕的宝贝;如果拿山下的女人与她相比,哪里及得上她一个零头呀?”他说完,就连忙呸了数声;他说,“我怎么能拿人跟她比呢?这不玷污了她的清白吗?她是和氏璧,完美无瑕。”
我笑他:“你是被她迷住了?”
他忙否定道:“不。不。”
他说:“我都不敢想象,我还能过上宁静的日子。老和尚说人都是有定数的,命中注定你今世只能用十块钱,你就连十块零一分都用不到。但我显然昏了头,我就想下山去弄些钱来,让他们过上更好的日子。我在山下有的是钱。钱对我而言,只是银行里的一串阿拉伯数字而已,除了加重我的罪行外,别无用处;但对老和尚他们来说,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是可以把钱当做钱来用的。我在庵里呆了七天,那是一段多么美妙的时光呀。第八天一大早,我辞别他们爷孙俩。小仙女执意要跟我下山。你说我怎么敢带她下去呢?那种地方哪里是她能呆的。我说我最多三天就回来。是的,我那时候打定了主意,在山下处理完事情后,我就赶回来,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想和他们隐居在昙花庵也好,和他们云游四海也好,我就想和他们在一起,再也不问山下之事了。”
“小仙女死扯住我的衣袖不放,眼里含着泪。‘乖!我说,‘我马上就回来的。”他说,“我硬是扳开她的手,我好狠心呀!我说,‘我去去就回。我都忘了吻她,就这么下山了。我走出很远,见她依旧站在庵门中央,站成一个‘囚字,我毫无察觉,只朝她挥挥手,大声喊‘等我!”
“我好傻呀。我不该下山的。我下山去干什么呢?”他说,“对他们而言,钱并不重要;真的,一点都不重要。钱在他们眼里算个屁!我不就是羡慕他们清贫的生活吗?”
他说:“我失联了七天,山下早就传开了,他们说我是畏罪潜逃,纪委和司法已经介入了,已经立案侦查了;我还傻乎乎地下山去,我一下去就被逮进去了。我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我被判了八年刑。我积极配合,伏罪态度好,减刑三年。我只想早点出来,我只想尽快地回到他们身边。五年后,我从牢里出来,那些因为我而进去的很多人里,有不少对我恨之入骨,甚至要取我的性命。”
“我在牢里一遍遍地回想这七天时间,山中七天,胜于人间百年哪;我在牢里,无时无刻不念到老和尚和小仙女,我悟透了老和尚所说的佛法,我思念小仙女。”他说,“我并不是怕死的人;真的,人吗,有哪个能活着回去的?我出狱后,在山下只呆了两天,我就再也呆不下去了;今天我谎称自个儿出来散散心,就直奔这儿来了。我哪里会想到他们已经不在了?他们怎么就走了呢?我们都约好了的,他们怎么就不能多等些时日呢?”
我说我不知道。
我来时,庵里就空无一人了。
我还问:“你说的那个小仙女壁画上有吗?”
他说:“有呀!怎么没有呀?”
我记得我看过东壁画,我肯定看过,但我不记得壁画上有他所描绘的小仙女呀?
我们在僧舍谈了一宿,一直谈到天快亮,我们才睡下。
山里风大,一宿的狰狞声。
这些无孔不入的家伙,趁夜黑,总能从人间偷走一些寂寞无主的东西。
侵骨的夜寒中,我见他谈得那么诚恳,他的事,又不像是假的,我也就谈了我的事。
我又在山下犯了事,这回麻烦可就大了。秦向晚和老五,又都进去了。我连夜逃上皋亭山,再次跪倒在龙居寺方丈主持无尘大师面前,恳求他老人家收留我。这回我是铁了心,决意昄依佛门,青灯黄卷了却一生。你就是赶我下山,我也不下了;我哪里还敢下山呀?我在山下犯下的事,足以要了我的命。可是,无尘大师却让师兄们将我无情地逐出了山门。
他说我尘缘未了。
这个老和尚,他哪里有什么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肠呀?
上回我在山下犯了点事,也挺麻烦的;秦向晚和老五相继进去了,我要再晚一步,也进去了。但我总算上了龙居寺,无尘大师说我年少无知,却具慧根,亲自剃度了我,赐我法号——舍得。我在龙居寺,做了三年多舍得和尚,结果让秦向晚发现了。她就引诱我下山。她上嘴唇有颗小痣,就像吃过麻饼还粘着粒黑芝麻;我第一次见到她时,还真以为是黑芝麻呢,我提醒她,她就笑,问我想吃吗?可香了。她还真的凑上来,将嘴凑到我嘴上。这些年,她一次次地让我吃黑芝麻;但我每次吃,总归没有好事情的。这个白骨精!她把上半身给了我,却把下半身给了老五。我不辞而别。谁知在山下只混了大半年,又犯事了,而且犯的还不是一般的事;我们打伤了几个年轻人,还失手打死了一个。那不是我的错,都是老五挑起的事端,而且人也不是我打死的;但是我参与了,我想秦向晚和老五他们这会儿早就把我供出来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又会像上回那样,串通好了,把责任全推在我头上;我就是有千张嘴,也无法洗清自己的罪名。秦向晚这个白骨精,真是个祸水,她与老五狼狈为奸,却一次次利用我对她的感情,骗我去背黑锅;可惜我现在才醒悟,已经迟了。
我被逐出龙居寺,哪敢下山呀?我逃往更深的山里,我在天子岭上找到这座昙花庵;当时庵门紧闭,我敲了半天,也没有人答应。不过,对于我而言,庵门锁与不锁,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在山下就是干这个的。我进去了,发现庵里,我避难所需的物品应有尽有;它给我的感觉,庵中应该有人,应该一直有人的;只是这天他们锁上门出山去了,晚一歇就会回来的。我就住在庵里,等着庵主回来。我想恳求他老人家收留我,让我做他的弟子,让我一辈子隐居于此。
但是半年过去了,我等待的人始终没有回来,我差不多已经把自己当做庵主了。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刚刚入睡呢,就听到大殿里突然爆发出惊慌的大吼声。
跟出人命似的。
“舍得师傅!舍得和尚!舍得!……”
顾彼救命似的喊我。
我跌煞扳倒地爬起床,连衣服都没穿整齐呢,我就冲进大殿。
顾彼站在东壁画前。
他好端端的,用得着这么大吼大叫吗?
但他像个醉鬼,站都站不稳了,身体前后摇晃,手指着东壁画,急赤白脸地叫我看。
我看了。好好的,没什么呀?
他指着落在最后的小仙女,拼命地喊我看。我看了,这位小仙女身着紫裙,梳着形似螺壳的发髻,髻上系着两根粉色丝带;怀里抱着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婴,虎头虎脑的,伸出两只肉嘟嘟的小手,揪着她肥胸前的衣裙,向着她开怀大笑;而小仙女呢?她侧过脸来,凝视着壁外;她的眼里,半是爱怜半是哀怨,半是期待半是失落……
这画好好的。就是这样的呀。
我问:“怎么啦?”
顾彼说:“小仙女变了,我当时看到的,她还是个小姑娘,梳双马尾辫子,长长地挂到腰间;她一只手提着百花篮,另一只手拈花……但你看现在,她已经是一副少妇模样了,盘起了发髻,手里拎的不是百花篮,而是抱着一个男婴……”
“我……”顾彼结巴道,“她……”
我奇怪地盯着他,我都不知道他想说明什么?
这只是一幅壁画,他用得着这么惊头怪脑吗?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