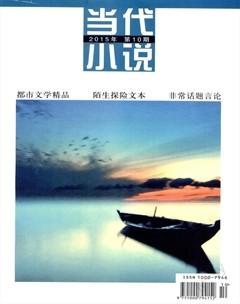手印画
袁省梅
不要因为你一家的事,影响了大家。
婆婆坐在门前。婆婆坐在修鞋箱子后。婆婆坐在尘雾里。
土尘轰隆隆呼啸着来了,又呼啸着跑了。土尘浓稠、黑黄、呛人。土尘里看不见人。有声音从土尘里挤了过来:八哥奶奶,快让开吧,推土机来了。那声音纷纷杂杂的,一声一声,却是掩不住的焦灼、担心和不耐烦的恼火,压抑在尘雾中,闷闷的。婆婆听不见人们的声音。怎么说呢?婆婆根本没理会这些声音,没理会土尘,没理会身边一堵一堵的墙轰轰地被推倒了。房倒屋塌。婆婆手抓着她的修鞋车把,只盯着前面的街道。
八哥是从这条街上走的,婆婆说,她肯定还要从这条街上回来,八哥认得这条街,认得我们家,认得这堵墙。
婆婆说,八哥就是认不得这条街,认不得我们家,认不得这堵墙,她也认得这墙上的手印啊。
婆婆的声音不大,她好像是说给自己的,好像是说给罩住她的土尘的。没有人听婆婆的。人们都在吵吵楼房什么时候能盖起来,什么时候能搬进去,自己喜欢哪个楼层,怎么装潢……谁听婆婆的话?谁有闲心管什么认得认不得?
婆婆的声音跟那些人的声音一样,裹在白的黑的尘土里,就像是裹在了水底下压在了山下面锁在了箱子里,沉闷闷的,也滞重,也轻飘,像清早醒来前的那个梦,明明在眼前生动着,却抓握不住,不知去向。
土尘小下去时,一个人走了过来,是工程队的队长,胖子,奓着俩浑圆的胳膊,踩着砖块瓦砾,粗短的腿一跳一跳的,像个孩子般蹦跳着。胖子催婆婆离开,这儿危险。胖子说,就是人长眼,推土机挖掘机可不长眼哪,砖头水泥疙瘩可不长眼,呼噜噜墙倒屋塌时,砖头瓦片要飞就飞了起来,谁也保证不了,要飞到哪儿落到哪儿,谁也保证不了。胖子说,伤了您,我可赔不起,这活儿我本来就不挣钱,钱不好挣哪,钱难挣屎难吃,没有假,您说,我还要付推土机挖掘机的钱还要付运垃圾打扫场地的钱,一天干不干活也得好几千的给人,我上有老下有小,挣俩钱不容易,您老就挪挪让让,叫我把活儿利利索索地干了,成不?我给您鞠躬了。
胖子说着话,就把腰背弯成了一张弓,抬起头时,左眼里眯了尘屑或者是别的什么碎屑,说着话手就在左眼上揉。人们远远地看着他,都说这胖子给婆婆唱哭戏去了,婆婆吃他那套吗?
婆婆紧紧地抓着她的小平车,平车上放着她的修鞋箱子,还有一个红颜色的塑料凳子。婆婆仰着头,看着胖子,等胖子的手从脸上放下来了,她伸出三个手指,说,三天,就三天,缓上三天等不上我的八哥,我保准离开,不为难你,不耽搁你们干活。
胖子的眼睛还是没有擦利索,他不停地眨巴着眼睛,还是不行,手又在眼睛上使劲地擦,也是不行。他把手在裤子上蹭蹭,捏着左眼皮,蹲在婆婆跟前。婆婆站了起来,把马扎让给他坐。他叫婆婆坐,说我坐这个吧。伸手从平车上拿那只塑料凳子,被婆婆拦住了。婆婆喊,不要动这个凳子。婆婆又把她的马扎递给他,说,那是八哥的凳子,八哥的东西她看得紧,从来不让人动一下。
胖子讪讪地站了起来,站起来时,他的左眼好了。他说,好了,没了。他眨巴着眼,说,真的是眼里揉不得沙子。婆婆没说话,看着他,很忧伤。他又蹲了下来,说,我知道你们家八哥的事,我也替你难过,我把八哥的事讲给好多朋友了,你知道我朋友很多,我叮嘱他们留心着,见了八哥给我打电话。婆婆的眼圈红了,说,谢谢你和你的朋友,要是你的朋友真的碰巧见了八哥,就告诉她我等她回来哩,我没有不要她,她是我的孙女,我咋能不要她呢?胖子说,肯定了。胖子说,您看,让推土机先干活?咱一起找八哥,人多力量大,肯定能找着八哥的,您放心地离开这儿让推土机干活吧。
婆婆半步也不动。婆婆躲开胖子伸出的手,往后缩了缩背,伸出三根手指,说,就三天,你行行好缓我三天,我八哥这三天没回来,我就离开,我说话算话。
胖子说,您老是糊涂了吧,十天前,您就说缓三天。要是活儿不催得紧,您就是缓上三十天三百天,我也没意见。我有什么意见呢?我一点意见也没有,谁家没个难心事呢。胖子指着尘雾里的人们,说,就是我愿意叫工程停上三天,您去问问他们,他们可愿意?
都是这条街上的人。他们站在远远的地方,眼看着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倏地成了一堆废墟,黑的灰的瓦砾砖块看上去也悲凉,也凄惨。人们的脸上呢,却是兴奋奋、喜滋滋的,灰尘一层一层地扑到了脸上,也不离开,都在说着不久以后这里就要建起来的楼房、花园。
婆婆不看胖子,也不看那些人。婆婆看眼前的街道。
这是一条南北街。婆婆家正好在十字路口。老城区的街道窄小,细长。街上有小百货店,也有小超市、小饭店,还有个小小的菜场,却一点也不嘈杂,买的卖的,都是熟头熟脸的人,斤两上价钱上,是没有可说的。老城区的人呢,走路也慢,说话也慢,好像从来没有什么着急的事,碰到一起,就要说上好一会儿。走到南街口或者是北街口,哗地一下,眼前的景象变了,是两个天地了。怎么说呢,这里的街道宽得能抵上小街的十个八个了,却没有小街松快了。车也多,人呢,不知从哪里来的,突然一下子就拥挤了起来,来来往往的,一个个撵着脚后跟,走得匆忙。
婆婆的修鞋车在她家门口,小街的深处,坐在修鞋车后,抬头张眼的,就能看见街口不断闪过的人。婆婆不明白那些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着急事,就像她不明白儿子儿媳弃家舍业地跑到广州打工一样,世上好多事,她都不明白。婆婆说,都说人老成精哩,我看我成了鬼了。婆婆认为鬼都是糊涂的。婆婆的话有时说给前来修鞋的人,很多时候呢,是说给八哥的。八哥坐在她旁边,仰着脸,看着她,老鬼。婆婆每次听到八哥说她是“老鬼”,就咯咯地笑,指着隔壁老张,问八哥,张爷爷呢?八哥说,鬼精。这些话都是老张教给八哥的。老张对八哥说,你奶奶啊是个老鬼,鬼精鬼精的。
老张退休了,门边靠一块小黑板,在黑板上写字。老张写的字,婆婆一个也不认识。老张写的是篆体,婆婆觉得好看,跟画儿一样。老张在他的黑板上用篆体写了一行字:免费书法教学。可是摆了一个多月了,白的粉笔字都成了灰黄淡白的瘦弱弱的了,快要在黑板上挂不住了,也没有一个人前来学习。倒是八哥,看见老张在黑板上写字,就凑了过去。有一天,老张把一截粉笔塞到八哥手上,横竖撇捺地教她写字。婆婆正抱着一只凉鞋在修,听见老张叫八哥横线要平、竖线要直,就摇摇头笑了,想劝老张别费那苦心,八哥没上过学,哪懂什么横竖平直?还书法哩。可她没有说。她是存了一点私心,怎么说呢,得有人跟八哥玩啊。
八哥啊。
八哥啊。
我的八哥啊。
婆婆说,八哥就是从这条街上走丢的,她回来了,找不见我找不见我家房子了,可咋办?
工程队队长的胖脸吊吊着,冬瓜一般,一说话,脸蛋就嗖嗖嗖嗖地抖动。他说,八哥从这条街上走的,我看您最好坐在街口,她要是回来了,远远的,就能看见您,来往的人也多,您的生意也肯定好,再说了,您也可以再多托付些人帮您找八哥啊。
婆婆摆着手说,不是这么回事。婆婆指着她身后的房子,说,八哥认得房子,房子这么大,八哥远远地就能看见,我老了,八哥再见我,还不知道认不认得我了,五年了,八哥走了五年了。婆婆说着,脸上就滚下两行清泪,黄灰的脸上犁开了般黑湿了两道。
胖子急得直跺脚,揉红的眼睛瞪得傻大,跳脚就嚷开了,那您啥意思?那您啥意思?不让拆了?你一家不拆,你知道不,工程没法往下走,一街上的人都不能早早地住上新房子。不能因为您一家,影响了大家啊。
八哥戳着墙上的手印,说,妖怪。一会儿又说,叶子。一会儿又说,树。再问时,她说,老鬼鬼精。
胖子跟婆婆说话,却把脸扭向站在推土机铲车旁边的人。那些人看推土机铲车不动了,就围了过来。很明显,胖子的话是说给婆婆的,也是说给他们听的。那些人果然有急了的。怎么会不急呢?楼房还在纸上,房子已经拆了。他们呢,都是在外租着房子住。人们叽叽喳喳地吵嚷得比树上的鸟儿还要欢实,话语里全是不满和气愤。人们都认为,八哥,婆婆的孙女,没了都五年了,一时半刻的哪能回来?婆婆挡住不让拆,就是故意地想多要点钱。有的说,啥钱啊,就是想多要一套房子。
婆婆听见了。隔着渐渐落下的灰尘,那些人的话一字不漏地钻到了婆婆的耳朵里。婆婆的脸涨得青紫黄黑,双手紧紧地抓握着平车的横杆,忽地站起,想去跟那些人理论,又想起她要是离开了,没准胖子就会叫推土机推倒房子,还有,身后的这堵墙。她又忽地坐下,双手在车杆上攥了又攥,好像那铁的车杆是毛巾,她要拧出水来。
老张来了。
老张筛晃着一身的灰土,从人群里挤了过来。老张一来,就蹲在了婆婆身边,也不说话,点了一棵烟抽。烟抽完了,他才开始说话了。他倾着身子,劝婆婆不要挡工程。老张说,胖子说得对,不要因为咱一家的事,影响了一街人。大家在外面租房住借房住,拖家带口的,锅碗瓢盆的,容易?都不容易,照我说,你把鞋摊摆到街口,等八哥,也能挣俩钱,照我看,街口的生意肯定比咱这小巷子好。
老张的声音小小的,话说得慢慢的,一字一句都是不急不慌的,却一字一句都落入了婆婆的心里。贴心贴肺了。婆婆抓了一把脸上的泪,说,挣钱是小事,你知道的,这几年,我就是为了等我的八哥才不敢挪地方,我得等我的八哥啊,老张你说这房子拆了,八哥回来看不见这堵墙了,不又走丢了?我老了,这墙上的画不会老吧?八哥总该记得这幅画吧?她那样的喜欢这幅画,睁眼起来就要举起手在这画上比划来比划去,没人跟她玩,她跟这画玩得那个高兴啊。婆婆的声音慢慢地低了下去,低到最后,老张只能听见她的呜咽,涌在胸口上,堵在喉咙里,是想哭又竭力不哭的样子,却给人一种出格的疼痛。
老张的眼也软了。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扭过头,看婆婆身后的墙。
墙上是一幅手印画。
画是用手掌印上去的。大手印是婆婆的,小手印是八哥的。老张记得,那天修鞋摊上没有活儿了,婆婆教八哥认字数数。八哥已经七岁了,同龄的孩子都上学了。婆婆在墙上写一个“人”字,教八哥念“人”,八哥不念;婆婆又在墙上写一个“1”,教八哥念“1”,八哥还是不念。婆婆看着八哥不懂不醒的傻样子,心里愁死了。八哥刚过满月,她妈妈爸爸就把她留给婆婆,出去打工了。婆婆哪能想到一个高烧就能把一个人毁了。八哥半岁时发高烧,药也吃了,针也打了,输液瓶子也挂了,可还是落下了毛病,脑子有了问题,痴痴呆呆的,没有同龄孩子的灵性。出去玩,就找不到家了,好在这条街上的人都知道八哥知道婆婆,看见了,就把她送回来,或者是,喊婆婆领去。八哥的爸爸妈妈呢,出去打工,好几年了也不回来看八哥,过年过节了,电话里问问婆婆问问八哥,就算是尽了做儿子做父亲的心意了。每天,婆婆看着八哥,愁死了。家都找不见,以后呢,咋办?想起自己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几年活头了,八哥呢,还小啊,还有长长的大把大把的日子啊。婆婆每天都紧紧地看着八哥,手上修着鞋,就要抬头看一下八哥,喊她不要乱跑。喊一声没有八哥的回声,婆婆就放下活儿,去找八哥。有一天,八哥从老张那里玩“字”回来,满手的粉笔灰也不去洗,就往墙上抹。黑灰的墙上,一抹一个白手印,也清晰,也分明,像那墙上长出来一片小叶子般,安静,美好。八哥看着自己的手印,乐得直蹦高,直着嗓门喊奶奶看。婆婆正在修鞋,顾不上看她。她就跑过去,抱着婆婆的头,拧着她的头非得让她看。
八哥说,画。
婆婆看见了墙上的那个小手印,呵呵地笑,说,好,八哥的画。
八哥说,叶子。
婆婆又说,好,八哥的叶子。婆婆叫八哥自己玩去,她还要赶紧地把手上的鞋子修好了,脚边上还堆放了好几只鞋子等着修。儿子儿媳在外打工,婆婆不让他们寄钱。她知道,他们在外也不容易。她说,鞋摊挣得钱够我跟八哥吃喝了。婆婆给八哥说好时,又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手印,淡白的手印还挺好看。婆婆问八哥那是啥?八哥说,画。八哥说,叶子。八哥拍着手,看一眼婆婆,看一眼她的画她的叶子,斜着眼睛,翘着嘴角,也开心,也得意。那一刻,婆婆恍惚了。婆婆觉得她的八哥也不傻不痴啊。婆婆就着急地说,八哥再画个叶子?八哥却不理她了。八哥坐在小红塑料凳子上,把大拇指塞到嘴里,嘬得吧唧吧唧响。
婆婆的心思却动了。
婆婆推下手里的活儿,把门边的那块墙刷得雪白,又买来各色颜料,都是专刷外墙的那种耐腐蚀的颜料。婆婆把红色涂在八哥的手上,涂得满满的,叫八哥往墙上印。八哥说,奶奶印。婆婆只好给自己的手上也涂抹上绿颜料,叫八哥看着,她轻轻地把手印印在了墙上。白的墙上倏地出现了一个清晰的绿手印。八哥咯咯咯咯笑着,把自己的小手按到了墙上。绿手印的旁边印出来个红手印。八哥不顾手上的红颜料,扯着奶奶,大嚷大叫,画,画,八哥的画。那天上午,婆婆没有修一只鞋子。婆婆和八哥在那块白墙上印了好多的手印。八哥的手印有的五指张开,有的紧紧靠拢在一起,有的呢,只有半个手掌,小小的手掌,像半个月亮一样黄灿灿的,有的只有三四根手指头,细细的、嫩嫩的小枝条一样……
老张过来了。他是看见了墙上的手印过来的。他一过来,就给八哥举出一个大拇指,夸奖八哥厉害,说,照我看我们八哥的画最漂亮。
婆婆搂着八哥,呵呵笑,我们八哥聪明呢。
老张问八哥画的啥?
八哥戳着墙上的手印,说,妖怪。一会儿又说,叶子。一会儿又说,树。再问时,她说,老鬼鬼精。
老张和婆婆笑得直抹眼泪。老张说,谁说我们八哥傻呢?八哥想象力多丰富。老张拿来毛笔,在那些“叶子”上画了树干、枝条,还在叶子上画了鸟和蝴蝶。这些手印被一条线牵住了般,找到了家般,轻盈,自由,是一棵正在春风中成长的小树,又明亮,又芬芳,充满希望了。
老张问八哥,好看吗?八哥说,好看。八哥指着老张的黑板,伸出小拇指,耸着鼻子,哼哼着,不屑的样子。老张拍了一下八哥的头,骂她鬼机灵,说我帮你画好了,你倒瞧不起我的字了。他又对婆婆说,这孩子要送到康复医院,让人家医生给专业地进行训练,没准能好了,就是好不了,也没准能在某个领域有成绩,这孩子,不笨。婆婆看着八哥,愁着一张苦脸,说,哪有钱?老张默了一会儿,又说,没准长着长着就好了,开窍了。婆婆说,但愿吧,看她的命了。婆婆看着兴奋地在墙上印手印的八哥,也忧伤,也无奈。她想,没准真能好了。她沉浸在柔和又幸福的想象之中。
此后,八哥睁开眼就跑到门外,看她的画,把手按在手印上,一个一个地挨着按,一边按,一边念叨着,八哥,奶奶,八哥,老鬼,老鬼,奶奶……按完了,才去吃饭。晚上睡前,婆婆给她洗干净了,嚷她上床,她还要趿着鞋跑到门外,把手印画再挨个按一遍。每一下,都像是第一次按手印,快乐,新奇。婆婆想不明白这么一幅画能给八哥多少的快乐?可是,明显的,八哥在街上玩耍时,再没跑错过家。远远地,她就指着墙上的画,大喊大叫,我的画,我的画。
是八哥走的那年秋里,区委会派人给街上的老年人照相,说是办理什么证,统一的红底子照片。一块红布就挂在了婆婆门边的墙上,巧巧的,就在那幅画上。八哥从老张家回来,看不见自己的画,愣怔地盯着奶奶看看,又盯着红布看看,眼睛呆呆的,痴痴的,突然,转身就要走。婆婆一把扯住她,问她干啥去?她瓷着眼睛,小脸皱成了苦瓜,说,找树去。
你再不让开,就给你儿子儿媳打电话,叫你儿子儿媳回来做你的工作。
可是,现在,八哥还没回来,他们要把墙推倒,墙倒了,哪还有画?没了画,八哥怎么能找见家?就是八哥找见了家,她要是看不到她的画,该有多伤心?
婆婆对老张说,再让他们宽限几天吧,你帮我说说,让他们宽限几天,没准这几天,我的八哥就回来了。
婆婆说,你还记得吧,那天,我就趴在箱子上打个盹,就一眨眼的工夫啊,你还记得吧,睁开眼八哥就不见了。
婆婆没说她在迷迷瞪瞪时,看见八哥往街口走去了,一直往街口走。她非常清晰地记得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是冬日的一个傍晚,从早上到下午就没看见太阳,傍晚时,天是愈发的阴沉了,却不觉得冷。整个冬天都没有冷过。风在巷子里悄悄地吹过来吹过去,很长,很慢,暖湿湿的。婆婆记得,那个冬天没有见过冰。婆婆不知道,这看似暖和的冬天深藏着一个残酷的玩笑。属于她一个人的——“玩笑”。
那天,街口有个卖泥哨的,花里胡哨的泥哨,扎着涂了红颜色绿颜色的鸡毛,一吹就嘀嘀地响。城里已经好多年不见这东西了。婆婆觉得,这两年里,好多年不见的东西,时不时地在城里也能看见了,比如叮当,比如糖人,比如这泥哨。婆婆喜欢这些东西,小时候玩过的,看见了,就觉得有一股子亲切,就会买一支两支的给八哥玩。好多时候呢,八哥也不玩,看一眼,就给扔到了修鞋箱子上。婆婆再捡起来,举在眼前看半天,然后,小心地插在箱子上。那天,八哥就是听见了泥哨嘀嘀叫的声音,就走了过去。婆婆想喊住八哥,不要往街口走。街口人多车多,乱。每次婆婆走到了街口,都莫名地心慌,何况不懂不醒的八哥呢?可是,她没有喊。她想八哥会像以往一样听她的话,跑跑就回来了。
八哥却没回来。
婆婆找了一栋楼两栋楼。婆婆找了一个小区两个小区。婆婆找了一条街两条街。不大的城市,婆婆找遍了,没有八哥。婆婆坐在门前的手印画前等八哥;坐在空荡荡的家里等八哥。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从冬到春,一年一年,婆婆忧伤地计算着八哥走丢的分分秒秒,冰冷的泪水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流得横横竖竖。
有人说,一个傻孩子,养着有啥用?丢了就丢了。
有人说,没准婆婆就是故意地让八哥走丢的。
当然是背地里说。婆婆听说了后,一股冷气从脚后跟倏地蹿到了头顶,她的额头上突地就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我没有,她说,我没有,我亲亲的孙女,我哪舍得?婆婆没跟人理论。婆婆也确实这么想过。也不过是想想而已,想想就是做了吗?很多时候,婆婆也不多想以后。婆婆只想多挣几个钱,等她不行了,把钱给福利院交了,把八哥送到福利院去。老张说,福利院不收费,收费还叫福利院?婆婆呢,也不知道福利院要不要钱,可她想着有了钱,给了人钱,人家总归是会对八哥好吧。
可是,八哥却走丢五年了。
婆婆对老张说,八哥就是出走十年八年,她也会记得这墙上的画,她那么爱见这画,咋能忘得了?你给人家说说,把八哥的画再留三天。
老张说,人家能听我的?再说了,人家也不容易,挣个受苦钱,一级压一级,咱再为难人家?
婆婆说,我没为难人家,我就是想再宽限几天,缓上几天,没准这几天里,我的八哥就回来了呢?
老张说,你再不让开,人家说要给你儿子儿媳打电话,叫你儿子儿媳回来做你的工作。
婆婆听老张说叫她儿子儿媳回来,她一下就软了。他们打电话回来,问起八哥,婆婆就说,睡了,出去玩了,去老张家了。八哥丢了五年了,她一直没有给儿子儿媳说。是不敢啊。当然是,也担心。儿子和儿媳都在工地上干活,不能让他们往心上再搁事。婆婆想她自己找。婆婆相信她能找见八哥。
老张说,照我说,八哥要是能回来早回来了,五年了,一点音讯也没有。老张顿了一下,又说,照我说,丢了就丢了吧,傻傻呆呆的,你养到啥时候是个头?你都这岁数的了。
婆婆瞪着老张,好半天不说话。婆婆有时想要是八哥没有来过人世就好了,或者是,没有生在她这个穷家也好啊。八哥刚丢了那年,婆婆找得乏累,也生气,她想丢了就丢了吧,有时,看着八哥痴痴呆呆不懂不醒的模样,婆婆想自己七十的人了,还能活几年,自己死了,八哥怎么办?指望她爸妈又指望不上,不能说她爸妈嫌弃八哥,就是真的不嫌弃,他们打工挣的那点钱,还要供八哥的弟弟上学,能管了八哥?这个时候,婆婆就很烦恼,她想要是我死了,我就一把老鼠药让她吃了让她跟我一起走。可转眼她又想她再不好也是一个命啊,哪里下得了手?婆婆下不了手,婆婆又想要是丢了呢,丢了,眼不见为净,一了百了。婆婆想她活着可有啥意思?人世的好她不知道,人世的不好她也不知道,啥也不懂。想八哥啥也不懂时,婆婆就想起了门边的这幅画。婆婆又说,八哥不傻,八哥傻啥呢傻?傻能画下这么好看的画?婆婆认为八哥的手印画咋看都好看,是平常的孩子都画不出来的好看。有时,婆婆故意地不让自己看那幅画。那些手印,一个就是一个八哥,它们是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八哥,是一岁的八哥三岁的八哥,那么多的欢笑和哭泣,那么多的希望和疼惜,那么多那么多,它们都好像藏在画里,藏在小手印后,那些手印也会长了嘴,喊婆婆;长了手和脚,跑到她跟前,扯她拉她:不要毁了她的画不要毁了她的画啊。
婆婆就是这样,一天这么想,一天呢,又那么想,怎么想心里都挖了一块似的疼,终归呢,还是不舍得。今天,听老张说八哥丢了就丢了,婆婆的心就蜇了般疼痛。婆婆烦恼老张说这样的话,她嫌恶地白了老张一眼,她不明白老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可她没有责怪老张。她不是也这样想过吗?她不声不响地、神情专注地看着八哥的手印画。婆婆把她糙黑的手掌按在一个小手印上,她觉得八哥的小手就被她牵住了,抓握在手心了,安然,妥帖,舒心了。婆婆挨个的,在每个小手印上按一下,摸一把,好像是,她触摸的手印也有了温度,变得柔软了,有了生命了,活过来了,八哥呢,就藏在这些小手印的下面,喊她:
奶奶奶奶奶奶。
婆婆果然看见八哥喊她,倏忽又不见了,忽地又在另一个手印上出现了,挤弄着眉眼,撇着嘴角,逗惹着她,咯咯咯咯地笑。
婆婆扑在墙上,把头抵在手印上,喊了一声,八哥,我的八哥啊。
婆婆嚎啕大哭。
老张在废墟上捡来一本杂志,走到婆婆身边,把书打开,两手捧着,说,放这里吧。
婆婆对老张说,不要给我儿子儿媳打电话,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还在找,我肯定能找到我的八哥的,你给他们说去,这堵墙,我来拆。
婆婆不舍得让人把八哥的手印画胡乱地推倒、铲掉,粉碎在一堆的尘土瓦砾中。婆婆护着墙上的画,说,我来吧。
婆婆说:
我来吧!
婆婆又高声大嗓门地,对推土机铲车上的人,说,求求你们让我来拆这堵墙吧,我拆了这堵墙,剩下的,你们想咋拆咋拆吧。
机器的轰鸣声没了。
人们吵吵嚷嚷的声音没了。
只有尘埃还在乱纷纷地跳出一团黑白灰黄的雾,腾腾地滚着,飘升,散开……看上去也喧嚣,也嘈杂,好像在呐喊:
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
人们看见婆婆用手在揭墙皮,先是顺着手印用她的修鞋刀子划开一条缝,然后,一只手塞在墙皮下,一只手按在墙皮上,墙皮下的手往上掀,墙皮上的手紧紧紧紧地跟着按。她小小心心地,一点一点地,揭下一片手印,放在她的修鞋箱子上。有人给婆婆送去一把小铲子。铁的小铲子。八哥也有一把。八哥用小铲子在沙土上玩。婆婆看了一眼小铲子,苦笑着,摇摇头。婆婆担心小铲子把八哥的手印画铲坏了。她又小心翼翼地顺着手印划缝,然后,一只手塞在墙皮下,一只手按在墙皮上,小小心心地揭下一只“小手印”,放在箱子上,又小心翼翼地揭下一只小手印,放在箱子上。婆婆揭着墙皮,就像她抱着八哥、给八哥喂奶、给八哥洗澡,仔细,认真,缓慢而忧伤。
安静了一时的人们不耐烦了。人们看着婆婆,都说她这样子要到啥时候才能弄完啊?一个一个地弄,好几十个手印子。胖子又甩着他的胖胳膊,舞弄着粗短的腿,踩着瓦砾,蹦跳着过来催婆婆快点,胖子说工程要赶时间,延误一天工钱都要打折扣,合同上写着呢。婆婆不理他。他又对一旁的人说,她有个傻孙女,她也跟着傻了吧。
人们哗地大笑,笑声肆意,流畅,没心没肺。
老张的脸黑了,他捡起一块瓦片,指着胖子,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句老子放你的血。
胖子的脸倏地僵了,他缩了一下背,向后退了几步,扭脸看了一眼老张,咕哝了一句,老张听见了,嗖地就把瓦片砸在他的头上,他捂着头,嚷着,不干了不干了,这地方的人都他妈的是疯子。嚷着,又担心老张的瓦片,逃走了。
老张在废墟上捡来一本杂志,走到婆婆身边,把书打开,两手捧着,说,放这里吧。
婆婆忧伤地看了一眼老张,看了一眼他手里的书,眼圈红了。
婆婆小心小心地揭下一片小手印,放到老张手上的书里;揭下一片小手印,放到老张手上的书里。婆婆的动作轻柔,缓慢,就像是从床上抱起一个婴儿。婴儿。刚出生的八哥,那么小,那么小。粉粉嫩嫩的一团,眼睛却大。黑的眼睛看着她。
那些红的绿的小手印,就像一枚枚书签,安静地整齐地夹在了书里。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