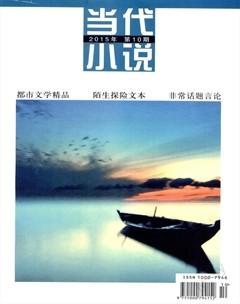蓝鸟
杨袭
单身女人走出家门时,又看到了那个男孩。
男孩穿戴齐整,头发有些乱,抱着两只膝盖蹲在楼梯拐角。前一天,也是在这个时候,单身女人也看到了这个男孩,也是蹲在这个位置。但她刚想开口,男孩迅速站起来跑上了楼。单身女人想不起这是几楼的孩子。再一次看到他,单身女人直觉上确定这孩子并不是她们楼上的,最起码不是这个楼道的。因为她看到孩子还是穿着昨天的衣服,裤角处缀着的收缩绳扣,给单身女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是谁家的孩子?
男孩看到单身女人,脸上好像出现了短暂的惊喜。但稍即,又黯淡下去。男孩低下头,拿手指捏着一根楼梯撑杆,从上捏到下,再一路捏上来。好像外科医生在确定一根骨骼是否折断。
你不说,你不说阿姨可要上班去了。
单身女人往下踏了两阶。她已经判断这个孩子需要帮助,并且,已经选定了她帮助他。单身女人一边往下踏,一边拿余光瞄男孩,男孩在慢慢站起来,等她到拐角的平台上。男孩喊:
我饿了!
直到那碗面温度足能入口,男孩还在哭,涕泪交加。单身女人挑起面试了试温度,将碗推到他面前,他才再次拿袖筒抹了抹泪,抓起筷子往嘴里拨拉,边嚼边不住呼着热气,转眼工夫就连汤带水一块儿下了肚。
还有吗?
男孩说完摇了摇头,往旁边推了推碗。刚才单身女人下面时他看到了,锅里所有的东西已经倒在碗里了。不等单身女人回答,他就拿起碗和筷子到厨房洗了。接着到卫生间洗脸。单身女人跟在他后面,看到他后背和屁股上褐色的污渍。单身女人提议他洗个澡,换下衣服。这时候,男孩已经打开水龙头洗起了脸。听到单身女人的话,关上水,抬起头,对单身女人说:阿姨,你不要笑我,我哭,是因为我太感动了,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
单身女人点点头,男孩松了口气的样子:
洗澡是可以,但是你家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男孩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和刚才“感动”的时候的表情格格不入。
单身女人吃了一惊。单身女人离婚已经好几年,有个十来岁的女儿判给了前夫。刚开始,她还能去看看。但一年之后,男方又成了新家,并且全家移民去了澳洲。一个单身女人的家,简洁得逃不过任何人的眼睛的。偶尔的荒唐后,她也总是一丝不苟地打扫战场,没有人监督她,她在这个地方没有内心里认可的好朋友,住在另一个城市里的家人时不时打电话关心她的个人问题。平日里来往的几个女性朋友甚至都不断催促她投入另一份感情,没有感情,哪怕是“搭搭架子”也是好的。可以说,所有关心她的人都乐于看到她的“荒唐”,但她从不迎合她们的好意,她本能地拒绝着来自外界的揣摸激励。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给自己交待。
她是个单身女人。
你几岁了?
男孩说八岁。单身女人一边点着头,一边到卧室拿出一套灰色家居服。男孩默默地接过衣服进了浴室,并且关上门,反锁上。单身女人心想,小屁孩。在水不响的时候,单身女人问他父母的手机号,家在哪里,等等,无一例外,男孩都大声吆喝:我出去再告诉你。
但男孩并不想告诉她,等他穿着那套显得过于宽大的灰格衣服缩进沙发里。他就不再这样说了,男孩说他不想回家,当然不能告诉她父母的手机号。男孩说的时候一直盯着对面墙上挂的电视机。单身女人让他明白她不可能收留他太长时间,她很忙,现在已经耽误上班了。男孩像没听见一样欠身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开了电视:
你尽管去上班,我又不捣乱,嘿,你家的电视能打游戏么?
什么?打游戏?
单身女人有点反应不过来。
你别怕,我就在你家住几天,再长也不会超过一周,行不行?我不白吃白住,最后,我要让我爸给你结账。他会把你该得的钱给你的,我爸有的是钱。你快上班去吧,我爸会付你双倍的饭费住宿费,但可不会付你误工费。
嗯——
单身女人长长地清了下嗓子。其实,单身女人遇到了难题,近四十年的人世经验,不足以让她游刃有余地应付这样的局面。这孩子的所作所为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有一种,一种——怪异,对,怪异。单身女人想起这个词时看了男孩一眼,男孩正无聊地将电视关上放回了遥控器。嘴里咕咕哝哝地抱怨着什么。单身女人在沙发上坐下来,理了理头发,伸出双手,刚打了个手势,被男孩制止了。
你别说,我知道你说什么,你一定说这样做不对,你不要多说了,这么说吧,今天,这十来天,你要不收留我,我就跳楼。看见了没有,我就从你家阳台上跳下去!你想想吧,我要是从这里跳下去,一定摔得头破血流,你就等着每天夜里我血头血脸地趴在你家窗玻璃上看你睡觉吧——
单身女人双手僵立在脸前,倒吸一口凉气,迅速在沙发上远离了男孩一大截。但立即意识到这样被这个毛孩子吓倒该显得多么可笑,她索性继续往后靠,倚上沙发扶手处的抱枕。男孩看了她一眼,耷拉下眼皮,脸上一副得意和不屑。
你信不信,我打110?
憋了大半天,单身女人自以为憋出一句有分量的话。但话一出口,她又后悔了。难道她近四十年的人生阅历给予她的智慧和定力不足以让她凭自已的力量对付这么个毛孩子?还非得把公权力搬出来让他屈服,单身女人感觉自己有点失格。她遇到了挑战,但她正在努力让自己脸上露出一个笑容,把刚才的话宣布为玩笑来挽回她的自尊的时候。男孩冲她做了个鬼脸,尖声尖气地说:
唏,110,你还是直接打120吧,不过,110、120、119这三个号码是联动的,你拨哪个都差不了多少。噢,还是有点差距的,那你直接打120好了,不过,不等他们过来,我就跳下去了,“唰——咚——”,不信,你拨拨试试,你试试啊!
男孩凑过来,推了推单身女人握着手机的手。单身女人缩回手,男孩听到单身女人嘴里禁不住发出的“嘶嘶”之声后,满意地笑了。说实话,男孩长得好看,眼睛大而水灵,刚洗过的头发刚被他戗起,根根朝上竖着,很精神。
单身女人搓手的动作马上就被男孩看在眼里并在脸上表现了出来。他凑近单身女人,伸出手摇晃她的胳膊:
阿姨,刚才我是和你开玩笑的,我就是看你好,心好,长得也漂亮,我就想跟你住几天,而已。你放心吧,我不白住,除了我爸付给你费用外,我还会帮你做家务。我会擦地,会洗衣服,还会——
男孩说着看了看四周:
还会洗碗,我就帮你洗碗吧。我洗得又快又干净。
单身女人看着胳膊上的两只小手,洗过澡后,手指修长干净,皮肤很细——但是,她还是没法把他留在家里。男孩巴巴地望着她脸的神情让单身女人想如果向他说出这些成人间心照不宣的理由,一定会伤了这个孩子的心。尽管看起来,他的心也不是那么好伤的。在单身女人左右为难的时候,男孩提议,如果她不放心,可以把他绑起来,他可以和她一起出去买绳子,还可以用生胶带贴上他的嘴。男孩说:
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
男孩说得委屈而小心翼翼。单身女人望着男孩乞求的眼神,真的有点不忍就这样把他赶出去。可是,单身女人咬起嘴唇环视着客厅,陷入困境。
这时,单身女人在两难之间抬头时,看到了沙发上方那张简笔着色的鸟儿画,那是女儿四五岁时,当然,也是她还没离婚时,画的画。单身女人几乎每天都凝视一会儿这张画。当然,每次凝视,对女儿的想念和对旧事的伤心,总是有些几味杂陈。但是这一次,单身女人突然感觉轻松起来,她想起当时按女儿的要求用透明胶将画粘在墙上问女儿为什么是蓝色的时,女儿说,蓝色的,飞得更远呀。单身女人当时很不解,问为什么蓝色的飞得远,女儿说,很简单哪,蓝色,和大海一样的颜色呀,大海认识它呀,不会淹死它的,它要飞累了,也许会浮出一只海龟,也许,会跳起一只海豚,它不就飞得远么?单身女人记得听完后有点哭笑不得。但是,这总是个理由,她记得女儿解释完后看她点头,自豪得小胸膛挺得高高的。
好吧。
单身女人将目光从蓝鸟上收回来。走出家门。
当她走到车边,拉开门把手将要伸进去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想回头看看,甚至已经朝后转动起脖子,应该是已经转动起脖子了,但并没有转过去。她想,这个时候,男孩应该站在窗口看她。不要回头,不要回头!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梗着脖子钻进车里,发动后转了圈,当走过她家对面时,尽管一再嘱咐自己不要看,但她还是用眼角余光扫了一下,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天上午非常忙,有好几张报表需要她提供,其间分管的胖领导还来找过她一次,但是,不管是认真地写下一个数字,还是绞尽脑汁地向胖子解释可能会引起争议的一个汇总结果,她脑子里老是有那么三四个壮汉从她家里往外搬东西,接下来是空空当当,蛛网和灰团四处乱飞的空房子。中间,有那么一刹那,她几乎要告诉坐在沙发上的这个她平时厌恶透顶的、总是斜吊着眼有企图地盯她,头直接墩在肩膀上的大胖子,她家里“来”了一个小孩。产生了这样的冲动后,她再看着胖领导的三重下巴,心里就有了莫名的感动,胖子也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向她挑了挑眉毛,好像鼓励她把心里的话告诉他。单身女人明显感觉到了那句话像条蛇一样沿着她的什么组织和器官往上爬,一直爬到她嗓子眼儿,在那里重新发育分裂,撑得她半张开嘴。她感到了一些薄翼状的东西在喉咙处翕动,它们就要飞出来了——她多么庆幸她没有告诉他这件事啊,她是那么讨厌他——胖子的手机突然响了,他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手机看一眼站起来,朝她点点头出去接电话了。她重重朝桌面擂了一拳,随后疲惫不堪地仰在椅子背上。她想起来,她家没有值钱的家具,更没有贵重物品。除了衣服被褥,有限的几件沙发桌椅,就是厨房里的盆碗瓶罐,都不值钱。更不可能有蛛网和那么多灰尘。但无论用怎样理智的分析告诉自己那场面是多么荒谬,也还是制止不了那些让她崩溃的画面一帧接一帧闪过。快到中午时,这些画面竟然自行配了音,沙发与楼梯撞击的“嘭嘭”声,他们乱翻她的衣橱,企图要找出点什么细软的“啪啪”声,衣物勾裂的“嘶啦嘶啦”之声,好多种基于偷盗和破坏制造的混乱、发出的噪音搅动着她已经快爆炸的大脑、敲打撕裂着她的耳膜。
该死,得回家了,必须!
她咬牙切齿地对自己说。
男孩已经成为一颗定时炸弹一样的存在。她不知道他会给她带来什么,但直觉上,总是与麻烦、凄惨,甚至是与灾难连结在一起。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能不被自己的直觉左右。当年,她发觉前夫有了别的女人,就是靠的直觉。她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能作为呈堂证供来质问她前夫的理由。等他们各自捧着一本离婚证,在民政局前的路口分手时,她前夫请求她告诉他,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她的怀疑。她当时望着一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泡桐,翘了翘鼻子说,你没闻见吗?空气中都是背叛的味道。
是的,连空气中都有阴谋的味道。
平时车来车往的局大院,今天竟然冷冷清清,往门外望望,两辆警车一先一后无声驶过,警车过后,一白两黑三只猫拖着尾巴,将身子拉长到了不可思议的长度,缓慢地在道路中间踱步。单身女人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后拉上车门,戴上安全带。车子从单位门口的大街向西行驶了几分钟后,向北拐经过了一段两边种着双行白蜡的单行路,然后进入了人潮涌动的商业街,终于在路边一个停车场熄了火,走下车来时,单身女人才明白,自己原来要来一趟百货大楼,好像蓄谋已久。等她将两套休闲装,一大包熟食青菜和零食在后备厢放好,“嘭”一声扣上后盖,长出了一口气,像完成了一件重大任务。但是,从百货大楼到她家楼下十来华里的路上,搬动家具的画面又一次钻进她脑海里,在她眼前晃来晃去,越来越密集升起的慌乱和烦恼让她在临近小区的路段上接连撞倒了两个临时性塑料隔离墩儿。
她将车停在了楼侧,而没有像往常那样停在楼下,从窗口看得到的地方。她轻手轻脚打开后备厢,将大包小包拿下来,锁上车后再一样样提在手里,斜着身子望窗口——一切如常,并没有发现半掩的窗帘后面男孩的影子,也没有看到哪块窗玻璃碎掉。当她步上楼梯,仔细察看了楼梯墙壁,扶手,也没有发现楼梯上大块或小块的遗落物后,她想,有可能,男孩已经走了也说不准,她这样想时竟然发现自己很失望,还有些伤感。好在不一会儿后她就听到她家门响了,接着一阵“踏踏踏”的脚步声后,男孩的脸探了下来:
嗨!
单身女人发现自己的声音很愉快。
阿姨,你回来了!
紧接着,男孩跑下来,接过她手里的大包小包。单身女人用腾空的手抚摸着男孩的头,男孩回头看了她一眼,咧开嘴冲她笑了一下。
哎呀,你可回来了,我怕你中午在单位吃饭,再不回来,那我又得饿一天。
男孩跨进门,将手中的东西放在茶几上,小跑着去阳台为她取来拖鞋。男孩将拖鞋摆在她面前,摆得很整齐,两只淡紫色的,已经穿了两年,右脚的一只一根带子已经断裂了小半截的拖鞋,此刻让单身女人感觉陌生了。男孩抬头看着她,两只大眼睛澄澈无比。单身女人带着小心褪下皮鞋,将脚缓缓地伸进拖鞋里去,凉丝丝的,脚稍一动,有点痒痒。
谢谢!
单身女人提着手里的包进了厨房。她想,得有多长时间,没有享受过有人为她拿拖鞋的幸福了?她将手里的包放到台面上,同时发现原来她提的是那两套衣服。她怔了会儿,转身隔着门玻璃朝向客厅,她什么也没看见,但分明有什么让她不自在了,她分别察看了下两只袋子里的东西,摸了摸额头,然后打开水龙头“哗啦哗啦”很阔气地洗了个脸。
很好,沙发,电视,当然,卧室就不用确定了。一切东西都呆在原地。男孩还是穿着她那套宽大的家居服。当她拿出衣服,交给男孩让他试的时候,男孩告诉她,他穿脏的衣服已经洗干净了,应该快干了。单身女人说那是她送给他的礼物,不用他爸爸付款后,男孩变得无比高兴,说:
谢谢阿姨,让您破费了。
多好的孩子!单身女人在心里说。她想伸手摸一下男孩的头,却在半途折返到自己的脸上——她竟然不知不觉地流出了眼泪。
男孩有点慌乱,扯着过于长的裤脚退了一步,说:
阿姨,我是不是不该要?你是不是生气了?
单身女人摇了摇头,说:
不是,阿姨突然想起了一些事。
接下来,男孩倚在厨房门框上,看她做饭。两个人用了简单的午餐,单身女人提议男孩吃块蛋糕。
我给你买了蛋糕。
单身女人说着,伸出一只手指着她想像中蛋糕应该在的地方,从客厅的茶几一直指到餐桌,门口,电视柜,哪儿都没有。
男孩不等她问,站起来打开冰箱取出那块黄金海绵蛋糕。
是不是这块?
单身女人说,是。
男孩说:嗯,太香了。这种蛋糕爱坏,我刚才放到冰箱里了。
很显然,男孩不能确定这块蛋糕给不给他吃,多么敏锐的小东西啊。
单身女人心里感叹着,很自然地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女儿现在,也在吃蛋糕吗?单身女人打开包装,让男孩吃蛋糕,告诉他她要睡一会儿。好长时间了没这样放任自己了,单身女人趴在床上,结结实实哭起来。
门轻微一声响后,单身女人应声坐起,靠到床头上,看着男孩手捧着一盒抽纸,慢慢走进来。其实几分钟后,单身女人就感觉到了里面某种预演或者约定的成份。男孩将抽纸递给她。她抽了两张攥到手里,拍了拍身旁的位置,男孩坐下了。
单身女人已经止住了抽泣,将一张尚平展的纸巾在食指上绕来绕去。男孩一会儿看看纸巾,一会儿看看她的脸。单身女人想,他们就是两只偶然搭上话的奇怪动物。她的来历或者他的来历都不重要。至少,对这一刻来说,是不重要的。单身女人伸出手将男孩搂在怀里,男孩顺势在她肩膀上趴了一会儿,抬起头说:
阿姨,我想我还是对你说实话。
单身女人将食指竖在嘴上,说,嘘,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告诉我。
男孩挣脱了女人的手臂跳到地上,说,阿姨,你有危险!
按照男孩的说法,他是被两个人贩子绑架到本市的。人贩子在他跳下校车从小区外的路口绑架了他。他从昏迷中醒来后发现自己在一只袋子里,感觉在车上颠簸,他不敢哭出声,生怕他们会怕他引出麻烦而杀害他。男孩说:
你知道吗?他们也许会用刀片割开我的喉咙,也许会把毒药捂在我的鼻孔上,还会用绳子把我的脖子勒断。
男孩的假设让单身女人不寒而栗。
那我们报警吧!
男孩告诉单身女人尤其不能报警,因为谁也不知道警察与人贩是不是有勾结。男孩说他们学校已经失踪过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说:
你知道吗?我听到大人说,如果被绑了去卖了,还算好的,最怕——
对,最怕被分解了卖器官。
单身女人抢着说。
男孩点点头。
那你告诉我你家的地址,我送你回家吧!
单身女人探起身子,重新将男孩拉到床上。男孩看着女人,眼珠儿转得飞快:
不行,行不通的。也许,他们正在我们附近找我,你知道,他们都是团伙做案,虽然绑我的是两个人,但他们绝不是两个人。他们要知道我在你这里,就麻烦了,说不定,连你都有生命危险。
单身女人大吃一惊过后点点头,深以为然。紧接着,女人下床拉窗帘,但被男孩制止了。男孩说她这样更会给人贩子发出这家有情况的信号。女人抓着窗帘停在头顶上。
那怎么办,他们也许会在对面楼道里拿望远镜看到我们。
男孩说:阿姨,你放心吧,我一开始就很注意,我在的地方,都是他们看不到的。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他们就看不到。
单身女人看看窗外,再看看他们的所在,是,如果人贩子不是站在对面楼的太阳能上,是看不到他们的。
女人不安地看着男孩:要不,我给你父母打电话,让他多带点人,来接你。
男孩眼里顿时充满泪花:对不起,阿姨,我骗了你,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爸爸在我四岁时在下班路上被车撞死了,我妈妈带着赔给我们家的钱跟人跑了。我跟着奶奶长大,前不久,老师还让奶奶装电话,但奶奶说,装电话得有钱,买手机,就更贵了——
啊!
女人惊叹中透出不悦。但不等女人开口质问,男孩就说:
你不要生气,阿姨,我怕你嫌我,嫌我麻烦不肯收留我,我才说我爸会付钱给你。其实,其实——
女人手机响了。女人跳起来往客厅跑,男孩先一步将手机拿在手里递给她。是胖子的电话,不等他开口,女人就小声惊呼一声,坏了,耽误上班了。男孩紧张地看着女人,女人拍了两下胸口,然后慢慢走到沙发上坐上,正了正色告诉对方要请个假,家里“有点急事儿”。
男孩大大地松了口气的神情让女人看来有点做作。
女人提议男孩说出他家在什么地方,她要与当地的警方联络,把男孩接回家去。
男孩说:阿姨,你太粗心了。这边的警方有可能会和人贩子有联系,我们那边的,也有可能。
女人怔住了。
你的意思是,我们就没办法了?眼睁睁等着那些坏人有一天把你找到,还,还,对我不利?
男孩坐到单身女人身边,说:
阿姨,你不要太着急,再想想,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接下来,单身女人和男孩就人贩子有多大的可能与两边的警方都有勾结和一出门就遇上绑他的人贩子的概率发生了短暂的争论,女人在话语中透露出的男孩在虚构危险的信息被男孩牢牢捕捉到了,男孩说:
阿姨,难道你认为,我好好的会从家里跑出来,找你的麻烦,我年龄这么小,我还耽误了上学,并且,我还拿不准有没有人像你这么好心收留我——
女人看了看男孩没有说话,走到窗前,刚想拉开纱帘,突然想起对面楼上的监视住了手。她接着想,白天,外面光线比屋里光线要亮,危险是不大的。关键的问题是晚上不要开灯,或者,开灯之前,一定要拉上遮光的布帘,并且,千万记得不要让男孩走到窗前去,以免影子落到窗帘上。
单身女人转身想嘱咐男孩,刚说了个“哎”,突然发现,她还不知道男孩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女人问。
男孩在沙发上坐正,严肃地看着她说:这个时候,你知道得越少对你自己越有利。
这天下午,女人再没有问男孩任何问题,由于考虑到身处的危险,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早一些吃晚饭。这一天的夜晚,如他们愿地早早来临了。女人拉严窗帘,把阴面卧室的床铺收拾好,让男孩早一些休息。男孩很顺从地爬到床上,跟她说晚安。
单身女人回到自己床上躺好,将手机拿在手里划开屏幕,逛了好几家网站,进出了好几个聊天群之后,在目不睱接的看似非常重大,实则极其无聊的信息中慢慢地感觉到了白天所发生的一切的荒谬。
不说别的,一个被绑架的孩子,无论如何,不会有这样的从容。还什么“知道得越少对你自己越有利”,“警方有可能会和人贩子有勾结”,这样的话,对一个他这样年纪的孩子来说——嘶——单身女人倒吸一口凉气,是的,孩子是想不出这样的话的,这一场戏,只能是出自一个或者几个成人的精心编排,并且环环相扣,滴水不漏。那么,他们为什么选中了她?他们要从她这里拿走什么呢?一个单身女人,一没有色,二没有钱,手中也没有权力,更没有什么会被人当做把柄的丑闻或者错误。她有什么呢?
这个问题比一开始关于荒谬的问题更让她痛苦起来。
她在痛苦中梳理了她近四十年的生活和人生,发现,她竟没有任何与别人,别的女人迥异的东西。无非是上的不是一家幼儿园,但同样有被孩子们站不齐队气得暴跳的阿姨,无非上的不是一处小学或者中学高中,但同样有天天点着学生们的脑袋重复“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老师,她与她们上的不是一座高校,但一样是坐在合堂教室里看闲书打盹考试前突击一阵过后一切如常,虚度光阴。毕业后也许和没进机关事业单位的同学不同了,但一样是起早贪黑端人饭碗看人脸色心里满是憋屈——她绝望地发现,她一无被男孩和站在他身后的势力选中的资格和幸运的理由。
为什么是我呢?
她问自己。
这时候,她听到对面卧室的门响了,男孩“突突突”从卧室出来。天哪!女人吓得坐起来,也许,下一秒钟,男孩就会打开门,放进一群手拿砍刀棍棒甚至手枪的歹徒。她听到男孩推开卫生间的门,紧接着,传出来小便声,而后没有悬念地跑回卧室,关上门。
女人吐了口气,心想,真可笑,我紧张什么呢?我有什么呀?女人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
单身女人,在又一个不眠之夜里辗转反侧。失眠对她来说并不陌生,但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为现实中的烦恼和担忧失眠了。所以,她感觉这天晚上的失眠很充实。是个有模有样的失眠。不是吗?她家里莫名其妙地挤进来一个莫名其妙的男孩。并且,现在这个男孩就躺在对面的卧室里。她至今不能确定他究竟要干什么?她已经多年没有感受过自己的好奇心了,甚至忘了自己也有好奇心。复苏的好奇让她在黑夜里精神抖擞,她急需一个倾诉对象。她要把男孩到来的前前后后讲给一个人听。她很自然地想起了校长。校长是位于本城富人聚居区一处私立学校的所有人。校长是在为办理一件牵涉政府审批项目的最后一项手续时来到她办公室的,一件工作将要完成的轻松和因轻松引起的懈怠使他话音低沉,语速迟缓,还有坐在沙发上一再摘下眼镜搓脸的动作使女人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具有潜在攻击性的男人。但后来女人却想,短暂的公务对话并不可能引起校长对她更进一步的好感。结论是,只要是男人,都要提防。但这时候他们已经开始交往,都是校长来她家。有时候,他们会看部电影,有时候一起做顿饭,还有一次,他们跳了一支华尔兹。校长舞技熟雅,让她对他有了某种期待性的好感。但也只是止于好感而已,她知道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贪婪和虚伪,都基于对自已的认识对这个世界悲观。校长笔挺的西装之下破洞的底裤和右手小指上的长指甲有时候让她感觉他肮脏而变态。但是,她现在却想起了他并且拨通了他的电话。他接了。
你告诉我,我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女人的直接一定让校长摸不着头脑了。女人听到他说,你好,噢,没事儿,没事儿,你说。一股强烈的恶作剧冲动让女人“咯咯”地笑起来。女人笑着说:
我家里来了个帅哥,咯咯咯——
短暂的沉默过后,女人听到校长咳了一声。
噢,噢,这样啊——你看你问一下陈工能处理么?要能处理的话就先撑一晚,处理不了的话再打电话给我。
处理你妈!
女人骂完挂了电话。女人当即下决心与校长一刀两断。
恶作剧的兴奋和要和校长一刀两断的决绝使女人感受到了很久以前就离她而去的自信。她跳下床穿上睡衣光脚来到客厅,她很想抽支烟。单身女人如果有秘密的话,就是抽烟。她的财产成不了秘密,一个月就五千块钱工资,一处房子,都登记在案。她与校长的交往也不是秘密,除了对校长夫人来讲。这年头,对门都不认识,谁也不关心谁的死活,甭说交往了。就抽烟这一件,她是任谁也不让知道,校长也不知道。她的烟盒在电视橱下一只抽屉的最底层,上面是过期和将要过期的药瓶药盒和药包,大人的药少,很大一部分是蒙脱石散粉,小儿消食片,小儿感冒冲剂和蓝色散袋装的臣功再欣,这都是孩子小时候用的药,离婚后,女人将其他一切他们共同生活的东西都扔了,就留下了孩子的照片、沙发上方孩子的画和这些过期的药。这些不愿意舍弃的念想下面,隐藏着一个女人的颓丧和寂寞。女人蹲在电视橱前,拉开抽屉,轻车熟路地将手伸到一堆药的下面,拿出烟盒和一支火机。
“嚓——”
女人发现了窗前那个黑影。
黑影迅速放下手里的窗帘一角转过身来。
不用说,是那个男孩。
“天哪!”
女人低低地叫了一声。火机灭了。女人在黑暗中听到自己在急喘。
“你要干什么?”
女人的直觉,男孩一定是在给什么人传递信号。女人后退了几步打开客厅的灯。下意识地将分别攥着烟盒和火机的手藏在身后。
“吓死我了!”
男孩说着,走到沙发前坐了一会儿。双手捂上脸哭了起来。
女人不好当着男孩的面往那堆药袋底下藏烟盒,于是回了卧室,将烟盒和火机放在床头柜里。
“对不起,阿姨,白天,我骗了你。”
当女人在沙发上坐定,男孩挨过来趴在女人腿上后,告诉她白天说的那些关于自己被人贩子绑架的话,都是瞎编的。男孩哽咽着诉说,说他跑出来,是因为他爸和他妈都打了他。按男孩这次的说法,他爸爸是一个油田勘探工程师,他妈是本市人民医院的医生。上个月,他放学回家,发现他妈和“刘伯伯”在他妈的卧室里。
“我认识他,他是刘伯伯,我妈医院里看心脏的医生,他们家就在我们家后面楼上。我趁他出门时把一只拖鞋扔到他背上。”
男孩说刚开始他妈并没有打他,而是回卧室呆了一会儿。在他洗过手,坐在餐桌边等着吃饭时,他妈才从卧室里跑出来,手里抄着一只玫瑰红色的胸罩,冲到餐厅将他摁在椅子上没头没脸地抽了一顿,边抽边骂他:你个没良心的,天天在外头疯,天天在外头疯,有本事,你不回来呀!你死在外头好了,你还回来干什么你?
男孩说着脸上挂下两串泪花,男孩抹了抹泪,抽动着肩膀说:“我很听话,一放学就回家,从来不在外头瞎跑——”
但男孩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是他爸回来后也打了他。隔了一周,他爸回家,在他妈妈上班后,他告诉他爸,说他妈领着“看心脏的姓刘的”来家里。男孩说他还没说完,他爸就举手制止了他。随后,他爸点了支烟,抽着一会儿到厨房转了圈儿,一会儿又到阳台上,然后回到客厅里,将烟头扔进鱼缸,把他扔在沙发上,用一册《家庭之友》把他的屁股抽破了。
男孩的爸爸一边抽他,一边喊:叫你瞎说,叫你瞎说!
“阿姨,我没有瞎说,我说的都是真的!”
男孩涕泪交加:“把我养的金鱼全都毒死啦!我再也不回去啦,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啦!”
单身女人将男孩紧紧搂在怀里。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女人喃喃地说。她搂着男孩,望着对面墙上的电视,也许只是望着墙,想像着男孩被追打的场景,想像着那个或方或圆的鱼缸里飘着的泡散的烟丝和翻着白肚的金鱼,感觉这个世界,一点儿也不真实。
这一次,女人看着男孩洗了脸,将他送回到床上,男孩躺好后,女人细心地拉起空调被盖在他肚子上。在回卧室时,女人想,多么可怜的孩子啊,瞧这些大人们,都造了什么孽。但等关上门,爬上床,躺在完全的黑暗中后,女人又不这样想了。她断定自己再一次被男孩的故事欺骗了,虽然,她找不出漏洞在哪里。她想,也许,最大的漏洞,就是没有漏洞,一个孩子的叙述,怎么说,也是应该有点毛疵的。想到这里,她不得不佩服睡在隔壁卧室的男孩严丝合缝的逻辑能力——他竟然编得让她找不出问题,不对,不对,女人想,这也许不是他编的,而是——有人预先编造了故事,对,有人预先给他编造了很多故事,男孩所做的,只是根据场景不同,选一个较合适的故事说出来而已。
但是,这一切,又为了什么呢?又为什么选择了她?
我一个单身女人,有什么呢?
女人躺平,双手搭上腹部。有什么?我有什么呢?女人用几根手指敲着自己的肚皮,指肚触到肚皮上,有微微的弹动,不一会儿,一个答案“扑楞”,仿佛从肚皮上冒了出来。
——她有器官!
心,肝,肺,肾,她一样不缺,并且,从前不久体检的结果看,还相当健康。
这个答案像一个黑色的炸弹,把她炸得一激灵,接下来全身发冷,毛骨悚然。
男孩深夜不睡,跑到客厅窗前,一定是在给什么人发信号。难道,他们就是网上传的盗卖人体器官的犯罪团伙?
女人上上下下按摸着自己的身体,确定在几次亲密的接触当中没有被男孩用什么针头或者什么东西碰到过。她的手经过小腿、大腿内外侧、臀部,在右后腰侧停住了,有一个痛点。女人用右手食指反复摁了又捏,确实有点疼。女人打开灯,在床上站起来反转身子,企图查看那个痛点。看不到,她把腰扭得都疼了,还是看不到。女人跳下床站到梳妆台前,在梳妆镜中隐约看到了那个红点,像小米粒那么大,艳红色。拿手一摸,也像小米粒那么硬。
坏了,坏了。
女人想,之前,她从来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这个东西。会不会是某种缓释的麻醉剂,或者毒药?早已进入到了她的体内,此刻,正沿着她的血液扩散到全身?
她不能等到歹徒蹿进家门后再采取措施,就现在,现在就把这个骇人的小东西赶出门去。女人迅速抓起床边的睡衣套在身上,往门边跨了几步。在抓住门把手将要把门打开的时候,女人想,看这次,他还能给我编个什么故事呢?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