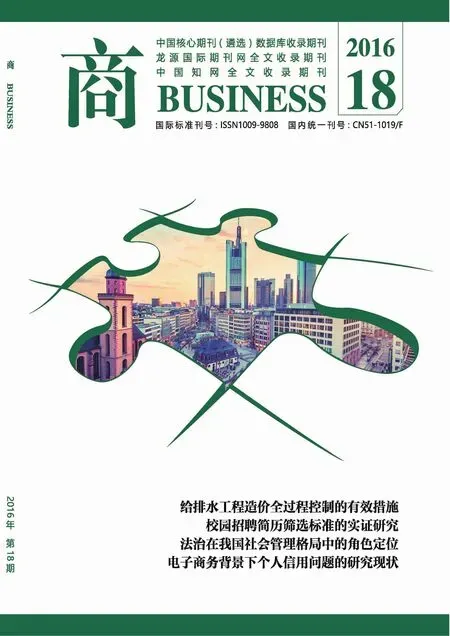水西彝族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融合研究
雷洋等
作者简介:雷洋(1994.09-),男,汉,贵州省黔西县,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方向:历史学。
张正勇(1992-),男,汉,贵州省黔西县,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方向:历史学。
黄瑶(1993.06.11-),男,汉,贵州省黔西县,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方向:历史学。
熊付(1992.09-),男,苗,贵州省黔西县,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方向:历史学。
指导老师简介:程永奎(1969—),贵州六枝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摘要:水西作为彝族地方统治政权存在时间最长的地区,其历史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有着深刻而久远的关联。通过对水西彝族历史文化的追溯及其与汉文化的碰撞融合研究,大概了解水西彝族文化风貌及其因汉文化影响而致的历史文化变迁。明朝奢香时代为彝汉文化交流的高峰期,促成了水西文化的基本形成,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彝族历史地域文化,是为文化融合之典型。而其中制度文化将水西彝族的个性展现得尤为突出,具有三大特点的土司制度在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弭,改土归流是制度文化的变迁,也是彝汉文化碰撞融合的又一高潮。
关键词:水西彝族;水西文化;文化碰撞;改土归流
一、 历史记忆:水西彝族简史及其文化风貌浅析
(一)同源异流:族群历史文化追溯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彝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也是我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其中贵州彝族人口约占全国彝族人口的10%,主要分布在黔西北一带,古水西地区就是历史悠久的彝族聚居区,也是独具特色的彝族地方政权。彝族历史源远流长,又是一个支系繁杂,地域性明显的民族,彝族在“共同的文化表现形式下,各支系文化表现出了明显的个性”。[1]水西作为彝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民族政治区域,虽和整个彝族同源异流,但其也保留着独特的个性。水西来历有史可考,据《三皇五帝年表》记载:“宋末元初以鸭池河为界,将贵州分为水西和水东两部分,因慕俄格的政治中心在水西,所以水西词就演变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区域名称。”水西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区划,追根溯源,其政权兴起于汉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彝族罗甸国君长妥阿哲(济火)助诸葛亮南征,被封为“罗甸王”。据贵州《大定府志》记载:“今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水城诸地,凡安顺以北、四川宜宾以南一带,周初期为卢夷之国,其君称徵”。[2]其地域与后来的水西故地基本一致,因而水西地域实质要从罗甸水西王国开始算起。其开国君长勿阿纳开始建立政权,统治了以水西为中心的大部分地界,这是水西文化的本源,而蜀汉时期的妥阿哲(济火)则奠定了水西作为彝族方国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基础,也奠定了顾全大局、爱国统一的民族文化基石,固其是水西文化的奠基人物。据《西南彝志》记载其开国君长勿阿纳约与汉光武帝刘秀晚年同时代,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安胜祖逝世,乏嗣,此后推行改土归流,水西土司政权历时长达1474年,而水西作为独特的政治区划实质上存在了几千年。只是直到783年皮逻阁建立南诏奴隶制政权为止,各彝区的差异性并不大明显,直到之后贵州出现罗甸等奴隶主集团或政权才为后来贵州水西、水东相对独立的彝区文化单元奠定基础。
然“水西”之名,最早也仅溯及到《元史》。《大定府志.旧事志》:“额规,普色盖当宋之末造,复侵有贵州,乃分其地有水西、水东二部”。[3]所以水西在历史上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晰的行政区划,只是在明代起才有一个基本轮廓,甚至名字都是元代以后才出现的。但无论怎样,水西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区域和文化单元由来已久,水西彝族在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内,在黔西北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区域内和中央王朝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一个地区主体民族就同中原汉族发生各种交流,伴随着的是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二)水西彝族文化简析及早期彝汉文化交流
水西彝族作为整个彝族的一支,其有着鲜明的支系性和地域性特点。我们说,整个彝族不同于中原汉族文化,相较不以发达的物质文明为特征,而水西彝族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彝族文化,其是整个彝族文化体系的一环,同时有着自己浓厚悠久的历史积淀,在婚丧、礼仪、信仰等诸多文化元素上形成自己鲜明的特点。
前提及水西文化的渊源当溯罗甸国君长勿阿纳时期,从勿阿纳开始建立政权,统治了以后的水西地区和贵州大部分地区,这当是水西文化的本源。而蜀汉时诸葛亮对妥阿哲(济火)的封赐,奠定了水西作为彝族方国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基础,同时奠定了顾全大局,爱国统一的民族文化。因此说勿阿纳是水西文化的开拓人物,妥阿哲则是水西文化的奠基人物。后继者将水西文化一代代传承下来。到了明朝,在奢香夫人及其后继者的努力下,才促成了水西文化得到极大的丰富,终于形成独具特色的彝族历史地域文化。后来的改土归流则是彝汉文化碰撞的典型,它影响了水西的经济形态和社会进程,彝族文化走向衰微。
将水西文化分解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方面加以考察,更能发现其区别于其它文化的特征。当中彝汉文化交流并融合碰撞的轨迹和特征也更加明显。
物质文化方面,水西物产丰富,其中水西的漆器、咂酒、水西马尤为著名。其中水西马是贵州名马种之一,元朝时期水西是元政府的军马场之一,“明朝洪武年间水西就向中央王朝进贡或交易水西马达35次之多”。[4]水西咂酒在贵州也很有名,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有诗赞曰“万粒明珠一瓷收,君王到此也低头;五龙抱起擎天柱,吸得乌江水倒流。”叹的便是彝族咂酒之魅力了。另外,交通和建筑方面也有奢香夫所开辟的龙场九驿及后裔所建水西十桥和大方宣慰府、九层衙门作为代表,具有明显的彝族古代文化特色,也隐含着彝汉文化交流的轨迹和倾向。
制度文化方面,水西地区长期实行土司制度,其主要有三个特征,政权与族权相结合的“宗法制度”,军政合二为一的“则溪制度”,以及以“九纵九扯”为特征的职官制度。其中则溪制度的特征最为突出,其“是水西文化的主要特色,也是最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一种制度文化”。[5]实质上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做法,其统治者兼有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双重身份,监管军事和民政,而平民也有农民和士兵两种职能和双重身份,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
精神文化方面。“从总体上说,水西文化体现了以彝族传统文化为主体,以彝汉文化交流为主线的格局”。[6]水西文化崇文而不僵,尚武而不怠,崇尚先进文明而不固步自封,爱好勇武而强调开发进取,这就使得如济火、奢香等众多统治者有着战略前瞻性眼光和政权的整体意识,对彝汉文明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在重大历史关头被迫进行抉择时,为长久打算而作出必要的放弃甚至牺牲,这也是水西政权得以保存并发展一千四百多年的原因之一,自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深明大义的爱国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是在早期的彝汉文化交流中得以开创并传承。然而彝汉文化交流应从明朝奢香夫人谈起,这一时期水西彝族文化和汉文化发生交流融合,最终促成了水西文化的形成。
二、 奢香时代的彝汉文化交流
彝汉文化交流的主线具体到水西彝族上来,就更能体现这种由文化碰撞融合而带来的社会变迁。这与当时中央政府的延边政策息息相关,包括水西彝族在内的整个西南彝区,以明清为文化交流的界点。明清以前,彝汉文化交流多是彝人对汉人的影响,汉文化吸收许多彝文化的成分;明清之后,汉人移居彝区的数量增多,伴随着对地方的开发,彝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但应当明确,作为“圈外”或“化外”的彝族地方文化并没有在国家文化权力的渗透下消失,因为无论影响的倾向性如何,这种交流都具双向性。以明朝奢香时代的彝汉文化交流为例,彝汉文化交流反而促成了水西文化的形成。两种文化产生了冲突、磨合、交流,最后融合,“开始一种新的文化的创造,而这种创造是一种双向的流动,双向的选择,从而也就没有所谓主流文化对‘圈外吞食”。[7]同样,彝族文化也存在对外适应性,彝族与汉民族发生交往,尤其是产生激烈冲突的时候,作为发展阶段较低的彝族文化要逐渐适应发展阶段较高的汉文化,只是这种文化适应不能理解为文化代替,“彝族文化由缓慢的变迁进入剧烈的变化阶段,这种变迁存在着传统文化的衰落和外来文化的移入两方面的对立统一”,[8]这种对立统一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两种文化文明程度造成的文化交流的落差。
水西由奢香夫人当政时期为彝汉文化交流的高峰。奢香夫人深受马烨毒害而不举兵泄私愤,看透其企图寻求借口以便武力消灭土司而代以流官的政治阴谋,对力主报复的四十八部土目陈述利害,言:“反非吾愿,且反则歹得天兵以临我,中歹计矣!我之所以报歹也,别有在也”。[9]“别有在”也即是采取告御状伸冤的方式,这正是继承并发展了水西彝族深明大义、识时务而知进退的历史传统。内附大明朝,避免了水西动刀兵而伤黎民,客观上一定程度的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奢香当政时注重改善交通,组织人民凿山开路、修建驿站,从而将云、贵、川、湘、桂几省分治地域联结起来,沟通周围四省,联系“大西南”,突出贵州的战略地位,客观上为贵州建省准备了条件,也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10]交通的改善大力促进了水西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为文化交流、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便利,也可以视作早期彝汉文化交流的例证。
在交通改善的基础上,奢香夫人时期水西彝族还重视学习和引进汉族文化,加强和促进了彝汉文化交流。奢香夫人带头派遣子弟进京学习,在其带领下,水西各土目甚至乌蒙、芒部各土司多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中央也在水西置儒学、设教授,文化交流热烈频繁。这一时期,彝汉文化交流以相互融合为主导。受汉文化的影响,水西彝族开始重视文明财富的积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出现了《西南彝志》等彝文典籍的集大成者。这时彝汉文化文化交流融合更多的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此时水西地区出现了彝汉双语并行之局面,且在当时彝汉双语互译成为一种时尚。今大方存水西文物《成化钟铭》 《水西大渡河建桥碑记》 《千岁衢碑记》都有彝汉双语并刻,可作一佐证。当时在国子监读太学的土司子弟将彝语彝文带入京城,国子监所属的四夷馆据此编成《华夷译语》,可谓迄今为止最早的彝汉文互译工具书。[11]可见当时彝汉互译的风尚。其次是水西地区广设学校,汉儒之学勃兴。水西民间将“读汉书”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并出现了水西教育史上的第一个进士张谏。在水西官制中,无论是最高层次的“苴穆”还是地方“则溪”和司署都有许多汉族人士参与,这与民族狭隘性、排他性的淡化和彝汉文化深入交流是分不开的。反映在生活习俗上,汉族的二十四孝故事被译成彝文广泛传颂,后来在丧葬上应朝廷要求改火葬为土葬,普通百姓读汉书仕科举、作诗撰文。同时也反映出彝汉文化交流的倾向性,虽是双向影响,但更多的是汉文化强大辐射作用下水西文化的变迁,只是表象为文化交流融合的大潮,也体现出水西文化的对外适应性以及水西人兼容并蓄的性格。
奢香时代的彝汉文化交流主要倾向为文化融合,水西彝族吸收汉文化促成水西文化的最终形成,而到清代康乾时期水西地区的改土归流则主要是彝汉文化交流的碰撞方面,水西的制度文化变迁。
三、 改土归流:制度文化及其变迁
两种文化相碰撞,落后的一方总是吸收先进一方的文明,先进一方的文明也总会受到落后文明的影响,双方会有一段碰撞融合的过程。水西地区彝族文化和汉文化的碰撞结果在这里主要体现为改土归流。两种制度的更迭,土司制度受到流官制的强势冲击,在长期存在的土地上渐渐隐没,流官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得以在水西地域上建立,从宏观上看对彝区是一种解放、一种进步。
彝汉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民族隔阂是一个顽疾,历朝历代西南彝区就是中央政府的边患,因而历代中央政府对边疆无论是文化施教、武力征伐还是推广垦殖,都是为了解决“夷患”。和大小凉山不同,水西彝族和汉族来往密切,明朝奢香夫人时即为第一个交流高峰,到清代改土归流前夕文化同化融合程度亦更深矣!无论是土官制度还是流官制度都是当时的封建王朝的沿边政策,只是由于彝族社会发展缓慢,所以才会短时间内发生制度更迭,文化碰撞也更烈了。
土司制度是我国古代边疆政治的一种特殊历史产物,是一种封建的政治制度,其经济基础是封建领主制经济,实质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相妥协而产生的权利结构或政治制度。土司制度“以土官治土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地方自治制度,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推行的间接统治。一般认为,土司制度渊源于汉晋时代,元朝初具规模并最终形成,在明代得以完善,衰败于清朝。在水西地区,蜀汉时期诸葛亮曾封济火为王,后有“济火碑”记载,这可能是最早的类似于土司的政权形式,说明水西地区的土司制度推行较早。但土司制度也并不是单一的“以土官治土民”,它是结合彝族家支单位的等级制度而存在的,事实上是土司与家支势力共同实现统治,所以显得比较特殊。就水西土司而言,也形成自已统治的特点。它有以下三种统治方式:一种是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即“政权与族权相结合,核心就是确保君长地位继承的世袭特权,君长是最高家族长,在统辖范围内有行使政治、军事、祭祀以及经济等权利的最高地位......”,[12]可见,宗法制度是一种家族统治,族中大权只适用于一姓,在利用联姻等方式联系异姓,使得统治区域内形成一个大的家族系统,政权与族权合并为一,以家支为纽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在宗法制政权下,水西地区形成了“十二宗亲,四十八目,一百二十骂裔,一千二百夜所”;一种是则溪制度,以血缘为纽带的基础上在结合地缘,将军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共同构成严密的管理系统,“则溪”是土司下的行政单位,主要有两种职能:一是掌管军队;一是掌握地方经济,主管粮草。相应设置两类官吏,每个单位则溪需向大土司及君长报告军事赋税情况,这样既分权又集权,将血缘与地缘紧密结合在一起。则溪制度是水西整个统治结构中最有特色的组织制度,影响深远,改土归流后仍有一些残余,现在贵州西部含“溪”的地名,如贵阳的花溪,毕节的撒拉溪等,可以说是早期则溪制度的遗存了。水西十二宗亲加上最高统治者“苴穆”,形成水西十三则溪,实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水西土司制度还有“九扯九纵”的特征,九扯九纵就是君长之下的官吏设置,自君长下,共设九个品秩,君、臣、布三官共同处理国家要事,是一种职官制度,是部门分权和层级统御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制度,有着十分独特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也是水西的独创。水西政权的基本行政单位为“则溪”,下并未设司,权力集中于君长,利用血缘及地缘再加上以官职为基础的业缘影响和控制地方,“将三大制度有机结合,尤其是家支纽带层层深入基层......”,[13]将水西纳入一个庞大的家族式统治之下。客观来讲,水西土司政权一定时期内曾起到积极的作用,顽固的家族统治有利于地方的稳定;从中央政权来看,起到巩固边疆、开发地方的作用,这也是土司政权得以长期存在的前提。随着流官制的推行,君长丧失统治权,血缘纽带断裂;流官流动任职,地缘、业缘优势丧失;国家将地方大权收归中央,原来的土司官吏品秩无法维系。两种制度碰撞下,大势所倾,流官制经长时间的实践得以在水西地区确立。
改土归流是水西地区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彝汉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改土归流的推行,两种制度文化发生激烈碰撞,并对水西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是在政治体制上结束了水西长达一千多年的方国政权和土官统治,打破了固有的行政区划。在土司制度之前,包括水西在内的西南彝区多为奴隶制,从父系制的酋长制度演变下来,因其各支系和各地域的发展程度不同,包括黔西北彝区的许多彝族地区发展到宗法制阶段,血缘和地缘更加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形成顽固的土司统治。但流官制度破坏了这种基础,其是中央政府强制推行的沿边政策,它是一种强制文化的渗透。推行流官制,打破了水西以往的土司政权和行政区划,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这从始皇帝推行郡县制始,便是一大趋势。
其次是改变了水西地方的民族结构,迎来了彝汉文化交流的新时期。改土归流使水西地区的民族结构发生变化,之前为“夷多汉少”的局面,现逐渐向“汉多夷少”转变,民风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文化的走向,从以水西彝族文化为主体转变为学习和接受汉文化为主。[14]由此掀起了两种文化碰撞融合的第二次高潮,相对前一次倾向性更为明显,水西彝民主动学习并使用汉语,已有诸多彝人通过科举考试参与王朝政治;水西彝人改变自己风俗,学习汉族先进技术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变服从俗不断汉化,为一大趋向。
两种文化的碰撞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流官制在实践中克服了土司制的阻碍力量,尽管改革过程中过于血腥和残暴,对当时当地经济是一个极大的破坏,且不彻底,保留大量的土司残余。但从长远看,两种制度交融加强了水西彝族地域同外界的来往,为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打下基础,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而彝区人民所承受的文化碰撞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四、继承发展:文化保护、传承问题的回顾与前瞻
应该明确一个态度,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所在,我们不能随之弃之恶之;同时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也不能仗着文化的深厚而固步自封,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优秀的民族皆因其经济与文化上先进才著称优秀,若一个民族只喜于历史的源远流长,而不注重时代的发展,可能难免于毁灭性的灾难”。[15]因此我们要正视现代化的形势,不能盲目排外和抵触,同时也不能在这样激烈的文化碰撞、文化变迁中迷失自我,丧失文化传统,“丧失现代化意味着民族的贫固;丧失文化传统则意味着民族的消亡”。[16]不仅如此,我们还要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一个民族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有自尊、有民族的光荣感、自豪感,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接纳任何外来文化。如果在适应现代化主流文化发展过程中丢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就失去了一个民族的“根”。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莱克所指出的:“传统价值模式是社会凝聚的基础,而采用新知识又必须改变传统价值体系。对社会的自下而上来说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17]彝族文化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这样的新形势,自然也必须得保持这样微妙的平衡。
对于水西彝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应该坚持内外因共同作用的原则。我们不能无视彝族人的生存空间受多重挤压,彝族人多脱离彝区的现实而高谈文化继承问题。彝族人是彝族文化的第一继承人,不能忽视彝族人的主体作用。增强彝族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前提是发展彝区经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水平,增强彝人的民族认同,而“民族认同的关键在于民族的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这些需求包括民族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与更高层次的尊重、自我实现等内容”。[18]以此来减少人民脱离本区的现象,毕竟传统的民族区不存在来讲文化的传承是不现实的。外因上,要关注教育体制,现在中小学的教育课程缺乏民族文化的版块,要保护就要普及,而将民族文化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是较好的普及方式;另一方面,学校的寄宿制影响了文化的传承,家庭是民族文化传承优良的环境,脱离了这样的环境,许多孩子忘记了本民族的语言,对于其它文化更是知之甚少,当然,这要求教育网络达到一定的程度,或者学校实行双语教学;其次,在行政上地方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特色旅游产业,为彝族文化的传承寻求土壤,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和利用相结合,在保护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只有保护继承才可以促进创造;建立健全文化保护条例,政府制定切实方针,履行好职责;最后,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包括数字采集、数字储存、数字处理、展示传播等手段保护文化遗产,使少数民族文化得到共享。
两种文明进行交流,落后的一方和先进的一方总会因矛盾的因素而相碰撞,会有因相和谐的因素而促进融合,最后落后的一方文明总是吸收先进一方的文明。水西彝族文化是整个华夏文明的一支,是历经千年历史积淀而成。而这其中是以彝汉文化交流为主线不断发展的,奢香时代的彝汉文化交流奠定了水西文化的基础 ,改土归流则是在汉文化影响下水西制度文化的变迁。近代化以来,水西彝族文化初传统汉文化外又受到一些文化新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外来的文化新思潮,还是传统主流文化,对彝族文化都是一个大的冲击。对彝汉文化碰撞、同化、融合的原因、过程及结果的探究,最后不过是要对彝区进行改革,而“改革背后的主要目的是想建立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历史而达到文化自觉”,[19]最后达到对彝族文化进行保护传承并发展的目的,然而文化的先进性因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应该正视的问题,挖掘文化内核,寻求这种生命力,为文化保护、传承提供条件,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作者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历史系)
贵州省2013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310977009
参考文献:
[1]贵州彝学研究会.贵州彝学[M].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109.
[2]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2009.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M].民族出版社,154.
[3]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点校.2000.大定府志[M].中华书局,950.
[4]王明贵 王继超 .2011.水西简史[M].贵州民族出版社,130.
[5]王明贵 王继超.2011. 水西简史[M].贵州民族出版社,42.
[6]王明贵 王继超.2011. 水西简史[M].贵州民族出版社,108.
[7]李列.2006.民族想象与学术选择——彝族现代学术的建立[M].人民出版社,154.
[8]贵州彝学研究会.2004. 贵州彝学[M]. 贵州民族出版社,223.
[9]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点校.2000.大定府志[M].中华书局,953.
[10]余宏模.1996.试论明初奢香夫人维护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绩[J].《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第三期.
[11]王明贵 王继超 .2011.水西简史[M].贵州民族出版社,110.
[12][13]李美兴.2012. 水西彝族土司文化价值研究[C]. 青年与社会教育版2012年第一期.
[14]王明贵 王继超.2011.水西简史[M].贵州民族出版社,110.
[15]贵州彝学研究会.2002. 贵州彝学[M]. 贵州民族出版社,28.
[16]贵州彝学研究会.2004.贵州彝学5[M].贵州民族出版社,225.
[17]张纯德 李崑.2007.彝学探微[M].云南大学出版社,144.
[18]赵心愚.2010.西南民族研究 第一辑[M].民族出版社,399.
[19]费孝通.1997.反思 对话 文化自觉[C].北京大学学报. 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