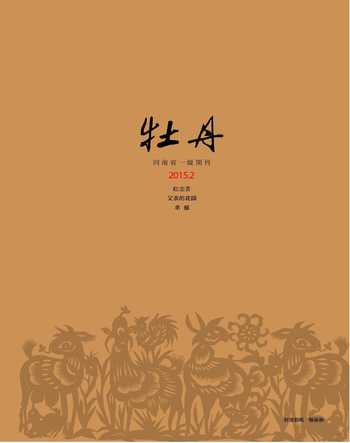编辑手记
李坤
文界常言:俄罗斯文学乃世界文学之青藏高原。这并非虚言。俄罗斯文学从尼古拉二世开始,一直是以思考人生问题为旨归的,其深度不亚于德国哲学对人生的探索和思辨。对人生意义不间断的叩问,对人生困境穷根究底的思索,且以小说故事的形式鲜活地呈现于世人面前,我觉得这是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一个独创,这其中尤以阿尔志跋绥夫、安德列耶夫等人最为典型。阿氏的几乎每部作品都打上了十分鲜明的个人印记,其主人公的痛苦与欢乐、对人生的困惑、绝望及憧憬无疑都是作者自身的画像。阿尔志跋绥夫的文学造诣不只在长篇小说,其中短篇作品也同样精彩。《幸福》即是其一。
我认为它是短篇小说中的极品,如果不是因为特殊的缘由使之被埋没的话,或许它今天早已像《变色龙》《我的叔叔于勒》等一样为我们所熟知。《幸福》的文学语言如阿氏的其他作品一样既精炼又意涵深刻;而故事情节却既简单又颇耐人寻味。如此高水准的纯艺术品,在我们的文学中是难以找到的,如果非找出一篇,我觉得鲁迅的《孔乙己》与之有一拼。
妓女萨什卡鼻子突然烂掉了,怎么烂的,小说没有交代,这含蓄的一笔,让人想起了卡夫卡的主人公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甲壳虫。但阿尔志跋绥夫是写实的,虽未点明原委,但足以使人联想到萨什卡平素生活的可悲与不幸。如此一来,她曾经赖以为生的资本——青春与美丽,即会大打折扣。生活渐渐陷入困境,也就不可避免。基本的生存已然成为一个严峻的事实。至此,小说的笔触直抵人性的底线,继续存活的求生本能使得陷入绝境的不幸女人不得不在寒冷的雪地里,接受一个变态狂——一个麻木不仁的市民——的无情杖击,以此获得能使之继以为生的五个卢布。
发人深思的是,刚刚遭受杖击、仍带着剧痛的萨什卡看到五个金光闪闪的卢布,想到将会享有食物、温暖、宁静、伏特加,“突然她全身充满了一股巨大的轻松的快感”,“整个身心都充满了光明的幸福的想要欢歌的感觉”,“而刚才对她那怪诞和极端令人厌恶的殴打,她已经忘记了。”对此,鲁迅曾深刻地指出:作者在这里将“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识的本能”,浑然写出;便以事实而论,也描尽了“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