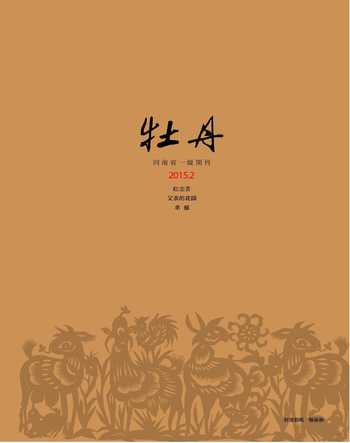打麦场
赵明宇
一个个打麦场其实就是散落在村落和田野之间的一块块空地。
麦收前,三五家凑在一起就为打麦场做准备。在村外找一片有风的地方,用农具划破土层,碾轧成面粉一样细密的绒土。这道工序叫磨场。然后是泼场,一家老小齐上阵,均匀地洒水,覆上麦草,让表层的绒土在阴凉中被水分浸透。趁着不湿也不干,套上牲口或者用拖拉机,拉着石磙在上面碾轧。最后除去麦草,呈现一层坚硬的皮层,像镜面一样光滑平坦,打麦场就算大功告成了。
田里的麦子被捆成一捆捆,聚集在打麦场上,堆积如山,打麦场就热闹起来了。为了防火防盗,家家户户都有人睡在打麦场上。有的人劳作一天,累了,也困了,干脆连饭也不吃,倒在打麦场上就鼾声大作了。衣服也不脱,脸也不洗,睡得那么香,直到第二天黎明,被风吹醒了,揉着眼睛又开始劳作。
如今,在城里的单元楼里,晚上洗热水澡,躺在软软的床上总是失眠,不得不怀念在打麦场上的睡眠状态。
把麦子摊开,抖落在打麦场上暴晒,这个过程叫匀场。午后,麦子被晒焦了,套上牲口拉着石磙在上面碾轧。日头毒烈,赶牲口的人手持缰绳,站在麦场中间,吆喝着牲口,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几个小时下来,太阳快落了,开始起场,挑去麦秸,下面就是与麦糠混杂在一起的麦粒。如果有风,就开始用木锨扬场,借助风势让麦糠和麦粒分离。
随着扬场人手中的木锨起起落落,麦糠被吹走,胖胖的、褐色的麦粒落下来,越积越多。小孩子在打麦场上奔跑,喜欢站在扬场人身边,感受麦粒像雨点般落在身上的感觉。这时候,往往会遭到扬场人轰赶麻雀一样的佯怒,小孩子嬉笑着跑开,旋即又跑过来。
麦粒们聚在一起,让人禁不住舒展眉头,眼睛像新月,用手指插进麦粒中间,掬一捧,麦粒就会水一样从手指缝中慢慢流下来。农耕时代,一年的生计全指望这些麦粒们,一日三餐自不消说,婚丧嫁娶的开销全指望麦子换钱。我曾看到一个急着浇地的乡邻,用自行车驮着一袋麦子出去,回来时变成了半桶柴油。他说一年到头赚个穷忙活。
还有一个乡邻说孩子要结婚,卖了麦子添置家具。可见一年的希望全在这打麦场上,所以对打麦场也就多了几分敬畏。比如望着打麦场上的麦堆,万万不可“估堆”,也就是估算这堆麦子有多少斤。如果有人说漏了嘴,泄漏天机,就会得罪五谷神灵。
麦收过后,打麦场闲下来,变成了麻雀的世界,麻雀们成群结队,在打麦场上叽叽喳喳地啄食被遗落的麦粒。
夏日里,家里闷热,打麦场、树荫下就成了纳凉的好地方。尤其是晚上,人们抱着被子到打麦场上睡觉。打麦场上凉风习习,黑暗中有萤火闪烁的地方是成年男人聚在一起抽烟。小孩子则只顾嬉闹奔跑,天晚了,累了,才躺进被窝里,听村里传来的狗叫,听身边虫子的啼鸣,望着满天星斗,不知不觉中昏昏入睡。
半夜起来小解,月明星稀,鼾声四起,虫鸣唧唧,不由得想起老人讲的鬼故事,就急忙溜进被窝,蒙上脑袋。
随着机械化的进展,脱粒机代替了牲口和拖拉机轧场。而联合收割机掀起一场麦收革命,忙碌的三夏不再忙,人们只需拿着口袋在田间地头等着收割机就是了。
打麦场也逐渐退出了乡村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