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
黄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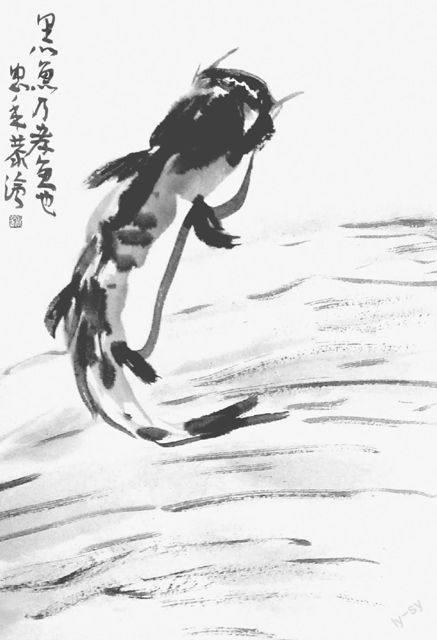
结婚不过六年,陈刚已经不知不觉丧失了他的大部分激情,这主要表现在他跟周宁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生硬和懒心无肠,做爱的次数也逐月减少,同时开始尖刻地嘲笑那些当街亲热的情侣们,对自己当年同样的举止却流露出羞愧和不可思议的神情。周宁对此也曾采取过许多力所能及的措施,比如说很刻意地打扮自己,在腋窝和脖子上喷洒据说是世界上最性感的香水,把她和陈刚恋爱时写给对方的情书翻出来,就着特意调低了亮度的台灯用普通话低声朗读(虽然她的普通话说得相当蹩脚)……但所有的措施显然都无法改变陈刚的倦怠和冷漠。周宁也考虑过生个孩子,她想,家里多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说不定会不同,但话还没说完,陈刚就高举双手,做出投降的样子,说拜托千万别出这馊主意,他还不想年纪轻轻就惹上一身屎尿味。
有个闷热的周五,那是他们第六个结婚纪念日。晚饭后周宁又在自己的腋窝和脖子上喷洒香水,用普通话朗诵了陈刚写给她的情书,再次详细描述了恋爱时他们第一次亲热的情景。那个情景在结婚的初期曾像春药一样令他们激动,每次只要提到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提到陈刚那张嘎吱作响的单人床,他们的兴致就会高涨起来。兴致高涨的结果不仅是激越澎湃的欢爱过程,还有接下来对未来生活的种种不厌其烦的琐碎设想,其间夹杂着忘乎所以的爱情表白,使用的词汇千奇百怪,几乎达到荒唐的程度,最后干脆变成了满嘴胡言乱语。
周宁还提到婚礼上,朋友们挤在他们不足二十平米的校职工宿舍布就的新房里,硬要周宁蒙住眼睛在六七双男人的手里把陈刚的手找出来。周宁居然毫不费力就在那些指头里拧出了陈刚的食指。朋友们大呼小叫说,肯定是陈刚给了周宁某种暗示。陈刚得意地说,这就叫心有灵犀。周宁后来说,她在那些众多手指里摸到了陈刚食指上那块长年拉琴留下的老茧疤。
但事实证明周宁的一番苦心都是枉然。陈刚歪着头斜靠在床头,似听非听地在昏暗的灯光下凝视对面墙上一张很大的白桦林彩色照片,然后东拉西扯谈了一通物价和收入的关系,中途静默了半天,突然又开始莫名其妙地诅咒起他的上司来。凭着夫妻六年对陈刚的了解,周宁知道他其实一点也没真生气,不过是拙劣的表演而已。看着陈刚像只没有气囊的蛤蟆却努力地想要对手相信它的怒气,周宁强撑起的一点兴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等陈刚表演完就背过身去,她发现身上的香水味突然难闻得要命。
那个周末他们哪儿也没去。从周六下午到周日的整个白天,周宁都把垫子铺在客厅里,照着瑜伽教学碟片反复练习,而陈刚却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网络上,跟一个据说厉害之极的高手下围棋。晚饭时陈刚神色诡秘地向周宁宣布,他肯定那人不是聂卫平就是马晓春,阴险、狡诈、高深莫测……他说,不过我今天还是让他紧张了那么短短几分钟。那天周宁学会了两个具有相当难度的体式,全身上下血气畅通,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加上陈刚情绪不错,所以她决定晚上再试一次。
陈刚像是事前就揣度到周宁的心思,晚饭过后借下楼买烟的工夫,顺便从旁边一家碟子店租了一套美国连续剧《越狱》回来,一同带回两个菠萝面包、一袋油炸花生米和三瓶立泉啤酒。并对周宁说,这可是今年最畅销的一部大片,非看不可。
陈刚邀周宁一起看,周宁却坚持说困得很,想早点睡,明天大早第一节有课。陈刚体贴地说,那你早些睡吧。她坐在沙发上跟着陈刚看了半集,怎么都进入不到情节当中去,于是冲了个澡,懒懒地躺在床上翻一本时尚杂志,看了几页困倦便袭来,几乎没有过渡就睡了过去。
半夜时周宁被席梦思床轻微而有节奏的晃动从一个梦带到了另一个梦,梦里她站在东山电视发射塔的顶端,张开四肢纵身跳下,无声无息地在夜半的城市上空风筝一样滑翔,最后轻盈地降落在她小时候住过的那幢老木屋的房顶;整个城市灯火辉煌却阒寂无声,就像一道神秘的命令一夜之间疏散了全城居民,一种又亢奋又紧张的预感胀满了四周的空气,憋得周宁喘不过气来,她想要尽快飞离黑瓦铺就的房顶,却发现双脚已经被青苔牢牢粘住了。周宁从梦中醒来,躺在仍在摇晃的床上好一会儿,这才意识到,原来那个诡异的梦境以及梦中奇怪的紧迫感实际上都跟身旁的陈刚有关。
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周宁心情复杂地偷觑着陈刚的脸,那张脸这时已经恢复了平日那种淡漠的孤零零的神情,很难把眼前这张脸跟凌晨时黑暗中的那张脸联系在一起;在周宁的想象中,那张脸是放纵和痴迷的,带着某种非人的狂热。周宁突然有种强烈的好奇,很想知道是哪个女人出现在了陈刚的想象里。
不要脸。她说,真是不要脸。
什么?陈刚愕然地从碗边抬起了脸。
就在那个时候某个男人的气息从周宁的身旁倏忽而过。大前天,她一面想一面说,因而说得相当慢。我去沃尔玛买麦片,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男人的手推车,那人大约三十多岁,跟你差不多年纪,他车里的东西撒了一地,他没怪我,倒冲我笑了一下。
那有什么稀奇?陈刚放下碗,用纸巾胡乱擦擦嘴,站起来准备离开。
今天中午我又遇上他了,周宁自顾自地说。她仍然一面想一面说,说得跟刚才一样慢。下班之后我不想坐车,就顺着人民广场往回走,路过沃尔玛时我发现那个男人就站在超市门口,
他也认出了我,又冲我笑了一下。
那又怎么样,陈刚说,我没听懂。
不怎么样,周宁平淡地说,我只是觉得,就那么点事,他倒冲我笑了两次,你说,这男人是不是有点……那个?
陈刚站着想了想,骂了句神经病,就转身回到了客厅。也不知道他是骂那个男人还是骂周宁。
隔了一天,又是吃中饭的时候,周宁第二次向陈刚提到了那个男人。我今天又看见那个男人了,我坐在公交车上,他还跟那天一样站在沃尔玛的大门口,东张西望的,不知在等谁。
第三次提到那个男人时,周宁表现得有些大惊小怪。今天我去沃尔玛买了两提卷筒纸两提抽纸,还有一个报夹和五袋水饺,刚交完款,旁边突然就有人伸手接了过去,说要帮我拿,我吓了一跳,调脸一看,你猜是谁?
那个男人。陈刚有些迟疑地说。
你怎么知道?周宁一下挑起了眉毛。
你让他帮你拿了?
当然,为什么不?周宁笑起来,那么多东西,有人想帮你……
陈刚看了一眼周宁,那人什么样?
这倒没注意。周宁说。陈刚的话提醒了她,那人的确应该有个样子的,但什么样子呢?她有些茫然地盯着陈刚的脸,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她发现陈刚的脸很像几天前曾在电视上出现过的一只小猩猩的脸,那只小猩猩被人从刚果拐卖到了欧洲,蹲在一根巨大的树干上,神态既幼稚又苍老,让人看了有些手足无措。
如果,周宁犹犹豫豫地看了一眼陈刚说,下次再遇上他我会看仔细点。
接下来的两天,周宁开始专注地想象男人的那张脸。首先要解决的是他的体型和相貌。体型的问题要好办些,一个三十五岁左右引人注目的男人,他的体型理所当然应该是高大嶙峋的,有两条强壮有力的长腿,长得就像是直接长在腰杆上似的——关于体型,周宁觉得这就够了。但男人相貌如何,却使周宁很费了一番脑筋,她对男人的五官向来不太敏感,认为那是一个男人身上最不重要的部分,拿不准到底是英俊的、漂亮的、粗犷的,还是清秀的,哪一种类型更容易引起别的男人的嫉妒,或者具体说陈刚的嫉妒。最后,出于某种无法言说的复杂心理,周宁为那个男人的相貌定下了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应该正好跟陈刚截然相反。周宁突然意识到,就在刚才,在确定那个男人的体型时,她早已本能地把男人跟陈刚作了完全不同的区别。从结婚第二年起,陈刚开始发胖,他是那种骨骼纤细的男人,一发胖,整个人就显得圆乎乎的没了棱角,尤其是他的屁股,发面似的突然膨胀起来,按周宁玩笑的夸张说法,如今的陈刚即便已经朝前走了八步,他的屁股还仍留在原地来不及挪动。
原则一旦确立下来,那个原本如烟如雾的男人很快就显出了基本形象,一张长方脸,下巴朝前微微翘起,底端有个小小的凹痕,也就是俗称的英雄结;跟陈刚清秀的、眼皮很双的眼睛相反,那个男人是一双细长的丹凤眼,嘴唇薄而宽大,正好跟他的眼睛协调;陈刚的鼻子在他的五官中长得最好,又挺又直,周宁有些舍不得放弃,但又不能违反原则,最后她虽然决定保留,但放大了鼻翼……
外形具体起来后,周宁又加上一条,男人不是本地人,说的不是纯正的普通话,带几分北方口音。周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加上这条,但她觉得这是必须的,她认定,在这个南方小城土生土长的男人是长不出这种长相的。
有几天时间,周宁故意一字也不提那个男人,陈刚果然先忍不住了。
某个晚上,陈刚躺在床上抽着烟,若有所思地闷了一会儿,突然问躺在旁边看书的周宁,你后来没有再遇到他?
周宁转过头,远远盯着门的方向,谁?
你知道我说谁。
不知道。
别装了。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陈刚没有说话。
噢。周宁愣了半天,像没回过神来。
噢什么,我问你后来有没有再遇到他?
吃醋了?
我吃什么醋?我是那种小家子气的男人吗?
那你问我干吗?
不说算了。
想知道吗?周宁大脑里立即跳出那个被她反复想象,已经清清楚楚印在大脑里的男人形象。遇到过,周宁停了一会儿想想说,具体几次也不太记得清了。打个招呼而已。
世道多乱呵,小心骗财骗色。
哈哈,周宁笑起来,我会小心的,我一定会千万小心的,这点你放心呵。
你准备怎么小心?以后换个超市。
换个超市也可以,不过呢,谁敢保证别的超市没有骗子呵。他要真打我主意的话,这么多次“机会”,别人也没怎么样嘛,是你小心眼了。再说了,我敢肯定他是个好人。
你凭什么肯定,看上去越像好人的人越要警惕,哪个小偷把“贼”字写在脸上?三十多岁的人了还这么幼稚。
是吗?我幼稚吗?
陈刚不说话,转头灭掉烟,用被子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背朝周宁一动不动。
周宁继续愣在那儿,也一动不动,她想,生活里真有这样的奇遇吗?她甚至在想,如果真的遇上这样的男人,她会跟他说什么呢?
那晚,一入睡周宁就梦见了那个男人。梦里,男人跟她设计的模样不太一样,看上去年纪更大些,那个男人在身后叫周宁的名字,然后等周宁转身时,便看见男人的半个身影站在她办公室的桌前,像是在等她……
昨夜我听你叫一个人的名字。一个周三的大早,陈刚还来不及漱口就追着在厨房做早餐的周宁说。
是吗?我从来不说梦话的,你不要无中生有呵。
我敢肯定你说梦话了。
那你说说我叫谁了?
嗯,记不清楚。
那你就是胡说八道。我会叫谁?该不是我的前男友吧?
周宁笑说。
也许,反正我从来没听见过这个名字。
叫什么。
汪总?汪祖?王筑?记不清了。
瞎编。
我干吗瞎编。我冤枉你对我有什么好。
我要叫也是叫你的名字呀。周宁扯着嘴角笑说。
好好好,不说了,算我瞎编吧。
我觉得你现在疑神疑鬼的,这么紧张干吗?
我干吗紧张,至于吗?只是提醒你,以后睡觉警醒些。
你晚上倒是很警醒呵。
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你晚上跟白天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那当然了,难道你晚上跟白天一个样呵。
不说了不说了,无聊。
周宁低头吃早餐,却突然晃过梦里的那张面孔,这让她隐隐地有些觉得理亏,好像她真的红杏出墙了。
周宁并没有真把这当回事,倒是陈刚的反应开始如了周宁的意,她并不想把真相就这样随便就告诉陈刚,那就白白浪费了她一番苦心设计。
周宁不再谈论这个男人了,但周宁明显感觉到,其实陈刚心里记住了这个男人。她发现陈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变得心细了,主要是对周宁的行为上表示出异常敏感,比如哪天周宁的手机信息提示音一响,或者周宁接电话,陈刚看着书的神情就冻住了,或者盯着电视的目光便涣散了。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说,什么事就不能打电话说吗,你是不是喜欢玩味这个暧昧的过程?你累不累?周宁白了陈刚一大眼,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什么叫玩味,你干脆说我用手机调情得了。
周宁对陈刚的表现刚开始时假装不在意,但后来陈刚的反应变得像弹簧一样,她便不得不作一些让步,比如说再有短信来的时候周宁不急着看,或者看的时候干脆念出声来。
除此之外,陈刚对周宁上下班的时间也很在意。如果哪天周宁下班晚回来,陈刚就会问是不是学校有事,她要么说下班高峰,等了几辆车都挤不上,或者说到超市去买什么东西了。周宁故意不说到哪个超市,陈刚倒要问一句,去沃尔玛吗?
陈刚接着会问是一个人吗?
我倒希望有人陪我去,这么多年来你有陪我逛超市的兴趣吗?什么时候不是我一人大包小包往家里拎。
陈刚停了一下,接着冷冷地说了句,我们家有那么多要买的东西吗?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周宁说。
你反应这么大干嘛?
你在猜疑我,我说得没错吧。就因为上次跟你说的那个男人,你以为我去约会了。你就这么点心思还遮遮掩掩的。
是呀,我是觉得你最近不太正常。
我要约会也不会选超市呀,你真的傻还是装傻,那么多双眼睛,那么多张嘴,难说不碰到一张认识你的嘴。再说了,你见过哪对男女在超市幽会的?
那我让你换个超市,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沃尔玛呢。
好吧,如果你觉得这样更安全,那我以后就换别的超市。周宁说完就笑起来,这样你该放心了吧。
但是陈刚仍在每次周宁晚回来的时候都显得异常烦躁,要么说些阴阳怪气的话,要么一声不吭死板着脸。
从前陈刚阴着脸一句话不说的时候,周宁是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的,非得把问题解决了才行。她最怕打冷战。所以结婚这么多年来,周宁明白婚姻就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再说夫妻间有什么不能说清楚的事呢,吵闹过后还不就很快和好如初了。他们会在周宁眼泪还挂在脸上,就又相拥一起说些检讨自己的话。但现在的周宁,对陈刚阴着的脸显得无所谓了,周宁的变化像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现在的情形是这样,还没等陈刚把气缓过来,周宁却没心没肺地照样哼着歌,在厨房里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当响,不再像从前那样,觉察陈刚情绪不对就寻根问底。
其实周宁对陈刚的表现并不是不在意,相反,她注意了陈刚的反应,并努力配合陈刚,有时候她甚至故意在街上走上半小时再去乘公交车,有意延长到家的时间。她想让那个虚空的男人真实起来,来打破陈刚的死气沉沉。她不过是无意间布下了一个小小的陷阱,让陈刚使足全身气力扑个空。她甚至在想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他肯定会拍着脑门嘲笑自己当初是多么的愚蠢。
昨晚我梦见你鬼鬼祟祟躲在卧室门后藏一封信。一个周末的早上,陈刚一边用电动剃须刀刮着胡子一边跟周宁说。
具体点。周宁说。
也没什么。
后来呢。
没有后来,整个梦只有这一个情景。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不跟你瞎扯了,我要上街买点东西。
我陪你去吧。
周宁很吃惊地转过头来盯着陈刚看。
至于吗?大惊小怪的。
你今天不是有学生来学琴吗?
他妈妈打电话来说孩子病了。
出门的时候两人都没谁主动说去哪个超市,却都心中有数地直奔沃尔玛去了。那天逛的时间很长,陈刚说既然来了就多逛逛。周宁没反对。有那么一瞬间,周宁自己也恍惚觉得在这些密匝的人群里,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个人,是不是真的会出现在她跟陈刚面前。她有点不自觉地把眼睛从货物架上移到人堆里,但这种心思很快就被周宁自己的嘲笑赶跑了。她偷偷在心里骂自己神经。但当她继续跟着人群慢慢移动脚步的时候,她却又感到仿佛有双眼睛把她牢牢地抓住。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两人都处在一种很奇怪的状态中,从周宁这边想,完全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谎言,说白了就是一切都在原地不动;但从陈刚这里想呢,生活里似乎正在发生着什么,像影子,抓不着,但是在那。
一天中午周宁像往常一样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出了门,沿着马路往车站走,手机响起来,她看了电话,是个陌生号码,本不想接,但手机不停响。她按下接听键,一个男人的声音,周宁?我是刘力,还记得吗?街上声音干扰实在太大,周宁没听清楚,电话那头也是,不断的汽车喇叭声穿过,周宁“喂”了两声,大点声,我听不清。那边声音也大得想盖过汽车声,我——是——刘——力。周宁笑起来,你在哪呵?怎么突然冒出来了。我在马路对面。周宁转过头正看到刘力站在路边朝她挥手,接着刘力便穿过车流小跑过来。几年不见了,你的手机号居然没变。两人在路边说了半天话,说得两人都觉得那话里没有告别的意思,刘力说,要不去我画室坐坐?聊聊天,我请你吃饭。周宁见了刘力,那些小时候的记忆立即让她兴奋起来,好呵好呵。
在去刘力画室的路上,两人不停地聊着小时候在一起学画的情形。周宁说自己都快忘了曾经想当画家的梦了。他们先在刘力的画室看他的画,然后又去刘力画室旁边一个小馆子里点菜吃饭,刘力还要了瓶啤酒。你真是多年的习惯不改呵。周宁看着刘力倒出满满的啤酒。你也喝一杯?庆祝我们重逢嘛。两人聊得正高兴,周宁的手机响了,她拿出看是陈刚,正要按接听键,鬼使神差的却碰到了挂机的键,再回过去,陈刚的手机却占着线,估计是陈刚也在往这边打。她等了半分钟,又打过去,仍占线,重复了几次,竟一直没打通。周宁的心思开始恍惚起来,心里隐隐的有些焦虑。刘力看出来了,说,有急事?周宁说我老公找我。刘力体贴地说,家里有事?要不,你先回去,有空我们再聚?周宁想想,说那好,我先走了。
回到家,陈刚的脸色自然不好看,但一句话都不问。
今天中午下班路上遇到小时候一块画画的朋友,便一起吃饭聊天。周宁主动说。
周宁看着陈刚的脸,就明白陈刚一点都不相信她的话。两人草草吃了面。其间,刘力打过一个电话来,问周宁到家没。周宁说早到了,正吃饭呢,刘力那边便挂了电话。
刚才在楼下碰到我们学校搞基建的黎老师,说要给我们这幢楼扩一间出来。周宁说。
陈刚懒心无肠地说,嗯。
要真这样太好了,我们就差一间孩子的房间呢,等房子修好了我们就要个孩子吧。
陈刚没说话,拿着电视遥控器摁来摁去的。
这种情况,我们得补多少钱。
不知道。
还说明年开春就动工呢。
……
周宁见陈刚的样子,也没心情再说什么,起身到书房打开电脑,在淘宝网上看今年的流行服装。在网上跟在实体店逛商场一样,时间过得飞快,不同的是,在现实生活里逛商场是脚累,在网上逛商店是眼睛累。周宁直到逛得眼睛酸胀才关了电脑,然后准备洗个澡。陈刚还在看电视,没有要睡的意思。
等周宁从洗手间出来,手机便在客厅的茶几上响起来。是刘力打来的。
打我电话有事吗?接了电话你又不说话。刘力那边问,刘力的声音听上去十分灿烂,整个人像是站在阳光底下的。
没有呵,周宁愣了一下说,可能是我误碰到电话键了,挂了呵。周宁挂了电话,她打开已拨电话,看到电话上显示了一个拨出去的电话,时间是十分钟以前,拨给刘力的。那时她正好在洗手间。周宁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陈刚,骂了句有病便转身进了卧室。
几分钟后周宁就听到客厅里摔东西的响声。她从卧室踅出来,便在客厅里见到地上的电视遥控器,已经四分五裂了。
躺在床上的时候,陈刚点着一支烟,慢吞吞地说:
我们都是成年人,老大不小了,别做蠢事。
我不懂你的话。周宁转过头来面对着陈刚。
你真不懂吗?
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不和你讨论这个话题,鬼迷心窍。
是我还是你!
别说了,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
你说没事就没事?我可不想这样不明不白地过。
不管你信不信,我并没有做任何有损你尊严的事情。
你不觉得你这一段不正常吗?
我的“不正常”只跟你有关。
不会吧,把自己说得这么清白,那个叫什么刘力的,方便问一下吗?究竟是谁?
是我小时候一块画画的,不都跟你说过了吗?干吗你就是不信呢。
噢,今天你都跟他呆在一起?
是的,中午下班在路上遇到他……周宁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过程。
就你俩待在他的画室?孤男寡女的两个人?
说得这么难听,什么叫孤男寡女?
不是吗?那你说说还有谁?还让他画你了?
是,这也没什么不正常嘛。以前我们一块画画的时候,就是轮流做模特的。你想到哪去了。
陈刚这次摔的是手边的烟灰缸。烟灰缸发出巨响从墙上弹落下地,而烟灰却是慢慢地轻手轻脚地铺在地上。
这是两人吵得最厉害的一次。周宁觉得此时一切都像是安排好了的,从那个念头开始,而刘力的出现就像是要更完美地配合这场游戏。
我不跟你瞎扯,如果我们再这样下去,还不如……
不如什么。你说出来。
我的意思你清楚。陈刚不愠不火地说。
你是说离婚吗?周宁吃惊地看着陈刚。他们从来没有谈论过分开。从前再吵再闹,他们都知道不过是些婚姻里不可避免的小矛盾。周宁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周宁委屈地想,自己没做错什么,倒要落得个这样的结果。周宁哽咽着说,随你。
从那天起他们之间再没有提及此事,只是陈刚开始时常的彻夜不归,要么去跟朋友喝得不醉不归,要么就通宵达旦打牌。按陈刚的说法是,他得为自己活。
周宁想过好好跟陈刚谈一次,把那个谜团揭开,但是此时她去跟陈刚重提那个虚幻的男人,以她对陈刚的了解,他听不进去,也不会轻易相信,甚至一定会嘲笑她编出这样个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她想,等过一段时间,等他的情绪过后再说也不迟。周宁重重地出了口气,端着杯热茶坐在沙发上想,自己没做错什么,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他们婚姻的事情,她只不过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让陈刚重视起他们的婚姻。周宁想着突然对自己笑起来,这不过是他们婚姻生活里的一剂强心针。这样想之后周宁便释然了许多。
周宁开始调整自己,她让作习时间比任何时候都更正常,她甚至在学校一分钟都不多留,下课铃声一响,回了办公室拿了包就走。周围的老师觉得周宁每天都这样,有些担心地问她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是不是老人病了。周宁总是笑嘻嘻说,没事,就是怕遇上下班高峰,连公车都没法挤上去,到家天都黑了。问的人当然理解,但周宁却又觉得心里堵得难受。刚开始陈刚还在家吃饭,后来陈刚连饭也不在家吃,丢下周宁一人,打电话陈刚从来不接。周宁不想把事情闹大,到了周末还是强忍着要陈刚和她一同回母亲家,陈刚倒也识大体,在岳母家有说有笑,回到家又照例板了面孔不说话。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周宁觉得心里快撑不住了,决定再和陈刚好好谈一次。
你是不是打算就这样过一辈子。
陈刚抬眼盯着周宁看了半天说,那你打算怎么过。
你不觉得我们之间出现问题了吗?
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挺好的。陈刚一副死乞白赖的样子。
你究竟怎么想的。周宁说。
我倒要听听你是怎么打算的?陈刚歪在沙发上,脸色有些发青。
我做错什么了你要这样对我。
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装什么淑女?
陈刚我告诉你,我没做任何有损我们婚姻的事。
你这样说我就信了?你哄三岁小孩?
那你要我怎么说你才信?
怎么说都容易。
你是不是认定你心里想的那些事就一定是事实。好,就按你说的,我在外面有人了,是不是我承认了,你就死心了。
陈刚转过头来,盯着周宁,你承认了,承认了就行。陈刚扯着嘴角笑起来,但是别指望我会原谅你。我恶心。陈刚说完,手上的玻璃杯就在对面的墙上溅出无数的碎花散落一地。
你别逼我,周宁满眼是泪。
我怎么逼你了?你要没做什么不要脸的事,就你这脾气,我逼你你也不会承认的是吧。你想想,从结婚到现在,哪次吵架到最后不都是我的错,都是以我认错来结束每一次争吵。你忘了?陈刚脸上一直挂着一种很难看的笑。
陈刚一声不吭地抽了整整三根烟之后,凝固的空气开始化开。
我不怪你,真的。陈刚平静地说。
周宁泪眼婆娑地看着他。
你不信?我不怪你,也不恨你。真的。
那……是不是,是不是你真的信了?周宁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信不信不重要,虽然我没见过那个人。
我也没见过。周宁在心里不自禁地这样说。
但他肯定比我好,我不懂得成天口口声声地说些肉麻的话,是我的错。
不说了,我们和好吧。周宁擦着眼泪,主动过去抱住陈刚。陈刚把周宁环绕着的手掰开。温和地说,趁年轻,我们都别误了对方,再说这也是你想要的结果。我成全你。
不是这样的,事情不是你以为的那样。我要怎么解释你才相信。
陈刚反倒平静了,就像一个警察终于把案犯捉拿归案。在他看来,周宁的表现都只是一种试图逃脱罪责的强辩,但事实就是事实,再哭再闹也不能让事实化为乌有。
如果我告诉你,什么事情都没有,你不会相信了是吧?如果我说这只是一场闹剧,什么超市的男人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我这样说只是想刺激你,你信吗?那只是我编造的一个根本没有的男人,真的就是这样。
做男人最大的屈辱是什么你知道吗?陈刚咬咬牙,把一支抽了半截的烟摁灭在烟缸里,抽身撞门而去。
陈刚又一次彻夜未归。
事情就这样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周宁开始住回到母亲家。母亲问起,周宁只说陈刚到北京学习,要半年时间才回来,又说一个人在家待着害怕,不如回家陪陪两老。母亲听了不信,但又不便多问,只是时常拿一种担忧的眼神看她。
过了一段,事情像是平息下来,因为几次周宁给陈刚打电话,陈刚的语气听上去都很平常了,就像他真的待在北京,只是久不见,倒找不到话说了似的。周宁想想,事情起因在自己,陈刚再怎么赌气也合情合理。所以,一天下班后,周宁觉得应该回家去看看,至少她要给自己一次机会。
那天下午周宁没课,中午下课后就立即往家赶。快到家门口,门卫值班室的李阿姨神色诡秘地招呼她问,好久没见你,你和小陈没闹别扭吧?周宁觉得这话问得奇怪,只好说没事没事,这段时间我出差了。李阿姨说没事就好。那是我看走眼了。
周宁听了就面朝李阿姨,正色地问怎么回事。
小周,我不是个搬弄事非的人,我不知道说出来会不会给你惹麻烦,但是我真是看不下去,就你出差这段时间,我经常看见陈刚领着个女人来,两人很亲热,关系肯定不清白。
周宁当时从头到脚就像突然被人兜头泼了一盆水,湿透了心。她有点不知道是不是该继续往家的方向去。宿舍是周宁单位的,上上下下住的都是周宁单位的熟人,陈刚这样做显然横了心了。
周宁那晚一人躺在床上,从头把所有经过好好的想了一番,第二天大早便收了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叫了辆出租车,全部搬回了母亲家。
暑假时周宁陪母亲去了趟海南,看望已在海南工作十来年的妹妹一家待到快开学才赶回来。
陈刚没找周宁,周宁也没心情去过问离不离婚的事,离不离似乎都不重要了。离婚对别人来说,表明自己还有所期待,还想把这一页赶紧翻过去,但周宁不想去翻,她觉得翻过去的新的一页也没什么意思。
那是一个与平常没有分别的下午,太阳火辣辣地烤在头顶上,周宁不想再去挤公车,出了校门便叫了辆出租,坐在车上懒懒地看着窗外密匝的人群和车辆。司机是个话多的人,不停地抱怨物价如何高,抱怨老板如何苛刻他们,治安不好,跑夜车的出租时常遇到不测……她没有一点回应,司机有点讪讪的,便打开收音机听广播。周宁松了口气,继续把目光懒懒地洒在人群里,大脑里却混混沌沌的。广播里正在播出一个心理访谈节目,一个女人问节目主持,她要离婚,但是她很害怕,问主持人怎么面对这种变故。主持人的回答像计算器一样快速地就敲出了答案,不过一些陈词滥调的文艺腔:每个人的一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变故,勇敢地面对,往前走,学会放弃,学会爱你自己……你会在……周宁听得心烦,转过头继续看窗外。车行驶到大十字环行天桥刚过的那一段,在密匝的人群里,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突然从周宁的眼前一晃而过,那张面孔让周宁几乎晕眩过去,就像在暴热的阳光下的突然中暑,恍恍惚惚的,但面孔就在那里,在众多的面孔里突出地在周宁的视线里晃动。周宁紧紧地用目光抓住那张正在人群里晃动的脸,周宁再次睁大眼睛,那张一直躲在她想象里的面孔,就这样真实地在这个烈日当空的正午时分,出现在这个周宁熟悉得已经厌倦的城市里。周宁突然大呼停车,司机被吓得把车急刹在路边,周宁跳下车,奔向人群,挤在人堆里,朝着面孔的方向追赶,但她的脚步怎么都无法快速向前迈动,那张面孔很快变成后脑勺,混在大片的后脑勺里,越来越远,直至完全消失。
责任编辑 李国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