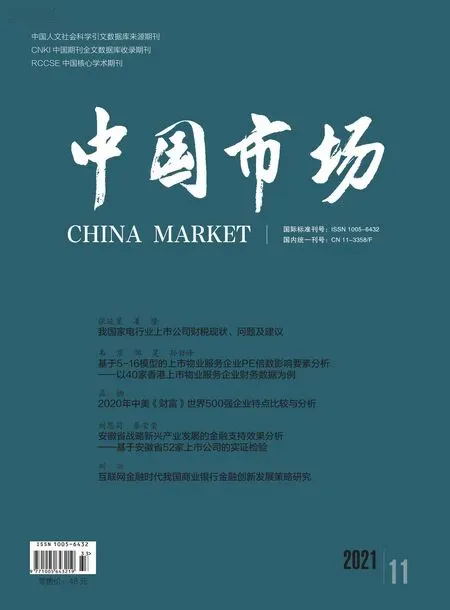论赫斯顿象征手法在描述珍妮成长历程中的运用
孔维贵 赵颖
[摘要]《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是一部美国黑人文学经典之作。佐拉·尼尔·赫斯顿在其创作过程中,为了阐释小说主题、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形象,创造性地运用了象征手法。小说中珍妮的头发、梨树和地平线、骡子等这些普通事物,都被赫斯顿赋予了重要的象征意义。文章探讨了这些象征意义在展现珍妮寻找自我身份和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佐拉·尼尔·赫斯顿;《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象征手法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3176
佐拉·尼尔·赫斯顿(1891—1960)是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称之为“一位南方的天才”,被公认为黑人女作家的先驱。赫斯顿一生坎坷,生前出版了大量作品,但一直默默无闻。晚年中风,穷困潦倒地在佛罗里达的一家福利院辞世。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文学的再次崛起,赫斯顿的作品才重见天日。她1937年出版的代表作《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已经被读者奉为美国黑人文学的经典之作。
小说以20世纪初期的美国南方社会为背景,描述了美国黑人妇女珍妮·克劳福德历经了三次婚姻,寻找自我身份和精神解放的思想启蒙之旅。珍妮的第一次婚姻是在祖母的安排之下嫁给中年男子洛根。但毫无幸福之感的珍妮随后与乔迪私奔,来到伊顿维尔镇生活。伊顿维尔镇是一个完全由黑人自治的社区,珍妮在那里感受到了集体生活的快乐。然而,身为伊顿维尔镇镇长的乔迪具有极强的男权主义思想,粉碎了她对家庭生活的憧憬,这种沉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乔迪的去世。年轻男子茶点的出现重新燃烧起珍妮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让她不顾伊顿维尔镇上居民的非议,与茶点到佛罗里达的沼泽之地生活。不幸的是,她与茶点的幸福生活由于茶点患了狂犬病而忽然中断。只身一人的珍妮重新回到伊顿维尔镇,但她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一位懵懂少女成长为一个充满自信和意志坚强的新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展现珍妮身份意识的成长,赫斯顿在这部小说中运用了包括珍妮的头发、梨树、地平线、骡子等在内的象征意象,通过象征手法表现了珍妮追求心中理想的爱情和幸福的过程,透视了珍妮成长的心路历程。
1珍妮的头发
在小说的开篇,重新回到伊顿维尔镇的珍妮走在大街上时,女人们对她的头发就指指点点,“那个四十岁的老女人,却留了小姑娘的及腰长发,摇摆在后背上,究竟要干什么?”[1]4在这些女人的眼里,珍妮披散的长发和她的年纪并不相符,有失体统。但此时的珍妮已不同于当年出走伊顿维尔时的珍妮,在历经了三次婚姻和在大沼泽地的磨难之后,她已经获得精神上的独立,找到了自我。她昭显于众人眼目之下的头发展示了她挑战世俗性别陈规的勇气,象征了她的人格独立和个性力量。
实际上,在珍妮不同人生阶段和诸多场景中,赫斯顿对珍妮的头发做了大量的细致描述。身为黑白混血儿,珍妮头发不同于黑人卷曲的头发,而具有柔顺的直发。在像伊顿维尔这样的黑人自治社区里,她的身份独特。
在珍妮的第二段婚姻中,赫斯顿描述了珍妮的一头漂亮长发,以揭示她的性感。珍妮独特的女性魅力让她成为了伊顿维尔镇上男人们的中心话题。这对于占有欲和控制欲望极强的丈夫乔迪而言,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在乔迪眼里,珍妮只是他的财富和权力的点缀品,乔迪无法容忍镇上其他男人对珍妮头发的窥探,勾起别的男人的欲望,他必须抑制这种性感和魅力,这样才能完完全全地占有她,成为他心目中所希望的“镇长夫人”。此时,珍妮的头发成为性别权力斗争的象征。为此,赫斯顿还特别使用了大量的性语言刻画珍妮的长辫子,让它具有了男性生殖器的意象,体现珍妮的头发所蕴含的雄性力量。而这种雄性力量严重挑战了乔迪的统治地位,他要压制和消除这种雄性力量。于是,他强迫珍妮用破头巾束起了头发。但珍妮并非情愿如此,她希望社区能够接受和认可她的本来身份,而不是别人强加给她的身份。珍妮选择在沉默中暂时屈从乔迪,但此时的珍妮并不是逆来顺受,失去了自己的梦想和激情,而是在为寻找自己的身份积蓄力量。乔迪刚死,珍妮首先想到的就是撕掉破头巾,打碎束缚自己头发的枷锁,放开了已被禁锢已久的秀发,重现自己的女性魅力和力量之美。但她意识到此时尽管自由了,但是如果过于放纵,社区的人们就会对她评头论足,于是又扎起了头发[2]86。直到完全操办完乔迪的葬礼之后,珍妮才烧掉了曾经束缚她的所有头巾,把头发梳理成直垂腰际的粗辫子。在经历漫长沉默之后,珍妮重新确立了自己作为一个注重自我身份的新女性形象。
2梨树和地平线
梨树和地平线是小说中两个重要的意象,梨树和地平线相互交织,象征了珍妮对大自然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中,梨树本身象征了“女性的性与生育力”。[3]47梨花的意象贯穿于整部小说,它象征了珍妮向往的两性关系,是她一生追寻的理想的爱情和婚姻。地平线象征了珍妮心中自然世界中遥不可及的神秘,一种她渴望与之交流的神秘,一种与她现实生活相反的新生活。在小说第一段,赫斯顿就提及了地平线,“船承载着每个男人的希望……船永远在地平线行驶……”。[1]1一部分男人并没有采取行动去追求梦想,只是在等待。珍妮与他们不同,而是投身去积极追求梦想。
十六岁时,情窦初开的珍妮躺在梨树下,见证了大自然的和谐完美结合,“她看到带着花粉的蜜蜂落入一朵梨花的圣所中,成千上万的花萼起身来迎接这爱的拥抱,……”。[1]15梨树和蜜蜂的激情交流,充满了性爱力量。雄性的蜜蜂虽然主动,但并不是侵犯,只是“落入”花萼;雌性的梨树也不是消极的被动等待,而是起身迎接爱的拥抱。梨树下的片刻成了珍妮的人生转折点。珍妮看到梨树和蜜蜂相互补充和平等的关系创造的美好统一体,希望自己是“一棵开花的梨树……有亲吻它的蜜蜂歌唱着世界的开始。”[1]16在其后珍妮婚姻的不同阶段,梨树反复出现,象征和映衬了她不同阶段的婚姻现实状况。
在外婆准备把珍妮许配给洛根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洛根的形象玷污了梨树……”。[1]19在与洛根结婚前几天,她一次又一次地走到梨树下思索将来的婚姻,以少女之心理解和期待自己的婚姻,不停安慰自己会爱上洛根,开启理想的婚姻生活。但婚后生活并非如此,珍妮非常失望,珍妮向外祖母哭诉,“我希望婚姻能带给我甜蜜的生活,就像坐在梨树下遐想的那样。我……”[1]31
在与乔迪的婚姻中,乔迪为她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还和她谈及“遥远的地平线”,但她不知道地平线之外还有什么,乔迪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新生活。但乔迪对她的压制使她确信自己追寻的地平线是乔迪物质主义的世界观无法给予的,乔迪“代表不了日出、花粉和鲜花盛开的树”[1]37,地平线对她来说还是遥不可及,只是一种希望。在第三次婚姻中,茶点对她的尊重和双方的平等关系让她意识到这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她心目中的梨树。“他会成为花儿的蜜蜂——属于盛开在春天的梨花的蜜蜂。”[1]128此时的珍妮找到了自我,实现了梨树下对爱情和婚姻遐想。在小说的结尾,“她如同收大渔网那样收拢自己的地平线” [1]231,珍妮完成了寻找自我的漫长旅途,到达了地平线,找到了爱情,独立和自己的声音,发现了自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3骡子
在现实生活中,骡子忍辱负重,默默地为主人辛苦劳作。在小说中,赫斯顿反复描述骡子这一意象,它象征了遭受奴役和苦难的黑人,更指代了以珍妮为代表的成千上万的黑人女性,她们处于社会最底层,遭遇了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的双重压迫,承受白人和黑人男性强加的两种重负。用珍妮外祖母南希的话说,黑女奴就是世界上的骡子,白人扔下担子命令黑男人捡起来,但他又把担子丢给了他的女人[1]19-20。
在珍妮的前两次婚姻中,她都经历和验证了黑女人是“世界上的骡子”这一说法。讲究实用的洛根视她为骡子,婚姻毫无浪漫而言,甚至还准备买一头珍妮可以驾驭的骡子,驱使她从事扶犁耕地这样的重体力活。由于不堪忍受“骡子”的命运安排,珍妮逃离了洛根,跟从乔迪私奔到了伊顿维尔镇,期望在那儿摆脱骡子般的生活。但期望再次落空,珍妮并没有过上“在走廊里自由聊天的生活”。在麦特的骡子插曲中,乔迪花钱买下并解放了受虐的骡子,镇上居民也把这一拯救骡子的善举媲美到了林肯解放黑奴的高度。乔迪的善举表面上是为了取悦珍妮,但对珍妮来说,这种爱和取悦并不是建立在两者平等基础之上,她感受到的是乔迪竭尽全力对她的控制,这次的善举无非是自负心理极强的乔迪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在骡子死后,乔迪不允许她参加镇上居民为骡子举行的葬礼,更是扼杀了她的话语权利,在精神上囚禁了珍妮。只有在乔迪死后,珍妮才真正摆脱精神的枷锁和外来力量的压制,不再是一头沉默的骡子,重获表达自己的话语权,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在这部小说中,赫斯创造性地运用象征手法,使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普通事物具有了强大的象征意义,突出了小说的主题,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成功地展现和透视了珍妮的成长历程,留给读者更广泛的空间解读这部美国黑人女性经典小说。赫斯顿对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对艾丽斯·沃克等后辈作家产生了积极影响,构成美国黑人女作家独具文化特色的创作手法。
参考文献:
[1]Hurston,Zora Neale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M].Urbar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
[2]哈佛蓝星名著导读: 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M].孔维贵,译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3
[3]HowardLilllie P,edAlice Walker and Zora Neale Hurston: The Common Bond[M].Westport: Greenwood,1993
——八师天业集团工会主席李彤的结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