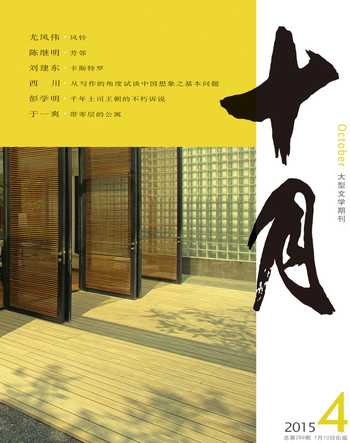钢丝上的舞者
王干
认识于一爽的时候,还不知道她会写小说。只知道她在一家网站当编辑。后来在《人民文学》上看到于一爽的小说,不敢相信是她写的。问了施战军,果然是。原来光知道她是做网站的,是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没想到还写一手好小说,让人刮目相看。于一爽说话特别逗,让我时时想起王朔来。王朔现在封山了,小爽出山了。喜欢于一爽的小说是因为她语感非常好,语感是个不容易修炼的才华。好多小说家硬是练不出语感来,语感背后隐藏的是情绪。情绪是不好操练和模仿的,所以好的小说家是有着一般人没有的独特情绪。北京人的语感好,是他们的情绪里有一种反讽的情绪。而反讽,是现代小说最不可缺少的情绪。
于一爽很容易让人想起张辛欣、刘索拉那些曾经在文坛桀骜不驯而又才情傲人的女作家。她们都不是正规学文学的,都是学艺术出身,张辛欣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刘索拉则是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于一爽学的是电影,她们身上的艺术气质带到小说里,常常会开辟一番新的天地。小说家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艺术家型的小说家,一种是小说家型的小说家。小说家型的小说家常常是熟稔小说的历史、套路、程式、技巧,因而小说也中规中矩,表现在形态上,常常是创作生命长,能够写长篇。而艺术家型的小说家,常常出手不凡,一鸣惊人,不按常规出牌,才华在瞬间爆发,流星一样耀眼,但创作生命完成得快,也少长篇小说。
当然,于一爽与王朔更为亲近。这不仅是时间上的近,而且是精神内核的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出现了精神信仰的危机,工业生产、物质水平的高速发展,各种矛盾不断激化,人们对西方传统文化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产生了怀疑。“怀疑的精灵已经降临”(司汤达)。无独有偶,本土20世纪80年代后,王朔等人开始了反抗传统话语形式的小说实践,从而也把“怀疑的精灵”传播到了读者的心里,而先锋文学则在中国延续二战后的西方小说革命的命脉,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日益加深,与此同时是小叙事的崛起,小叙事是90年代以后中国小说一项重要成果。这一崛起像是多方力量的合谋。提出小说发生学理论的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契说:“小说一定与一定历史的文化结构形式之间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它以独特的形式力量来重建一个史诗般的世界。”同构就是小说与现实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
和王朔不一样的是,于一爽的攻击目标不是那些宏大的叙事,不仅因为那些宏大的坚硬的玩意儿已经被王朔折腾得百孔千疮,而是作为王朔孩子辈的80后感受的压力已经不是外在,而是内在的存在感。他们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于一爽小说中的年轻人处在怀疑主义盛行的新常态下,没有信仰,怀疑爱情但相信情感,物质并不匮乏但生活中缺少存在感,他们很难参与到推动社会发展中去因而没有都市主人翁感,他们需要“感觉到我的存在”(汪峰),一首叫《北京,北京》的流行歌曲居然有这样的歌词。这无疑是一种时代性的话题,“流行”已经暴露了一切,一代人的生命觉醒程度以方阵的形式达到了新的哲学高度,他们在找“我的存在”。“我的存在”其实不是可以向社会讨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纠结,自我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于一爽小说对女性主义的解构,女性主义曾经是女作家寻找存在感的利器,但过多的女性扩张和对男权的刻意攻击,反而让女性主义有更多的男权主义色彩。在女性主义作家那里,女性往往是爱情的受害方,或者牺牲品。而在于一爽那里,男女平等是骨子里的平等,不仅爱情,性爱也是如此。这和比较的另一个80后女作家周李立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把她们称为中性主义叙述。
食与色,是于一爽小说经常采用的噱头,这当然也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生活。食色是本能,二者分不开,但每一代人的食色,意义完全不一样。见面就问“吃了吗?”也是一个时代的显著特点,描绘饥荒的苦难叙事里面有公共记忆,而阮籍喝酒那是名士风度,他喝酒后写文章。鲁迅曾写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批评那些学名士皮毛的人“许多人只会无端地空谈和饮酒”。可是,一个时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空谈和饮酒?空谈和饮酒为什么让那么多人觉得欣悦,让读者觉得有趣、有味?这就不只是空谈与饮酒的问题了,有人在空谈与饮酒中看到遗憾,就有人在空谈与酒中灌注对激情与活力的渴望,对存在的迷惘。
新作《三人食》中的“我”、杨天、王凡,《带零层的公寓》中的严田、刘海东、舞蹈演员、毛小静、齐玲玲都在找存在感。喝酒、做爱,他们通过这些参与性很强的活动,把自己和另一个生命联系起来,从而确定“我在”。《小马的左手》通过现实来回忆历史的结构,但你能感到生活中的每一点能触及小马的痛,小马麻木的外表更能让人想起当年那场灾难的剧痛。痛定思痛,但创伤难以愈合,痛变成了小马家的空气,无处可见,又处处可触。
于一爽属于那种艺术家型的风格,个性凛然,才情突兀,语感奇妙,《每个混蛋都很悲伤》等小说把同时代的作家吓了一跳,而小说集《一切坚硬的都烟消云散》居然再版,可见她的小说风格征服了读者。于一爽天性里的对人性、对情感的敏锐把握和奇特表达,几乎是流出来的,但我隐隐担心这种自然流淌会曲终人散,因为艺术家型的小说拼的是才情,而才情不是无限可以挥霍的,没有其他支撑、其他资源辅助的才情是脆弱的。于一爽得天独厚,有着张辛欣、刘索拉、徐星一拨人的语言气势,但又是当下年轻人的情绪特征。再一个或许是学电影的缘故,她的小说的场景经常跳动,时不时好像有音乐穿插进来似的。这就让她的小说现代质地强烈,叙事是带着旋律和镜头摇曳的。北京青年作家往往一鸣惊人,但好像任性而不韧性,常常流光耀眼,转瞬又淡忘于江湖。张辛欣、刘索拉、徐星等当年的娇子们远离文学,留下一声叹息。
于一爽会不会呢?读了她最近的作品,担心有些多余。她不再是当年那种正面强攻的愤青做派,而喜欢在艺术上经营,尤其喜欢从侧面去展现时代和人的印记。这种从侧面落笔,从日常生活的场景去呈现内心的风暴和历史的记忆,是现代小说攻克的难题。理查德·耶茨、理查德福特、门罗、卡佛等小说家对此都有深刻的体验,于一爽委身于这种技术型的行列,说明她不想做一颗耀眼的流星,她想写得长久些,不仅是为了写长篇。另一方面,于一爽的叙事技艺不仅融汇西方,也是对一些非主流作家成功进行了移栽。她自己在创作谈中就说过受到南京作家韩东、朱文的影响,她作品的京腔下有南方文体的特征,轻逸、轻灵,思絮如织,江南烟雾一般。京腔和北京,都不再是于一爽小说的单独符码。北京——“北上广深”一线现代大都市之一,所以,南京和南方的文体,也不是于一爽这文体的唯一特征,她是承接南方作家的技艺,当然,叙事方式中也会带着看问题的方式。不可否认的是,于一爽小说实现了南北交融。她的叙事作品,是一种“北腔南调”的聚合物,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话语平台。如果不想到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几乎无法想象一个年轻的80后作家能完成这样的整合。
于一爽的写作采取的是一种近乎走钢丝的方式,优美,高蹈,但风险系数比一般作家也要大得多,因为她没有安全带,随时可能落地。另一个风险在于,才情与节制的关系如何把握,也是两难。
责任编辑 宗永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