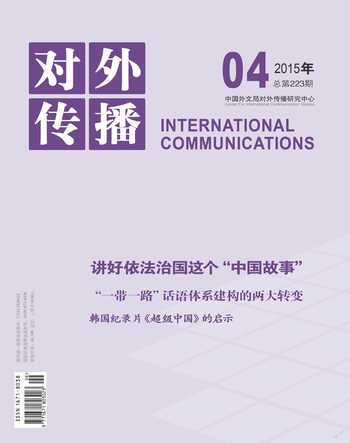国际传播研究须把握国际权力格局
吴飞
国际传播实质上是符号权力之争,而符号权力是一种柔性权力,在国际权力竞争中,有着与硬权力(主要指军事、经济方面的实力)同样重要的作用,但软权力又往往需要与硬权力匹配才能充分发挥效用。中国虽然着力推进软实力建设,无论是国际宣传片,还是参加国际事务,承担大国责任方面都在用力经营,但效果并不理想,问题的关节点何在?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如何在国际话语场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本文认为,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把握国际权力格局。
一、国际权力分析要把握“综合权力”
在当下,在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取代美国地位的对象出现的时代,美国独领全球是一个既成的事实,而且估计未来20年左右还看不出新的领导者。也就意味着,我们当下要争论的问题不是美国是否一霸独领天下,要回答的问题是美国称霸是为了什么?是否有利于全球人民发展需求?是否有得于全球局势的稳定?需要过问的是美国是计划在利益分享的基础上重构全球体系,还是仅止于利用现有独大的力量谋求自身利益与安全?
冷战40年,虽然没有爆发恐怖的核战争,甚至也没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代价同样是巨大的。有学者认为,冷战使美国付出了8万亿美元的国防支出,10万人失去生命;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损害了许多人的事业和生活;而且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50年最为严重的经济萧条。发展中世界到处发生血腥的冲突,在这里的美国人和俄国人——更多情况下是他们各自的代理——相互残杀,在朝鲜、越南、中东、中美洲和阿富汗及其他地方的战场上,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丧命。①等到冷战结束,美国人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9·11恐怖袭击又发生了。人们没有等到世界大同的和平颂歌上演,又投入到一场反恐怖的战争之中。西方民主主义者惊奇地注视着各种各样的种族、宗教和国家冲突的爆发,他们原以为这些只是属于一个过去了的年代。“‘世界新秩序的预言、普遍价值的胜利、‘后传统的同一性的普遍化都没有实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诸多排他主义的爆发以及不断增长的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挑战”②。
世界为什么总没有太平的时候呢?西方社会推行的普遍价值为何遇到阻击呢?或者我们换个思路追问一下,为什么人类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呢?无数学人皓首穷经,提出过不同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者提醒我们经济的不平等,阶级之间的权力和利益的斗争是战争之源;而约翰·霍布森更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又导致战争;约瑟夫·熊彼得则认为国际冲突之根源在于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和个别领导人“原始的”不安全感。对于这些不同答案,以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学派间的争鸣最为激烈。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权力是国家自发的追求,人类无止境地增强军事实力的本性引发了普遍性的“安全困境”。1979年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标志着“新现实主义”学派对“传统现实主义”学派的挑战。在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假设下,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构成体系的原则,主张国际体系结构是由同类的重复彼此行为的单元构成,并由单元之间的权力分配来决定的。这一理论强调体系结构和单位结构,指出“只有结构的变革才能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因而也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不同,“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手段。并且,“权力”不仅仅指的是军事实力,而应是国家的“综合实力”。这两种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实际的国家战略中,体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尊崇“国家的自我保护最终只能通过武力来实现”的信条,以追求绝对的权力保障自身安全;而防御性现实主义则以建立安全同盟的方式營造相对安全的环境。
二、霸权之后,会进入和平的时代吗?
古典自由主义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国家间的交往越广泛,和平的机会就越大。它认为,经济依赖使战争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各国都逐渐在生活用品上彼此依赖,因而无法承受战争的代价。它还提出,文化交流导致国家之间对彼此的关切更为了解,进而降低误解的可能性。简言之,古典自由主义假设,“人与人”的接触使得国家间更好地相互“了解”成为可能,因此,它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也就降低了。对此,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评价说:“这些结论让人很乐于相信,但显然不能为历史事实所证实。”③肯尼思·华尔兹更是发现,“最激烈的内战和最血腥的国际战争都是发生在事务密切交织、人口高度相似的地区”④。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冲突》和其与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又引发了“新自由主义”学派与“新现实主义”学派之间的争论。“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国际关系理论应超越民族国家,注重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注重经济、环境和相互依存。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国际关系领域研究“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更加重视其他角色,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国际制度”作为国际体系最主要的特征,认为其能够保证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合作,降低合作的风险。因此“新自由主义”也被称为“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将权力、安全和生存放在首位的思考方式不同,“新自由主义”将国家的经济利益放在与国家安全同样重要的地位,并对现实主义的“自助”主张提出质疑。鉴于当时世界局势的全面缓和,“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合作将取代军事威胁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批评“新现实主义”过分强调“无政府状态”而忽视“相互依存”的现实。而“新现实主义”则坚称国际合作更加依赖于国家权力,认为实力是国家安全和独立的基础,“新自由主义”夸大了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制度分析与结构分析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与“新现实主义”学派的根本区别: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间相互作用的体系过程;而新现实主义关注的重点则是体系角色间的权力分配。
进入九十年代,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理论,加入了论战。“建构主义”理论建立在社会理论和批判理论基础上,强调观念与意图对行为选择的意义。它认为,对国际体系结构最终起作用的不是“权力”“制度”等物质本身,而是国际共有观念的分配。“建构主义”认为人、组织或国家的行为都是社会建构的,国际体系的进程是国家主动构建国际体系观念结构的实践活动,机构、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此情况下,现实主义强调的“均势”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均衡带来的“威胁感”和均衡所产生的“安全感”,“安全困境”取决于国家自身对于“安全“与”国家利益”的认知。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社会认同反映了利益,而利益反过来推动国家的行动。文化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动机,而且影响国家的认同,国家间正是存在许多误解才使得国际关系复杂化。罗伯特?杰维斯在他的代表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中指出,政治决策者对国际信息的错误解读和对情势的误判将导致国家间的战争。而导致误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差异。马克思主义者提醒我们经济的不平等,阶级之间的权力和利益斗争是战争之源;而约翰·霍布森更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导致了帝国主义的产生又导致战争;约瑟夫·熊彼得则认为国际冲突之根源在于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和个别领导人“原始的”不安全感。所有这些解释,似乎都对,又似乎太过于简单。
“9·11”之后,布什政府越来越将使用武力与基督教的“正义之战”联系在一起,于是在2002年的美国社会中,越是常去教堂做礼拜的美国人,就越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表示支持。美国最新的民调机构“美国对外政策信心指数机构”2005年5月的调查显示:83%的受访者给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打了“A”或“B”的高分,58%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美国赢得伊拉克战争的决心,并对美国能够给予“专制国家”人民自由充满信心。⑤曾任新加坡外交部长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教授认为,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变成了“一个被意识形态所驾驭的实体,民主的氛围——这一不容置疑的道德高尚的想法——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东征:他们坚持将民主输出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不管这个国家正处于哪个政治发展阶段。灾难在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相继发生”⑥。
三、不同的文明之间必然会有战争?
塞缪尔·亨廷顿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去发掘事实之真相。1996年出版了之后影响巨大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的落幕,象征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文明冲突却已经拉开序幕。亨廷顿强调冷战后世界政治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不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文化的区别和差异将成为引发冲突的新的根源。他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⑦。这便意味着“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的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⑧他将世界主要文明分为如下七到八个不同的类型,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亨廷顿同意普鲁士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一个观点:“正是战争使人们结成国家。”因为,他发现战争或外部威胁的确使美国国民更加团结。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失去了与自己同等地位的竞争者,敌人没有了就需要再找一个。那么,谁最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亨廷顿认为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他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与美国的基督教和盎格鲁-新教文化在文化上的差异加重了伊斯兰构成敌人的资格。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结束了美国对敌人的搜寻。纽约和华盛顿受到的袭击,以及随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还有比较笼统的‘反恐战争,使伊斯兰好战分子成为美国21世紀的第一个敌人。”⑨
敌人既然已经找到了,作为一家独大的美国,似乎又找到了一个世界格局的平衡点,在“9·11”之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但这场战争似乎不同以往,这是一场看不到结局的战争,虽然美国人认定的头号敌人萨达姆·侯赛因和本·拉登先后被处决和击毙,但战争的硝烟还弥漫全球。
不过,美国人又将目光投向亚洲。亚洲四小龙、日本、中国等亚太地区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使得冷战结束以来亚太板块凸显其在全球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亚太地区因而也成为了美国实现其国家战略的“利益攸关”区域。出于对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不保的担心,美国开始从伊拉克、阿富汗抽身,调整战略重心东移,开始“重返亚洲”的谋划。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10月的演说中强调,未来十年美国外交战略的最主要使命之一是将外交、经济、战略等方面大幅度增加的投入“锁定于亚太地区”,打造“跨太平洋体系”,全方位“重返亚太”。⑩美国寻求在亚太重新发挥领导作用首先插足的是经济领域。当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重要特征是充分整合防务、外交和发展资源,大力融合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将军事活动作为美国对亚太“展开全面接触”的关键基础,将加大“发展援助”,提升发展中国家“伙伴”能力作为解决诸多外交难题的综合性战略。11同时,美国强化与亚太盟国关系,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美菲军队访问协定》的签订以及规模逐年扩大的联合军事演习等行动,无不体现出了奥巴马政府的“新亚太战略”对亚太地区事务的重视。美国“重塑亚太”的战略包括:在经济上利用自由贸易、技术输出管制和金融资本流动加紧了参与、控制和渗透;军事上加强了亚太的前沿部署,并通过实施新的联盟战略,对该地区崛起中的大国实行秘而不宣的围堵和遏制,展开了自越战结束以来最有企图的战略出击态势。此外,美国还热衷于以亚太地区的“人权”和“民主”问题为借口,将“软”与“硬”两手工具密切结合,企图巩固和发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12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文章所指出:“美国‘重返亚洲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在经济和外交战线,也在军事战线。”13“重返亚洲”战略出台后,美国一方面举行多场军事演习,充分展示自己的硬实力,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在运用所谓的“巧实力”,或挑拨离间,或煽风点火,或纵容他国制造事端,或左右逢源,两边下注。他又在寻找下一个敌人么?
亨廷顿说:“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外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14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仍然有一定的启发性。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因为美国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发动这次战争的理由——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反,他们被指责发动战争不过是看中了伊拉克遍地流淌着的石油。托马斯·弗里德曼哀叹道:
“我们面临失去比伊拉克战争更重要的东西。我们面临失去美国作为世界道德权威的鼓舞人心的工具的地位。我一生中还从未见过美国及其总统像今天这样在全世界遭人厌弃……反恐战争是一场思想战争,要想拥有获得的机会,就必须维护我们思想的权威性……我们仅靠自己无法赢得(与“9·11”袭击者的)思想战争。……但当你变得像无人愿意靠近的放射性物质那么危险时,则很难找到伙伴。”15
但布热津斯基仍然认为,美国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当今全球稳定的根本保证。当外界质疑美国的作用,他在世界地图上画了一个动荡之地集中的“冲突圆地区”——画两条交叉的线,一条从西到东,从西奈半岛到印度再到中国,另一条从北到南,从俄罗斯南部边疆向下直到印度洋。根据这两条线画一个圆,里面大约会有6亿人,到处都是种族、宗教和社会矛盾。他问道:“如果美国国会要求迅速从国外的3个主要驻军地区——欧洲、远东和波斯湾——撤回美国的军事力量,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16
四、小结
总之,国际交往需要充分展示自己的硬实力,但世界和平却无法通过美国那种四处展示自己的肌肉而获得。符号性权力的重要作用往往又要与硬权力有机结合时方能更有效。中国的国际传播战略,必须走一条综合权力展示之路,一方面大力推进国家的硬权力,另一方面又要在西方意义下的“普世价值”之上,通过充分挖掘中国文明和东方文明追求和平、讲仁义、讲究中庸与平衡之道,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提供新的普世价值坐标。这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意义之所在,也是中国的责任之所在。
「注释」
①[美]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牛可、翟韬、张静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页。
②[美]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③[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296页。
④Waltz,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p.138.
⑤Daniel Tankelovich, Poll Positions, What Americans Really Think About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 Vol.84, No. 5( Sep/Oct,2005), pp.2-16.
⑥[新加坡]馬凯硕:《新亚洲半球——势不可当的全球权力东移》,刘春波、丁兆国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⑦[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⑧[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⑨[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⑩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 October 20,2011,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article/2011/10/2011101116 1233su0.8861287.html#axzzlabozaFZs.
11赵明昊:《“重返”还是“重构”:试析当前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当代世界》2010年第12期。
12赵楚:《软与硬:美国面向21世纪的亚太国家战略——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战略的一种新解读》,《国际展望》2000年第21期。
13转引自李长久:《世界经济重心回归亚洲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经济》2011年第1期。
1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国际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15“Restoring Our Honor”, New York Times, May 6, 2004.
16张欢、王大骐:《布热津斯基:国际大棋局的影子棋手》,原载《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