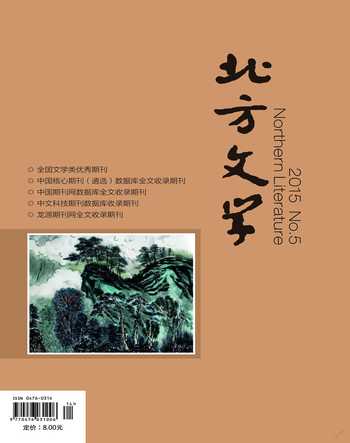情与法的复调叙事
摘 要:文章以法律文化作为切入视角,结合《唐律疏议》的具体内容,从人物形象、悲剧根源和法理内涵三个方面,重新解读了唐代传奇小说《霍小玉传》,认为李益具有自觉的法律意识但懦弱、逃避,他的行为受到性格因素和法律意识的双重影响,霍小玉则是一位积极追求爱情、敢于反抗自身不平等的法律地位的女性形象,二人的悲剧是在李益的性格因素和唐代法律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关键词:霍小玉;李益;悲剧;唐律
中国古代文言小说至唐代而发展成熟,诚如鲁迅所言:“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①唐代传奇小说继承并发展了秦汉史传文学传统和六朝志怪小说的创作手法,“作者云蒸,郁术文苑”②,堪为有唐一代文学之翘楚。其中,蒋防的《霍小玉传》是唐代婚恋传奇的代表作品,备受后世作家、学者的推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据该篇故事写成《紫钗记》,胡应麟则称赞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故传诵弗衰”③。
近年来,学术界对《霍小玉传》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着意于考证小说中人物、事件的真实性,进而考察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创作时间。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首推卞孝萱前辈,据他考证,《霍小玉传》创作于唐穆宗长庆初年,是蒋防为了攻击政敌李益而作④,目前这一观点已被学界普遍接受。二是致力于阐释作品内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霍小玉传》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理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悲剧意蕴。当前,学者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以程毅中先生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李益的好色、自私和负心造成了霍小玉的悲剧⑤;而关四平、刘存斌等学者则认为,李益“负约”并非“负心”,是唐代门阀制度导致了李、霍二人的爱情悲剧⑥。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尝试从新的角度对《霍小玉传》进行阐释,例如,刘秋娟先生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为依据,认为李益患有精神疾病,从而对他抛弃霍小玉、猜忌妻妾的行为给出了合理的解释⑦;虎维尧先生则运用叙事学原理,指出李、霍爱情经历了四个阶段,并分析了唐代中后期文人士子的婚恋观⑧。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关于《霍小玉传》的研究可谓思路多样、成果众多,但也存在不少争议性的问题有待解决,且其跨学科研究初兴、成果尚少。因此,笔者认为,唐代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仍然存在着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广阔的研究空间。
本文尝试从唐代法律文化的角度重新解读《霍小玉传》的人物形象、悲剧根源和法理内涵,以期对当下学界研究中的疑点和热点问题提出一些可供商榷的拙见。
一、情对法的多方渗透:礼法融合的唐代法律
在运用法律文化视角解读小说文本之前,有必要先对唐代的立法思想和法制情况做一概述。
唐代立法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继承了我国自西汉中期以来法律儒家化的传统。两汉以《春秋》决狱,即将儒家经义作为司法断案的依据,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礼法融合的基础。此后,引经决狱、以经注律的趋势不断发展,儒家思想日益渗透到法律中来。至唐代,统治者立法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⑨,形成了德主刑辅、礼法融合的法律文化。并创制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本的典范——《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颁行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又名《永徽律疏》,共12篇⑩,502条,每条皆由律文和疏议两部分组成,疏议是对律文所做的法律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唐律疏议》为核心,唐代法律的形式分为律、令、格、式四种,而律居于中心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违反令、式、格者,都要依律制裁。《永徽律疏》在《武德律》和《贞观律》的基础上修定而成,是对唐代前期立法经验的总结。“唐高宗永徽以后,唐律已有定本,基本不再改动”,玄宗开元年间曾刊定形成《开元律》,使唐律更为完备。“其后经唐末、五代、两宋,直至元朝,最终定名为《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保存完整的古代成文法典,标志着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法制的成熟与完备,它集中体现了唐代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准则,是对儒家忠孝礼义观念的法典化,对唐以后历代法律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人纪昀称赞曰:
唐律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故宋世多采用之,元时断狱皆每引为据。明洪武初命儒臣同刑官进讲唐律,后命刘惟谦等详定明律,其篇目一准于唐。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政书类》)
《唐律疏议》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其影响远及同时期的东亚和东南亚诸国,如日本制定的《大宝律令》即大体上采用唐律,朝鲜高丽王朝制定的《高丽律》亦是效仿唐律而定。可见,唐律在东方世界的地位,几乎可以与罗马法在西方世界的地位相媲美。
近年来,学界对唐代法律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部门法的角度出发,选取唐代刑事、民事、行政等某一领域的法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探討其具体规定和法律特征;另一方面,以唐代法律制度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另一朝代的法律相对照,进行法制史的对比研究。目前,学者们对唐代诗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法律问题关注较少,若能对其深入开掘,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文学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也许能对唐代法律研究的推进有所助益,笔者即尝试在这一方向上做出努力。
二、法与情的两难选择:人物形象的再认识
蒋防在《霍小玉传》中描写到的人物较多,其中,尤以李益和霍小玉的形象最为精彩动人。如何认识李、霍二人的形象,关系到对作品悲剧主题的把握,是当下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亦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所在。
(一)李益形象分析
李益究竟是好色的负心汉,还是软弱的负约者?本文以法律文化的视角观之,相对认同后一观点,认为李益具有自觉的法律意识,却懦弱、逃避、多疑,他的行为受到其性格因素和法律意识的双重影响。
首先,李益知晓唐代法律,他自身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小说中曾两次写到李益参加吏部的“拔萃”考试,
试看:
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其后年春,生以书判拔萃登科。
(蒋防《霍小玉传》)
所谓“拔萃”,《新唐书·选举志》载:“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试判”即拟写判词,因而,考生必然通晓唐代法律的相关规定。由此可见,经由书判拔萃而授官的李益,对唐代法律规范定然相当精通。李益学习过法律知识,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对法律的熟知促使他形成了自觉的法律意识。
其次,李益自觉的法律意识对他的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李益的言行中发觉,尤其是当他得知母亲已为自己定有婚约时,他的行为充分展现出了其性格因素背后的法律认知,文中写道:
未至家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成。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
(蒋防《霍小玉传》)
面对母亲为自己定立婚约的事实,李益选择了顺从母意,他并没有把自己与霍小玉相爱的事实告知母亲。李益这么做,固然与他懦弱的性格有关,但其深层的动因却在于他头脑中的法律意识。根据唐代法律的规定,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具有决定权,《唐律疏议》云:
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疏】议曰:“卑幼”,谓子、孙、弟、侄等。“在外”,谓公私行诣之处。因自娶妻,其尊长后为定婚,若卑幼所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所定。违者,杖一百。“尊长”,谓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姑、兄姊。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
由此观之,李益的母亲作为尊长,享有为儿子主婚的法定权利,而李益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则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制,在定婚这一民事活动中,当事人李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他的母亲则享有法定的代理权。那么,李益与霍小玉相爱且共同居住两年的事实,是否可以认定为“卑幼在外自娶妻”的情形呢?这须得考察李、霍二人的情况是否符合唐律对婚姻成立之法定要件的规定。根据唐代法律的相关规定,婚姻成立的首要条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次还须订立“婚约”、具备“六礼”,达到法定婚龄等,试看:
为婚之法,必有行媒。
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议。
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
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诏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
“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戴炎辉《唐律通论》)
据此,反观李益和霍小玉的爱情生活,“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二人均已达到法定婚龄。他们的相识经由媒人鲍十一娘介绍,有“媒妁之言”,但无“父母之命”,李益的母亲并未知晓二人之事。李益曾写下盟约,但文中并未提到他给小玉母女送过娉财,“有私约”而未“纳娉财”,“六礼”亦不具备。因此,李益与霍小玉的爱情生活至多算作事实婚姻,并不被唐代法律所认可。况且,李益“门族清华”,而小玉“出身贱戍”,依据唐律的规定:
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合宜配合。
即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妾者,准盗论;知情娶者,与同罪。各还正之。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
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同,禁止通婚。李益既然通晓唐律,对此自然明白。所以,李益与霍小玉应当被认定为“卑幼自娶妻,未成者,从尊长”的情形。因此,在得知母亲与卢家“言约已成”时,李益深知母亲享有法定的主婚权,若违抗母意,他必将遭到“杖一百”的惩罚,且他与霍小玉“良贱既殊”,法律不允许他们走进婚姻的殿堂。然而,唐律在赋予父母为子女主婚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其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疏】议曰:“嫁娶违律”,谓于此篇内不许为婚,祖父母、父母主婚者,为奉尊者教令,故独坐主婚,嫁娶者无罪。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
《礼记》曰:“孝子之养亲也,乐其心,不违其志。”《唐律疏议·名例》亦规定:“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受到儒家教育多年、又熟知法律规定的李益,不可能要求母亲同意自己与霍小玉“嫁娶违律”的婚事,此时,李益自觉的法律意识告诉他应当“从尊长”,而“生逡巡不敢辞让”就是这种法律意识表现于外的行为方式。因此,李益选择了压抑自己的感情,顺从母亲的意愿。
其三,李益的行为方式还受到其性格特征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李益追求爱情,在情与法的矛盾爆发之前,他对小玉的感情是真诚的,他中宵之夜的言行和书写盟约的行为皆可以证明这一点:
生闻之,不胜感叹。乃引臂替枕,徐谓玉曰:“平生志愿,今日获从,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发此言!请以素缣,著之盟约。”……生素多才思,援笔成章,引论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染毕,命藏于宝匣之内。自而婉恋相得,若翡翠之在云路也。如此二岁,日夜相从。
(蒋防《霍小玉传》)
不论是“引臂替枕”的动作,还是称小玉为“夫人”、主动写下誓约的行为,都表现出李益对霍小玉是真心爱慕,否则,不可能两年如一日般地相恋相谐、日夜相从。当听到小玉的“八年短愿”时,李益的表现再次证明他对小玉并非虚情假意:
生且愧且惑,不觉涕流。因谓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尤恐未惬素志,岂敢辄有二三。固请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
(蒋防《霍小玉传》)
若李益只是好色之徒,在听到霍小玉主动提出“八年短愿”时,他应当感到轻松愉悦,不可能愧惑流涕。那么,李益所惑何事,又因何而愧呢?原因就在于他已有的法律认知,李益清楚地知道现实法律不会允许他与小玉缔结婚姻关系,霍小玉提出“八年短愿”是不愿让他为难,面对如此善解人意的小玉,他深受感动却也心怀愧疚,他为自己不能给小玉妻子的名分而惭愧,因而“不觉涕流”。但此时的情境只有李益和霍小玉二人,不存在迫切的現实压力,被真情所打动的李益依然渴望追求爱情,所以他答应小玉必当奉迎,并安排了行程。
另一方面,李益的性格具有懦弱的一面,面对情与法的现实矛盾,他妥协、逃避,幻想通过不作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当李益得知“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成”的消息时,从前停留在意识层面的爱情与法律的冲突就变为了现实,此时,他性格中懦弱、妥协、逃避的一面开始显现。如前文所述,李益固有的法律认知使他在理智上清楚不该违抗母命,而母亲又“素严毅”,这就在无形中给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境下,李益更加不敢向母亲说明他和霍小玉之事,“逡巡不敢辞让”表现出他懦弱、妥协的性格特点。此后,李益为娉财奔波而“辜负盟约”,面对爱情誓言最终破灭的现实,他没有选择及时写信向霍小玉解释,而是“欲断其望”、封锁消息,并始终逃避与小玉见面,直接造成了霍小玉相思成疾、命归黄泉的悲惨结局。李益的这些行为反映出,他面对矛盾和困难,不是积极解决,而是消极逃避,借用法律术语来说,就是消极的不作为,即他幻想通过消极的不作为方式来逃避情与法的两难选择。
同时,李益的性格还有多疑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中。霍小玉去世后,李益受到她的诅咒,家室不宁,他日益对妻妾“猜忌万端”,甚至“暴加捶楚”、“因而杀之”。文中写道:
生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生当时愤怒叫吼,声如豺虎,引琴撞击其妻,诘令实告。……而后,往往暴加捶楚,倍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暂同枕席,便加妒忌,或有因而杀之者。……出则以浴斛覆营于床,周迴封署,归必详视,然后乃开。……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
对于这部分描写,卞孝萱先生认为其意在影射现实,《旧唐书·李益传》记载“(李益)有疾病而多猜忌”,这是蒋防对政敌李益的丑化。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汤显祖在改写《紫钗记》时,便删去了这部分内容。此处,笔者认为,这些文字表现出李益多疑的性格特征,在这一性格因素的主导下,他时常对妻妾暴力相加,对此,唐律规定:
夫者,妻之天也。
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
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若有心乖唱和,意在分离,背夫擅行,怀有他志,妻妾合徒二年。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
妻殴夫,徒一年,重伤者,加凡人三等;夫殴妻,未伤者,无罪,伤者,减凡人二等。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斗讼》)
“夫为妻纲”的唐代法律对丈夫殴打、拘禁妻妾的行为没有规定严格的惩罚措施,且丈夫有权单方面“出妻”,夫妻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李益的施暴行为不能受到到法律的有效规制,促使他有恃无恐、疑心日重,最终造成了卢氏、营十一娘等人的悲剧。
(二)霍小玉形象分析
在文学史上,霍小玉是一位善良、痴情、勇于为爱情奉献的女性形象。目前,学界针对这一人物的讨论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小玉身份的界定,二是如何理解她死后“诅咒应验”的问题。本文对霍小玉形象的分析即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
先来谈谈霍小玉的身份问题。主流观点认为她是歌妓,是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人物;但也有学者不认同此说,如周承铭先生认为霍小玉的身份是城市贵族。对于小玉的身份,小说中曾两度提及,一次是出自鲍十一娘的转述,另一次则是出自小玉自己之口。分别来看这两处描写:
鲍具说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爱之。母曰净持。净持,即王之宠婢也。王之初薨,诸弟兄以其出自贱庶,不甚收录。因分与资财,遣居于外,易姓为郑氏,人亦不知其王女也。”……玉忽涕流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
(蒋防《霍小玉传》)
文中指出,小玉的父亲是皇亲霍王,母亲是霍王宠爱的奴婢净持。唐代法律将作为权利主体的人分为“良”、“贱”两个等级,他们享有不同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良人泛指普通百姓;贱民又有“官贱”和“私贱”之分,官贱民隶属于官府,包括:官奴婢、官户、杂户、工乐户、太常音人等,私贱民隶属于私人,包括:私奴婢、部曲、客女等。唐律规定:
(良人与贱民)其所生男女,依《户令》:“不知情者,从良;知情者,从贱。”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
由此可知,霍小玉母亲的身份属于贱民,是隶属于霍王家的私奴婢,霍王对她的身份应当是知晓的,因此,霍小玉的身份应当依法“从贱”,亦为婢女。
余宗其先生指出,“典型性格取决于人物自身的法律地位”。霍小玉作为奴婢贱民,其法律地位低下,唐律曰:
奴婢贱人,律比畜产。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贼盗》)
诸买卖奴婢、牛、马、驼、骡、驴等,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
([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
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
在将奴婢视为牛马资财的唐代社会中,霍小玉身份卑微,不仅其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还可能受人欺压和歧视。她虽是霍王的女儿,但父亲去世后,家人嫌弃她“出自贱庶”,将其母女二人赶出家门,并不许从父姓,她只能改姓别居,沦落为倡。然而,小玉对自己的法律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突出反映在她中宵之夜对李益说的话和她后来的“八年短愿”之中,试看:
玉忽涕流观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至。”……玉谓生曰:“以君才地名声,人多景慕,愿结婚媾,固亦众矣。况堂有严亲,室无冢妇,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约之言,徒虚语耳。然妾有短愿,欲辄指陈。永委君心,复能听否?”生惊怪曰:“有何罪过,忽发此辞?试说所言,必当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室之秋,尤有八岁。一生欢爱,愿畢此期。然后妙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夕之愿,于此足矣。”
(蒋防《霍小玉传》)
霍小玉自知是婢女出身,与“门族清华”的李益“非匹”,故在“极欢之际”而悲伤落泪。两年后,李益登科做官,小玉更加理智地预感到自己不可能成为李益的妻子,为免对方为难,遂提出了“八年短愿”,只求爱情,不奢谈婚姻。面对情与法的两难决择,霍小玉善解人意、甘于奉献,她在选择了爱情的同时,也成全了礼法,却牺牲了婚姻。“八年短愿”是霍小玉对不平等的法律制度作出的最大让步,也是她爱情追求的至高境界。在法律与爱情的矛盾面前,相比于李益的妥协、逃避,霍小玉坚定、执着、勇敢的爱情追求显得尤为可贵,她是唐代文学史上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之一。
关于如何认识小玉死后“诅咒应验”的问题,学界主要存在两种看法:一是将其视作霍小玉对李益的报复,带有因果报应的色彩;二是认为这部分情节损害了霍小玉形象的审美意蕴,属于作者的创作意图不适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情形。笔者认为,小说中“诅咒应验”的描写表达了霍小玉对不平等的法律地位的反抗,也展现出她性格中刚烈的一面。且看小玉的临终之言:
“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羅管弦,从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赐。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
(蒋防《霍小玉传》)
霍小玉与李益分别后,李益辜负盟约,小玉多方打探消息而不得,最终相思成疾、沉绵病榻;在她得知李益已定婚约后,只盼求一见,可李益却百般躲避。面对这样的现实,她只能“冤忿益深”、“委顿床枕”,却申诉无门。纵然是“风流之士,共敢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情”,但现实社会并没有给予一个下层婢女获得权利救济的机会。所以,作者只能借助超现实的力量来帮助霍小玉完成她对自身不平等的法律地位的反抗,这与《窦娥冤》中窦娥临终的三桩誓愿得以实现的写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所述,霍小玉是执着追求爱情的唐代社会下层婢女的典型形象,她对自己不平等的法律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温柔而善解人意,刚烈而具有反抗精神。
三、情与法的矛盾冲突:悲剧根源与法理内涵
霍小玉和李益的爱情悲剧,究竟是李益个人因素造成的,还是该归因于唐代门阀婚姻制度?这一直是《霍小玉传》研究中的疑点问题。笔者认为,李、霍二人爱情悲剧的根源在于唐代不合理的法律文化,而李益的懦弱、逃避则是引发这一悲剧的直接因素。
唐代社会的法律文化鲜明地体现出儒家“礼”的精神和原则。首先,就制度性法律文化而言,唐律纳礼入律,“失礼之禁,著在刑书”(《全唐文·薄葬诏》)。《礼记》云:“婚礼者,礼之本也。”《唐律疏议》中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定即充分体现了“别尊卑”、“异贵贱”的儒家礼仪秩序思想。例如,唐律规定:
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疏】议曰: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买卖,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俦类。若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违别议曰,便污夫妇之正道,黩人伦之彝则,颠倒冠履,紊乱礼经,犯此之人,即合二年徒罪。
(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户婚》)
据此可知,“门族清华”的李益与婢女出身的霍小玉之间的爱情跨越了等级贵贱的鸿沟,具有超越时代法律的进步意义。因而,他们的婚恋也为“一准乎礼”的唐律所不容,唐代的制度性法律文化为二人爱情的悲剧结局种下了根源。
其次,就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来说,唐代青年男女的婚恋行为受到氏族门第观念的深刻影响。据史书记载:
李义府为子求婚不获,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劝上矫其弊。壬戌,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然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異姓为婚。
(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
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杜兼传》)
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 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刘餗《隋唐嘉话》)
唐代以“五姓七族”为代表的高门氏族声望甚高,彼此之间互为婚姻,即使皇帝颁布诏令亦不能止之,足见此种风气之盛。有唐一代,无论是皇子、公主还是文人士子,皆以能与“五姓”家族联姻为荣。这种门第婚姻观念虽然没有成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却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社会中青年男女的婚恋行为,可以认为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民事婚姻法律文化。在唐代传奇小说中,多篇故事的主人公皆由“五姓”氏族出身,如《李娃传》中的荥阳郑生、《枕中记》中的山东卢生等,这种门第婚姻法律文化对文人创作心态的影响可见一斑。蒋防在《霍小玉传》的开篇即写到“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可知李益出身于“五姓七族”之一的陇西李氏之家;其后又交代“卢亦甲族也”,可知李益的母亲为其选聘的妻子亦属“五姓”之一的范阳卢氏。在唐代看重门第的民事婚姻法律文化的感召下,母亲为李益所定的亲事无可厚非,而霍小玉身份微贱,如何能与出身甲族的卢氏相比?唐代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性法律文化间接扼杀了李益与霍小玉的爱情。
总之,不论是唐律的相关规定,还是唐代社会盛行的观念性法律文化,都体现出鲜明的等级性,不同等级的权利主体之间的社会地位不平等。正是这种不合理的法律文化,限制了李益与霍小玉的婚恋自由,并最终导致了二人的爱情悲剧。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个社会的法律文化并不能直接导致个人婚恋的失败,李益与霍小玉爱情悲剧的产生还应当同个人的主观因素有关,而李益懦弱、逃避的性格就是导致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得知母亲为自己定亲,李益懦弱屈从;面对辜负小玉的事实,李益又百般逃避。比之黄璞笔下以身殉情的欧阳詹,李益对爱情的态度显然是不够赤城的。如果李益能够像《李娃传》中的郑生一样,即使身受困厄也依然为爱执着,那么,他就不会在母亲面前完全沉默,更不会在事后不向小玉解释缘由而任其命归黄泉。可以说,正是李益的懦弱、逃避,造成了霍小玉因情而死的结局,李益的性格因素是促成他与霍小玉爱情悲剧的直接原因。
恩格斯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实现之间的冲突。”唐代社会的法律文化严重限制了青年男女的婚恋自由,使有情人难成眷属,不知造成了多少像霍小玉和李益这样相爱却不能相守的爱情悲剧。清代律学家薛允升称赞《唐律疏议》“繁简得其中,宽严亦俱得平”,但是,即使是被奉为我国古代社会立法之典范的唐代法律,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之处。唐律涉及婚姻的法律规定具有不平等性,且使用刑事手段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对违反民事法律的行为皆施以刑罚措施,体现了中华法系“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特点,但是,以国家法律的强制干预取代私人的自治,这违反了法的价值追求。公平与秩序都是法的价值,而自由是法的终极价值,唐律将法的秩序价值凌驾于公平和自由之上,造成了法律价值体系的不平衡。当然,法的目的价值具有时代性,不同时代的法律文化,在它们所追求的立法尊旨和社会目的方面,可能存在不同的价值选择。在唐代社会,儒家礼仪伦理原则是法律文化所服务的目的价值,故而,家庭中的尊卑有别、“奉尊长教令”和婚姻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被视作是善意的、应当的、有价值的。然而,正是唐代社会这种善意的、应当的、有价值的法律文化,铸就了法与情的矛盾冲突,也间接酿成了无数有情人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小说中,霍小玉的死亡则是对这一不合理的法律文化的沉痛控诉!
四、结束语
霍小玉和李益的爱情故事既是文学语言的生动叙事,也是法律文化的隐含叙事。目前,文学界关于《霍小玉传》的研究成果已经较多,法学家们对唐代法律文化的研究亦方兴未艾,本文尝试对此二者作出了结合式的探究,期望对当代文学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有所启迪。
注释:
①参见: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②参见:鲁迅校录,蔡义江译《唐宋传奇集·序》,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③参见:陈国斌《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④参见:卞孝萱《<霍小玉传>是唐代牛李党争的产物》,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⑤参见:程毅中《唐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⑥参见:关四平《唐传奇<霍小玉传>新解》,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⑦参见:刘秋娟《浅析<霍小玉传>中李益的神经症人格》,载《枣庄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⑧参见:虎维尧《<霍小玉传>的文化意蕴》,载《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5期。
⑨参见: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序》,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⑩据《新唐书·刑法志》载:“律之为书,因隋之旧,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参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07页。)
据《唐六典》载:“凡律所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参见:李林甫等撰《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2页。) 另据《新唐书·刑法志》载:“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参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刑法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08页。)
参见:张晋藩、朱勇《中國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参见:赵晓耕《中国法制史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
参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选举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72页。
参见:卞孝萱《<霍小玉传>是唐代牛李党争的产物》,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参见:周承铭《<霍小玉传>思想价值再评估》,载《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参见:余宗其《法说红楼梦》,中国财富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参见: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参见:关四平《唐传奇<霍小玉传>新解》,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依据张文显等学者的观点,法律文化的基本结构分为两层:其一是制度性法律文化,包括了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其二是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包括了法律信念、人们的法律价值观、法律心理、法律习惯、法律学说等。(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2007年第三版,第392页。)
参见:恩格斯《致斐·拉萨尔》,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所谓“法的目的价值”,即在整个法的价值体系中占突出的基础地位,它是法的社会作用所要达到的目的,反映着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会理想,集中体现着法律制度的本质规定性和基本使命。(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2007年第三版,第298页。)
参考文献:
[1] 张友鹤选注. 唐宋传奇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2] 鲁迅校录,蔡义江译. 唐宋传奇集[Z].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
[3] 陈国斌. 隋唐五代小说研究资料[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 程毅中. 唐代小说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 卞孝萱. <霍小玉传>是唐代牛李党争的产物[J]. 社会科学战线,1986(02).
[6]关四平.唐传奇<霍小玉传>新解[J].文学遗产,2005(04).
[7] 周承铭. <霍小玉传>思想价值再评估[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0(05).
[8] 刘秋娟. 浅析<霍小玉传>中李益的神经症人格[J]. 枣庄学院学报, 2012(01).
[9] 虎维尧. <霍小玉传>的文化意蕴[J]. 固原师专学报,2004(05).
[10] [宋]欧阳修等撰. 新唐书[Z]. 北京: 中华书局,1975.
[11] [后晋]刘昫撰. 旧唐书[Z]. 北京: 中华书局,1986.
[12]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2012.
[13] [唐]刘餗撰,程毅中点校. 隋唐嘉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 [清] 纪昀总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Z]. 北京: 中华书局,1965.
[15] [唐] 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 唐律疏议[Z].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16] [唐]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Z]. 北京: 中华书局,1987.
[17] [日] 仁井田陞撰,栗劲等编译. 唐令拾遗[M]. 长春: 长春出版社,1989.
[18] 戴炎辉. 唐律通论[M]. 台北: 国立编译馆,1964.
[19] 张晋藩、朱勇. 中国法制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0] 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2007.
[21] 馬小红,姜晓敏. 中国法律思想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2] 甄艳楠. 浅议唐代婚姻法律制度[J]. 法治与社会,2011(23).
[23] 王立民. 略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伦理——以<唐律疏议>为中心[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03).
作者简介:周洁,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