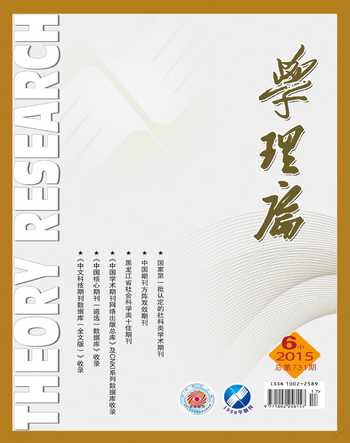论清遗民的独特性
陈晶华 王艳秋
摘 要:清遗民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遗民,因其身历“千年未有之变局”,独特的历史境遇赋予了他们特殊的遗民性格。从清遗民的遗民立场、文化取向以及民族观念三个方面展开清遗民独特性分析。
关键词:清遗民;独特性;文化遗民;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96-02
身处新旧王朝交替之际,且不仕新朝,内心对旧朝故国怀有深切眷恋的士人,被称为遗民。遗民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上至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下至清末民初的清遗民。清遗民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代遗民,身处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清遗民,在心态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都体现出历代遗民所不具备的独特性。
一、遗民立场的独特性
“遗民”这一概念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故而遗民身份的认定,既要从当事人的政治立场考量,更不能忽视其文化立场的考量。与以往各代遗民相比,清遗民的“文化遗民”色彩更加浓重,有学者称清遗民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民。
在封建社会内部,因王朝更迭而出现的历代遗民,无须面临文化立场抉择的问题,故而他们对遗民身份的选择,主要源于政治动因,且他们的社会活动也以政治活动为主,故而历代遗民身上政治色彩浓厚,是典型的政治遗民。清遗民身上依然承续了传统遗民的政治特色,但因他们所经历的不再是封建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文化结构的彻底转型,故而使得他们对于“新朝”与“故国”有了更为复杂的心态。他们的遗民立场,不仅仅体现了个人的政治取向,更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
“当一种文化衰落之时,必然会有一种新文化的兴起,那些为旧文化所‘化之人,在即将兴起的新文化环境里,无法融入其中而深感痛苦,并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或传承那种即已衰落的旧文化。这种遗民,由于其文化情结的根深蒂固,由于其遗民立场的文化含义,使其所有的表达都富于一种文化内涵,”[1]许多清遗民正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时代背景之下,一方面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另一方面因文化大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双重因素作用之下,选择了自身的遗民立场。
在清遗民心中,逝去的清王朝更多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让他们能够获得人生价值和自我尊严的传统秩序。清遗民这种强烈的“文化遗民情结”,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站在文化立场上,看待旧政权和旧社会。他们难以割舍“旧朝”,更多的是源于对传统社会生活,稳定秩序的眷恋。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他们往日的旧经验无法适应新变化,從而使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尤其是那些文化修养较高,并自视为代表了传统文化价值的士人,他们感受到了更强烈的心理冲击。他们所重视的不是一家一姓的王朝更迭,而是更看重他们赖以生存的,并从中获取价值与尊严的文化土壤——传统文化的兴亡。在他们看来,清王朝对他们来说并非是完美的生活世界,但它却是传统文化的象征和载体。因社会政治秩序变革而引起的传统文化的衰落,是清文化遗民产生的根本动因,因而复兴传统文化秩序亦是清文化遗民的最终理想追求。这种实现传统文化复兴的夙愿,是与现实中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的,是要依托于清王朝——这个传统文化载体的复辟而实现的,这就决定了清文化遗民必然关注甚至参与复辟的政治活动,但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通过恢复旧社会的政治秩序,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秩序的复兴。
二、文化取向的独特性
民国初年的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逐渐丧失其主流思想地位,被新式文化所取代,而选择依然坚守传统文化立场,拒绝接受新文化的清遗民,他们无疑成为民初社会中的文化边缘群体。在他们看来,民国初年的政治腐败、社会动荡、道德失范、学术不端等问题,根源就在于传统文化的解体。沈■植■感叹“学士者,国之耳目也,今若此,则其谁不盲从而踬蹶也,且学者,礼之所出,礼也者,国人之准则也,今若学士,可谓无学,国无学矣,而欲质之以礼,其可得欤?”[2]被誉为晚清文化怪杰的辜鸿铭,是清遗民的代表,他多次抨击袁世凯取清朝而代之的行为,认为袁罪大恶极之处在于“破坏了中华民族的政教和文明”,并多次向他的外国友人宣称自己对清朝的忠诚,是源于对中国政教和文明的忠诚。
少数清遗民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即殉节。殉节是历代遗民表达自身对旧朝忠诚的最高方式,是遗民情操的最高境界。令清遗民感到尴尬的是,清灭亡之时,竟无一人殉国。反倒是时隔数年之后,王国维和梁济双双投水自杀,开启了人们对于清遗民殉节的话题。王国维之死,给后世留下了谜团。对于其死因,在他去世后,社会各界有各种猜测。陈寅恪被认为是最了解王维国死前心态的人,他将王国维死的阐释是为传统文化而殉节。他说王国维生当中国文化衰亡之时,自视为此文化的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
梁济选择在民国七年(1918)自杀,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轰动。而梁济在自己的遗书中说明自杀原因时说,“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3]“故我身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则必当忠于清,是以义为本位,非以清为本位也。”[3]从梁济的遗书所述,可以看出他的死,最终目的不是为一家一姓的天下殉节。民国初年黑暗的社会状况,人伦道德的失序,导致了他对现实的绝望;清朝的覆灭这一事件背后所包含的文化理想与道德价值的覆灭,才使得他最终选择了自杀。
在清朝灭亡之际,并没有遗老为此而殉节,反倒是时隔若干年后,梁济和王国维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理想与道德价值的崩解而相继自杀,足见晚清遗民对于传统文化的依恋有多深厚,竟不惜以死殉之。
在清遗民心目中,传统文化以及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一切无疑都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晚清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政治腐败问题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很多清遗民都曾经是维新运动拥护者乃至参与者。如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和林纾等人,都热心于维新与立宪改革。清遗民能够接受在不改变传统文化体制前提下,在内部对其进行改革,也认识到了这种变革的必要性,但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是一种新的异质文化全然取代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他们将自身视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全盘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否定,就相当于在否定其自身的生存价值。传统文化相关的一切,既是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更是他们精神皈依的家园。
三、民族观念的独特性
中国近代社会最重要的历史主题之一就是抵御外辱,挽救国家危亡。这一历史难题是历代遗民所不曾遇到过的。随着现代民族主义概念的引入,国人对“国家”、“民族”有了全新的认识。梁启超提出了“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的概念,“小民族主义”内涵为国内民族关系,主要是指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关系;“大民族主义”是指中国各民族团结作为一个大民族与世界其他国家与民族关系,他认为中国现在“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4]上述民族主义观念已突破了旧式的“夷狄”观念,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将“大民族”的利益置于“小民族”之上,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
在上述独特的国内国际形势作用之下,清遗民在处理“大民族”与“小民族”问题上,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形势和更艰难的抉择。一方面,外来殖民势力对中国国内问题的干预,客观上造成了清遗民的主要政治活动——复辟运动多了一种外援。而是否借助外来殖民势力实现匡复大业,对于这一问题,清遗民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这一分歧促使清遗民在民族立场上作出了不同的抉择,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日本是对清遗民复辟运动投入支持最大的国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便于对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1932年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政权,扶植清朝已废皇帝溥仪出任该政权首脑。溥仪及选择追随其参与建立“伪满洲国”政权的清遗民,为了他们匡复大清帝业的梦想,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实乃民族的罪人。他们的行径,给清遗民群体的历史造成了最大的污点。
这些成为汉奸的清遗民,以郑孝胥为首,积极主张借助日本的力量,完成复辟大业。东北沦陷的消息传至天津后,郑孝胥立即劝说溥仪与日本合作,“昨夕陪膳时,郑孝胥又大談其开放政策,言之津津。”[5]郑孝胥最终说动了复国心切的溥仪,选择在日本扶持下出任“满洲国”执政。郑孝胥对“伪满洲国”政权的筹建倾注了大量精力,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出任“伪满洲国”总理,一心期望通过这个汉奸政权实现他的王道理想。
郑孝胥出卖国家的行为无疑为后世所不耻,他个人善于投机钻营、极富政治野心的性格是其最后成为汉奸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郑孝胥身上所体现出的清遗民作为中国最后一代遗民荒唐而悲哀的政治命运。郑孝胥希望通过与日本合作,回复王道纲常,从而恢复传统的政治秩序,悲哀的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日本选择利用溥仪及其追随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殖民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帮助他们复兴大清基业。郑孝胥等人沦为历史的罪人,也充分体现了一部分清遗民并不具备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一家一姓的天下即等于国家,所以在民族立场抉择的问题上,犯下难以挽回的错误。
应该看到,以陈宝琛为首的另一部分清遗民对于民族大义问题则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溥仪自己回忆说,对于是否赴东北与日本合作一事,陈宝琛第一个提出反对意见,并多次劝阻。“光复故物,岂非小臣终身之愿?唯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6],这充分体现了陈宝琛虽然也一心希望复辟能够成功,但反对与日本合作,拒绝追随溥仪北上。伪满政权成立后,曾经拟定陈宝琛出任“府中令”一职,被陈拒绝。
郑孝胥和陈宝琛同为清遗民的一员,都以匡复清室为最终的政治理想。但在是否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与殖民者合作从而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问题上,两人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前者突破民族大义底线,沦为历史罪人;而后者则更清醒地认清当时的现实,坚守民族立场,值得肯定。这也充分体现了清遗民群体内部个体差异以及生存状态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张步洲.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2]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J].读书,1995(5).
[3]粱济.粱巨川先生遗笔[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N].新民从报,1903-
10-04.
[5]胡嗣瑗.直庐日记[M].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
[6]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