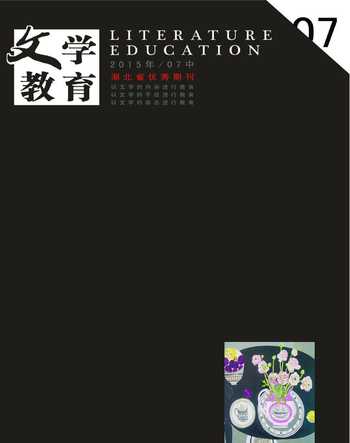浅析叶芝的审美现代性
刘娟
内容摘要:叶芝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现代性问题近来成为评论界争议的焦点。本文试以卡林内斯库提出的两种现代性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叶芝主要诗歌作品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以及拯救现代人两个层面,分析并揭示叶芝特殊的审美现代性。
关键词:叶芝 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 批判 拯救
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Yeats1865-1939)在世界文坛上无疑是位举足轻重、颇具影响的人物。他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里,为世人留下大量优秀经典的诗歌作品。学术界对叶芝的研究与关注从未间断。叶芝的现代性问题,评论界普遍存在两种观点:反对方指出叶芝对欧洲宗教和艺术传统的质疑并没有庞德那样深刻,且艺术创新上也没有庞德和艾略特那样彻底。支持方却坚持认为叶芝在19世纪诗歌语言上的创新为庞德的“直接对待事物”诗歌理论做出了贡献。有谁在读到“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1919)不被作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现时的一种深深的焦虑所震撼[1]?在安妮·福格蒂(Anne Fogarty)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找到最新关于叶芝现代性的论述。安妮以叶芝广泛投入到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被视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运动一部分),和其作品呈现出的自省性来重新探讨叶芝特殊的现代性[2]。
相比之下,国内对叶芝现代性的研究似乎显得较为贫乏。何宁曾在2000年的一篇题为《叶芝现代性》文章中突破简单地以艾略特创作为标准的瓶颈,代之从叶芝作品所反映现代人的精神状况等方面来探讨叶芝现代性问题。
一.理论基础
在讨论叶芝现代性这一问题之前,首先梳理下其中几个关键概念:现代性,现代主义与现代化。它们看似相似,却有着不同的内涵。“现代化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指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断发展的一个转化过程。现代化可视为一个如鲍曼所言的‘未完成且无法完成的一个过程,我们及世界文化正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而这个发展过程是指向未来的[3]。”可见,现代化是一个表示过程的动词,是动态的。关于现代性,卡林内斯库认为它是一个时间∕历史概念,我们用它来指在独一无二的历史现时性中对于现时的理解,也就是说,在把现时同过去及其各种残余或幸存物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性中去理解它,在现时对未来的种种允诺中去理解它——在现时允许我们或对或错地去猜测未来及其趋势﹑求索与发现的可能性中去理解它[4]。卡氏还进一步提出存在“两种现代性”的观点。“无法确言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可以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剧烈冲突的现代性。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相反,另一种现代性,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放[5]。”这两种现代性一直处于一种对抗的态势,形成一种张力,而也正是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性与对抗性推动社会的进步。
现代主义则是一场运动,一种文学思潮,是现代性的一种载体。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是分别表过程,本质和理念的词。梳理完三个核心概念,再来审视叶芝的现代性,我们不难发现其特殊性。作为风格多变,创作年限长,自诩为“最后的一位浪漫主义者”的过渡性诗人,叶芝同时又被称作爱尔兰的“第一位现代主义者”。本文试以两种现代性为切入点,从审美现代性的两个层面分析诗人特殊的现代性。
二.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
卡林内斯库认为,在西方现代化历程中,不知从何时起,逐渐产生了两种现代性:一种是以进步、理性、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并渗透到社会各领域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一种是对此予以否定、批判、反思与超越的审美现代性∕美学现代性。所谓审美现代性,是对前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重商主义、功利主义与市侩主义,对资产阶级和世俗阶层的现代价值观的否定与批判,是一种反资产阶级现代性的“现代性”[6]。
以艺术和文学为代表的审美现代性同资产阶级现代性之间一直处于紧张的对抗中。作为反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以审美的方式站在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正是现代性这种内在的矛盾与冲突才使得现代性达到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那么叶芝的诗歌又是如何体现诗人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的呢?
首先,叶芝对资产阶级文明所取得的成就是嗤之以鼻的。诗人早年在母亲的家乡斯莱戈(Sligo)小镇渡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斯莱戈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同伦敦工业化城市中杂乱不堪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叶芝来说斯莱戈代表的是工业革命前的爱尔兰,一个宁静、和谐的世外桃源,而伦敦和英格兰则是资产阶级工业化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摇篮,充斥着脏乱、嘈杂的工厂与贫民窟。叶芝将英格兰与其厌恶的现代物质世界的一切——帝国主义、贪婪的物质主义、城市的丑陋、肮脏与阴暗面联系起来,将爱尔兰视为资产阶级所谓文明中的一方净土。在《1913年9月》(September 1913,1913)中,叶芝运用犀利的反讽,尖锐地抨击了爱尔兰新兴的天主教徒中产阶级庸俗的市侩气及其自私吝啬的拜金主义:“清醒过来之后,你们需要什么,∕除了在油腻的钱柜里摸索,∕给一个便士再加上半个便士,”∕给颤声的祷告再加上祷告,直到∕你们把骨头里的精髓榨干;∕因为人们生来就是为祈祷和攒钱:∕浪漫的爱尔兰已死亡消逝,∕随欧李尔瑞一起在坟墓中。”当时戴着伪善面具的资产阶级们,面对爱尔兰的民族事业,他们是麻木、妥协的,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独立的爱尔兰,而是金钱、地位,是唯利是图。
《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1919)中叶芝又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现代西方文明已成荒原的全景图:“盘旋,盘旋在渐渐开阔的螺旋中,∕猎鹰再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万物崩散;中心难再维系;∕世界上散布着一派狼藉,∕血污的潮水到处泛滥,∕把纯真的礼俗吞噬;∕优秀的人们缺乏信念,∕卑劣之徒却狂嚣一时。……[7]”诗人用两个交相渗透的旋转的锥体图形来说明造成人类历史循环的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一个文明从其中一个锥体的尖端开始,呈螺旋形旋转到底部而“崩散”结束,然后又从另一锥体的尖端开始反向旋转,开始另一个文明的循环。叶芝认为从一个文明结束到另一个文明开始要经历两千年的时间并预言旧的文明(意指二十世纪前的西方文明)已走到尽头。诗的开头三行是螺旋锥体象征的形象变体。文明的发展从锥体的尖端开始,呈螺旋形旋转,“渐渐开阔”,到底部而“崩散”结束;然后从对立锥体的尖端开始反向旋转,开始另一个文明的循环。诗人采用了一系列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旋锥”、“猎鹰”、“大漠”、“世界灵魂(大记忆)”等,构成一幕幕充满混乱、疯狂的景象。“世界上散布着一派狼籍”,“卑劣之徒却狂嚣一时”,荒漠中的“狮身人面的形体”(两千年历史文明的象征) 在动摇……急迫的节奏、夸张的语调、奇诡的形象,渲染出一派阴暗、恐怖的气氛,显示出诗人崇尚的贵族文明——“纯真的礼俗”,已淹没在这片恐怖之中。就诗而论,我们只看到历史的“旋体”转向了黑暗的反面,能否再转回到诗人理想的正面,真正实现“基督重临”,不能不让人产生质疑。
总之,叶芝一开始就拒绝了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带来的进步,他认为资产阶级发展与进步并不能将人类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相反,它造成世界一片混乱,给人类还带来更多的危机,使现代人深陷泥潭不能自拔。那么现代人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三.拯救之路
随着十九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兴起,西方工业的高速发展与进步,日益膨胀的商品经济与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给世纪之交的西方物质世界带来巨大的财富。然而,物质世界财富的积累似乎并未给现代人带来快乐。相反对物质财富过分的追求给人的思想戴上工具理性的枷锁,造成信仰的缺失,精神世界变成一片荒原。文化产业过分追求世俗的结果使人在大量低俗文化产品面前,显得更加茫然失措,无所适从。怎样才能将人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审美现代性给出了答案。
拯救世俗是审美现代性内含的一个层面。现代社会之前,宗教始终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上帝能否拯救人类产生了质疑,宗教开始衰落。社会学家韦伯曾提醒我们:“生活的理智化和理性化发展改变了这一情境。因为在这种状况下,艺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觉把握到得有独立价值的世界,……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8]。”在人们已丧失宗教信仰的年代,审美取代宗教而承担起救赎世俗的责任。审美将主体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的同时,还实现对现代文化的提升。这种提升表现在通过审美,人感觉的灵性得到恢复,人在审美过程中得到美的享受,陶冶情感,获得情感上的财富。艺术作为主要的审美形态,成为审美现代性发挥救赎功能最重要的载体与方式。艺术在宗教衰落的现代社会中成为生存意义的提供者,一方面向人们敞开了一个科学技术无法提供的关于生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把人们带回到“本真”的领域,遭遇到自己的感性身体、欲望和情绪,这正是“救赎”的深意所在[9]。
1928年,叶芝出版了代表其最高艺术成就的诗集《塔》(The Tower,1928),这部诗人在晚年完成的现代派诗歌的经典之作汇集不少杰作,包括《驶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1927)、《塔》(Tower,1926)、《一九一九》(Nineteen Hundred and Nineteen,1919)、《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1923)及《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1926)。该诗集问世之前,面对现代世界的精神荒原,诗人并没有告诉我们人类的出路到底在何方。在《塔》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诗人呼唤现代人通过艺术实现自我救赎,在艺术为人类建造的“乌托邦”中得到永生。
诗人想通过艺术拯救现代人的思想突出表现在《驶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1927)这首诗中。“拜占庭”包含了两种对立的概念。一是爱尔兰,另一个则是拜占庭。拜占庭是小亚细亚古城,后由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一世(287?-337)重建,在330年改名为康斯坦丁堡;公元六世纪时为东罗马帝国首都,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繁荣一时,叶芝视之为理想的文化圣地,艺术永恒之象征[10]。诗中的爱尔兰不仅仅是指叶芝生活的地方,它同时象征叶芝所处的当下现实世界。在叶芝心中自然物质世界“绝非老年人适宜之乡”。而拜占庭完全是神圣的理想国度,宁静祥和,保持着古时繁盛的风貌,它是艺术的世界,永恒的国度,神圣的殿堂。叶芝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肌体已衰老,他将老年人比作无用之物犹如一根竿子撑着的破衣裳。但诗人却保持着年轻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他要离开爱尔兰,犹如渡过生命之海,去到拜占庭,求得永恒的艺术,在艺术中永生。诗人曾写道:“我觉得我应该花一个月的时间到我选择的拜占庭去过一段时间[11]”,可见拜占庭是诗人向往的理想之地。诗人描绘出现实物质世界的一派景象:年轻人沉湎于感官的刺激中,沉浸在青春、情欲和自我放纵的可爱盛夏季节里。但他们却忽视了对精神、智慧的追求。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到希望,所以“我”要拒绝这种年轻人的感官享乐世界,摆脱肉体束缚,在永恒的艺术世界里求得永生,得到救赎。诗人来到向往已久的圣地拜占庭后,请圣人们从火中走出来,成为“我”灵魂的导师,火要将“我”所带有的尘世欲望之心烧尽。圣人们从火中走出来拯救“我”的灵魂。“我”来到这“神圣的城堡”,“神圣的城堡”在这里已经没有宗教意味,它是神圣崇高的,远离土、气、水等俗物,卓立于灿烂的净火之中。叙述者“我”强烈希望自己变成古希腊金匠制成的金鸟,栖立在金制的枝条上唱歌,将皇帝唤醒,向贵族歌唱历史、现在和未来。这时诗人也“脱离自然界”,变成停在金枝上婉转嘀啾的金鸟。可以说,这虽是一首关于“歌唱”的诗文,但是其象征意义远远超出故事的本身。叶芝在一本关于拜占庭艺术的书中读到过这种描绘:鸟儿与它的歌声不分彼此,它们即是在烈焰中锻造成的灵魂和灵魂所创造的诗歌。虽然叶芝本人并没有去过拜占庭,但拜占庭在他心中是艺术永恒的象征,诗人认为尘世中的一切终归会消失,只有艺术才能永恒,艺术正是叶芝为现代人探寻的拯救之路。
作为不断追求诗艺创新——从后期浪漫派﹑唯美派﹑象征主义到现代派的过渡性诗人,叶芝在长达四十几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批评和内省,使其整个创作体现出无所不在的变化感。其作品反映出诗人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批判,诗人进而又为现代人探索出一条拯救之路,并体现出他独特的审美现代性。
参考文献
[1]Holdeman David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B.Yeat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59,118.
[2]Fogarty, Anne. “Yeats, Ireland and modern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t Poetry. Davis Alex, Jenkins M. Lee.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胡鹏林.文学现代性[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2.
[4][5][6]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6-337.
[7]叶芝.叶芝诗集(上中下)[M].傅浩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5,450.
[8]H.H.Gerth and C.W.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342.
[9]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187.
[10]Jeffares,A.Norman. Poems of W.B.Yeats A New Selection. London: Macmillan,1950.367.
[11]Yeats, W.B. A Vision. 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5. 190.
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2013年科研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3SB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