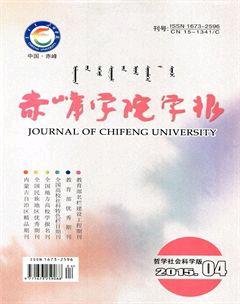民族经典的建构与传播
杨文艺
摘 要:《白毛女》经典地位确立和传播的过程所裹挟着的丰富的政治文化信息,使得长期以来对其的学术批评不仅在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方面,而且在社会历史及政治文化等层面都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空间和争议性的学术话题。因此,从《白毛女》“经典”地位的建构和确立过程及其借助电影、政治外交等媒介和手段加以巩固和扩散的历史逻辑出发,反思“新的人民的文艺”体制下的美学规范与生产运作过程,对认识不断“集体”修改着的“红色经典”及其文艺传统,有着重要的文艺史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白毛女》;“经典”;“新的人民的文艺”;“集体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132-03
2014年,随着林白和王昆等“第一代白毛女”扮演者的相继去世和芭蕾舞剧《白毛女》“50周年”纪念活动的开展,围绕《白毛女》经典建构和文化扩撒的回顾和反思再掀波澜。作为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的“典范”,《白毛女》从1945年前后的诞生,历经“17年”文化外交,再到当前“经典式微”时代的红色文化符号,似乎从未游离于主流文化的话语中心。因此,从考订《白毛女》文学剧本的修改和流变出发,反思“集体创作”体制下的美学规范与生产运作过程,不仅能透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演变历程,而且为认识当前文学文化领域的“反经典”潮流提供思路。
一、“成熟”与“完善”:“经典”的建构和确立
1945年前后,新歌剧《白毛女》问世于延安。据贺敬之回忆,作品诞生后,从1946年在张家口正式出版到1949年被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及改编为同名电影剧本之前,先后经历了多次重要修改。这其中,确立了后来不断改编基本方向的是1947年7月在哈尔滨的这次修改,它以“集体创作的形式”,形成了之后诸多《白毛女》文学版本的依据。相关资料显示,这次修改“汇集了多方面意见”,经历了“集体创作组”的“讨论”,“最后决定全剧改为五幕”[1]。
根据执笔者丁毅回忆,1947年7月的这次修改,是因为新歌剧《白毛女》文学剧本虽在多个地方“出版过几次了”,但之前的六幕剧文学剧本“还不成熟”,有必要“再努力使它走向完善”[2]。鉴于对六幕剧剧本的这些不满,综合了“多方面的具体意见”,20世纪后半期以来《白毛女》文学剧本的世纪之旅在整体性压缩、调整及“再创作”活动中开启了。
不过,这次修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白毛女》文学剧本趋向“成熟”与“完善”,其中剧目结构上的删减与修改及人物身份与人物关系的重塑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修改者们特殊的艺术用心。就剧目结构的调整而言,修改者们“经过讨论”,决定“去掉”六幕剧剧本“原先的第四幕”,原因是“同志们都感到沉闷”、“显得累赘”和“没有生活的根据”,且“原先的第四幕”“减低了剧本主题发展的速度”;修改者们同时认定“原先第五幕”的剧情“距主题意义也较远”,因此决定予以“修改”。通过修改前后的文本比较不难发现,这次修改中被删去的“原先的第四幕”刻画了“喜儿”和“喜儿之子”在山洞中相依为命的生活情景。这一幕之所以被删去,是因为它被认定为“没有生活的根据”。人物身份和人物关系的重塑是这次修改的另一“成功”。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是“杨白劳喜儿之父,佃户”被改为“地主黄世仁家之佃农”;二是突出白毛女为“杨白劳之女”的血缘关系与女性身份;三是将含混的“赵老汉”角色修改为“赵大叔——杨白劳之老友”;同时李栓、大锁等配角形象的叙事功能也得以有效调动[3]1-2。从“集体创作组”期待实现的“新—旧”社会叙事与“人—鬼”革命主题的“完善”看,这次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重建重构清晰地定位了正反面人物的政治属性及阶级关系,也突出了人物历史命运的文化关联与社会认同,从而增强了“阶级斗争”的叙事效果。
这次修改不仅确立了新歌剧《白毛女》的叙事主题,而且也确立了后来《白毛女》的各种艺术改编活动及其经典化进程的艺术规范和方向。其后,以五幕剧为基础的电影(1949)、川剧(1958)、京剧(1960)、芭蕾舞剧(1964)相继诞生,并被翻译成英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和非洲语在50、60年代的苏联、东欧、朝鲜、古巴及“非洲小兄弟”国家演出,被当时的官方媒体誉为“解放了的创作力”(席明真,195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具有“革命热情和中国气派”的艺术(胡沙,1962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和“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革命样板戏”(1970年01月02日,《人民日报》)。同时各种版本的《白毛女》作品也成为50、60年代的中国政府接待各国客人的必演节目。以“白毛女”为关键词的“知网”搜索,整个“17年”里,仅《人民日报》刊载的相关政治活动的报道就50多篇。这种以政治力量推动并不断完善、强化和传播艺术经典,建构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历程与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针对《白毛女》1945年前后诞生以来的70年文化实践,王荣教授感慨于《白毛女》作为主旋律文艺或‘红色经典对当下的文艺生产的深刻影响,指出,在“新的人民的文艺”实践史上,似乎还没有哪部作品如《白毛女》一样,从问世之日起便历经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的磨合与洗礼[4]。
二、“相宜”与“明确”:“经典”的巩固和扩散
出于对电影艺术及其社会功能的重视,1949年4月“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时,就明确提出了建立“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电影”的目标[5]。同年9月,由作家杨润身、导演水华和王滨等联合组成的《白毛女》电影文学剧本改编与拍摄工作组迅即投入工作。
这次电影版改编的突出特点是实现了对歌剧版的借鉴和超越。据当时的改编者的事后回忆,改编是在“党的领导下”“搜集了广大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改编目标明确,即“去掉歌剧中经群众鉴定后留下的几点黑斑的问题”。当时所谓的“黑斑”主要有三:一是歌剧中“‘小白毛的问题”。改编者“经过讨论之后,觉得孩子留着实在不相宜”,“这一情节并非主题核心”,于是与“‘小白毛有关的情节和场景被删除了。二是“大春和喜儿的关系问题”。为了突出黄世仁霸占人妻的恶霸行为,电影文学剧本明确了两人“不只是爱情关系,而且是法定的夫妻关系”,以消除新歌剧中“不够鲜明”人物关系留下的“黑斑“。三是删去了被认为“不健康的情节”。如为杨白劳送葬的民俗情节,认为它“表现出一种灰色的阴暗的思想感情”,后来“经领导指出,删去了”[6]。此外,还从民间习俗和传统审美方面把杨白劳的“躲账”修改成“还账”,让喜儿与大春最后“终成眷属”[3]204,以更加“相宜”而“明确”地表现最初期望实现的叙事主题和审美观念,即“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于是,围绕这个叙事主题,电影《白毛女》借助电影蒙太奇对情节安排和人物形象进行了重组。首先是叙事场景的“亮化”。电影把新歌剧开场戏“大雪纷飞的年三十晚上”被置换为“晴空,炎午,一群羊在吃草”,“一棵大树下,老赵抱着放羊鞭子,在歌唱”,“歌声里,引出一片米粮川”等一个个长镜头特写,用以隐喻阶级社会语境下的中国乡村的生存对立,从而避免了“灰色的阴暗的”画面运动对故事情节及正面人物塑造可能带来的损伤。其次是人物形象的生活化重构。无论从故事原型、斗争经过,还是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的安排,五幕剧中的“喜儿”都多少被涂上了“传奇”色彩。为了突出喜儿作为“工农兵电影”人物形象的“正面性”和“少女情怀”,塑造其“三里五乡最出色的闺女”及“结实、年轻、能干、美丽”形象特征,电影版的改编者通过如“爹,你先歇着吧,我把这一垄割到头”以及“擦汗,把辫子往后一甩,把手巾缠在胳膊上”等语言动作的设计和避开老人为大春缝衣服等电影镜头的运用,不仅创造了一个典型的农村少女形象,而且强化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等政治主题,“从而使人们更加热爱党、热爱今天的新社会”[7]。再次是身份政治与象征叙事的运用上。电影文学剧本延续了五幕剧中赵老汉等人中共“启蒙者”“引路人”的身份定位,同时通过“大春参军”特写镜头的运用,使大春成为代表着人民大众“自觉”的力量与“希望”的化身。这样,个人的感情与阶级的解放、青春男女的磨难与民族国家的历史等叙事内容通过身份政治的建构和象征叙事手法的运用较为完整地整合进了“新的人民的文艺”,同时,也将“被压迫者们”的身心解放的必然性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永远、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从当时中国社会及文化语境上看,无论是六幕剧到五幕剧的删改,还是新歌剧到工农兵电影的改编和拍摄演出,《白毛女》从一开始就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建构和文化策略联系在了一起。而电影则以其高度组织化的传播和接受特点,不仅在社会文化功能上重构了它与其他艺术的秩序,同时也因其群众性、可复制性和接受效果的震撼性等特征,使得电影艺术有了组织和重构大众的政治文化的功能。政治认同以及全面服务于“工农兵文艺”等方面都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主导性文化权力。50、60年代,电影《白毛女》在亚非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放映,获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第六届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1951)和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1956),被誉为“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新胜利”(永卫东,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新时期以来,《白毛女》进入教材和中学课堂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一部《白毛女》剧本改编、传播的历史,既是“经典”建构与传播的历史,更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演进的历史。
三、“新的人民的文艺”与“集体创作”:“经典”的驱动和反思
纵观中外艺术和政治文化传播史,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艺作品被反复修改、不断改编是一种屡见不鲜的艺术现象。然而,在今天“经典重构”的文艺浪潮中,审慎地反思延安文艺及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不难发现,“《白毛女》现象”的形成、流播乃至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文化传统,其背后的主导性驱动,与其说源于艺术自身、创作观念或审美趣味的变化,毋宁说来自现实政治的“想象共同体”诉求及其权力话语的道德规约。
对《白毛女》这部被誉为延安文艺运动“实绩”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当年参与《白毛女》剧本修改和改编的张庚曾断言:“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不可能出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只能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之后。”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催生了《白毛女》的诞生,那么它所指示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方向及其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后“经典”地位的确立便在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中渐次开启了一种由党的领导者、广大群众、作家艺术家组成的所谓“三结合”集体创作模式,其中1945年4月新歌剧《白毛女》首次演出后,中央书记处的“三条意见”[8]无疑是这一模式的滥觞,其显著特点是领导策划、命意、干预对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左右和影响。
此后,文艺运动成为巩固“集体创作”主流地位以确认“经典”的唯一方向性与合法性的常态化方式。1950年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57年开始的文艺界的“反右”斗争、1958年对丁玲、王实味“毒草文学”的再批判、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对苏联“裴多菲俱乐部”的批判、1961年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1961)以及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指示”(1963、1964)和“文革”期间的“样板戏运动”等一些列的文艺运动,促成了包括《白毛女》在内的大批作品的“成长”和繁衍,也使得新时期以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构和政治理想成为“集体创作”能够在那个时代成为“共识”和主动服从的基础。
80年代以来,在西方各种文学观念和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理论的影响下,“重写文学史”“重塑经典”的呼声伴随着新的文学生态滋生蔓延,特别是90年代中期后,“革命化”遭遇“商业化”的文化情境中,“经典反思”一度成为热点话题。针对这一浪潮,童庆炳指出:“艺术价值”、“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是立足当下反思经典必须把握的6个要素[9]。如是观之,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的“经典”的确是一批内涵复杂、需要认真辨析的文本,就其内容而言,多以反映革命斗争历史、歌颂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宏大叙事为主题,就其流变而言,从原创到改编定型,大多经历了较长加工和提高过程,并以多种艺术形态长达数十年的推广,覆盖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影响了几代受众。但其艺术上的概念化、类型化倾向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都使得“经典反思”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因此,文革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经典”和“样板戏”一度销声匿迹,但90年代中后期影视业的发展、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威介入、近年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政策的出台再次将“经典”推上时代前台,“经典”借助商业的力量和逻辑,再次成为汇聚资源和人气的艺术重镇,只不过“经典重温”更多是以“经典代读”的方式进行。如何认识当代艺术史上的“经典”及其改编?经典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何在?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的不仅是文学史的构建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对待“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贺敬之.马可.前言[C].白毛女(修订本)[M].新华书店,1950.1.
〔2〕延安鲁艺工作团.白毛女(再版前言)[M].哈尔滨:东北书店,1947.1.
〔3〕延安鲁艺工作团.白毛女[C].中国人民文艺丛书[M].北京:新华书店,1949.
〔4〕王荣.调整与改造:从“新歌剧”到“新中国电影”的确立——论1949年前后《白毛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9):91-97.
〔5〕袁牧之.关于解放区电影工作[C]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M].北京:新华书店,1950.199.
〔6〕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白毛女(电影文学剧本)[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6.
〔7〕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白毛女》内容说明[C].白毛女(电影文学剧本)[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173-176.
〔8〕陈晋.文人毛泽东[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43—254.
〔10〕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71-78.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