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在他乡,面目全非
[文/张佳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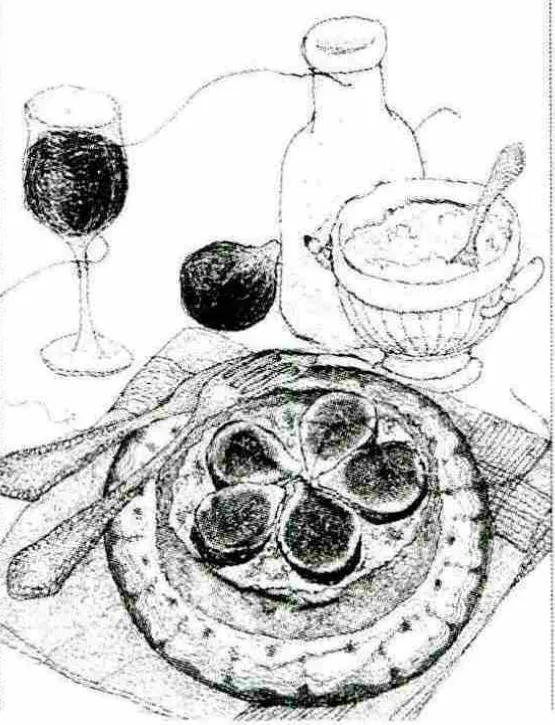
你去重庆,会发现满街望不到重庆鸡公煲的店面。而武汉也没有久久鸭,美国加州则没有牛肉面。十几年前,李碧华就写专栏文章认为:扬州炒饭,产地并不在扬州。
这些温暖了全国肠胃的饮食,各有一个被改头换面的,甚至虚构的故乡,为它们的滋味,提供一点依据。这并不奇怪:全世界都是如此。
比如,北美和欧洲的寿司店,都会卖一种“加州卷”寿司,是米饭和紫菜两层翻卷过的,外层蘸蟹子酱,内层有黄瓜、蟹柳、牛油果,加上蛋黄酱,味道醇浓,姿态威猛。但这个东西,你去京都关西的老牌寿司店,师傅不太会愿意做。理由么?嗯,加州卷寿司是20世纪70年代,洛杉矶的东京会馆餐厅想出来,哄美国大肚汉们的玩意儿。那时美国人觉得日本的刺身文化匪夷所思,给他们加了牛油果和加州蟹肉,却觉得理所当然;紫菜反卷,是怕美国人嚼不惯紫菜……
美国人最熟的中国菜之一,乃是General Tso's Chicken=左将军的鸡=左公鸡。美国人当然不知左将军何人,左宗棠自己都未必知道这鸡——左公鸡初起,最靠谱的说法,是出自厨子彭长贵之手,乃以鸡腿肉切丁炸熟,用辣椒酱油醋姜蒜炒罢勾芡淋麻油,拿来伺候蒋经国,说这是左宗棠家吃的——结果彭师傅没留名,左将军倒成了这鸡的发明者。
《忍者神龟》里,四位龟各自背着文艺复兴时四大宗匠的名号: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多纳泰罗,于是都爱吃意大利比萨。按官方小说,他们最爱吃馅料充足,布满蘑菇、三文鱼、色拉米腊肠、青椒到看不见馅饼本身的比萨,这其实有些矛盾:意大利人并不爱吃美国那种厚如椅垫,馅料琳琅满目的馅饼。在意大利,你能吃到的意大利比萨,通常薄而简洁,你能一口吃到脆香的面饼,而不是华丽的馅料。
美国英语里有个词,叫作French Fries,法式薯条。但最好的法式薯条,又出在比利时。听来很是奇怪,其实三言两语就能说明:薯条本是比利时人所创,但比利时和法国邻近,法国饮食又过于有名,以至于1802年,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一次白宫宴会上,吃了“以法国方式处理的土豆”。1856年,沃伦先生的食谱上第一次出现:“把新鲜土豆切成薄片,放进煮开的油中,加一点盐,炸到两边都出现淡金褐色,冷却后食用,这就是法式薯条!”这时候,比利时人总不能渡海到美国来揍他们一顿吧?
日本料理里有种玩意儿,叫作天津饭:你一看就会吓一跳,觉得这玩意很怪。做法是蟹肉蟹黄加入鸡蛋,加上豆芽、虾仁,放上米饭,再勾芡,乍一看,像是华丽版的蛋包饭,而且可以配汤。味道是好的,但绝对不是天津风格——吃惯天津的煎饼果子、嘎巴菜、贴饽饽熬鱼的,都会这么觉得。日本人说,这货叫天津饭是因为最初是用著名的天津小站米做的。日本人还吃中华凉面,但在上海,这种面一般叫作朝鲜冷面——可怜的冷面,日本人推给中国,中国人推给朝鲜。
当然,你也没法子多说什么。食物总是得因地制宜,而我们期望的,“原汁原味的美食”,往往并不一定符合我们的习惯。德国人的一个笑话是:一个德国人爱吃土耳其旋转烤肉,总是嫌德国的改良烤肉不正宗;真去了伊斯坦布尔回来,一路大骂,一头扎进德式旋转烤肉店就不出来了。
——血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