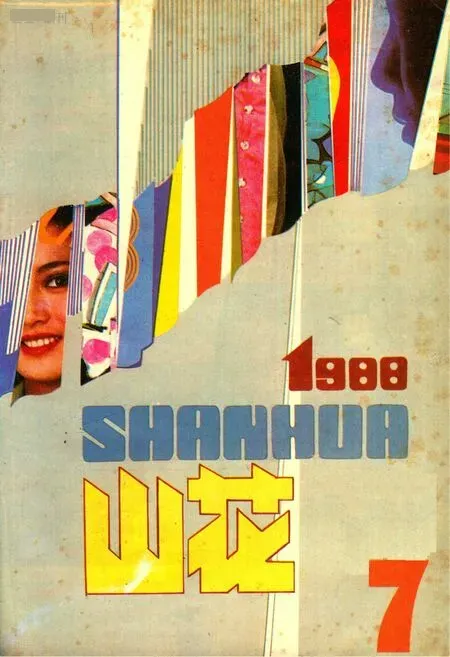在成都
凌仕江



一
我一直把过去生活的地方当作异乡,包括年少的故乡,甚至包括青春的拉萨。我的回忆就像多少年前布达拉宫周边长满的比人还高的三毛草,它们不仅长在野风浩荡的大地上,还长在藏族居民的屋顶上,它们的形象与气质受了音乐的影响,每每想起它们的样子,我就会想起雪域大地上的劳动者无处不飞歌的火热场景,尤其是那首充满泥浆磁场的《打墙歌》,当然还有油得可以照见自己脸孔的石板巷子,它们与那些窗前环佩飘带的古老民居组合在一起,总有一些神秘莫测的逆光从裂缝中极不规则地延伸出来,将你吞吞吐吐、重重包围。这时,你会发现人生只有突出重围之后才又渴望能够继续多历经几道裂缝,至少它可以让光照进现实。
而那些被佛眼擦亮的石板和裂缝则是历史的基础。
后来,我离开拉萨,去西藏的后花园成都定居。我最初进入成都时,这座曾被称为芙蓉国的古城到处都在修路,地面上坑坑洼洼,空中不分昼夜地传出建筑工人的喊叫声与机器轰轰烈烈的操作声,叹息的路人们常常守着尘埃感慨万端。于是有人说:现在进城难,出城更难。与拉萨的安静相比,成都好比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都是坑,一个比一个深的坑,看着脚尖就打闪闪,而拉萨则是一朵安静中绽放的向日葵。据说,我走后的拉萨也被到处挖得坑坑洼洼,对于那些天天去八廓街朝圣的虔诚者,他们只能绕道而行了,我还想朝圣肯定是不存在绕道的,朝圣之路原本需要的就是曲折精神,因为地暖的植入必将改变一片地域的冬日生活。
我在成都想拉萨的时候,拉萨的那些低矮的房屋会显得更低、更矮,就像小时候故乡的篱笆墙,上面总有一些野花和蝶在诉说岁月的轻与重,有时想念拉萨,一个人就会马不停蹄地想起遥远天边那座让我人生最初见识孤独的哨所,因为哨所与拉萨有一种孤独质感的颜色——金色。不同的是哨所的墙壁上趴满了随风摇曳的喇叭花。而拉萨的墙壁上到处画着太阳、月亮、祥云、经幡,以及佛眼,它们以静坐的方式在阳光与飘雪里呈现大美与智慧的影子。而就在此刻,支撑我想象拉萨的成都建筑却在争分夺秒地长高、长大、长得密密麻麻,长得我路过文殊坊那一面长长的红墙只能停下来张望。文殊院外的文殊坊是成都近年出现的新街景,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同锦里与武候祠。过去自然纯朴的土街,如今全被铺上了规范又光滑的石板,这是现代都市商业与旅游并轨的视野模式。在这条长长的坊道里,各类门市牌匾看上去十分别致与统一,但少了过去大旗与烟火在风雨中飞舞的野趣与旧味。不过“坊”与“院”倒是互不干涉,即便被现代工艺做旧了的“坊”依然淹没不了那“院”往日的宁静,喧哗的终归喧哗,而宁静的风景独属内心,去文殊院寻找心灵隐地点燃香火的人始终不受文殊坊骚动的商业之风牵引,他们轻轻地进入一扇木门,并不见了踪影,那“嘎——吱”的关门声像是从远古大地传来,其实是风替他们挡住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滚滚尘埃,而那些人流长河中举着油纸伞的背影,则成了另一些手持数码人的风景,他们在明处的文殊坊消费彼此的目光,而暗处的文殊院在他们的影子里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标点符号。
大约是上世纪的一九九七年与一九九八年之间,我在文殊院两次见到中国十大高僧之一的宽霖法师。一次是大雾笼罩天府的冬日,经人引领,我在路边买了一束高高的腊梅去拜见他。当时披着袈裟的法师与一个穿着肥大军衣的少年谈了些什么,记不太清了,似乎提醒并告诫过我:茫茫人生路,不必与人争,朝着你的灵性走,须持之以恒……记得临走时,法师送了我几尊开过光的小金佛。距此不到一年后的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宽霖法师世缘告尽,在此圆寂,世寿九十五岁。
不懂法师的少年,法师就在少年面前。待读懂法师漫长又苦难的过往岁月时,那个少年却无缘再与法师面对面说话了。至今,依然仰慕那些灵魂特立独行的少年已步入半生为人的自省年境,我坚信过去所走过的路,或多或少有着法师灵魂的关照。每每路过老法师圆寂的文殊院,我就会刻意停在木质的院门外驻足片刻,欣喜一个人途经的某些迷惘还可以被另一个世界的他看见或指引。望着那些伸出红墙外的青亭楼阁,思绪如香烟缥缈,想着法师在文革灾难中为保护唐僧顶骨所付出的种种艰辛,不免对院里住着的文殊菩萨心生几分敬意。
成都是唐僧的受戒地,1942年南京发现三块唐僧顶骨,其中一块便送到了成都文殊院。如今宽霖法师已去,唐僧顶骨还完整无损地存放在文殊院里。当年很多与宽霖法师来往的老街坊因为文殊坊的改造而搬到了东郊。
如今的东郊已然成了工厂解体的记忆。随着城郭四面八方的扩张,那一片搁浅多年的旧工厂像是一下子找到了用武之地,被打扮得像是历史的战火中保留下来的博物馆一样,但里面承载的并没有枪杆与弹药,甚至就连一点硝烟味也没有,只残存着几颗镙丝与铁锈般的记忆,这种记忆,之于曾经在这里废寝忘食依然拦不住下岗指令的工人来说,最为疼痛。书吧、动漫、影院、音乐、酒吧、艺术超市……以及各类吃府隐盖不了他们已经装满车间的疼痛。
一个晚冬的下午,我在这里的无聊书吧会见了成都本土的一位女作家和一位女诗人,女作家对成都的吃喝玩乐可谓了如指掌。而女诗人则见证过成都诗坛的起起落落与分分合合,还参与了其中一些诗歌流派的组建,她至今愉快地书写着城内的物是人非。在这里,我没有找到前来此地瞻仰那些高烟囱的旧厂人,只遇到几个奥特曼一样造型的动漫人物,他们身着夸张的服饰,留着古代人的长发与胡须,手上持有长矛与短盾,在人群中追杀、飞奔,他们的样子已做好穿越的准备。
那一刻,我停在原地,望着灰色天空中耸立不倒的褪了红色的高烟囱,像一个迷路的小孩!
二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年少时,读到这样的句子而刹不住无边无际的想象,我想被花朵包围的城市有着怎样令人陶醉的芳香呵。那究竟是一座人的城市,还是一座神的花园?它的富丽堂皇与自然闲适曾一度让我对一个未曾到过的地方执念不忘。那注定是我当时的远方,远方之远,之于当时我所在的蜀南偏僻乡村仿佛不在同一个世界。
然而,二零一一年因工作,这句子被我激动地写进了成都重大晚会的台词。锦官城是成都西汉时期的别名,后来又被缩写为锦城,因此当年穿城而过的美丽锦江自然也就成了许多人一去不返的忆念了。我相信,巴金先生在上海外滩的晚风中漫步时也曾忆念过锦瑟漫漶的锦江水,因为水边系着他的童年和风筝。在成都,不是每代人都有资格忆念锦江,但锦城里派生出的经典诗句,却可以成为时间的文明共享。
真是无独有偶,现如今我工作的地方,恰巧紧挨着为锦官城写诗的杜甫所在地——草堂。在草堂里生之忧愁、活之忧民的杜甫每天吸引着他的粉丝前来造访,当然也有很多不是他粉丝、更不是诗人的家伙打迢迢北方赶来找他,只因他们与他葆有一份共世的愤俗情怀。换言之,我也可算作杜甫的邻居,但我不是他的粉丝,因此谈不上知根,我既不忧国,也不忧民,我不刻意亲近他,也不十分疏远他,我就坐在他的草堂旁边,朝九晚五聆听花香鸟语,聆听那些在多功能厅排练舞蹈时重复传出的《卷珠帘》等流行歌曲,我越来越不把流行歌曲当回事地听着,听着只是听着,不受它们所谓中国风与小清新配种的丝毫影响,我知道我内心已深深爱上那些结实又深沉,且美轮美奂的美声唱法,我在歌声里不再产生摇头晃脑的幻觉了,只顾默默地做着一个小公民份内的事情。
但我不可拒绝地羡慕杜甫才华,这是无须与内心争辨的实事,即使一个毫无文学修养的人面对杜甫的诗也有可能寸生羡慕,就像植物在季节的更替中挡不住天灾照样地发芽,只是像我这样的植物之于杜甫,发芽的过程十分缓慢。尤其是每每走在清华路两旁那些刻有杜诗的岩灰石板上,走着走着,便突然停下来,驻足凝视: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这首名为《江村》的诗写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杜甫经过四年的流亡生活,来到了还不曾遭到战乱骚扰、暂时可以保持宁静之心的西南富庶之乡成都郊外的浣花溪畔。当时,他依靠亲友故旧的资助而辛苦搭建的草堂已经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饱经离乡背井的苦楚、备尝颠沛流离的艰虞的诗人,终于有了一处可以借景抒情的安身之所。
时值初夏,浣花溪畔,江流曲折,水木清华,一派恬静幽雅的田园景象。他在江村之上,放笔咏怀,愉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此诗本是写闲适心境,同他的许多诗作一样,写着写着,到了尾声,就是落寞与不欢之情,这也是我不想带着怅怅然续读他诗篇的重要原因。之于杜甫和他的诗,我想大概能够感受他诗风的调调就行了。杜甫很多登临即兴感怀的诗篇,无不令人心生沉郁,原本有着忧郁气质的人儿,再多读他的诗情何以堪?
于是只好止步,蹲下身来,贴着大地的心,凝思,忽然抬头,仿佛遇见了陌生的老朋友,而我们之间没有多言,只有意会、点头、微笑,轻轻地伸出手去,可我握住的只有芙蓉树上随风落下的粉色花瓣,摆摆头,无法把刚才读到《江村》而产生的感想,传递给他。匆匆转身,加快步履,像认错了人一样头也不回,如此地决绝。
我的行为就像一场生不逢时的风对一场尚未降临就已告别的雨持了意境的否定。
虽与杜甫邻居,但一年之中却难得造访诗人的草堂,我更愿意保留一份清寂的氛围让给更多的诗人去思和忧。二〇〇三年十月,著名作曲家谷建芬女士来成都采风,两月后,谱写了一曲《走进草堂》,在音乐意境的广阔天地里,成都被喻化为一座葱葱绿绿的草堂。歌声中,我听见萦绕茅屋周边的那些竹子在秋风中拔节,银杏树上结出的白果在阳光下劈啪作响,同样与《三国演义》的片尾曲《历史的天空》那首歌一样,依然是歌者毛阿敏的演绎,时光纵横,清凉中透着大气磅礴的神秘与质感,悠远的旋律直抵人们的记忆,听者仿佛可以从歌声中看到迎面走来的不是今人而是古人,千年光阴,古人与今人在优美的旋律中完成了一次美妙的时空对话。
每每午后,或黄昏,独自漫步,亦或邀上三两好友走在草堂红墙里铺出来的竹影下,看路边或溪水边盛开的满树樱花,有时也看见几只白色的大鸟站在曲折的水边,或葱绿的树梢上,它们喜欢这人世间的成群结队吗?而在水边看白色大鸟的人倒真不少,除了头戴草帽聚精会神目视水面的掩面者,很多是艺术家,他们手持长枪短炮的摄影器材,为了大鸟们的一次飞翔或筑窝,有人不惜在此守候三天三夜。
当然,我也看见过在杜甫草堂门外守候林间小鸟的人——那是一对来自加拿大的年迈夫妇,他们各持一部长焦距相机,在阳光下学着鸟的叫声,痴望着红墙里泡桐树上跳跃的小鸟,欣喜若狂……我想:没错,这里真的就是红湿处,这里就是锦官城。
在认定锦官城的同时,那一刻,我把自己想象成了异乡飞来此地栖居的鸿雁!
三
有一回,成都土著同事陪着我逛浣花溪公园。路过杜甫草堂正门时,他甩甩头,说:莫进去,杜甫草堂白天没啥好看的,到了晚上才好看呢。同事所说的“好看”充满了悬念的意味,我疑惑地望着他求解?几步之后,他似有若无地回过头对我说:晚上,里面到处是监控器,保安也不敢动荡。
我说,这有啥吓人的呀,再吓人也不可能有抚琴路上的王建墓吓人吧?毕竟那儿只有一座巨大的坟莹,谁愿意在夜晚与坟堆堆相遇呢?不像杜甫草堂里,一年四季,花红柳绿,小桥流水,荷花绽放,鸟落民间,真是芙蓉国里的小天堂。
同事一本正经地摆摆手,说:王建墓倒不吓人,里面根本没有埋人,那只是一座衣冠坟。他说完这一句,便没有了下文。然后开始抽烟,边走,边抽,在我们身后,一缕烟带空尘绝后。他的眼神在斜视草堂林影,稀薄的阳光打在玻璃镜片上,让他的眼睛有些闪烁迷离。
我学着他的样子,望了望树荫掩映的杜甫草堂,想了又想,莫非里面的保安人员能在夜晚看到行如风坐如钟的杜甫?或者还能遇上一个叼着长长烟杆,抽着叶子烟,弯着背不时咳嗽几声来此探访杜甫而找不到门的老文青。这样的结局让我很是兴奋,能与诗圣杜甫相遇,那是何等的奇遇呀,可我不知道这究竟有啥吓人的?
同事挤了一下眼睛,转过身,神秘地指着河岸边的别墅群,补充道:十多年前,这杜甫草堂离城区还很远,周围到处是田坝坝,一年四季,春播秋收的场景,真是美不胜收……这样的景致的确很诗情画意,加之有杜甫、和尚、农夫,可我总感觉同事的话中弥漫着几重待解的答案,他始终没有说出他所知道的草堂真相。不过,他最终告诉我,以前的草堂里不仅住有杜甫,还住有和尚,以及浣花夫人。成都的老人们叫这里为草堂寺,仅从此名而言,我曾猜想和尚住进草堂的历史是否比杜甫还早?当然这样的猜想很快被江南才子诸荣会否决了,他说既然叫草堂寺,就应该是先有草堂后有和尚了。至于浣花夫人,众所周知是杜甫离开草堂之后住进那所茅屋的了。
后来,经多方访问与考证,得知南北朝时期,和尚便在此念经了。那时,这里一定是川西平原上最宁静最祥瑞的一块圣地。显然杜甫之于和尚,当是后来者。他们之间是邻居,依杜甫的性格,恐怕与和尚的相处是不会太容易的,毕竟他信奉的只是一个人的诗圣,而不是闭着眼的和尚念不完的经卷。即便如此,在我看来,唐时的草堂寺,和尚是诗性的和尚,诗人是佛性的诗人,黄昏或初晨,这里当是木鱼声声、经文低语、鸟儿啁梦,香火旺盛,住在隔壁的杜甫难道不会因此而产生挥毫欲诗的冲动?同样,听见隔壁杜甫的吟诗,和尚也有可能停下手中的经卷,一番诗意涌上心头……
不久前的一天,在年轻的藏族画家单巴的画展上,遇见一位杜诗的崇拜者,谈到这种可能的几率,他完全一副自信的姿态。他说杜甫的诗歌当中一定有表现个人与和尚之间的交往,遗憾的是这位杜诗的粉丝当时喝了二两烧酒,抒了半小时的情,也未能准确背诵出哪一首诗,他只好让我去《杜工部集》里去查找了。失望之余,我想象过,草堂寺里的和尚,当时面对杜甫这样一位诗人邻居,究竟持有怎样的态度?是欣赏他的诗?还是像当下一些艺术家在一起彼此不屑一顾?
由此,忽然想起曾经工作单位里的一位诗人。那天,诗人正埋头面对电脑专心致志地作诗。而另一位音乐工作者同在一个办公室。他在旁边的电脑上打歌谱,而且是使劲地敲打键盘。诗人很无奈,面对电脑坐那么久了,还写不出一句满意的诗来,于是愤怒地站起身,对音乐工作者说,你能不能小声一点,没看见我在写诗吗?音乐工作者大概知道诗人的脾气,一声不吭地甩门而去。诗人紧追几步,一把拉住音乐工作者,扬手便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还朝他疯狂地怒吼道:你知不知道,你甩门的声音严重毁坏了一个伟大诗人积蓄半年的灵感,五个手指像五根白骨清晰地印在音乐工作者脸上(实际上,多年以后,诗人回想起那五个指印,完全有可能是打在自己脸上)。很快,音乐工作者在抚摸手印的同时,重磅一拳击在诗人脸上。诗人顿时眼睛流血,倒在血泊之中……
四
是一个半阴半晴的中午,同事带着我从草堂北门进入其中,直接将我领到了一座杂草丛生的坟前。他叮嘱我先要拜谒一下坟的主人。我双手合十低头的一瞬间,发现一块小石碑上涂着一行红色的小楷:上光下荣智公老和尚之墓。时间是1982年清明。
我问曾经的寺庙在何处呢?同事摆摆头,耸耸肩,说他在此上学时寺庙就已不见。于是我们随处散步开去,同事对草堂里的景物简直是如数家珍。到了藏经楼、万佛楼面前,他站在原地开始抽烟,让我独自上楼去看风景。我爬上楼,看见他还在原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仰起头,把一个个肥瘦不一的烟圈圈吐给天空,他脸上掩隐着一丝不易泄露的草堂天机,而树林环抱的小河里肥得难以动荡的锦鲤在高空的视野中泛着金闪闪的光,四周是葱葱郁郁的银杏叶子和嫩绿中透着清光的竹子。
从木质结构的楼亭上下来,转身便来到同事曾经上学的地方。如今座落在二环路边的成都市艺术学校的前身成都戏剧学校的教室至今还在眼前的草堂里安静地坐着,只是它们成了一些存放杂物和草堂工作人员办公的地点。这里曾经是男生宿舍,那里是琴房、杂技的练功房、上文化课的教室,而围绕这教室的那一面青色的墙,不知同事翻过多少遍……那些拱门里的竹节上刻着的字已经随着竹子的成长而难以辩认,他不停地指给我看。然而,这些尚存的躯壳与印迹已成为一个即将步入中年者最青春的记忆。
五
应该说,我已经在为适应锦城生活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了,当然多年来成都本土的文化决策机构信奉的则是“成都表达、表达成都”的文化形式逻辑,对于一个创作者这似乎多少有些自闭,即使这个地方每天都有建筑如同橡皮树一样疯狂地长起来,但它毕竟代表的是一种文明的生机、繁荣的彰显。它表面的时尚并不影响我内心渴望的安静,每当上班或下班,坐在快速高架线上,独自构想着诗人杜甫与唐朝命运,身边无数人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许多史书记载或评说,认为杜甫的一生穷困潦倒,受人接济度生。言下之意,带着怜惜或悲悯。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说法,实际是缺少设身处地体会的。在我看来,杜甫能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写诗游吟自在逍遥,其生活条件并不可能差到穷困潦倒的地步。任何将杜甫生活片面性的断义加以放大化的宣传都可能导致人们对杜甫狭窄的认识。一般的穷人在那时即使有才可能也得每天为对付生计而难以实施写作这件过于高尚的事情!将历史倒过来看,杜甫简直称得上唐时明月下的贵族一类的诗人了,他既是诗人,又是官员,不仅有那么多友人支持欣赏他,还有相当级别的权贵关照,任他在茅屋里为秋风所破歌唱,保护他安心创作诗歌的灵感,这是何等的待遇呵。
今天中国那么多诗人,谁又享受了这样的待遇?
成都在四川的版图上堪称诗人最多的地方,即使将成都诗人放到全国的诗歌版图,其诗人们的重量和数量也可排在当今诗坛相当靠前的位置,可至于这里的诗人享受了多少真正像杜甫一样的待遇,只有诗人们自知。这事倒让我想起另一位同样伟大的人物来,他应该算不上诗人,但他在文学地位上所享受的待遇并不比杜甫差。
在世界的南拉丁美洲,有一个叫马孔多的小镇,那里住着一位神秘人物。一直以来,很多人去到那里找寻他的踪迹,可常常被当地的人们捉弄而走错路,故意不让人见到他——这个神秘人叫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写作才华不仅获得哥伦比亚和整个南美大陆读者的广泛认可,还得到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极力推崇与关照。在古巴革命刚胜利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赶到哈瓦那采访卡斯特罗,从此他俩成了私交。卡斯特罗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昵称加博(Gabo),他俩似乎真应了那句老话一见如故。为了文学写作,卡斯特罗拨给他一辆奔驰280,在哈瓦那市中心给他一所带游泳池的别墅,里面配备有四个佣人和一个花匠,还有一条只有极个别接待外宾的宾馆才装的国际电话线。古巴人都知道那是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房子。上世纪七十年代之间,马尔克斯就在哈瓦那写作,卡斯特罗常去他的别墅里喝酒聊天。他们之间无话不谈,政治与文学,权力与创造力,仿佛成了两个男人的魔幻现实。特殊的生活条件,之于一个靠文字实现自身价值的人来讲,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够高大上了吧。
在这之前,我曾有过一段坐地铁去一个名叫“鸟巢”的地方上班的时光。我在“鸟巢”并没有发现有何神奇的鸟,不过有一只像鸟一样的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阴影,那是一只官二代出品的鸟,他善于约束与指使他的年长者做一些工作之外的事。遇到我就偏不做。那只鸟欲对我动武,可我始终没予以理睬。现在想来,此时将笔尖顺然指引一只鸟是不是太浪费笔墨了。其实,这“鸟巢”与北京的“鸟巢”只是形状相似罢了,它怎能与世界级奥运场馆去比呢?显然,它们不具可比性,因为功能的不同,人们审视尺度也决定着不一样的方向。只是我住的东郊离“鸟巢”较远些,我现在坐高架线去杜甫草堂隔壁上班只需要二十分钟,高架线与地铁有一种相同的风景,他们看上去与我素不相识,但他们都能心安理得地接纳我保留在内心的孤独与想象,就像成都这座城市接纳所有异乡人的孤独一样。我的想象与他们的生活无关,虽然我们每天都穿行在同一条路上,有时望着他们长时间把自己的注意力交给手机,我觉得他们关心手机里的事情远远超过了关心这座城市里的自己。
那一刻,我感觉成都之于诗人是一座寂寞之城,之于一些鸟人,很可能是一场接一场的地震风波,之于芸芸众生,它适宜用于麻将与火锅伴随人这一辈子的回忆,够了,足够了。
如果在我过去生活的拉萨,我只要走出军队大院,就不能这样独立地想自己的事了。我一定会不停地遇着向我微笑或打招呼的藏族人,我只能打断我正想着的事,与他们说几句有意义或无意义的话。我在拉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扎西德勒!(吉祥如意)。”有时,是对阳光下走来的一条狗说话。拉萨也有鸟人,只是那些鸟非官人出品,而是军队的产物。在成都,一般人都不愿跟鸟人说话,跟狗说话的人家倒不少,他们对待狗的生活意见,远远超越了对待人,他们当中有为狗过生日的。实际上,据我所知,那些为狗过生日的人,根本记不住自己父母的生日。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在拉萨,更多的时候,没有人可遇见,但你却能够听见风声——它在给你传递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成都对我来说,是一座流水缓慢的城市。因为在这里,你看不到扬帆远航的船只。更多时候,你是一只寂寞的旱鸭子,总在自己的影子里遥想海的颜色和声音。因为水可以承载回忆的重量。而当我与一些刚结识的友人一开口说话,他们并不会问我来自哪里,反而我会问他们,听口音,你好像来自北方?然后,才是他们对我的打量,听你的歌声和口音,感觉你是甘(孜)阿(坝)凉(山)的吧?我不置可否地笑了!
我拒绝对他们说起我从喜马拉雅来!
我不是成都人,但现在我在成都工作。过去的二十年间,我的步履一直在朝圣中迁徙,像沙漠里的骆驼,当看见雅鲁藏布江的一瞬间,那么多水都成了骆驼的眼泪。我在这座城市里习惯了深居简出,偶尔去郊外的龙泉山看那些农夫摘桃。若有人约我去宽窄巷子的时候,我就漫不经心打的去那儿,消磨一点茶水或咖啡的时光。这样的人往往不是本地人,他们多是来自遥远的外省人。我不是成都人,更没有传说的成都故事提供给外来的友人分享,我想我的孩子以后比我更尴尬,因为他可以是地道的成都人,但他知道的成都掌故将比我更少。有时,我也在想,是不是该在孩子的成长中为他注入更多接地气的城市微量元素?
相反在约见我的外来者面前,我倒像一个异乡人,而他们先我之前等待我到来的那份安然则像本地人。如果有人约我去春熙路时,我就从府青立交坐公交车下去,五个站就到了。总之,在成都我很少主动去一个被外省人想像得极为神奇又容易将人淹没的地方,多数时候,我闭门不出,宅在家与自己种植的草木说话——在家里,草木就是我独自空旷的理想国。我不要求成都要怎样,成都也不要求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是好的,作为一个作家,永远不要把自己居住的城市弄得太懂,有时,小聪明往往误了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