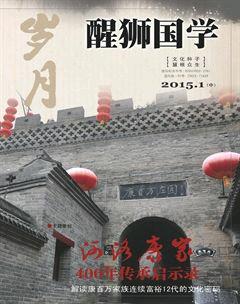高山流水遇知音
陈均
伯牙鼓琴子期会心
《流水》之曲,聆之尤以滚拂手法奏流水之音最为特出,由沥沥清泉空谷幽音渐至大江大海激荡汹涌,闻者自然惊心。考之曲意,《天闻阁琴谱》有描述曰:
“起手两三段叠弹起手二三两段叠弹,俨然潺缓滴沥,响彻空山。四五两段幽泉出山,风起水涌,时闻波涛,已有汪洋浩瀚,不可测度之势。至滚拂起段,极腾沸澎湃之观,具蛟龙怒吼之势,息心静听,宛然坐危舟,过巫峡,目眩神移,惊心动魄,几疑此身已在群山奔赴万壑争流之际矣。七八九段,轻舟已过,势就徜徉,时而余波激石,时而漩洑微沤。洋洋乎,诚古调之,希声者乎。”
《流水》之曲,现为大众所熟知,大约肇因于此。因如此听来,深者知其深,浅者知其浅。即使毫无古琴经验的听众,依然能知晓此曲是状流水之貌。
但是,如此一来,还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慨么?
一位朋友曾闲谈说:伯牙子期之遇,正因为“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弱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列子·汤问》)。所谓琴为沁,沁为心声,伯牙奏《高山》,必是少人解之。伯牙《奏流水》,定是无人知晓。所以当子期聆之,而道出伯牙之所志。正如《牡丹亭》里杜丽娘柳梦梅梦中初遇,“相看俨然,早难道好处相逢无一言”。
假如《高山流水》即如今日之《流水》,天下知音者何止千万。哪里还会有伯牙子期的“知音”神话?
千载之下,想象昔时伯牙奏《高山流水》,子期聆之会心。如元代画家王振鹏所绘《伯牙鼓琴图卷》,二人皆坐于石上,一人抚琴,一人静听。三小童,分捧香炉、书卷、如意。真真是一幅文人幽人图也。哪如现代音乐厅,借助音响散布,而将观众淹没于声浪之海中。
再看宋徽宗《听琴图》,演奏者虽是皇帝,听者亦只是三二人而已。虽然艺术史学者纷纷解读其政治涵义,但知琴之道,知音之说,亦只是在寥寥数子而已。
而且,在《吕氏春秋》里,当伯牙知子期去世后,便“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因此,“知音”之难,不仅在其稀少,而更在于“难再得”。故而有“人琴俱亡”之悲。
根植文化得悟山水
由伯牙子期《高山流水》这则公案引申的“知音”概念,不仅成为古琴文化的象征,亦是中国文化最根深蒂固的基因之一。因之,为后世文人反复吟咏、低徊不已。如嵇康《琴赋》云“伯牙挥手,钟期听声”,而岳飞《满江红》则叹“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声声不绝。
古琴虽传世约四千余年,由宫廷、文人至贩夫走卒,莫有不爱之人。但总体而言,仍是阳春白雪之艺术。笔记小说里偶有戏谑,如写一人携琴,至某地弹奏,听者哄然而散,仅有一人听完,且垂泪。奏者以为遇知音。不料一问,听者答道:一抖一抖听起来像弹棉花,故想起已去世的母亲当年弹棉花云云。
不知此则笔记是嘲讽琴者技艺之劣抑或是古琴与一般社会文化之隔阂。——要是如今之《流水》,岂非是皆大欢喜。
古之《高山流水》与今之《流水》,乃有一大变化。其变正在于增入滚拂之流水。据传,此法出自清末和尚张孔山,由他而流布天下。今之弹奏《流水》之琴人,皆是出于此《流水》,或是此派《流水》之变化。
此变化,不仅仅是一首乐曲的变化,更是古琴指法和技巧的变化。因弹奏此《流水》,古之指法不能敷用,张氏创造了更多的技法,因而使其呈现的面貌为之一变。《高山流水》从摹写高山流水之意,转变为描摹高山流水之形。
古琴风格亦为之一变,从言志之高古之调变为愉悦大众的俗世之曲。或者,文人依然能兼顾言志与愉人,但更高级的聆听的耳朵恐怕亦因此丧失。这也是如今现实中喧嚣纷攘的古琴界之象征了。
琴家杨典曾论及《高山流水》可能之变,即从《高山》中看出流水,从《流水》中看出高山。此变即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之悟,转于古琴之琴学,而期望未来会有更高级的古琴文化吧。
甲子立冬午夜,坐听《流水》之曲,计有管平湖、顾梅羹、卫仲乐、吴文光、杨典诸版。此时正移现代充电油灯一盏于案头,窗外寒风呼啸如虎,室内暖气乍起。激烈交荡之气氛,恰与这《流水》即兴之音相合。
编辑/林青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