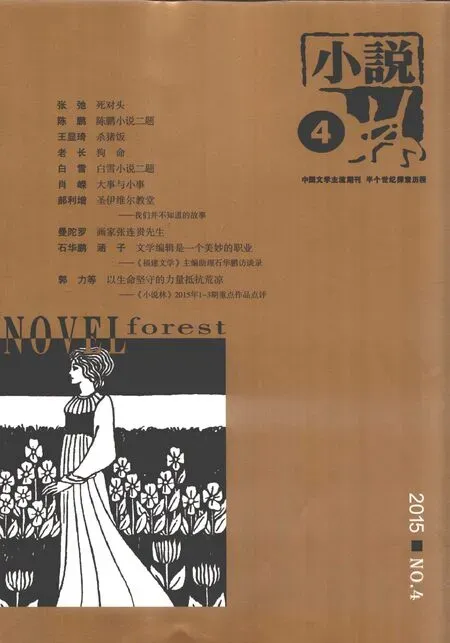文学编辑是一个美妙的职业
石华鹏 涵子
石华鹏:1975年5月出生于湖北天门。200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五届(文学理论与批评)高级研讨班。1998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文艺报》《文学自由谈》《文学报》《长江文艺》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100余万字。
曾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六届冰心散文理论奖、首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新人奖、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长江文艺杂志社“武当旅游散文奖”、江苏省第21届报纸副刊好作品奖。出版随笔集《鼓山寻秋》、评论集《新世纪中国散文佳作选评》。
现任《福建文学》主编助理。副编审。
涵 子: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生。
涵 子:你知道《小说林》“名刊名编访谈”这个栏目吗?读过吗?
石华鹏:知道。读过一些。因为是对编辑同行的访谈,尤其是名刊名编,还是很关注的,想看看别人是如何当编辑的,尤其是如何当成名编辑的。编辑是幕后人物,这个访谈让编辑站到前台来,亮亮相,意思是说编辑这一行当对文学的发展还是有些作用的,另外访谈编辑为观察文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是一个有创意的栏目,而且连续办了好些年,《小说林》有眼界。
涵 子:介绍一下你的编辑经历和你工作的刊物。
石华鹏:我本来不想接受这个访谈,因为咱心里很清楚,咱自己既不是名编,咱服务的刊物也不是名刊,如果也来这个栏目“凑热闹”,是名不正言不顺,不合适。但朋友诚邀,再拒绝就是矫情,感情是大事儿,访谈是小事儿,那就小事儿服从大事儿。
我2000年从华中师大中文系毕业,一脚踏进《福建文学》编辑部,到今天,已经做了十五年文学编辑。在学校时做过广播台的文字编辑、编过刊物,算是有编辑渊源。我到《福建文学》做编辑时,文学杂志已经“尴尬”起来:订数下降、办刊经费紧缺,所以文学编辑也由过去的“香饽饽”变成了“冷馒头”。一个例证是,我找对象找了好久也找不到,老编辑感慨地说,要是在过去,女孩排成队伍要找文学编辑。
《福建文学》与很多文学刊物一样都很老牌,1951年创刊,到明年(2016年)六十五岁了,我最近正在参与编一本《〈福建文学〉1965年小说典藏》,发现福建省内和省外很多作家都在《福建文学》发表过作品,尤其是福建省内的活跃作家没有哪一个没在上面发表过作品。所以说把眼光放长远来看,比如以五十年为一个刻度来看,一本刊物的作用和意义还是蛮大的。我们现在有些人目光很短浅,总认为文学刊物没什么用处,嚷嚷着要给刊物“断奶”,要把刊物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浅薄的表现。
涵 子:据说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文学刊物的日子都慢慢好起来了,是真的吗?
石华鹏:感觉是真的。别家刊物的真实情况怎样我不确定,但我们刊物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一是办刊经费、文学活动经费有了保障,二是稿酬也提高了不少。以前有两个压力,一是找钱的压力,二是找好稿的压力,现在主要压力在第二点上。不差钱了,就要把文学质量搞上去。追求文学的深度和广度,把社会效益放在前面,这是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刊物在办刊思路和实践上的根本变化。由此,《福建文学》也提出了“更纯粹、更现实、更未来”的文学之路。今年以来,《福建文学》加大投入,通过加大力度约名家力作、推介新人等举措,刊物质量有大的提升,一些小说被转载、获奖,这个办刊路子也得到了管理者和读者、作者的首肯。文学刊物终究是以“文学品质”立足的,这点把握住了,就会处变不惊,就会对未来有所交代。
涵 子:文学刊物的日子是改善了,但与活力四射、前景无限的网络阅读发展相比,文学刊物的数字化推广好像慢了一步,你认为是这样的吗?
石华鹏:你说的没错。与当下活力四射、前景无限的网络阅读相比,我们的文学期刊在这一进程中就显得“老土”和“过时”起来,其面临的不足和短板也毫无掩藏地显现出来。具体表现为:第一,网络推广不专业、粗糙化。很多文学期刊的网络推广要么简单地外包给期刊网络,被动地不透明地接受一点微薄的“点击阅读费”,要么就是本刊的文字编辑“业余地”承担起网络推广的任务,尽管很多刊物建起了微信平台,建起了网站、博客,但是推广效果并不算突出,但可喜的是步子已经迈开了。第二,忽视网络品牌的建设。文学期刊的品牌化是网络阅读的最大竞争力,但如何从众多网络文学期刊中脱颖而出,被读者记住,被读者信任,是一项需要创造力来解决的网络推广难题,而眼下很多文学期刊一是没有意识到此问题的重要,二是暂时没有人才来解决此问题,这是一个迫切且漫长的投入,文学期刊要登上新一拨网络发展的快车道,不能再错过。第三,缺少文学期刊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大视野和大举措。市场、资本、传媒、科技的融合正在主宰网络文学的发展,而很多文学期刊还是在单打独斗,还是在孤兵作战,发展视野和发展举措都有限,当然如何去融合、壮大不是一两家刊物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整个顶层设计的大问题。
文学期刊数字化、网络化阅读的路是必须走的,脚步才刚刚迈开呢。
涵 子:很多文学编辑除了是编辑外,还是作家、评论家,你写过许多尖锐的评论,还获过评论奖,也是一个评论家。你如何看待“编辑作家”“编辑评论家”这种现象?这几种身份之间是冲突多,还是促进多?
石华鹏:我认为做了编辑之后,再成为作家、评论家,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水流到了水渠也就成了。我们很多优秀的作家、评论家都做过编辑,写小说的贾平凹、毕飞宇、阿来,搞评论的李敬泽,等等,都是编辑起家的。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儿呢?首先,无论编辑还是作家、评论家,都是与文学打交道的,编辑解决什么是好作品什么是差作品的问题,作家解决如何写出作品的问题,评论家解决这作品有没有什么价值的问题,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是文学中人吧,身份彼此渗透,彼此交替也就成了自然的事情。其次,文学的根本问题是何为好作品、如何写出好作品的问题,因为编辑是职业读者,如果编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就去写吧,写出好作品——于是就成了作家;如果写不出好作品,那就去评判吧,就去说三道四吧——于是就成了评论家。
而且编辑成为你说的“编辑作家”“编辑评论家”,是有自身优势的:编辑见多识广,每天读很多稿件,哪篇能用,哪篇不能用,要做出判断,所以编辑既见识过好的,知道好到了什么程度,也见识过差的,知道是如何差的。我写点评论,算是个所谓的评论家吧,很多学院派的评论家瞧不上我们,说我们是“野路子批评”,没什么学术性。其实我认为这种说法恰恰是表扬我们,“野路子”多好啊,生猛、新鲜,比老气横秋,比不知所云的学院派靠谱。我做评论有点自信,这点自信唯一的根源是我是一名文学编辑,很多人都知道作品的好,好在哪里,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作品的坏,坏在哪里?是如何坏去的?但我告诉你,编辑读过很多坏作品,而且知道是如何坏去的,这是编辑成为作家、评论家最大的优势——既然知道是怎么坏去的,那么自己写的时候就绕道走了,少去犯错误。
总的来说,编辑职业对成为作家、评论家是促进多,冲突少。当然冲突也有,编辑做久了,容易眼高手低,就像美食家,他会品评,但你要他当厨师,他当不了,有些编辑能说会道,但写不了,写不出来。
涵 子:你认为编辑与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石华鹏:前段时间,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让我琢磨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上海的一个研讨会上批评中国的文学编辑,说“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 他认为这一点“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编辑“给作家提意见,修改之后出版”,是“美国出版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他甚至还推论,因为“中国没有严格的编辑把关”,“因此小说有毛病也就无法避免了”。
中国的文学编辑景况如何?究竟是不是如葛浩文所说的呢?琢磨了些时日后,我写了篇文章——《编辑与作家:愉悦或尴尬的合作》。我的基本观点是:编辑与作家是一种颇为微妙的亦师亦友、亦诤亦佞的关系,编辑与作家的合作呢?是一种时而愉悦时而尴尬的合作。要细细解说,话就很长,简单说说吧。
文学编辑——无论中国外国、无论杂志社出版社——主要做这样两件事儿:一是发现新人;二是寻找好稿件。
发现有写作潜质和市场潜质的新人、新作,是每一个编辑孜孜以求的事情,尤其是对那些在写作上刚起步、发表无门的文学新人,或者写作了多年仍无法打破退稿“魔咒”的文学老人,如果编辑有眼光有耐心,发现了他们的写作可能性,在此刻施以援手推他们一把的话,那么有一天当这些人成名、成家时,一段文坛“伯乐与千里马”的佳话便会就此流传。
这样的故事很多。比如莫言撰文专门提到的“我永远不敢忘记的毛兆晃老师”。莫言当年在保定当兵,给保定《莲池》投稿,《莲池》编辑毛兆晃老师感到这位初涉文学的年轻人与众不同,于是写信把这位爱好写作的年轻战士约到编辑部改稿。改稿后,莫言的处女作小说《春夜雨霏霏》就在《莲池》第5期上以头条发表了。
初涉文学的新人是编辑意见忠实的接受者,他们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着这个新鲜而陌生行业的一切知识。这个时候编辑与作家的沟通是有效而顺畅的。在一个作家还是新人,需要编辑提携的时候,编辑这个时候是最能行使自己职能的人。改稿交流,不是说编辑有多么好为人师,而是他们求贤若渴的心情和见多识广的文学经验向文学新人的一个表达。要知道,发现新人是一个编辑的乐事。
改稿至今仍是编辑的基本和重要工作,要知道,改稿对新人来说是迅速成长的重要途径—— 一位编辑说我从来不改差稿,改你稿是看得起你呢——那些久经沙场的老编辑稍一动手,就能让一篇稿件“活”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葛浩文所说的中国编辑“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的说法并不成立。
但是,当到了编辑要做的第二件事——寻找好稿件时,葛浩文的说法又成立了。
寻找好稿件,好稿件在哪里呢?当然在好作家、名作家那里。这所谓的“好”是指两方面:好品质和好市场。要寻到这两好或其中一好的稿件,就得去找名作家。名作家是出版的绝对生产力,是出版只“赚”不赔的法宝——赚精品力作、赚盆满钵满、赚吆喝赚眼球,无论哪种“赚”都是“赚”。但是中国的杂志社、出版社太多,彼此林立,都去找名作家,这样,名作家便成了比熊猫还少的稀缺资源。要找到名作家,拿到好稿件,只得各显神通了:打情感牌,请名家去采风游山玩水;打金钱牌,提高版税稿酬;还打一些乱七八糟的牌。
稿件终于拿到了,编辑可是高兴极了,这个时候编辑还会与作家去讨论稿件“构思是否谨慎,结构是否严密,是否有错误,前后是否一致,遣词用字是否有所变化,这样是否对得起读者”吗?还会让作家去反复修改吗?即使编辑看出来了稿件的问题,也会恭维说“太好了”“大师水准”;即使有些编辑认真倔强,让作家修改,但有些名作家爱“耍大牌”,一个字不改,心里是瞧不上小编辑的:你比我强吗?在名作家、好作家面前,编辑就如同葛浩文说的“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
我知道一件事儿,一个名作家在一本重要文学刊物上发了很多小说,编辑也算是认真、负责,发表时改动了一些词句——改得也是极好的——但是后来这位作家公开表示对编辑的不屑,这些小说在结集出版时,这位作家又花了大量工夫恢复成原样。有时候,编辑的痕迹在作家那里是不存在的。
还有很多“大腕儿”作家是瞧不上编辑的,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就是一位。有人问纳博科夫:“编辑的作用呢?确有编辑提出过文学方面的建议吗?”纳博科夫说:“我想你所谓的‘编辑就是校对员吧。我认识的校对员里倒颇有一些地道的,无比机敏、和善,他们跟我讨论一个分号的劲儿仿佛这个符号事关荣誉,当然,艺术的符号往往的确如此。不过我也碰到过一些自以为是的、一副老大哥样的混蛋,他们会试图‘提意见,对此我只大吼一声:‘不删!”不知道是才华使然还是修养使然,反正像纳博科夫那样对待编辑的人不少。
不过,还是有很多名作家、大作家对他们的编辑敬佩和感激有加的。比如2013年诺奖得主门罗,她对编辑也很客气:“基普·麦格拉斯是我在《纽约客》的第一任编辑,他真的很棒。竟然有人能看穿我内心深处的想法,这令我非常吃惊。有时我们审订得并不多,但他会不时地给我一些指引。”
编辑与作家的合作大多数时候是愉悦的,一篇小说或一本书成功发表、出版出来,双方均满意,算得上彼此之间做了一次精神交流,有缘再合作,无缘就此作别。事实是,因为一次合作,有些编辑与作家成为一辈子的朋友。但是有时候合作却是尴尬的,这尴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编辑看走眼,一部优秀作品没有被编辑发现出来,在多个编辑手中被否定,但若干年后证明这是一部杰作,这样的“走眼”故事并不少,这也是编辑日后遭到作家嘲笑的原因之一;二是作家对编辑的工作不满意,封面、错别字、印数等都不如作家意,矛盾和怨恨就此产生,彼此不再信任。
涵 子:有时看《小说月报》或《小说选刊》后面的“报刊小说选目”,发现好多文学刊物的作者都是重复的,感觉就那么一些小说作者,东家发,西家发,文学刊物是不是有同仁化的倾向?
石华鹏:我也注意到了,各个刊物作者的重复率比较高。有没有同仁化的倾向呢?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中国很大,刊物很多,这很正常,有时候某几个作家创作活跃,各个刊物都“盯上”了,所以经常见到那几个作家的名字,而且在中国你只要你混了个“名字熟”,你的稿件即使质量平平,这个刊物不发,另一家刊物也会发。所以感觉到仿佛中国的小说家就那几位。其实也不会出现同仁化,因为写作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从全国范围内到各省内,作者是不同的,只是能写出来,出名的,并不多,作者是那种金字塔形的,是流动的金字塔,下面的作者往上走,上面的作者也往下流。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有新人换旧人。这也是我们的文学刊物总是充满着活力的原因。
涵 子:一直在《福建文学》当编辑,姑且称之为地方刊物吧,有没有感觉到来自北京、上海那些国刊、大刊的压力?
石华鹏:老实说,以前有,咱就是一家普通的地方刊物嘛,与那些国刊、大刊相比,很多劣势,名气不大,影响力有限,好作家的好稿件很难拿到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文学刊物的风头都被网络文学抢去了,全国所有的文学刊物,大刊也好,小刊也好,发行量都是羞于启齿的,文学刊物归于到了正常的平静状态,大家都差不多,相反如果有些地方刊物得到的支持够多的话,还更利于做纯粹的、高品质的文学。而且现在数字化、网络化之后,地域性的差异和局限越来越小,只要你做得专业、做得好,任何地方都是中心,对文学刊物也是如此。说不定若干年后,好的文学刊物就在边缘的地方性的刊物中出现。
涵 子:有人说,现在的编辑都不看自发来稿了,是这样的吗?还修改新人的稿吗?
石华鹏:别人看不看,我不知道,但我们看,而且看得很认真,有潜力的新人的稿也修改。现在有一点很麻烦,就是投稿邮箱的稿件太多,我们小说、散文的邮箱是分开的,每次一打开都是上百封信,一个星期不看,就是未读邮件几千封,即使专门人看,有时也看不过来。其实这些稿件都是群发来的,而且质量大都一般,看一百篇能否选上一篇都是问题,所以就导致了有些编辑不看自发来稿了。
作家余华说:“我十分怀念那个时代,在八十年代的初期,几乎所有的编辑都在认真地读着自由来稿,一旦发现了一部好作品,编辑们就会互相传阅,整个编辑部都会兴奋起来。”其实今天的编辑也是如此,编辑们仍在认真地读,发现了好稿仍然会兴奋不已,只是出版业的急功近利掩饰了这一切,让人错觉编辑已经丢弃了那些本分。
有时候,我并不太愿意与作者谈论稿件的修改,因为有些作者自恃清高,认为编辑并不会比自己高明——有时事实也是如此——再者,即使提出了修改意见,有些作者也无法改出来,不如罢了,能用则用,不能用便拉倒。但是有些时候遇到一些有潜力、也听得进去意见的作者,我还是愿意说出我的真实意见——因为我相信我的意见会对他有所帮助。有些作者按照我说的意见修改,往往能改出一篇好小说来。修改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创造。
涵 子:请从一个纯文学刊物编辑的角度,谈谈你对网络文学的看法?
石华鹏:在我的思维深处,没有纯文学和网络文学之分,只有好的文学和差的文学之分。但是网络文学又是无法回避的。对网络文学,我目前的基本看法是:第一,网络文学会成为未来文学的主导,最终变成主宰。尽管现在代表严肃、精英的期刊文学和代表通俗、娱乐的网络文学以及处于两者中间的代表市场的出版社文学看上去“三足鼎立”,实则“两足”已经“跛”了,期刊文学和出版社文学的读者日益锐减,原因除了纸媒传播不敌网络传播外,根本在于严肃、精英文学正在远离读者,正在变成引不起读者共鸣的无关现实、无关痛痒、自说自话的圈子文学,尽管现在“一足”独大的网络文学还显得通俗、低端,但是它会倒逼严肃文学改变自己,以提高自己的存在价值。第二,网络文学内部会逐渐分野、分化,会形成新的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阵营。其实网络文学内部的争论一刻就没有停止过,比如究竟是唐家三少好还是猫腻好?谁的是“经典相”的小说谁的是“滑屏”小说?这种争论预示着网络会诞生自己的经典、严肃作品和自己的通俗、大众作品,同时也预示着网络会带来小说新的革命和新的经典。第三,“网络文学”这一概念会消失。现在的“网络文学”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指依靠某网站,时常更新,经过漫长叙述的玄幻、武侠、言情等类型的、通俗的、大众的文学,传统作家粘贴到网上的已出版或发表的作品并不算网络文学。但是随着纸质文学的式微,当所有的文学都移至网络时,那么现具特指含义的“网络文学”这一概念便会消失,一切文学都在网络上传播、阅读,那时只有文学,便没有网络的概念了,那时的文学也是异常丰富、异常分化了。
涵 子:最后一个问题,好编辑的标准是什么?有这样的编辑吗?如果下辈子再选职业,还会做文学编辑吗?
石华鹏:好编辑的标准很简单:读者满意,作者高兴。标准简单,但是做到很难。美国《纽约客》的编辑威廉·肖恩是这样的好编辑,全世界的读者都满意他,作者,无论大名鼎鼎的还是无名小卒,也喜欢他。
比如塞林格,塞林格与威廉·肖恩的合作是在塞林格因《麦田里的守望者》名满天下之后,但是他们合作愉快,塞林格在后来出版的一本书的首页动情地表达了对编辑的赞誉,他写道:“一岁的马修·塞林格曾经鼓动一起午饭的小朋友吃他给的一颗冻青豆;我则尽力秉承马修的这种精神,鼓动我的编辑、我的导师、我最亲密的朋友(老天保佑他)威廉·肖恩收下这本不起眼的小书。肖恩是《纽约客》的守护神,是酷爱放手一搏的冒险家,是低产作家的庇护者,是支持文风夸张到无可救药的辩护手,也是生来就是艺术家的大编辑中谦虚得最没道理的一个。”一个好编辑应该具有肖恩这样的品格:热心、有眼力、敢探索、谦虚。
我下辈子还想做一名文学编辑,它让我的爱好和职业完美地合二为一了,可以想象你的每一天都是在阅读小说中度过的,那是一种美妙的感受,所以我说文学编辑是一个美妙的职业。
当然,文学编辑终究是文学的配角,留名青史的主角是作家作品,但如何把这个配角当好,却是一门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