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周期趋同,亦或“脱钩”
陈智明 郭永济 李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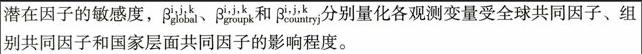
[内容摘要]本文对全球169个经济体1991-2013年的产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数据进行估计,以探究全球经济周期相互依存度的动态演变过程。运用动态分层因子模型将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三个组别的宏观经济波动分解为全球因子、组别因子、国家层面因子和异质性成分。研究结果表明,全球经济周期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强于对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明显与全球经济周期“脱钩”。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同性较为明显,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程度的趋同性,但也存在“脱钩”现象。中国的经济周期与全球经济周期“脱钩”,但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的趋同性。
[关键词]经济周期;趋同;脱钩;动态分层因子模型
一、引言
全球化促进各国贸易和金融的一体化,使得国家之间经济依存度不断增强,畅通和拓宽了全球性冲击向各国外溢的渠道,导致了全球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同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确可以观测到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总量经历了相似的波动,国家之间宏观经济总量波动具有明显的趋同性。但现实发生了转变。近年来,在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却以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发展。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全球主要经济体,但全球许多经济体并未受到严重的打击。这不禁使人们对国际经济周期传导渠道产生了怀疑,并猜测新兴经济体已经与工业化经济体脱钩,即世界经济周期不再与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紧密联系,新兴国家经济周期与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周期的两个独立力量。
研究国家之间的经济波动是不是相似的,理解其来源和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极为重要。一方面,经济周期是不是跨国相依或共同冲击的结果?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经济周期?跨国家、跨地域溢出效应能解释各国经济周期多大程度的同步性?回答以上问题有利于准确预测国家或国际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国家经济周期和全球经济周期的相互作用关系。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监测国内或区域经济周期通常关心的是某些国家的经济波动对国际市场带来的冲击和对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但是,如果不同制度、不同经济结构或不同经济政策的国家的经济波动是由一个共同的事件驱动,那么理解经济波动的同步性特征将是制定正确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研究1991-2013年全球经济周期相互依存度的动态演变过程,为把握全球经济周期协同关系和制定有效经济政策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对主要发达国家的产出波动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存在全球共同经济周期的结论。另一些学者则从主要发达国家的产出和消费展开研究,从各国之间这两个宏观经济变量显著的正向同时性关系得出了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同步性和全球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结论。然而,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支持国际贸易和金融一体化增加全球经济周期协同性的观点。Krugman指出,贸易一体化程度加深可能导致区域专业化水平提高,因此对特定行业的冲击并不会导致很大程度的产出协同性。相应地,Heathcote and Perri认为贸易的区域专业化带动了金融的区域一体化。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也表现出了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相似的特性,研究者认为存在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周期或全球经济周期。之后,学者们开始关注区域性经济周期的特征,探索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经济周期的相互依存关系。Kose st.al认为,全球经济周期因子是大部分国家宏观经济总量波动性的最重要来源,而区域因子和宏观经济变量因子的解释能力较弱。Helbliong and Bayoumi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一体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增加了全球和区域性经济周期的协同性。
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产出相关性不断降低,一些敏锐的学者们开始怀疑是否出现全球经济周期的去同步化。Necati Tekatli通过分析G7国家经济周期波动来源发现,尽管贸易开放度不断加大,但G7国家经济周期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协同性。将全球106个国家分为工业化国家、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三个组别,并同时选择产出、投资和消费作为研究变量,发现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经济周期波动趋同,但全球动态因子的相对重要性有所降低,即全球经济周期出现“脱钩”。
以上文献对研究全球经济周期特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主要选择工业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但这是基于工业化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周期的前提假设。随着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的地位日益突出,研究全球经济波动的溢出效应若不考虑新兴经济体是不全面的。其次,研究数据均为2005年之前,而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周期是否发生结构性变化未有涉足。最后,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周期特征探讨较少。基于此,本文选取全球169个国家或地区,划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三个组别,运用动态分层因子模型对1991-2013年产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国民收入的波动进行估计,并分解为不同的因子:全球因子、组别因子、国家因子和异质性成分。同时,本文还分别探讨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特征。
三、理论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Moench et al.的计量方法,构建动态分层因子模型。该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估计动态共同因子,并能根据方差分解结果判断各层级共同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同时,该模型为高维宏观经济数据情况下同时估计多种不同层次的联动效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有效地克服了现有研究方法不能灵活有效地处理高维数据以及不能同时提取多个加总层次动态因子的缺陷。
(一)动态分层因子模型
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包括:(1)全球经济体和所有变量的一个全球共同因子;(2)所有变量不同组别的共同因子;(3)所有变量的国家层面共同因子;(4)每个国家所有变量的异质性成分。模型的动态关系由每个因子和异质性成分的自回归过程进行刻画。动态分层因子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二)模型估计
本文运用基于Gibbs抽样的MCMC方法,对模型参数和动态因子进行估计。其估计过程大致如下:(1)提取主成分作为全球经济周期因子和组别因子的初始值,用这些值估计因子载荷的初始值;(2)基于国家层面共同因子提取组别共同因子的后验分布;(3)基于组别共同因子提取全球共同因子的后验分布,完成第一次MCMC过程;(4)重复上述的MCMC过程,直至生成收敛的马尔科夫链。
在MCMC估计过程中,通过对估计结果进行对比,本文的实证模型将共同因子和异质性成分的自回归阶数均设为1,同时也达到了简化模型和节约自由度的目的。扰动项方差的先验分布满足自由度为4,标度为0.01的逆x2分布。为确保马尔科夫链的收敛性,本文尝试采用不同的初始值和不同的抽样次数(10000-45000),本次的研究给出了40000次的抽样结果(剔除前5000次的抽样)。通过设定不同的先验分布形式和初始值,我们发现模型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受篇幅所限,具体过程省略。
(三)方差分解
四、研究数据及预分析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主要通过五个指标估计国家的经济周期,分别为实际GDP、实际国民收入、就业水平、工业产值和批发零售值。King et.al通过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联合研究来判断经济趋势和周期。Kose et.Al选取实际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支出三个变量衡量全球经济周期。借鉴以上经验,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全球169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GDP、居民消费支出和国民收入的年度增长率作为研究数据,其中实际GDP、居民消费支出和国民实际收入为现价美元计价。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家组别的划分参照IMF分类标准,分别选取31个发达经济体、24个新兴经济体和114个其他经济体。由于各变量数据的完整程度不一,本文采用非平衡组别结构。数据跨度为1991-2013年,即重点考量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和新兴国家经济增长加速的阶段,数据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等主要经济事件。所有时间序列均通过了ADF平稳性检验,限于篇幅,省略检验结果。
图1描绘了实际GDP、居民消费支出和国民实际收入平均增长率的时间路径。从图1中不难看出,各变量在全球经济体和不同经济体组别平均值的时间路径都比较一致,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经过两年左右的调整,2000年开始上升,并在2007-2008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快速下降。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的GDP平均增长率大部分时间高于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经济体(右轴),新兴经济体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大部分时间高于发达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但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下降幅度最大,2010下降了约四分之一,但随后较快回升。GDP的全球平均增长率波动幅度最大,其次为国民收入,而居民消费支出的全球平均波动率最低,且明显地滞后于GDP和国民收入波动。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动态因子分析
根据动态分层因子模型对(1)至模型(3)的贝叶斯估计结果,图2给出了全球动态因子和各组别动态因子的后验分布均值。1990-1991年美国储贷危机和海湾战争,加上1994年的莫斯科经济危机,致使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经济周期因子处于较低水平,并于1994年后开始复苏。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2002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以及2001年美国互联网业的衰退和“911”恐怖袭击事件等使全球经济跌宕起伏。直到2002年后全球经济迎来了风平浪静,各国经济在一片祥和的环境中争相发展。但好景不长,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相继而来的是冰岛金融危机、爱尔兰银行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欧洲次贷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直到2010年后才开始复苏。
进一步分析图2发现,发达经济体因子的动态路径波动大于新兴经济和其他经济体,而且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的组别因子并不是严格跟随发达经济体的组别因子,即相互间的协同性趋势并不明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的组别因子波动更为平缓,表明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周期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的依存度减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2000年之前,发达经济体的组别因子与全球经济因子的关系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引领全球经济周期,表现为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先于全球经济周期衰退,而早于全球经济周期复苏。但是2000年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率先由新兴经济体拉动,发达经济体引领全球经济周期的关系不复存在。因此,全球经济周期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趋同性减弱,全球经济周期出现“脱钩”现象。
图3为全球发达经济体及其组别动态因子的时间路径。其中,欧洲经济体为欧洲的发达经济体,其他经济体为除G7和欧洲经济体外的发达经济体。从图3中可以看出,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同样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衰退,2002-2007年的繁荣和2007-2010年的大萧条。但与图2不同的是,图3中各因子的时间路径较为一致,即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趋同性较强。需要说明的是,欧洲经济体因子的波动之所以大于全球最重要7个经济体的波动,是因为我们在欧洲经济体群组中重复加入了G7国家中属于欧洲的国家。因此,欧洲经济体组别的经济周期对全球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引领作用最强,其次是G7经济体,最后是其他经济体。
图4展示了新兴经济体及其组别动态因子的时间路径。按照新兴经济体的地域分布,将其划分为拉丁美洲、亚洲和欧洲三个组别。从图4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反而经历了一段繁荣发展的时期,同样的情况发生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并未像发达国家衰退得那么严重,这为我们上文新兴经济体“脱钩”的结论又一次提供了证据。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处于衰退状态,并于1998年后开始复苏。21世纪初期的能源危机给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新兴国家造成较大的影响,阻碍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墨西哥金融危机时拉美新兴国家的经济周期衰退幅度较大,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周期负面影响最大,可能受欧元区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欧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周期衰退最为严重。
(二)基于方差分解的联动效应强度分析
为了厘清全球性经济周期波动的来源,我们通过方差分解分别计算全球因子、组别因子和国家层面因子的方差占全球经济体宏观变量波动总方差的比重,来判断各因子与全球经济周期的关联程度。
表1给出了各因子占各组类经济体产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国民收入的方差分解,每一个表格均为各因子对相应组类经济体方差贡献度的平均值,如第一行表示全球因子的方差占全球经济体三个宏观变量波动方差的百分比。全球因子平均解释了全球经济体产出增长率波动的11.8%,而仅仅解释了居民消费支出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波动的0.5%和0.1%。产出增长率对全球因子的因子载荷绝大部分是正值,意味着剔除全球经济周期联动效应后,全球产出增长因子的上升趋于增加全球各经济体的产出增长率,即全球经济体的产出增长率存在明显的全球联动效应。更为全面衡量某一经济体经济周期波动与其他经济体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依赖程度的指标是全球因子和组别因子对全球经济周期波动的方差贡献度之和(Kose.et.al,2008)。表1显示,全球经济体的“全球+组别因子”分别解释产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波动的25.2%、8.8%和9.4%。尽管这些数值看起来较小,但全球和组别因子是大量经济体综合三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共同趋势。因此,该结果意味着存在一定程度的“全球经济周期”。
全球因子解释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宏观变量波动方差的程度不断降低,如解释发达经济体产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方差分别为23.6%、1%和0.2%,而对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相应宏观变量波动方差的贡献度分别为10.7%、0.5%、0.1%和1.1%、0.1%、10.1%。这表明,全球经济周期对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较弱。从“全球+组别”因子的方差贡献度来看,全球经济周期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较为明显(方差贡献度分别为50.5%、17.2%和27.7%),而与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经济周期的协同性较弱。因此,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周期与全球经济周期的“脱钩”较为明显。
表2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共同因子的方差分解。全球因子解释了所有发达经济体产出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方差的23.6%和46.4%,而解释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的方差较小,仅为0.6%,但是“全球+组别”因子解释了所有发达经济体产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方差的45.8%、21%和57%,有力地证明了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的趋同性。同时,“全球+组别”对发达经济体不同组别各变量的方差均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特别是对处于欧元区的欧洲发达经济体,解释程度分别达到了75.1%、35.7%和82.8%。这说明受欧元区国家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深的影响,其各经济体经济周期的溢出效应较强。其他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可能因空间限制而表现出的经济周期趋同性相对较弱。总体说来,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具有较强趋同性,并未出现“脱钩”的迹象。
新兴经济体动态因子的方差分解表明,“全球+组别”因子解释所有新兴经济体产出、居民消费支出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波动的16%、22.2%和23.7%,咋一看这组数据较大,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仅有24个,如此程度的解释能力并不能使我们得出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具有趋同性的结论。进一步分析“全球+组别”因子对新兴经济体各组别宏观变量方差的解释程度,可以发现该因子对欧洲新兴经济体组别各宏观变量波动的解释能力很弱,即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与所有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相互依赖度较低。亚洲和拉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与所有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有一定的趋同性,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脱钩”(对产出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波动的解释程度较低)。
(三)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
为分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我们提取动态分层因子模型估计的全球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动态因子的相对重要性(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贡献度较小,分别解释产出、居民消费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波动的0.2%、0.69%和0,均低于0.59%、0.83%和0.66%的各经济体平均值。这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全球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依赖程度较弱,即中国属于与全球经济周期波动“脱钩”的经济体之列。全球经济体的组别因子对中国产出增长率波动的解释程度为14.7%,大大超过了4.17%(100%/24)的平均水平。这表明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产出增长率与新兴经济体产出增长率具有明显的趋同性。
国家层面共同因子对中国的产出和国民收入增长率波动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如解释了中国的产出增长率的31.5%。从图5描述的中国产出增长率与国家层面动态因子的标准化时间路径可以发现,国家层面共同因子捕捉到了样本期内大部分时期中国的经济周期,如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经济增长为7.6%的低谷的经济周期、2000-2007年经济增长连续8年处于8%以上的经济周期、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周期,以及随后的经济反弹和回落。
六、主要结论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波动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波动依存度减弱,发达经济体引领全球经济周期的能力大大降低,即全球经济周期波动出现“脱钩”现象。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依赖程度较强,并未出现“脱钩”现象,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一定程度的“脱钩”。发达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同性较为明显,全球因子与G7、欧洲和其他经济体因子具有较强的趋同性,特别是对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深的欧元区发达经济体的趋同性最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具有一定程度的趋同性,但也存在“脱钩”现象,特别是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与所有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的相互依赖程度最低,而亚洲和拉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在部分变量表现为“趋同”,部分变量又表现出“脱钩”。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与全球经济周期波动的趋同性不明显,即中国属于与全球经济周期波动“脱钩”的经济体之列,但是中国的产出增长率与新兴经济体产出增长率具有明显的趋同性。准确把握全球因子和组别因子驱动中国经济周期的相对重要性变化,有利于准确评估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冲击对本国经济的溢出效应,为制定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提供依据。
责任编辑:邵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