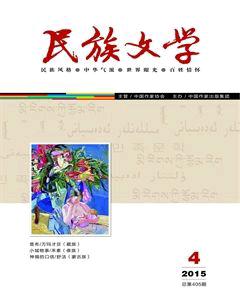一头是龙洞,一头是逻楼
罗南
在这之前,老家龙洞只是父亲嘴里偶尔的只言片语,像裂开的一道缝,在幽远狭长的时间深处,隔着几百年的距离。我窥见罗氏先祖的浮光掠影,像一部传奇。
有关龙洞,父亲知道多少,我没问。没想过要问。我的年轻让我的目光和我的心无暇于这些。我终日忙碌,在家乡之外疲于奔命,像一只候鸟,只在每年的几个重要传统节日停栖在父母身旁几天。我总以为时间还有很长,长到我每次回到那座名叫逻楼的小镇,都会看到父亲母亲迎过来的温暖笑脸。
父亲却走了。一切猝不及防。我甚至来不及赶到,看他最后一眼。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春节,全家人围坐在火盆旁,木炭通红,暖意融融。我们全都笑呵呵的,看父亲试穿我买回来的大衣。父亲张开双臂,像一个听话的孩子,任凭他的子女在他身上扯扯拍拍。父亲上下打量自己,也笑呵呵的。他略带遗憾地说,暖是暖了,可惜太重。
大衣厚实,里面还衬有一层厚厚的绒毛,我买它的时候,光想着它的暖了。我说,那明年我再买一件暖而轻的吧。
可是没有明年了。那年春节过后不久,父亲就离开了我们。
我很惊慌。第一次看到时间的短促。
父亲这一脉共有六个兄弟一个姐姐,他们都已走在父亲前头。父亲一走,他们这一辈人便只剩下母亲和满婶。两个外姓女子,守着罗家,老成了罗家最后的掌门人。
关于龙洞,母亲和满婶知之不多,从嫁进罗家那天开始,她们一直生活在逻楼,在那个远离龙洞的小镇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她们是罗家媳妇,却不是龙洞媳妇。
只有父亲,他知道龙洞,他曾无数次牵着祖父的衣角往返于龙洞与逻楼之间。他是脉,一头连着龙洞,一头连着逻楼。罗氏先祖的气息通过他,源源不断流到罗氏后人那里。对我们来说,只要父亲在,龙洞就不会远。
父亲一直在。我们便都习惯了一推开家门就看到他笑意盈盈的脸。哥哥姐姐们谁也没有想过要沿着父亲溯流而上寻找龙洞,他们和我一样,目光和心都太忙碌。我们无暇于这些,甚至无暇坐下来和父亲好好说一说话。我们总以为时间还有很长,父亲会永远坐在家里等我们回来。
父亲却走了。我们与龙洞的联系蓦然断开,像两块漂浮在茫茫大海上的大陆板块,父亲一放手,我们就被强力推开,阻隔在时光之外。没有父亲,我们无从触摸先祖的气息。
龙洞彻底像一个谜,存放在某一处我们不知道的安静角落里。
从我出生起,睁开眼就是逻楼特有的温暖阳光。祖母,父亲母亲,伯叔姑婶,哥哥姐姐,围挤在我生活里,满满当当。我以为生活从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罗氏和逻楼这座古老的小镇一样,在桂西北的大石山区里,祖祖辈辈,天长地远。
我没见过祖父,他在我还没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从我记事起,祖母就老得只剩下皱纹。她和姑妈坐在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里,没日没夜地织土布。蓝格子黑格子白格子的土布一匹匹从织布机里摇出来,又一匹匹被背到市场上卖。
祖母脾气很坏,她时常眨巴着流着泪水的眼,用拐杖敲击地面大声咒骂。大人们置若罔闻,埋头继续手上的活儿,小孩子们则像遇到猫的老鼠,小心翼翼地绕着她走。祖母没有对手,便一个人蹲到屋后厕所旁的大树下悲声痛哭。她把自己的委屈哭成曲调,哀婉无望,像一只手,伸进旁人胸腔,死死揪住心脏不放。
那是一种奇异的感觉,很多年后,当所有的壮族女子都丧失了哭唱这一表达悲伤的传统功能,祖母的曲调仍氤氲在我胸间,长久萦绕徘徊。
大多数时候,祖母是在骂祖父,骂他是骗子。祖父曾对祖母说,他家里有很多银元,多得要用摇相晒。
我们家也有摇相。那种直径能达两米的竹篾编的竹器,别人家都是晒谷子或玉米用,在我们家,却多了一项功能——床。白天,摇相里装的是我们家的稻谷或玉米,在前院的晒坝上,摊躺在炙热的阳光下暴晒,黄灿灿白晃晃的灼人双眼。晚上,摇相里装的是我们家的孩子,他们摊躺在火塘旁或神龛前的泥地上,在宽敞的摇相里,自由辗转嬉戏,最后累了,才睡成一只只酣甜的虾公。
一摇相的银元该是怎样的壮观?我们小孩子用稚嫩的脑袋想象不出来。它们会不会像那些炙晒在阳光下的稻谷或玉米,也发出灼人双眼的光芒?每每这时候,龙洞就会从那个遥远的陌生地方潜过来,在我们家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摊成一地黄灿灿白晃晃的稻谷或玉米,就像多得数不清吃不完的松软喷香的米饭,摊满我们家的锅碗瓢盆,让我们心醉神迷。
父亲还在世时,我曾跟他提到这段往事。父亲说,祖父倒也不是骗祖母,祖父家也曾是大户人家,用摇相晒银元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只是娶祖母的时候,祖父家就已经败落了。
祖父背井离乡来到逻楼的时候是多少岁?我没问父亲。只知道祖父一到逻楼就给一黄姓大户人家帮工。祖父勤劳实诚又相貌堂堂,主家喜爱,便把最疼爱的小女儿许配给他。黄家有十一个女儿,最受疼爱的小女儿就是我的祖母。
祖母的父亲,我的曾外祖父想把小女儿留在身边,因此尽管家里已经有几个儿子,他仍然招了上门女婿,让女婿住到家里,和儿子享受同样的待遇。只是好景不长,曾外祖父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我祖母的几个哥哥就把祖母和祖父以及他们的孩子赶出了家门。祖父没有办法,只能另择宅地,他掏出所有的积蓄,建了一座茅草房用以安置众多的子女。
一个上门女婿的尴尬和痛处,从祖父那里,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波及到父辈那里,再波及到我们这里——只不过,我们的感受不会有父辈深,我们离那段历史终究更远些;或许,大的哥哥和姐姐们的感受会比我更深,他们毕竟比我年长许多。在我,便只隐约闻见那其中的刀光剑影。那些有关住宅地的纷争,以及亲人间长年累月的嫌隙,在我童年记忆里只是一些印记。它们真切存在,却模糊不清。
时间会淡化一切。就算仇恨也不例外。
祖母怎么会不知道祖父并没有骗她呢,只是生活太苦,她委屈愤懑,她心里有恨。她一个倍受宠爱的大户千金何曾受过这样的苦?就算把所有的嫁妆一件一件当掉,就算没日没夜织布卖也填不饱肚子。
我不知道祖父跟祖母提起龙洞那些晒在摇相里的银元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是缅怀过去优越的日子,还是和我们这些小孩子一样,饿得受不了了,就想象能拥有多得数不清吃不完,松软喷香的米饭来安慰自己的肚子?
在罗氏漫长的贫困日子里,龙洞一次次伴随祖母的哀婉哭唱出现在我们脑际,它不再是祖父嘴里的一摇相银元,而是早化身为多得数不清吃不完的松软喷香的米饭,无数次撩拨我们空荡荡的稚嫩的胃。
父亲很少跟我们提起龙洞,他像是遗忘了它,又像是龙洞根本就不曾存在。
父亲太忙了,他根本无暇去想龙洞,我敢肯定,他甚至忙得无暇看清他八个孩子的脸。为了填饱全家十口人的肚子,父亲绞尽脑汁,挖沙,搬运,赶马车……干得最久的营生是卖老鼠药。一小包一小包的磷化锌,剧毒,父亲把它稀释,浸泡进谷子里,再把谷子用废纸包成一小包一小包地卖。老鼠爱吃谷子不爱吃磷化锌。
那年头,大街上卖老鼠药的外地人特别多,他们大多从贵州、四川等地来,操着浓重卷舌的西南官话,用小喇叭对着路过的行人聒噪:老鼠药老鼠药,老鼠吃了跑不脱。
相比别人的热闹,父亲的生意倍显冷清。为了招揽顾客,父亲把毒死后的老鼠尾巴剪下来,用绳子绑成一小扎一小扎的摆在货摊上。他向顾客承诺,买了他的老鼠药,药倒老鼠后,把老鼠尾巴剪下来,十根就能换他一小包磷化锌或毒谷子。
后来,父亲又想出另一招,他剥下死老鼠的皮,塞进废纸或木屑,再重新缝合,一只只胀鼓鼓的死老鼠就趴满他的货摊。父亲是想向顾客证明,他的老鼠药很灵,比那些只知道聒噪的外来的老鼠药都灵。
父亲的生意仍然冷冷清清,却到底也养活了我们,尽管我们时常感觉到饥饿。
没有人再提起龙洞。事实上,随着祖母去世,那一摇相银元就已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我们长大,上学,工作,像蒲公英的种子,各自撑着单薄易碎的伞,在尘世里蹒跚而行。我们都遗忘了龙洞。
龙洞却在某一个深夜猝然撞入我梦里。
那是一座大瓦房,有很多房间,迷宫般一个连着一个。我在那些房间里兜转,却没有找到一个人。堂屋正中墙上是一个香火台,台前烛火摇曳,光线昏暗,我仰头,努力想看清香火台上的字,那些字却始终模糊着。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你在梦中,你却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见到那座大瓦房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在做梦,而且,我还知道那里是龙洞,那房子是我的祖屋。因此,我在那些房间里兜转的时候,很希望能找到我的某一位先祖。可是,没有。就连香火台上的字都没能给我透露半点有关罗氏先祖的秘密。我只记住了那座大瓦房,粗犷整齐的麻石条屋基,结实的石柱礅,威武的石狮,黄泥夯筑的墙,飞翘的房檐在清冷的月光下是一种无以言说的傲慢和透彻心骨的孤独。
很多年后,当我第一次去到龙洞,我的呼吸瞬间凝住了。我看到了那座大瓦房,我的祖屋,它残败得只剩下一堵黄泥夯筑的大墙,坚韧顽固却又孤独傲慢地直指蓝天。凿雕粗犷的大麻石条屋基足有一人来高,霸道沉默地固守原地。
我触摸石条和墙,心在猛烈狂跳。我确信,它就是我梦里见到的祖屋。只是那些迷宫般的房间全都不见了,它们变成了一地痕迹。
我的血液在血管里欢唱。我的眼睛贪婪地大把大把地拥抱抚摸龙洞。我静立在一棵大榕树下,身旁是潺潺轻流的山泉。我闭眼聆听,深深呼吸龙洞淡泊纯净的空气。我想象我的先祖,他们是否也曾如我一样,某一天的午后,站在这棵大榕树下,闭眼聆听泉声?龙洞瞬时与我贴得很近很近,仿佛它不曾遥远,仿佛我不曾陌生。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找到龙洞了。我找到先祖了。
寨子寂静。满眼是雕凿粗犷的麻石条。小道,台阶,屋基,全都由粗大的麻石条垒砌而成,看似随心所欲却又浑然天成。屋舍俨然,所有的住房是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桂西北壮族特有的吊脚楼。
时光在这儿似乎被割切了,只不过隔着几重山,只不过隔着十八公里,山里山外已俨然是两个世界。古朴空灵的气韵让我们恍惚,宛若穿越到很多个世纪前。
一眼就能看出寨子的孤寂。我们穿行在巷子里,听不见犬吠,也看不到人影。或远或近的地方,不时有一整栋一整栋的吊脚楼在寂寞地朽败,坍塌的瓦片和檀条下,房主人的锅碗瓢盆、衣物,甚至火塘里烧了一截的柴蔸,甚至床铺上铺着的床单挂着的蚊帐,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像是主人只是暂时离开,却不承想一日已是百年。
终于见到人。一个背着背篼赤着脚的女人,一个倒背双手赤着脚的男人。他们踩在被时间和脚步磨蹭得光亮温润的麻石条上,闲闲淡淡地望向我们。
走近,交谈。我说我姓罗,龙洞是我老家。我的祖父在龙洞出生长大。我还报出了我祖父的名字。男人女人的眼睛便温暖起来。他们也姓罗。我们各自亮出字派,排资论辈。原来我辈分较长,我是姑,他们是侄儿。
他们于是叫我姑。按规矩,我直呼他们的名字就可以了。我却无论如何也张不了口,他们都比我年长许多,我不习惯直呼一个比我年长很多的人的名字。
可关系终究还是近了。在那声“姑”里,我立马从一个逻楼人变成和他们一样是同祖同宗的龙洞人。这让我找到了自己在龙洞的存在感。
他们带我去看祖屋。他们都知道我的祖屋。
那堵黄泥墙就在我们刚刚走过的路旁。刚才经过它的时候,我就莫名感觉亲切眼熟,像是一位久未谋面的故人,又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轻轻拉扯我的衣角,我忍不住回头看了它一眼,又看了它一眼。
我年长的侄儿在向我描述祖屋当年的气派。他们说,以前这峒子的山地全都是我们罗家的,峒子外面的田地也都是我们罗家的。你们那一脉早早搬离龙洞,你们家的房子也就只剩下一堵墙了。
我站到高高的麻石条屋基上望向那堵固执挺立的黄泥墙,在湛蓝的天空下,它刚劲有力,顽强而又绝望地凝望某一处罗氏后人所不知道的更深邃更遥远的地方。我又看到很多年前,我的梦里,飞翘的房檐在清冷的月光下那一种无以言说的傲慢和透彻心骨的孤独。
我的心瞬间融化,融进龙洞,与它合为一体。它们糅合着父亲、祖父,以及更久远的先祖们的血液和气息。
我把我的喜欢告诉侄儿。他们只是笑笑,说,现在寨子里,只要能找到一点儿门路的人全都搬走了。剩下来的人,不是因为留恋,而是因为没有能力离开。
我语塞。感觉到自己的矫情。
我把目光移向头顶层层叠叠向我们围箍压迫而来的大山,那些坚硬岩石间单薄清瘦的土地,再移向那一整栋一整栋朽败坍塌的吊脚楼,想象它们的主人在离开时内心里的欢欣和迫不及待——他们真是太厌倦这个地方了,厌倦到连锅碗瓢盆都不愿意带走。
我明白那种厌倦。生活毕竟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诗情画意,在旷日经久的柴米油盐里,谁也经受不起太多的贫瘠和艰难——我再怎么无知也不会真的认为龙洞的土地丰腴到足以养活人滋润人。
我们只是过客,或者是看客。尽管龙洞是我的老家。我们惊叹于龙洞摄人心魄的麻石条、吊脚楼,以及纯净空灵得恍如隔世的古朴气韵,可我们谁都不会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我们不用每天去面对那些瘦薄的土地和艰险难行的山路,忧心每天的柴米油盐。生活在这里的人却不一样,他们找不到门路离开,就得继续在龙洞生活下去,而且是长长的一辈子。他们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坚韧。
我很羞愧我对侄儿说出的关于喜欢的那番话,回想起来,它们是那么地肤浅轻浮甚至无耻。它们带着来自山外的优越,自以为是地高高在上。这使我不敢再直视侄儿的眼睛,那双眼睛深处,隐藏着生活的疲惫和焦虑。
我的心爬满忧伤。我心疼那一栋接一栋朽败坍塌的吊脚楼,我也心疼仍生活在龙洞的罗氏后人们的艰辛。可是除了忧伤,我无能为力。
侄儿带我去寻找先祖的墓地。我的曾祖、高祖、天祖躺在泥土里,倒也没有太多的忧伤。他们不看世事,不食人间烟火,他们成了龙洞最淡定从容的部分。
上百年的时间浸染,墓碑全都镀上了沧桑。古老的雕艺,精致雍容却又内敛的雕刻细节,无不在提示一段历史曾经的辉煌。我仔细辨认墓碑上的字,想从中窥见那段历史的片段,罗氏先祖生前鲜活的故事场景。无果。碑文模糊,一时无法辨认。只好用相机一一拍下,想着回去后再把照片存进电脑放大了细看,我相信,碑文会告诉我一些有关于罗氏先祖的秘密。
关于那段历史,侄儿语焉不详。父亲说,罗氏曾修得有族谱,某一年,乱匪进犯龙洞,老家的房屋连同族谱被他们一把火焚成灰烬。罗氏后人便再也无从得知先祖们的生活轨迹。
失去文字的记载,龙洞仍然是一扇被关闭的时光之门,罗氏先祖的故事封锁在时间深处,沉睡成一个秘密。我们不能得知,几百年前,是龙洞选择了罗氏,还是罗氏选择了龙洞?我们的先祖为什么会在这么偏僻险恶的地方安顿下来?
谜底会在那些字迹不清的碑文里吗?
一个人是一段历史,一个家族也是一段历史。在时间皱褶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尘埃。
几百年的时光飞逝,一切恩怨和名利都已是过往烟云,只有偏僻得几近与世隔绝的龙洞装满了罗氏先祖的故事,等待着与我相遇。
这不仅仅缘于血脉。
责任编辑 徐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