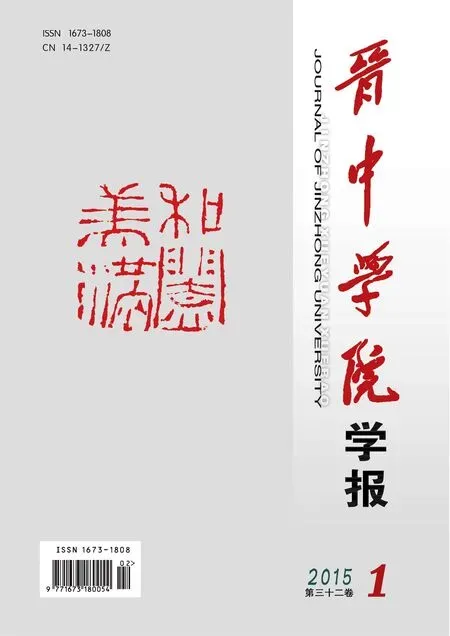从孔孟到《易》《庸》——钱穆论先秦哲学衍化及其当代启示
杨生照
(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山东青岛266100)
作为中国哲学的原创和奠基阶段(中国的“轴心时期”),先秦哲学奠定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和思想特质,是重建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回溯并汲取的思想资源,故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核心之域。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一生以研究和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亦曾通过对先秦哲学衍化的考察,提出了一个与传统旧说迥异的钱氏先秦学术谱系,并对中国文化如何应对吸纳西方文化从而实现当代复兴作了一种有意义的思想探索。本文便试对钱穆先生的这一考索工作展开相关讨论。
一、总论先秦哲学衍化
钱穆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对先秦哲学的衍化过程有过总的论述:
(天人之际)问题,本是世界人类思想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唯一最大主要的问题。春秋时代人的思想,颇想把宇宙暂时撇开,本专一解决人生界诸问题,如子产便是其代表。孔子思想,虽说承接春秋,但是其思想之内在深处,实有一个极深邃的天人合一观之倾向,然只是引而不发。孟子的性善论,可说已在天、人交界处明显地安上一接榫,但亦还只是从天过渡到人,依然偏重在人的一边。庄子要把人重回归到天,然又用力过重,故荀子说其“知有天而不知有人”。但荀子又把天与人斩截划分得太分明了。这一态度,并不与孔子一致。老子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明确口号,而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界实际事为上,都有一套精密的想法,较之孟子是恢宏了,较之庄子是落实了,但较之孔子,则仍嫌其精明有余,厚德不足。而且又偏重在自然,而放轻了人文之比重。《易传》与《中庸》,则要弥补此缺憾。[1]82
短短数百言,钱穆不仅点明了人类哲学沉思的根本问题,即天人之际,而且端出了一个钱氏自己的先秦学术谱系:子产→孔子(→杨朱、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作《易传》《中庸》的新儒家。不难看到,此谱系与传统旧说有着诸多相异之处。如:旧说一般以《易传》为孔子所作,《中庸》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而孟子曾受业于子思门人,故《易》《庸》应在孟子之前,但钱穆认为《易传》并非孔子所作,《中庸》亦非子思所作,二者皆是战国晚期至秦汉间的“新儒家”(1)在融会以孔孟儒家和庄老道家为代表的先秦诸子思想之基础上创构而成,是先秦哲学发展的最高峰。又如:旧说一般以为老子在庄子之前,而钱穆则相反认为《庄子》应在《老子》之前,且庄子可能是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中的“颜氏之儒”一支。[2]148-149
本文将选取其中的孔孟、庄老、荀子及《易》《庸》等对后世中国哲学发展有过实质性意义的诸家进行讨论,来展现钱氏眼中的先秦哲学发展历程及其对中西哲学会通的某种启示,而如杨、墨等尽管在先秦时期曾影响广泛,但在后来皆沦为绝学,故略去不论。此外,尽管钱穆将荀子置于庄老之间,但虑及庄老两家思想的相近性,故本文将先采取庄老连述,之后再单论荀子。
二、从皇古的素朴宇宙论到孔孟的德性人生观
哲学沉思以天人之际,即人与宇宙或世界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其内含着对宇宙和人生两个方面的终极思索。钱穆认为,在中西文明和哲学发源的初期,往往都是对宇宙的思考先于对人生的思考,即“宇宙论之起源,乃远在皇古以来”,且由于“其时民智犹僿”,故“对于天地原始,种物终极”之种种“拟议”,“言其大体,不外以宇宙为天帝百神所创造与主持。人生短促,死而为鬼,则返于天帝百神之所。”钱穆称之为“素朴的宇宙论”,[3]25-26其实质上就是一种原始的有神论的宗教观念。紧接着:
迨于群制日昌,人事日繁,而民智亦日启。斯时也,则始有人生哲学,往往欲摆脱荒古相传习俗相沿的素朴宇宙论之束缚,而自辟藩囿。但亦终不能净尽摆脱,则仍不免依违出入于古人传说信仰之牢笼中,特不如古人之笃信而坚守。此亦中外民族思想曙光初启之世所同有的景象。其在中国,儒家思想,厥为卓然有人生哲学之新建。[3]26
这是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群数量的增多,人们要应对的问题不再仅是人和宇宙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即“天人之辨”),而且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群己之辨”),这就要求人们开始对人类自身的本质及其存在意义作出思考,从而产生了人类早期的人生哲学,其在中国文化中便是以孔孟儒家思想为代表。(2)
就宇宙观方面来说,钱穆指出:“《论语》里的‘天’字,是有意志,有人格的。……《论语》里的鬼神,也是有意志,有人格的”[4]266-267,这说明“孔子于古代素朴的天神观,为皇古相传宇宙论之主要骨干者,固未绝然摆弃”;[3]26至于孟子,由于当时“道家气化的新宇宙观方在创始,孟子未受其影响,故孟子胸中之宇宙观,大体犹是上世素朴的传统。”[3]56质言之,孔孟的宇宙观仍属于上古素朴宇宙论,即原始的有神论宗教观的延续。受此有神论宗教观影响,钱穆认为,孔孟儒家所论之人生,亦是“近于畸神、畸性的,偏倾于人文的人类心灵之同然,而异于专主自然者”。[3]31也就是说,在对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意义的思考上,孔孟儒家更强调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性的道德意识,即所谓“仁”“仁义”或“良知”等,而非人之“食色”本能意义上的感性的自然生命。这种理性的道德意识,不仅上接形上宇宙天道(天),而且下导形下社会规范(礼)。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孟子讲“居仁由义”、“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都是在强调人应当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通过不断地践行礼制规范以存其仁义之德性,从而最终体贴“性与天道”(《论语·公冶长》),实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此亦即孔孟“思想之内在深处”所蕴含的“一个极深邃的天人合一观之倾向”。[1]82要而言之,孔孟儒家以重人事、尊德性为其学问之主要特征和趋向。
此外,钱穆还指出,与其有神论的素朴宇宙观相联系,尽管孔孟儒家对现实的伦理政治实践活动总是能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态度,但是当面对整个无限的世界或宇宙之时,他们又往往流露出某种无可奈何或无能为力,从而使其思想亦常呈现出一种“尽人事,听天命”或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味,其在认识论上表达为一种不可知论的观点。[2]149
三、庄老道家的气化宇宙论与自然人生观
孔孟儒家之后,庄老道家继起。钱穆认为,庄老道家哲学的主要功绩是“对于……古代素朴的宇宙论,尽情破坏,掊击无遗”:
盖中国自有庄老道家,而皇古相传天帝百神之观念始彻底廓清,不能再为吾人宇宙观念之主干。故论中国古代思想之有新宇宙观,断自庄老道家始。[3]26
与古代素朴宇宙论将宇宙万物之存在看作“天帝百神”之“创造与主持”不同,庄老道家认为“宇宙万物皆不过为一气之转化也”,[3]33无始亦无终。包括古代素朴宇宙观中作为最高主宰的“天”,在庄老道家思想中亦多是与“地”连称并举:“地有体,属形而下,……天地为同类,天亦近于形而下。”[2]158天地作为形而下者,亦皆为一气之所化而成。盈天地间,唯有此一气之化。此“一气之化”正是庄老道家所讲的宇宙本体之“道”。钱穆称此宇宙观为“气化的宇宙观”,并指出它不仅“破帝蔑神”,且具有“归极于自然,偏倾于唯物”[3]28的特点。与此气化宇宙观相应,并与孔孟儒家之积极的德性人生论不同,庄老道家采取了一种轻德贵道、崇尚自然无为的消极人生观。
不过,除了表明庄老道家之与古代素朴宇宙论的决裂及其与孔孟儒家德性人生观之不同外,钱穆更突出强调了庄老二者在关于气化之道之具体内容和态度(即认识论观点)上的重要差异,后者又进一步影响了其各自的人生观。
首先,就对古代素朴宇宙论进行彻底批判从而提出新的气化宇宙论的工作来说,钱穆认为以庄子首当其功:为了凸显与旧宇宙观之真正决裂,庄子不仅从观念上对“天”“帝”“神”的存在予以否定,且更从语词上破旧立新,即提出了“造物者”“造化者”的概念,后者并非任何有人格意志的天或帝或神,而只是一气之聚散转化。然而,对于气化之道的具体内容,即宇宙运行变化的规律,庄子则认为是不可知的,因为他从根本上以为宇宙大化是无常(即无规律)的。故钱穆说道:“在庄周,因于认为道化之无常而不可知,乃仅求个人之随物乘化以葆光而全真。……故庄周始终对宇宙实际事务抱消极之意态。”[2]175就是说,庄子以为,在大道之化中,人物无高低贵贱之分,惟有乘此大道之化,各随其性以臻逍遥(自然)之境,此外别无他事。庄子的这种不可知论,钱穆认为可能上乘孔门儒家。[2]163-164
继庄子之后,老子一方面继承庄子的气化宇宙观,另一方面又一反庄子的不可知论而认为:“道之运行……有其一定所遵循之规律,而决然为可知者。……庄子仅言道化无常,而老子则曰道必逝,逝必远,远必反,此为大道运行之一种必然规律也。”[2]167-168与庄子以宇宙大化为无常而不可知不同,老子不仅认为宇宙气化运行是有常的(即有规律),且此“常道”可以为人所识知。《老子》五千言之思想功绩正在于言明此宇宙气化之常道的具体内容,并可一言以蔽之,曰“反者道之动”(《老子》第40章)。“反”即是返,即复归之意。复归于何处?老子说:“复归其根”、“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等等(《老子》第16、28章)。此所谓“根”“婴儿”“朴”“无极”,都是指宇宙万物产生的终极根源(即“自然”之“道”),亦即是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质言之,万物既源生于无,亦复归于无。故欲知大道,必以“观复”(《老子》第16章)。进而言之,此“复归”之“道”能够为人所识知,则是因为“道”常显为“象”。《老子》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21章)
钱穆解释说:
老子意,大道化成万物,其间必先经过成象之一阶段。物有形而象非形。形者,具体可指。象非具体,因亦不可确指。……然象虽无形,究已在惚恍之中而有象。既有象,便可名。象有常,斯名亦有常。……道之可名,即在名其象。道之可知亦由知其象。
[2]172-173
道虽无形,然其在化生万物的过程中却有象可见。此象不仅是从无形之道到有形之物之创化过程的过渡,且亦是我们由物以达道的中介,即我们可以通过对物象及其相互间的内在动态联系的观察和把握来通达对宇宙变化之大道的领会。(3)与其认宇宙气化为有常且可知相应,钱穆认为老子对宇宙内的实际事务(即人生观)已不似庄子那样消极,而亦始转为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这从《老子》中所讲的各种人生处世之方及理想社会构想等都不难体会。然而,强调其为“相对”积极是因为尽管老子认为人在宇宙中可以有所作为,但由于他将人类一切礼乐典章、道德教化的文明创造都看作是一种退化,是对“自然”之“道”的离却,故要想真正实现达道保身,就必须摈弃一切礼乐道德从而回归自然无为的状态方可无所不为。所以钱穆说:“老子思想之于世事人为,虽若较庄周为积极,而其道德观,文化观,其历史演进观,则实较庄周尤为消极。”[2]185-186
总体来看,无论是在宇宙观上,还是在人生观上,庄老道家相对于孔孟儒家都表现出一种相当的反叛;但是由孔孟儒家所奠定的“天人合一”,即人与宇宙相统一的思想精神却依然得到了延续。
四、荀子的“化性起伪”与“明于天人之分”
在钱穆的先秦学术谱系中,在庄老之间还有一位重要的儒家人物,即荀子。钱穆认为,就思想贡献来说,荀子“驳击诸家,重回孔子。……其有功儒家,不在孟子下”,但在思想内容上,孟子道性善,荀子主性恶,人性论上的相反使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他们在后世中国哲学史上截然不同的地位。[1]54
庄子“破帝灭神”之后,中国哲学家基本都告别了原始的有神论的素朴宇宙观,转而为一种唯物气化的宇宙观,荀子亦不例外。故荀子之“性”主要是就人有血肉之躯而言,此血肉之躯与自然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由一气之聚散转化而成,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为了维持其自然的血肉之躯的生存,势必会向外界有所求,求而不能得便有所争,争则必导致乱,荀子由此得出人之性恶。(《荀子·礼论》)为平息纷争或避免混乱,圣人制定礼法以供常人遵守,从而使社会趋于和谐稳定,而人之循礼而行便是为善。与人之性恶相对,人之为善绝非出于自然,而是纯属人为,亦即所谓“伪”,它是对自然的恶之本性的否定。此即荀子的“化性起伪”说。钱穆认为,荀子指出人性中有为恶之可能,这是无法否认且有其所见的,但其认为人的本性中只有恶而无善,人之为善纯属人为,则显得“见识太狭窄”。[1]55
进一步来说,在荀子的性恶论和“化性起伪”说的深处其实蕴含着一种人与自然相分离和对立的观念,即“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对作为自然界的天,荀子认为其运行变化不仅“有自身的法则”(“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而且“是一个没有意志渗入的过程”(“不为而成,不求而得”)。杨国荣先生指出:“对天的这一理解,侧重的是其自然之维,它在某种意义上与道家关于自然的看法有相通之处。”但在天与人、自然(无为)与人为之间,“与道家之侧重于无为有所不同,荀子在肯定天道自然的同时,又确认了人经纬自然的能力,强调其职能在于‘治’天地”,即通过把握自然界的法则来“作用于自然”,从而使自然界“由自在的对象为人所用”,此即荀子所谓“制天命而用之”。[5]85-86由此不难看出荀子力图扭转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进而重新回归孔门儒家注重人生之思想传统的诉求。
然而,钱穆对荀子这一“扭转乾坤”的工作似乎并不是很看重。他认为,与庄子之只“知有天而不知有人”一样,荀子的“扭转乾坤”的工作亦有些“用力过猛”,即他从“明于天人之分”到“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疏离了由孔孟儒家所奠定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传统。[1]60荀子对于儒家思想的贡献并不在于其“化性起伪”说及“明于天人之分”等思想,而只是在于他对之前及当时各种反对儒家的思想(如道、墨、名家等)的驳击及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以期重新回归孔子关注人生,隆礼重德的思想。[1]55所以,在钱穆看来,荀子实为中国文化衍化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歧出”。荀子之后的《老子》再次回归“天人合一”这一精神传统,但又依然偏于自然无为,而轻视人文德性,故真正实现先秦哲学天人观建构之“完成”的任务便落在了创作《易传》《中庸》的新儒家身上。
五、《易传》《中庸》的德性天人观
从孔孟儒家到庄老道家,尽管在其各自思想内部,其宇宙观和人生观在相当程度上是融合统一的;但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在宇宙观上,庄老道家比之于孔孟儒家实是一大进步,而在人生观上,庄老道家比之于孔孟儒家更呈消极意态。故一方面剔除孔孟儒家思想中古代素朴宇宙观之残余,另一方面力挽庄老道家之“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危趋,并“熔铸庄老激烈破坏之宇宙论以与孔孟中和建设之人生论凝合无间而成为一体”,从而创构一新的气化-德性的天人观,便构成了此后中国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议题。钱穆认为,这一任务最终有“战国晚世以迄秦皇、汉武间”之新儒家所完成,其成果主要体现就在《易传》和《小戴礼记》中,后者尤其以《中庸》篇为代表。[3]27那么,《易》《庸》新儒家究竟如何完成这一熔铸和创构的呢?
钱穆认为,《易》《庸》新儒家乃是一方面“采用道家特有之观点”,即以宇宙万物皆为一气之所化,另一方面“又自加以一番之修饰与改变,求以附合儒家人生哲学之需要”,从而创构出一新的德性的宇宙观。[3]33此德性宇宙观与孔孟儒家原有之德性人生论融合为一新的气化-德性的天人观。钱穆将《易》《庸》新儒家对庄老道家宇宙论的修饰改进之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庄老道家以宇宙万物皆为一气之聚散转化而成,《易》《庸》新儒家继承此说,“又别有进者,即就此一气之转化,而更指出其‘不息’与‘永久’之一特征”,并以此为宇宙自然之运行变化的意义和价值。[3]33-34万物之所以能够在此气化过程中成就自身,且在其“已成”之后复能使其存在得以“粲然著明,以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正是赖于此过程之不息不已与永久。因为如若此过程“忽焉而即已,倏焉而不久”,则万物要么根本无以生成,要么“虽成而即毁,终将昧昧晦晦,虽成犹无成”,无以澄明于天下。[3]34
第二,对此宇宙气化过程,庄老道家“常疑大化之若毗于为虚无”,即更多将此过程看作是虚无的,而《易》《庸》新儒家则是“常主大化之为实有”,即将此气化过程看作是一个实实在在、真实无妄的过程。[3]36以其真实无妄,《中庸》名之曰“诚”,《易传》名之曰“易”。此“易”亦即“乾坤(成列)”“阖辟(成变)”。与庄老道家仅言宇宙为一气之化不同,《易传》作者又从《周易》古经中提炼出乾坤阖辟之道作为宇宙气化过程之发生的根源和动力及其不息且永久的原因:乾有至健之性,坤为至顺之物,乾坤阖辟即是至健者与至顺者的相互作用以化生万物。[3]37
第三,庄老道家言宇宙气化“皆倏忽而驰骤,虚无而假合”,自然无为,故其于万物之存在实无甚德性与功业可言,《易》《庸》新儒家则一转此气化自然宇宙观之偏,指明此宇宙大化流行的德性和功业,即“生生”,或曰“生”“育”“开”“成”,[3]41亦即《易传》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以生生不息之德、生育开成之功观宇宙之化,天地万物既非人格性的天帝百神所创,亦非纯自然无为的一气之聚散转化,而是兼具自然与德性为一体的。故钱穆说:
天地一大自然也。天地既不赋有神性,亦不具有人格,然天地实有德性。万物亦然。万物皆自然也,而万物亦各具德性,即各具其必有之功能。言自然,不显其有德性。言德性,不害其为自然。自然之德性奈何?曰不息不已之久,曰至健至顺之诚,曰生成化育之功。此皆自然之德性也。以德性观自然,此为《易传》、《戴记》新宇宙论之特色。[3]43
在德性宇宙论的观照下,人生亦不再是如道家所言的无所作为的、无意义无价值的自然过程,而应是一种积极有为、崇德广业的德性人生。《系辞传》载:“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夫子”盛赞易道之至深至神,正是强调人应当依据生生不已之易道,崇德广业,存其仁义之性,以法天地之德,以通道义之门,最终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言以蔽之:天德曰生,人道曰仁。《中庸》亦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此亦是说天道生生不息化育万物是真实无妄的,绝非虚无假合,故人亦当本此至诚之性,修其至诚之德,从而达致与天地合德。此亦可概括为:天道唯诚,人道思诚。此即是《易》《庸》新儒家的德性天人观,钱穆认为,它不仅是先秦哲学衍化的顶峰,而且奠定了后世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之“天人合一”的思想基调与“崇德广业”的实践精神。
六、先秦哲学衍化的当代启示
余英时曾指出,钱穆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与其说是为了“维护传统”,毋宁说是要实现“传统的更新”,[6]178即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复兴。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饱受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冲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钱穆对先秦哲学衍化的考察,所指向的亦正是如何吸纳会通西方现代科学从而延续和复兴中国文化生命的问题。
不难看到,在钱穆对先秦哲学演进的讨论中,尤其是在孔孟儒家和《易》《庸》新儒家之间,最终发生实质性变化的并非人生论,而是宇宙论,即:人生论依旧是儒家的德性人生论,而宇宙论却从“畸神”变成“畸物”的,且是有德性的,而非纯自然的。这种变化展现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德性论思想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稳定性,并为后世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即:以儒家的德性人生观为基底,不断吸纳和消化其他文化中的宇宙论,从而创构新的宇宙论,两宋理学之兴起便是证明。
继《易》《庸》之后,宋代理学家一方面继承传统儒家的德性人生论,另一方面吸收佛道的宇宙论,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畸于理”的“理性一元天人观”。钱穆认为,此理性天人观与《易》《庸》德性天人观的主要区别就在宇宙论上,即一个是“畸于理”的,一个是“畸于神”的。前者被钱穆称之为“理性一元的宇宙论”,其集大成者便是朱子的理气论。至于人生论上,宋代理学依旧上承孔孟,无甚大变。[3]65-66由此可见儒家德性人生论的开放性和稳定性之一斑。故钱穆认为,“以《易》《庸》思想与宋代理学来会通西方科学精神”,[3]74在宇宙论方面有一更新的“创辟”,应是当代新儒家努力的方向,即:继续以儒家的德性人生观应对吸纳西方现代科学,以期实现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复兴。因为:一方面,相比于道家的自然宇宙观和西方传统的宇宙论哲学(包括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对宇宙所持的静观态度,《易》《庸》思想和宋代理学所持的气化唯物且活动的宇宙观及通过“格物穷理”以达“豁然贯通”的探究方法与西方现代科学精神更为接近。[3]68-70另一方面,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易》《庸》思想和宋代理学所持的德性或理性的“天人合一”观,在相当程度上又可弥补或纠正西方哲学中人与世界的对峙分离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也将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所可能有的贡献。
注释
(1)钱穆称《易》《庸》作者为“新儒家”是要与孔孟等“旧儒家”相区别。在他看来,孟子思想更近于《论语》而远于《中庸》,而《易传》思想则类于《中庸》,且二者又皆“远于《论语》而近于庄老”。
(2)若补全些说,那么,在孔子之前则已有子产开启人文转向之端,在孔子当时及稍后则有杨朱和墨子之起,他们也都从不同视域和角度上表现出对人生问题的关注。而孟子继起,正是要“距杨墨,放淫辞”以复孔子儒家之道。
(3)值得一提的是,《老子》的这种“复归”思想和“象”的观念,很可能源自于《周易》,即:一方面《周易》正是通过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象变化来象征宇宙万物的运行变化,另一方面在卦象变化中亦具有一种循环往复的特点。故依笔者之见,《老子》一书很可能亦是一本战国时期的道家解易之作。台湾学者高怀民亦有此说(参见氏著《先秦易学史》第六章《道家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钱穆.中国思想史[M]//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4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2]钱穆.庄老通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M]//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8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4]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M]//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8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5]杨国荣.中国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6]余英时.现代儒学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