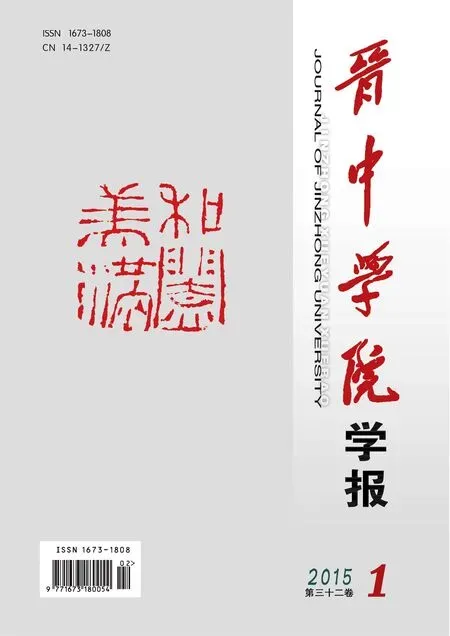大众传媒视阈下平遥说书的传承与发展
孙志岗
(晋中学院音乐学院,山西晋中030600)
平遥说书俗称“瞎子说书”,又名“平遥弦子书”“平遥鼓书”。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说唱艺术,流行于山西平遥、介休、汾阳、孝义等地。明末清初,由盲艺人在评书的基础上吸收口语化的地方民歌曲调,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一种属于板腔体、用地方语言说唱的地方曲种,“距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1)。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和多元化休闲娱乐方式的出现,平遥盲人说书,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通过媒体工具能进一步地扩大和加强不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知名度,促进多地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出现新的娱乐和消遣形式对传统茶余饭后精神文化构成巨大的冲击,很多引以为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大众所淡忘和冷落,受众面日趋减少,严重影响了其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持续性发展。
一、大众传媒的内涵
大众传媒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它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特指在人们日常的生活、学习、工作、商业交流等活动中进行大众传播活动的媒介,是一种专业化的媒介组织并结合运用当前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群体为对象,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活动。在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大众传媒的概念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传播方式也由最初原始的手抄传播方式逐渐转化为包括报纸、杂志、书籍、邮递广告等的印刷传播方式,以及目前最普遍的包括广播、电影、电视、国际互联网络、大型电脑数据库等电子媒介传播的方式。大众传媒作为各种不同文化资源的载体与传播阵地,打破了各地曲艺艺术相互传播的地域局限性,使得各种先进文化得以广泛而顺利地传播,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有效应用和不断完善,其促进不同地域的不同音乐形式广泛传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大众传媒视阈下的非遗传承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价值。在新形势下,如何在大众传媒视阈下更加有效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为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做绵薄贡献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大众传媒下平遥说书的调查与分析
当人类步入21世纪后,网络媒体的如此发达使得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地传播交流,因此对于全国不同的地方性曲种的研究和调查的视角不应仅仅局限于小范围区域性的受众群体,更应该关注网络和媒体上各地方曲艺受欢迎程度的相关数据,鉴于这样的背景,笔者从网络和现实受众两方面对平遥盲人说书做了调查,以期在新环境新背景下找出有效传承和发展平遥盲人说书的路径。
在搜索引擎百度视频里输入平遥说书可以搜索到104个条目(2),这些曲目上传时间的跨度是从2008年到2014年之间,经笔者比对发现重复的比较多,都是盲人说书的一些常见曲目,比如《娘们顶嘴》《蚂蚱算命》《赵州桥》《尼姑生娃》《大红纱》《回娘家》《闹弄悬》《接婆婆》等,新曲目不多。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地方曲种,平遥说书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诸如陕北说书2 985个,河南坠子28 673个,武乡说书149个,山东琴书1 278个,京韵大鼓6 606个,潞安鼓书1 910个,这些地方曲种不仅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在演艺团体和个人表演的数量以及曲目的点击量上也比较多。就表演团体来说,盲人说书的所有曲目都是旺日这个团体所演。随着网络、广播、媒体等各种休闲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再加上文化生态环境的不断破坏,当代年轻人的娱乐消遣方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对于传统的地方曲艺和戏曲已经失去原有的兴趣,各种流行音乐和商业活动充斥着现有的文化需求,这一切已经彻底改变了当地人的传统审美需要。人们通常通过村里庙会、文化馆活动和其他途径来欣赏盲人说书,如今由于盲人说书演出场次日益减少,人们听书看说书的机会也越来越少。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就平遥盲人说书的受众群体做了一次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涵盖了被调查人员性别、年龄(老、中、青)、对盲人说书的认识、喜好度、观赏途径等方面。通过分析数据表明,年龄越小对平遥说书的认知度越少,50岁以上的人群由于本土文化的厚重积淀对盲人说书的情感度比较高。对于平遥说书是否需要保护创新的问题,多数人认为平遥说人说书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平遥盲人说书不仅可以调节身心,丰富文化生活,还可以普及历史文化,宣传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促进社会和谐。大多数人认为非常有必要通过政府的努力宣传支持发展平遥说书。
三、大众传媒视阈下平遥说书的传承路径
“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阅读和观看趣味的多元化,一部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消费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再好的作品也需要媒介的推销。”[1]鉴于这种现实,对于说书的发展必须利用大众媒体开放、双向互动以及影响面广的优势,重建平遥说书的文化生存环境。作为地方性的民间艺术形式,应借助媒体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它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重塑文化自觉,提高说书的社会地位。将媒体文化和说书传承相融合,能大大促进说书的传承和发展。作为开放互通的网络环境,媒体也要打造相对集中的地方文化艺术平台,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网络资源,而不是将其置于博物馆或归之于私人所有。
(一 )建立互动的网络平台机制
中国自1994年获准加入国际互联网后,如今互联网在中国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美国哲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说,“不管我们度量时间的方式如何,这的确是一个变动的时刻。在20世纪后四分之一期间,一场以信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改变了我们思考、生产、消费、贸易、管理、沟通、生活、死亡、战争以及做爱的方式”[2]。我们必须借助网络平台充分利用网络的资源优势来促进传承和发展平遥盲人说书。各地方政府和高校可以建立开放的信息网络平台,创建网络数据库提供丰富的文化视频资源供人欣赏。在平遥官网戏曲文化一栏晋剧、秧歌、曲艺里,其中曲艺一栏中对平遥说书、方言快板、莲花落做了简单的表述。值得欣慰的是在视频专区里有一些平遥盲人说书的视听资料,如:《狗英英和懂不清》《骂鸡骂得真绝》《两头忙》《好媳妇当家(一)》《回娘家(一)》《夸土产》《好媳妇当家(二)》《吃嘴婆姨发孩日》《五子葬父》《好媳妇当家(三)》。这都表明了政府对曲艺艺术的关注,同时为爱好说书的人们提供了良好的互动平台,也为外界了解平遥音乐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有利于平遥盲人说书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此外,还可以开办网络曲艺大赛,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进一步拓展盲人说书这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形式的发展空间。
(二 )旅游文化资源搭台
平遥古城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对外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为当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硬件资源优势,应当借助平遥古城旅游资源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平遥盲人说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另外可以搭平遥“中国年摄影大赛”和“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顺风车扩大盲人说书的海外知名度。比如由文化部、国台办作为指导单位,中华文化联谊会与山西省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的“情系三晋——两岸文化联谊行”就是很好的例子。此次活动通过根祖文化、信义文化、晋商文化、佛教文化等板块,全面展示山西省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五彩缤纷的民俗风情。期间,举办了“三晋文化发展研讨会”、“两岸文化联谊座谈会”等交流活动,推动了晋台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三 )再组盲人说书会
长期以来民间艺人社会地位低下,一直遭受社会的歧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成立了专门的曲艺家协会,民间艺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国家一系列的政策下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曲艺文化资源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搜集整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单位改制以后很多艺人的生活又没有了着落,再加上多元化娱乐方式的充斥,全国范围内很多地方曲艺曲种都面临着艰难的文化生存和良性传承的问题。面对传承的问题,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培养一批掌握各种曲艺技能的文化传承的“活载体”,给这些活体资源予以适当的生活补贴,让他们安心地为传承当地音乐文化资源做出应有的贡献。现如今平遥盲人说书艺人已经出现授艺断代的现象,网络数据的分析情况也间接表明盲人说书从艺人数过少。当下非常有必要将现有的说书艺人组织起来重组说书书会并及时注入新的血液,为平遥盲人说书的进一步发展积蓄力量。
(四 )培养文化自觉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内涵说到底还是要靠资源地的大众来进行传承和接纳的。平遥盲人说书这种地方性的曲艺品种归根到底还需要平遥人民的接受和喜爱来保持其在文化传承链中的连续性。就目前的调查情况而言,情景实则令人担忧,90后的平遥学生多数对盲人说书都很陌生,更谈不上喜欢和传承。在大众媒体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挽救文化的这种自觉意识和培养当代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所在,也是多样性文化的根基所在。
(五 )培训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管理人员
在经济浪潮的社会大环境下,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必须拥有全新的文化创意和文化概念。平遥县文体广新局和城镇工业联合社、中小企业局联合举办“文化创意及其产业运营”专题讲座,对县150多名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管理人员进行集中培训,旨在进一步解放文化创意产业界的思想,推动全县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充分发挥县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发更多体现平遥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和层级。笔者也希望政府通过这些努力能进一步促进曲艺事业健康、稳定和良性发展。
文化是发展的,动态的。在文化不断发展的同时,重视文化的保护也极为重要。今天高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的境况下,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就显得尤其重要。随着全省非遗保护与文化创意论坛的举行,笔者也期望地方政府能够认清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现状,重视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把握其传统文化精髓,借助大众媒体的优势,促进本地区相关艺术的合作交流,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的创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必须转换文化创意的观念,提升地方文化的额外附加值。应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让平遥说书在非遗传承中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不至于断裂,同时也不被现代化的洪流冲淡而逐渐淡出平遥人民的日常生活。
注释
(1)平遥县文化局文化馆,平遥县文化志编写组.平遥县文化志.油印本,1985。
(2)http://v.baidu.com/v?word=%C6%BD%D2%A3%CB%B5%CA%E9&ct=301989888&rn=20&pn=0&db=0&s=0&fbl=800)。
[1]郭宝亮.大众传媒时代的“无根”写作[J].文艺研究,2007(7):4-11.
[2]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