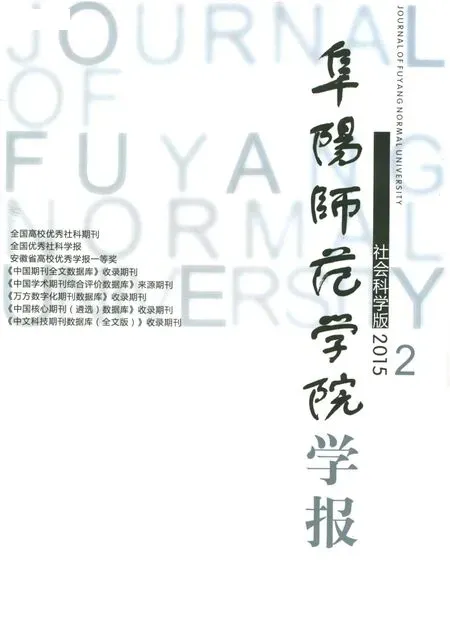略 论 镖 局
梁家贵,李恭忠(.阜阳师范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2.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0093)
LIANG Jia-gui,LI Gong-zhong(Colle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41;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历史学、文化学研究
略 论 镖 局
梁家贵1,李恭忠2*
(1.阜阳师范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2.南京大学 历史系,南京 210093)
学术界有关镖局产生的时间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镖局的产生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与社会环境的恶劣有关,同时与官府、豪绅及其他包括秘密组织在内的社会各界保持了密切联系。镖局产生的时间应该不会晚于明代中后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逐步衰落。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的保安组织就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翻版镖局。
镖局;商品经济;社会环境
镖局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民间组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社会现象,曾一度在中国的经济、政治舞台以及民众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据笔者目力所及,有关镖局的研究成果,影视、文学作品居多,严肃性的学术论著并不多见。本文拟在梳理以往关于镖局的研究观点的基础上,从社会经济变迁的背景着眼,分析镖局产生的原因、运行方式及特点,从一个侧面探讨民间组织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
有关镖局出现的时间,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文史爱好者中间均未达成共识。
一类观点认为,明代的“标行”就是以后的“镖局”。有观点根据清代褚人获所撰《坚瓠集》记载认为,镖局出现的具体时间是在明朝正德年间。《坚瓠集》云:“(打行)鼎革以来,官府不知其说,而吏胥又不晓文义,改做降字。但此辈惟得钱为人效力耳,何尝欲人之降。此予少时所亲见,今此辈久而不变,故记之。”[1]此处提到的“打行”,便被认为是早期的镖局。例如,有学者认为,打行就是那些身体强健、剽悍,而且武功高强的人所从事的一种职业。这种职业专为家产殷实之人提供保护,不仅看家护院,有时也充当“打手”组织或机构的角色。据记载,这类职业在正常营业时,一般要悬挂带有“拳头”标示的物品,故被人称为“铁拳头”。因此,这种职业被看作镖局的发端[2]。但是也有观点认为,“打行”是一个以暴力活动为职业的行帮,类似后来的打手组织,它的出现“从反面折射出商品经济发展的曙光”[3]。
有学者考察了“镖”字的词源,认为所谓“保镖”“镖行”,本为“保标”“标行”,因为常人多听说标客善用飞镖,以讹传讹,“标行”“保标”便衍作“镖行”“保镖”[4]。学者古彧对《江湖走镖隐语行话谱》《中国地理大势说》及《金瓶梅》等文献中“标”字的用法做了比较分析,认为明代有关镖局的事物采用“标”字,入清后“标”“镖”二字兼用,但仍以“标”字为主,民国以后均改用“镖”字;当代一律写作“镖”行[5]。
至于“标”字的原意,学者傅衣凌在《明代陕西商人》一文中对“标”“标客”和“标局”的来源作了阐述。他指出,清初上海人叶梦珠在其《阅世编》卷七提及“标”即“标布”,亦即棉花布的一种,为“上阔尖细者”,而“标客”即经营“标布”的商人,“标局” 亦即负责押运、护送“标布”的组织或机构(1)。
另一类观点认为,镖局的出现应该不会晚于清王朝的康雍时期。例如,有学者认为:镖局、镖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最初偶然而为,并不收取报酬,经过一个时期后才逐渐成为一种职业:“大概是在清代康雍年间,在一些尚武的地区,如冀南豫北,一些习武者豪侠仗义,好打抱不平,有时路遇盗贼抢劫商旅便挺身而出,而且在赶走强人后往往还会送上一程,直到商旅进入安全地界。被救人自然千恩力谢,但这里面基本没有金钱关系。到后来就有些过境商旅上门请求保护,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商机,于是些习武者抓住机会,逐渐以此作为了职业。”[6]亦有学者根据卫聚贤著《山西票号史》的记述,认为镖局的出现应该不会晚于清王朝的乾隆年间[7]。
关于镖局的产生时间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分歧,一方面与史料缺乏有关,因为镖局本身是一个下层民众的组织,受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的制约,自身很难留下明确的文字记录,而它要引起社会其他阶层尤其是上层以及官府的注意还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也明显受到研究者对相关史料的不同掌握程度以及解读角度的差异等因素影响。
二
何为镖局?学术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有关“镖局”的各种解释,认为:“镖局是以武术为基本手段,以保护商人人身、经营场所安全和商品、现银长途运输安全为主要目的商业机构,具有一定的保险性质。”[8]从中可以概括出“镖局”的两个功能,一是看护,二是押运。笔者赞同“镖局”的两大功能之说,但认为不能仅局限在商人及商品、货币上面,也就是说,“镖局”不仅仅保护商人,也保护其他各种职业的人;不仅仅押运商品、货币,也押运其他贵重物品,实际上还是“受人钱财,保人免灾”。
笔者认为,有关镖局产生时间的问题,也可从其功能方面来分析并得以解决。镖局的“受人钱财,保人免灾”功能取决于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就是商品经济要得到较大的发展,民间或个人财富有了一定积累,同时跨区域交流的需求越来越强;二是社会环境的恶劣,不仅阻碍了区域间的交流,也危及了财富拥有者的安全,一个专门从事“受人钱财,保人免灾”的民间组织便呼之欲出;三是这种民间组织与官方的关系很微妙,既不能作为秘密结社——也即得不到官方认可的民间组织而出现,也不能是一个松散的组织,而必须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而这恰恰又是官府所防范和禁止的。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镖局出现的经济背景,也是根本原因
有学者分析了镖局产生的经济背景,认为:“商品经济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清之前主要的经营模式为:国家的垄断贸易(专卖物资)和官方严格控制下的交易、为封建王朝和官僚贵族服务的长途贩运、邻近地域的民间交易。国家的垄断和控制下的贸易,是国家机器运行过程的一个环节,为封建王朝和官僚贵族服务的长途贩运自然有军队为其服务,邻近地域的民间交易因其路途短、环境熟、交易量小而不需要专门的武士去保护。因此,清之前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不具备镖局产生的历史条件。”[8]
笔者认为,上述内容中有关清代之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学者对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史进行了梳理,认为春秋战国、唐宋、明三个时期为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9]。其中,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尤其值得关注。在这一时期,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惠商、恤商政策,“一切弛放,任令通商”[10],并明确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在《宋刑统》中,宋代统治者不仅严禁擅闯民宅,而且特别对故意放火制订了处罚条例。例如,《宋刑统·盗贼律》规定:“诸故烧人舍屋及积聚之物而盗者,计所烧减价,并赃以强盗论。”《宋刑统·杂律·失火》规定:“故烧人屋舍、蚕蔟及五谷财物积聚者,首处死,随从者决脊杖二十。”[11]这些措施保护了商人利益,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此,有的学者对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一时期发生了“商业革命”[12]。还有学者研究了宋代的市场结构、城市化,充分肯定了其发展水平,认为是世界同类别行业发展史上“中世纪革命”[13]。但是相对而言,由于宋代战争频繁,加上统治区域不断缩小,其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应该不及明代。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为繁荣,这在大运河沿岸的城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漕运为运河两岸的城镇经济尤其是商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当时在这些地区,河中帆椿如林、轴轳相连,岸边车马络绎、货积如山,金店、银号、药铺、染坊等店铺作坊遍布城内。相应地,运河沿岸民风大开,商人地位显著提高,“崇商”观念逐步形成,大批外地商人纷至沓来,如“山陕”“江西”“苏州”“赣江”“武林”等地商人的会馆傍河而立,商贾云集,百业兴隆。在山东济宁,“其商贾之踵接而辐凑者,亦不下数百万”[14]。明清时期经济社会尤其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扬州、聊城、济宁、临清等运河沿岸城镇,甚至一些乡村出现。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萌芽,它的出现逐步改变了民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社会风气相应地发生变动,社会开始了局部的转型。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批外地商人在来到运河沿岸城镇经商的同时,也带来了自己的信仰。妈祖,又称作“天妃”“天后”和“娘娘”等,是由福建、广东商人带至运河沿岸城镇的。例如,山东德州、济宁等地原无天妃庙,明之后才出现,而且民众到天妃庙,“持香顶礼者无虚日”。王权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所作《天妃庙碑记》载:“德州旧无天妃庙,庙初立天文记岁月,天顺庚辰、成化辛丑两新之。”[15]信仰上的趋近乃至趋同,提升了外地商人对经营和居住地区的认同感,进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出现跨区域的商品流通,也必然形成财富积累,同时也为暴力掠夺行动和暴力护卫行为的出现提供了基础。有学者分析了商品经济与“打行”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打行’的产生从反面折射出商品经济发展的曙光。因为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会出现繁荣的市镇和频繁的城乡交流,而没有繁荣的市镇和频繁的城乡交流,就无法吸纳无业游民,也就无法为‘打行’提供活动空间;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无法促进江南绅士势力的高度发展,而没有绅士阶层的发展,就无法在地方社会生成一种与以州县衙门为载体的正式权力并行的以绅士为载体的‘非正式’的权力,而这种非正式的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然建立自己的权力自卫体系,从而为‘打行’的存在提供了社会需求。”[3]笔者认为,镖局出现的经济原因或可由此得到解释。
(二)社会环境的恶劣是镖局出现的社会因素,也是外部原因
宋代曾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其中的原因,一是战争、灾荒的破坏,二是统治者不抑兼并的政策,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后一个原因既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失地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经商;但也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农民暴动不断发生。为此,宋代统治者采取“招辑流亡、募人耕垦”等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京西唐、邓一带,原“尚多旷土,人草莽者十八九”,后经地方官招集,“流民自归,及淮北之民至者二千余户,引水溉田几数万顷,变硗瘠为膏腴”[16]。整体上看,宋代尚未存在严重的流动人口,社会秩序较为稳定。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如扬州因为食盐和漕运而成为“大贾走集,笙歌粉黛繁丽之地”[17]。全国出现了一批城市,据万历年间张涛修纂的《歙志》记载:“今之所谓都会者,大之而为两京(按:即北京、南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淮、扬、苏、松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18]城市的发展吸引了大量人口涌入,不仅有官僚权贵、豪强、世族、士人,也有富商巨贾和众多的小工商业者、苦力以及无业游民。另一方面,明代社会上始终存在较为严重的流民问题。例如成化年间(1465—1487年),仅北直隶顺天八府,流民就达26万多户,72万余口,“大小车辆,草行路宿,流徙而南”[19]。很多地方的流民“结成巨党,杀伤官军”。统治者虽经全力镇压,“调发官军,动数十万”,但都无济于事,因而社会环境较为恶劣[20]。官僚权贵、富商巨贾等财富拥有者,或为了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或为了商品或物品的顺利运输,迫切需要一种安全保卫力量,镖局便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三)官府的许可及其他社会各界的接受,使镖局的出现成为可能
明代初期对民间组织采取极为严厉的管制政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不久,便颁布法令,严禁各类民间结社,尤其是民间秘密宗教结社诸如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以及各类民间迷信活动诸如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等的活动[21]。明王朝颁布的《大明律》更是将朱元璋的禁令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加以固定、实施[22]。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官吏贪腐、宦官专权,政治出现严重危机,明初执行的户口登记制度和路引制度均遭到破坏,出现了大量流动人口,官府对民间组织的管束、控制也随之松弛下来。
作为一种民间组织,镖局的身份、地位极为尴尬:一方面,他们需要得到官方的许可、社会各界的接受,能够公开活动;另一方面,他们要与各种秘密组织尤其是土匪打交道,不仅自身要强大,更要熟悉秘密组织的运行方式、活动特点等。
首先,镖局的成立,要得到官方的许可以及社会各界的接受。有史料记载:“按照当时的江湖规矩,镖局开张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亮镖’。‘亮镖’很有讲究,如果亮不响,那这个镖局就开不成。‘亮镖’要由总镖头下帖,请当地的官宦世家、富商豪绅、社会名流和武术名家来共同捧场。如果是人缘不好,捧场的人少,那这个镖局就不好开;如果碰见‘踢门坎’的,要是打不过,那这个镖局就更不好开。”[23]
其次,镖局“走镖”要与秘密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他们不仅有自己的行规,如“水路三规”“三不住”“睡觉三不离”“三会一不”等,还有自己的隐语暗号,不同镖局之间可以通用。不妨试举几例:
保镖——唱戏的;镖旗——眼;钱搭链——蛇腰;个人——流丁;门半掩半开——夜扇马散;松林——林子马哈武;寺庙——神堂;晴天——天高;天黑——明路;走远——卜长;走近——卜短;墙头——马;庄稼把式——上等土风子;护院人——镇山虎;贼——芒古; 人胆大——点粗;胆小——点细;心眼多——全海;火药——夫子;洋枪——黑驴;有钱——海拉;无钱——念拉。[24]
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镖局是介于秘密组织与官府及合法组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民间组织。
三
由于成员文化水平的局限以及本身性质的决定,镖局产生的准确时间恐怕很难从史料中找到,但是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镖局的产生时间应该不会晚于明代中后期。
从本质上看,镖局是一种民间组织,它的产生既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因素,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社会现象,因而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仅从自身力量方面来看,镖局早期在以“镖头”权威作为维系力量前提下[25],主要依赖武术[26],但随着枪炮等近代武器的流行,他们也开始装备枪支。有学者利用自己工作的便利条件,曾看到清末巡警部管理京师地区镖局枪支的一些档案,从这些档案记载中可以反映当时镖局的装备情况:
永兴镖局:斜无烟炮枪 5杆、直无烟炮枪 1杆、九子十成枪4杆、十三响枪3杆、歪把毛斯枪1杆、大六出枪2杆,共16杆。北元成镖局:五眼枪4杆、十出枪2杆、毛丝枪2杆、开丝枪3杆、六响毛丝枪2杆,共15杆。隆泰镖局:五眼枪2杆、十三出枪5杆、毛丝枪5杆、开丝枪2杆,共14杆。东元成镖局:十三出枪4杆、铁板开丝枪5杆、木板开丝枪2杆、十响毛丝枪1杆、套筒五眼枪2杆,共14杆。东光裕镖局:马拐子枪6杆、十三出枪2杆、十七出枪2杆、直五匣枪1杆、后门炮枪1杆,共12杆。[2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镖局开始逐渐衰落,曾经兴盛一时的北京地区的镖局也纷纷关张。其中的原因,既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社会环境更加恶劣有关,更取决于现代意义上的安保组织如警察、保安公司、押运公司等的出现。民国时期,“匪患”极其严重,中华民国也被谑称“中华匪国”。这一时期的土匪已大量装备了现代化的武器,有的土匪本身就是由散兵游勇组成,呈现出“兵匪不分”“兵即匪,匪亦兵”的奇特社会现象[27]。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传统意义上的镖局已无生存空间,现代意义上的保安组织应运而生。可以这么说,后者应该就是镖局的近代翻版。不仅如此,当代的保安组织等在本质上应与镖局是一样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代的各类保安公司就是适应了时代需要并进行了调整的镖局。也就是说,只要社会环境还存在不安定因素,财产和人身安全的需要就仍将为镖局之类的民间组织提供存在的土壤。
注释:
(1)傅衣凌先生的这篇文章收入在他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中。在该文的注释中,傅衣凌先生又对“标”“标客”“标局”作了进一步阐述:“为了明清两代江南的标布多北鬻泰晋,我疑清代的标客,即源自标布客商,而标局则为护送布商而得名。褚华曾记其五世从祖之仆姚大汉尝为布商护货往来秦晋间,盗不敢近(“沪城备考”)。”但他同时又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认为“这种说法未知能否成立,姑志于此,以待讨论”——傅衣凌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8、174页。
[1][清]褚人获.坚瓠集[M].九集卷二,打行.
[2]李刚,郑中伟.明清镖局初探[J].华夏文化,1999,(4).
[3]郝秉键.晚明清初江南“打行”研究[J].清史研究,2001,(1).
[4]曲彦斌.中国镖行[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22-30.
[5]古彧.镖局春秋:镖行不容侵犯的生存之道[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7:31-33.
[6]哈恩忠.闲话保镖[J].北京档案,2004,(8).
[7]镖局兴衰数百年[J].国学,2008,(11).
[8]李金龙,刘映海.清代镖局与山西武术[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2,4-14.
[9]林文勋,杨华星.也谈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J].思想战线,2000,(6).
[10][宋]吕陶.净德集[M].卷1,四库全书本.
[11][宋]窦仪.宋刑统[Z].贼盗律.
[12]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00.
[13]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J]//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7:5-44.
[14](道光)济宁州志[Z].卷44.
[15](乾隆)德州志[Z].卷10,艺文•天妃庙记.
[16]宋史[Z].卷173,食货志.
[17](嘉靖)扬州府志[Z].卷11.
[18](万历)歙志[M].卷1.
[19]叶盛.京畿民情疏[A].明臣奏议[Z].卷2.
[20]项忠.抚流民疏[A].明经世文编[Z].卷46.
[21]明太祖实录[Z].卷53,洪武三年六月甲子.
[22]明律集解[Z].附例,卷11.
[23]揭开古代镖局的神秘面纱[J].国学,2008,(11).
[24]哈恩忠.闲话保镖[J].北京档案,2004,(8).
[25]梁家贵.从王伦起事看教门首领角色功能[J].齐鲁学刊,2012,(2).
[26]张春梅,段丽梅.明清镖局与武术传承关系探究[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11,(2).
[27]梁家贵.倪嗣冲与民初安徽匪患治理[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3).
A Brief Discussion on Biaoju
There are different augments about the origin of Biaoju. Biaoju came into being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 harsh social environment of un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the ruler, the gentry,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emergence of Biaoju should not be later tha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and declined gradually after the 1920s. Various security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time are other version of Biaoju.
Biaoju; commodity economy; social environment
LIANG Jia-gui,LI Gong-zhong
(Colle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41;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K26
A
1004-4310(2015)02-0105-04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5.02.025
2015-01-1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元明以降淮北地区社会变迁研究”(14YJA770008)。
梁家贵(1968— ),男,山东茌平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李恭忠(1974— ),男,江西遂川人,历史学博士,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