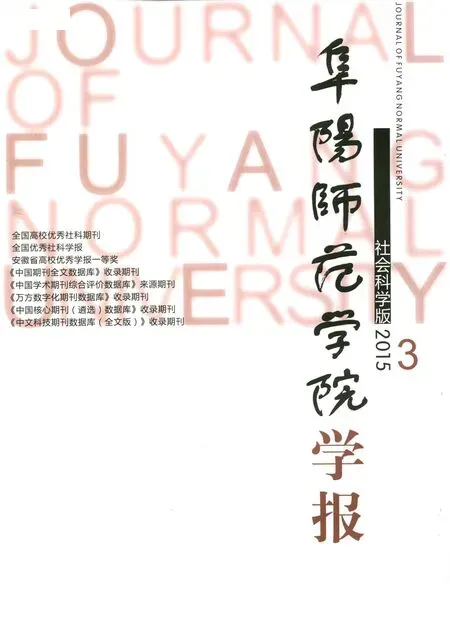“才尽”“田家语”与陶诗评价
——论钟嵘审美思想的折中倾向
郭世轩(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文学研究
“才尽”“田家语”与陶诗评价
——论钟嵘审美思想的折中倾向
郭世轩*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在整个东晋南朝时期,钟嵘是在审美坐标中率先对陶渊明做出相当中肯评价并予以较高定位的文学评论家。从《诗品》的“才尽”“田家语”等评语中不难发现,钟嵘对陶渊明的评价与其审美思想的折中倾向之间具有某种关联。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钟嵘在审美矛盾中的综合平衡与无奈选择。这种审美矛盾间接透露出他在审美趣味、审美表现和审美境界等方面所作出的权衡与规避。
陶诗评价;钟嵘;审美思想;折中倾向
在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对陶渊明做出相当中肯评价并在审美坐标中予以较高定位的文学评论家莫过于钟嵘(约 468~518)[1]585!纵观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史料可以看出,钟嵘给陶渊明诗歌创作以“中品”评价,尽管在今天看来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在当时已属非常不易,甚至是相当大胆的突破。要知道,在当时的主流娱乐圈和文化传播媒介中,陶渊明是以“隐士”身份出现在公共视野的。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文坛精英分子的文学价值观和对陶渊明诗文创作的评价中充分显示出来。至少从文学本位的立场上来看,钟嵘把陶渊明看成真正的诗人,而非其他。即使是“隐逸诗人之宗”,至少也是诗人呀!从《诗品》的“才尽”“田家语”等评语中不难发现钟嵘对陶渊明的评价与其审美思想的折中倾向之间的内在关系。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钟嵘在审美矛盾中的综合平衡与无奈选择。这种审美矛盾也间接透露出他在审美趣味、审美表现和审美境界上的权衡与规避。本文试图在钟嵘评价陶渊明等诗人的相关信息中寻绎出问题的答案。
一、审美趣味:趋新与典雅
在审美趣味的时尚选择中,整个南北朝时期是趋新求变的。南梁文论家刘勰(465-521)的《文心雕龙·时序》既已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2]527的主张。南梁史学家萧子显(489-537)的著名言论充分表明了这一时代的追求。“若无新变,不能代雄”[3]340恰恰体现出该时代文学以变求新的极端重要性:要想成为一代青史留名的文坛英才,就必须在前辈权威的基础之上做出新的变化以取代旧的权威。一个凡人如何才能摆脱沉重肉身的束缚而留下身后不朽英名?这是困扰人类的一个大问题。中国古代贤者建立了“三不朽”即“三立”的留名范式,那就是要在德、功、言三个层面上永垂不朽。萧子显这句话分明包含着这一时代诗人在建功立业观念上的突破:在立言上进行自我实现,在立言中实现对立德、立功的超越。因为立德并非人人可立,在德性上要想做到德高望重,必然要通过社会评价系统的高度认同;即便如此,道德完善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尚需时间的考量和历史的淘洗。况且,言人人殊,要想取得社会的高度认同,也绝非轻而易举。立功,需要的是机会与能力、胆识与才干同时兼备。飞将军李广虽具旷世奇才,但时运不济,最终归因于“数奇”[4]2202。相形之下,他那才能平庸的堂弟李蔡却能飞黄腾达[4]2201。李广之孙李陵虽战功赫赫,却因北匈奴的重兵包围而寡不敌众、战败假降而导致满门抄斩、母亲妻子灭族的旷世奇冤[4]2068,连路见不平、仗义执言的司马迁也卷入其间,成为“发愤著书”[5]2201的奇特案例。而只有著书立说,执著于“立言”,才是最可信、最现实、最可为的——无需外求,全靠自身,独立自主,立言不朽!“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作篇籍。”[3]14这里深藏着文人学者在乱世中求生存的最新思考:如何在年寿不假、祸福不定、时运不济、德性微薄、功业难成的生存语境中,播撒自己的光和热,使自己青史留名?扬雄“悔其少作”[6]459而作《法言》和《太玄》,桓谭对扬雄的推崇(称之为“扬子”,视《太玄》为玄经)[6]490,王充对“鸿儒”的呼唤[6]512,曹丕对“经国”文章的强调[3]14,无不为这种著书立说、立言不朽的观念提供了反思与深化的理论资源。可以说,这就是“影响的焦虑”[7],是时代的焦虑,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焦虑!
“为人须规矩,为文须放荡”[3]354,旗帜鲜明地亮出这样的立场:为文和为人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前者要规规矩矩,以理性为准绳,明确区分善恶是非,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要界限分明。后者则是以感性为依据,出奇制胜,变幻多端,美在耳目,赏心乐事,无限风光在笔端。这可以说是对儒家“变风”“变雅”[3]334观念的认同与改造,对“温柔敦厚”[3]275诗教和“心声心画”[3]463说的质疑与颠覆。“放荡”,主要指在审美想象王国中可以尽情展现奇思妙想,在艺术形式和意象经营中,不拘一格,争奇斗艳,鼓荡人心,产生惊心动魄之奇效!这里既有对偏重规训与统一的汉代文化精神的反叛,也有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式的权宜之计和文化选择。汉代的辉煌已成为过去,并且一去不复返。天下大一统的时代难以再现,一匡天下的雄心壮志积重难返,巨大时空的辉煌成就感和征服感遗失在昨天,偏安于风景秀丽、人杰地灵、丰衣足食、佳丽如云的锦绣江南之现实处境直接决定了南朝文人的感性风貌。现实生活环境直接制约着文学的生存空间。鉴于此,南朝的文学风貌也随之焕然一新:内容渐趋新奇小巧,形式偏于新奇惊艳,格调聚焦奇句淫词、声色犬马与视觉享受,趣味喜欢奇情丽采、锦心绣口,气象拘于曼妙艳丽,境界囿于玲珑剔透和赏心悦目。相比较整个南朝日益趋新的审美趣味,陶渊明的审美趣味则显得相对保守,表现为淡雅而持中。
因此之故,在对陶渊明的评价中,无论是颜延之的“文取旨达”[3]269,还是萧统的“尚想其德”[3]335,都是这种审美趣味的有声表达。谢灵运、刘义庆和刘勰等文学家对陶渊明的漠视,更是这种审美趣味的无声默认。即便是对陶渊明倾情有加的鲍照、江淹也只有在失意与落魄、激情与愤懑中偶一为之。这些皆源于陶渊明诗歌的独特追求。有研究者认为,陶渊明的诗歌追求在于自然清新,表现形式在于“高情淡采”[8]。因此,陶渊明独具特色的审美追求明显不符合南朝文坛主流的审美趣味与审美期待,遭到无视与强评(勉强论之)的待遇自然就在意料之中。从上品诗人的源流谱系中不难发现,钟嵘是比较喜欢气象宏大、辞采华丽、境界开阔、趣味雅致的诗歌作品的。他的这种审美趣味既是时代的表征,也是个性的体现。无论是曹植、王粲还是陆机、谢灵运,无不以辞采华丽和意象多变而著称,总体格调偏于华艳靡丽。至于气象宏大、境界高远、趣味高雅的曹操、曹丕和陶渊明、鲍照等人也只能在无奈的选择中屈居中、下品第。其中,追求清新雅致的审美趣味终于使他将陶渊明从被文坛遗忘的角落中发掘并置于中品的位置。这也许又是他折中思维的无意识表露。置于上品,会引起很大争议;置于下品,又于心不忍。放在中品,可谓恰如其分,便于自己在争辩中左右逢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事实证明,钟嵘是深刻领会“无私于轻重,无偏于憎爱”[2]586这种客观求实的精神的。其中蕴含着一位优秀文学评论家的无奈与智慧。在一千四百多年之后的今天,这种智慧的选择依然令我们心动,不禁为之击节叹赏!
二、 审美表现:华丽与清新
南朝文坛追求新变的结果就是直接表现为华丽的语言与精巧的形式。刘勰在划时代的巨著《文心雕龙》里专门开辟《情采》篇予以重点关注。这也许就是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最显著的审美表现。
如前所述,被南朝文人视为文坛巨匠的大都以辞采华丽而著称。尽管在个别作家(如曹丕与曹植)的评价上,钟嵘和刘勰不尽相同,但总体说来两人的审美趣味大体相似。尤其是在对王粲、刘祯、陆机、左思与谢灵运等重要作家的评价与定位上,则是大同小异。比如对王粲、陆机和谢灵运的评价则显现出基本的一致性。至于对曹丕与曹植的分歧,可能源于两人同情心和世界观的差异。刘勰基本上是扬丕抑植的,这既与曹植的行为狂放、以小凌大有关,也与刘勰的正统观念和宗经思想相连。这一点也可以从他对“三曹”的褒贬中见出分晓。曹操、曹丕作为帝王诗人在刘勰笔下熠熠生辉,而曹植作为落魄王侯则显得有点美中不足。一般说来,“三曹”中的曹操戎马生涯,转战沙场,诗风显得古朴苍健、气势恢宏;而曹丕、曹植兄弟不仅是锦衣玉食的王公贵胄,而且年少轻狂,相对地养尊处优,因此在诗风上则是后出转精,后来居上,尤其是在语言表达与技巧运用上。当然,这既可以看出时代的差异——曹操为汉声,曹丕曹植为魏响,也可以看出因年龄与经历的差异而导致不同的人生体验:曹操为风云变幻的时代英雄和一代领袖,具有雄才大略;而曹丕、曹植兄弟则为王孙公子,二者又有王侯与君臣之别。大体说来,曹丕、曹植兄弟在诗歌创作中,语言华丽远远超过乃父,其中曹植又略胜于乃兄。刘勰的这种观念使得他迥异于南朝的其他作家与评论家。而钟嵘对“三曹”的评价基本上大异于刘勰,来个乾坤大挪移。曹植作为建安之英的地位处于上品中的高端,可以说是建安以来诗人的顶峰,享受最高的称誉。相比较而言,他分别给曹操与曹丕下品和中品的地位,尤其是对曹操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为后世评论家埋下了纷争与不满的伏笔。当然,钟嵘的评价也是言之有据的,并非随意处置的。他褒贬曹植与曹丕的主要依据就是趣味的华美与构词的精巧。
事实上,作为“诗人之冠冕”的曹植之所以成为南朝文人大加追捧的对象,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曹植更能迎合南北朝文人追新求变的审美时尚,代表华美绮靡的审美方向;其二,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多才多艺的文人和英雄末路的落魄者,直接激发了南朝文人的情感共鸣,从而为自己的失意与不幸找到倾诉的对象和投射的目标。鉴于此,曹植顺理成章地成为“三曹”中的翘楚,这在无形中暗合了钟嵘的审美理想。有人认为钟嵘建立了布衣文学观[9],从这里也可以得到佐证。相形之下,刘勰则充分体现出典型的贵族趣味。最为极端而又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勰遗忘陶渊明,钟嵘抬高曹植并发现陶渊明。南朝政治生态的恶化与偏安一隅的局促,使得文人难有大的作为。政治上,门阀士族和军功阶层把持了各种晋升的渠道,一般寒门士子若想出人头地,不会投机取巧和见风使舵就只能英俊沉下僚。作为布衣文学家,钟嵘自然而然地力挺曹植与陶渊明,徘徊在华丽与清新之间,在迎合时代的审美潮流之外,又为南朝文坛招徕清新伟岸之风。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见出钟嵘为了捍卫清新之风而作出的甄别工作和诠释理由。那就是“田家语”[10]66与“才尽”[10]73之说。
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围绕清新与华丽而做文章。“华丽”的反面就是古朴,针对江淹而言,那就是“才尽”。在南朝史料中,涉及到诗人作家“才尽”者,一个是江淹,另一个就是任昉。任昉以笔见长,善于写实用文体,如表奏书启之类的文章。“沈诗任笔”之说似成定论。“彦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10]75钟嵘在这里介绍的任昉为诗不工之处与任昉深恨之情,充分说明“不工”在诗坛与文苑绝不是一个好词,有可能是一个极端负面的评价。与之仅一步之遥的词语那就是“才尽”。《南史》记载,任昉对世人评价他的“才尽”也是“深恨之”。[11]970这可以与钟嵘的《诗品》形成互文进行参考。对于任昉这样地位较高的贵族阶层,钟嵘只能避重就轻,仅写次要的“不工”,而将语气更重的“才尽”留给史学家置喙。而对相对贫民出身而主要成名于南齐时代的江淹似乎就没有那么客气啦!直接在《诗品》率先引用民间传说,从而使“江淹才尽”成为千古流传的典故,而青史留名的江淹之文名反而不显,流传在后人口中的就是江淹的幸运成名与不幸才尽。考之于江淹文集中的创作,似乎在印证着钟嵘记录的符合度。关于江淹才尽、江郎才尽的原因有许多种解释,但这一传说的出现与传播似乎提供给人们更多值得推敲的信息:一个作家的创造力与作品受欢迎的程度成正比;一旦创作力衰竭就将为时代所抛弃。而创作力衰退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文采不再,缺少文采就是思竭才尽。这则负面消息透露出社会公众对江淹的不感冒和极大的失望,从另一侧面也彰显着整个文坛与诗苑对华丽辞采的极端重视与趋之若鹜!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南朝士人对文采的高度重视远远超过对财物的占有。这一点在任昉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在乎财物的多寡,而在乎文名的受损[11]969-970。这也是时代使然,“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11]976。
当时南朝大多数士人之所以轻视陶渊明诗文的原因,大概与他诗文中田园生活的题材与语言相关。在士族文人看来,农村生活本来就够寒碜的,再用方言土语或村夫野老之言来表述无异于雪上加霜。钟嵘在《诗品》的座次排列中为他辩解的理由是:“岂止田家语也?”[10]66不难看出,钟嵘为寻找真美的境界而付出切实的努力!也就是说,陶渊明虽用“田家语”来表现,但依然能够突破“田家”话语的限制而抵达很高的审美境界。况且,陶诗还使用“欢言酌春酒”之类华丽清新的语言来表述。显而易见,这种辩解还是很勉强的,因为这种语言与曹植、陆机、谢灵运、颜延之等人相比还是显得极为朴实与淡雅的。
三、 审美境界:真美与巧制
巧制的篇章所要传达的审美境界难免显得做作与拼凑、堆砌与匠气,在繁琐与沉闷中显得孱弱和轻浮。在空间呈现上,显得局促与狭小,视角单一,偏于一端,如严冬腊月,了无生机。而真美的诗歌给人的审美感受是:清新自然,“直寻”以抵达真美境界。这种真正的诗歌给人的感觉就是气象廓大,其中的人生百态,全面展开,如春暖花开,万物萌生。真美的诗歌与巧制的诗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需要“直寻”。
何谓“直寻”?无需借助于理性知识和逻辑演绎而直接抵达诗意的境界,使人感受到活泼泼的诗情画意和生活乐趣扑面而来。有人又称之为“妙悟”[12]132,确实很有道理。“直寻”就是直接寻找诗意,毋须过多的理性旁证与文史用事。相比较而言,任昉等人的文名不高多与此相关。直寻的诗歌如沐春风,自然清新,巧夺天工。而非直寻的诗歌则需要借助于华丽辞藻与历史典故。这种区分在南朝以来就已经表现出来。比如,谢灵运与颜延之的区分,一个如芙蓉出水自然婀娜,一个似花团锦簇叠床架屋。前者给人春风拂面、神清气爽之美感,后者使人感觉过度华丽令人应接不暇和审美窒息之压迫。相比较而言,居于上品的几位“大”诗人多偏于用典少、多清新,而《国风》、小雅和汉乐府民歌更上层楼。当然,曹植、陆机和谢灵运这“三杰”无不以华丽著称。即便是王粲、刘祯和左思等居于上品的诗人也是丽词与故实并重、学问与才思齐飞的。只不过才思、情感更占上风,在二者的关系上处理得比颜延之更为巧妙而已。但同样也存在着美中不足之处。其美玉有瑕的表现就是知识才学与华丽辞藻过甚,往往掩盖了诗歌的真美。太康诗人与元嘉诗人之所以远逊于建安诗人处主要不在辞藻的华丽,而恰恰输在情感的真实及其表现上。
一般说来,诗人的创作是源于情感的自然流露,源于生活环境的激发与碰撞,是感动于外物变化和内在心灵的触动和呼应的结果。语境的变化使得自身在心灵感受上有所失衡。再加上身体状态的变化、人生处境的变迁的叠加效应,即使外物寻常的变化也会在诗人心中产生不同寻常的反响,从而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6]343被激荡起来的情感涟漪必然通过身体语言和文字语言来表现,如同遭遇到冷空气的突袭而得了感冒必然要打喷嚏一般,这应当是不可遏止的、情不自禁的必然反应。“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发狂大叫,流涕痛哭,不能自止。”[13]232也就是说,作家诗人只有处于这种创作状态才是真正的艺术创作状态。这也就是刘勰所极力主张的“为情而造文”。否则,为了创作而创作,为名为利为其他而滋生的创作就是“为文而造情”[2]405。这样的创作状态则是偏离了真正的情感真纯的状态,结果必然会在词藻上下功夫,这就是“情”不够“采”来凑。“为文而造情”难免出现文过饰非、“为赋新词强说愁”[14]9383的不自然、不真实的局面。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呢?这是因为文学艺术创造是最真实的情感表现,没有自然情感的真实体验就难以有审美情感的提纯与升华,在话语与境界的追求上必然会有所偏差。庄子所说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15]823就是这种效果。因为“少年不识愁滋味”,所以即使做出再大的努力,哪怕你登楼登山登科都解决不了这种愁苦的本真自然的问题。毕竟是“强说”“乱说”和“瞎说”的结果,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沦为虚假做作的滥说,陈词滥调如陨落的鲜花自然就难以动人。因此,华丽的名言辞藻和丰富的历史掌故难以遮掩艺术天赋和情感体验的不足,最终会陷入虚假创作的羞怯与难堪之中。
相比较而言,《诗经》之“国风”“小雅”、《楚辞》之《离骚》、汉乐府之民歌、古诗十九首之所以成为不朽的传世名著,恰恰在于这些都是诗人生命体验无可替代的绝代咏唱。《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西厢记》和《水浒传》之所以为金圣叹(1608-1661)赞之为古往今来的“六大才子书”[16],实在是因为这六者不仅仅是真情实感的体验极致,而且也是优美与淳朴有机统一的文辞绝境。同样,建安文学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也与其乱世中求生存、艰难中求超越的生命绝唱密不可分。“雅好慷慨”[2]537的时代风格与个人标识是由来已久、事出有因的。无论是“三曹”还是“七子”,抑或是其他建安诗人作家的创作,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空中留下生命足迹的诗意表现无不与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人生书写密切关联。因此之故,被钟嵘列入上品之诗人绝大多数是实至名归的,而有些诗人的定评也存在着明显的争议。而被列入中、下品的部分诗人也有不当之处,留有更大争议的空间。这当然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强求古人,而应该从当时的阅读语境和审美时尚来判断。前者如陆机、谢灵运和潘岳,后者如曹操、曹丕和陶渊明。陆机作为太康之英,谢灵运作为元嘉之英,皆可以成立。但如果将时代再放大放远一点,这种说法就值得推敲,难免存在时代审美趣味的偏差与审美鉴赏的前见。远的不说,即使和曹操、曹丕和陶渊明相比,这三位上品诗人就难以自持。甚至鲍照、谢朓等诗人也会超越其上的。这是时代的审美标准所致,在此毋须赘言,将是另一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主题。陆机、谢灵运和潘岳之所以高出曹操、曹丕和陶渊明,恰恰在于审美趣味的偏差和崇尚辞藻诗风的制衡。如果从情感真纯与诗语本色的高度统一来看,上述两组六人可以进行重新洗牌,来个颠倒。
相形之下,曹操、曹丕和陶渊明更接近于真美,或者说陶渊明就是真美的化身,而陆机、谢灵运和潘岳更多接近于巧制,或者就是巧制的大师。前者倾向于“为情而造文”,后者则更倾向于“为文而造情”。鉴于此,钟嵘在时代的审美风尚和阅读同情上偏向于曹植、陆机、谢灵运和潘岳等人,而在审美的真纯上还是不自觉地倾向于陶渊明。这在当时不能说不是一个大胆的抉择!在这种难以平衡中进行抉择,既是他进行折中权衡的结果,也表明他超凡脱俗的一面。当然,这种超越还不太彻底,那就是对曹操、曹丕等“为情而造文”的优秀作家之真正价值尚未给予公正的评价。而拘泥于审美时尚给予“为文而造情”的作家以不恰当的高评。这也许就是一个作家或评论家不能超越时代的具体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钟嵘能给予陶渊明中品的评价已经相当了不起!对比一下刘义庆、颜延之、沈约、刘勰等人对陶渊明的态度,钟嵘可谓高标一时,冠盖古今。这也许就是一位卓越批评家的远见卓识的独特表现:见常人所未见,言常人所不能言,道常人所不敢道。
事实上,钟嵘不仅在诗歌鉴赏中表现出如此的折中倾向,而且这也是他人生经历与选择的正常反映。也就是说,诗歌鉴赏是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必然表现。他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儒家思想在汉代鼎盛之后的汉魏六朝转入中衰,齐梁之时一度抬头。齐高帝即位之后,长于经学、礼学的王俭大振儒学。正值青年时代的钟嵘谙熟儒家经典《周易》入国子学,得到国子祭酒、卫将军王俭的赏识,被举荐为本州秀才[17]480。这说明钟嵘曾受到儒家思想较深的熏陶。在天监元年(520)上书建议清理军官中士庶寒门混杂的现象[17]481。这正是其世族出身门阀观念的反映。这种出身士大夫的阶级意识在《诗品》中就必然表现为重“雅”轻“俗”的审美趣味。儒家的折中思想又使之兼顾思想与艺术、世族与寒门、丹采与风力、《国风》与《楚辞》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着某种艺术张力而不至于走向极端。有宗经思想但不突出,同时尊重艺术规律,使之越出儒家艺术思想的藩篱[1]588。
总之,从审美趣味之趋新与典雅、审美表现之华丽与清新、审美境界之真美与巧制来看,钟嵘像绝大多数中国古典知识分子一样,表现出一定的折中倾向,但是这并未能遮蔽他的远见卓识,尤其是对陶渊明这样较为低调而诗名未显的大作家,一旦符合他的审美标准,他会毫不犹豫地予以认同,并作出在当时难能可贵的评价。这一点足以证明他是优秀的的大评论家。可以说,他穿越“才尽”“田家语”等时代偏见,最终抵达陶渊明的诗歌境界,并最终发现了陶渊明的伟大价值,实为《诗品》的伟大价值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钟嵘无愧于他的时代和他的称号。
[1]吕慧娟,刘波,卢达.中国历代作家评传(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
[2]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3]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6]张少康, 璘卢永 .先秦两汉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7][美]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8]郭世轩.萧统为何对陶渊明高评低选[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9]方志红.钟嵘“布衣文学观”初探[J].思想战线,2008,(2).
[10]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1]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朱良志.中国美学名著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3]蔡景康.明代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4]朱德才,薛祥生,邓红梅.辛弃疾词新释辑评(上下)[M].北京:中国书店,2006.
[1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金圣叹.杜诗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前言1.
[17]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I206
A
1004-4310(2015)03-0060-05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5.03.014
2015-03-08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晋-宋时期的文学传播与陶渊明的经典化历程”(ahskf09-10d79)。
郭世轩,男,安徽临泉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博士,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皖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